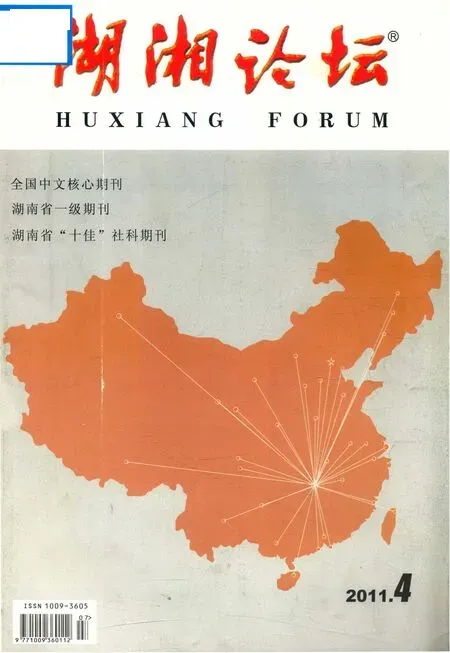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的若干影响
2011-04-11张忆军孙会岩
张忆军,孙会岩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200233)
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的若干影响
张忆军1,孙会岩2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200233)
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研究五四运动对党建文化的影响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在吸取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在党建方面的运用,认为五四运动中民主与科学、问题与主义、矫枉过正等对党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价值取向;党建文化;影响
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文化有影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中国共产党紧随着五四运动诞生,可以说五四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研究五四运动对党建文化的影响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这是因为,对五四文化及其影响的评价,在五四后至今的90多年里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各方学者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对此作出评判。同时,党建文化又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话题。笔者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撷取几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思考,提出观点。
一、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在党建方面的运用
“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回忆起政治性的细节;每当其后不得国家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的文化斗争细节。”[1]P151早期共产党人是五四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参加者,也是五四运动的最早研究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恽代英等,都对五四运动有过多方面的论述。
(一)五四运动在共产党人认知中的价值取向首先是政治化的
陈独秀把五四运动看作近代国民运动的开端,认为五四运动是高于以往一切爱国运动的“革命运动”。他特别赞扬五四运动的两种精神:“直接行为,牺牲精神。”[2]P130李大钊于五四运动两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3]P464张太雷于1925年撰文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释“五四意义”,他指出:“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4]P77-78瞿秋白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5]P155。他们的解读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情结与政治色彩,五四运动被视为“革命运动”且被赋予划时代的意义。
(二)早期共产党人也看到了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
1924年,“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开展关于纪念五四活动中要求“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意义:一是恢复国权运动;二是新文化运动”,并认为“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6]后来,张闻天撰文指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和爱国群众运动的合流,新文化运动是整个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意识上的表现,而又在爱国运动狂流中广达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读,是多视角的,也是历史性的,特别是把政治革命的五四与文化革命的五四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全部中国的历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7]P700。
(三)早期共产党人在党建方面对五四运动的合理运用
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与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联系起来。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般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他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8]P832因而,20世纪40年代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被称为继五四之后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奠定以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实际上成为共产党解读五四运动的代言人。这些解读及其喻史论今的方式,不仅左右了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影响,也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二、五四运动的价值取向及其对党建文化的影响
经过辛亥革命,爱国和救国已不再与忠君保皇联系在一起,而是建立在反对列强的基础上,寻求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总起来说,贯穿党建文化始终的五四运动价值取向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共产党的纲领建设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构筑党建理论和实践的体系之中,体现在整个党的实际行动之中。五四时期讨论的许多具体议题都是在爱国和救国基础上的延伸。这些议题对党建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五四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及其对党建文化的影响
在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的认知中,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的利器。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理想遭到军阀的肆意践踏,因而在五四时期民主依然是新知识分子使用的最多的口号之一。当时关于民主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拥有民主共和。新知识分子对康有为等人以国情为由,反对民主共和,鼓吹帝制进行了批驳。陈独秀等人道:向民主转变过程会带来一些混乱。可是,专制统治带来的混乱和阻碍社会发展的恶果更严重。至于新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民主,则接受了杜威的民主诠释:(1)政治民主,主要是实行立宪制和立法代表;(2)民权民主,如言论、出版、信仰、居住等的自由;(3)社会民主,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4)经济民主,平等分配社会财富。[9]陈独秀接受杜威的诠释认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0]五四时期的民主是与科学相结合的。新知识分子提出的科学口号主要侧重于科学精神或科学理性。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原则,也就是从改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意义上探求中国现代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执行,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1]民主与科学结合的价值取向,其锋芒指向封建礼教与迷信。即“以科学说明真理”,努力使自己的认识“步步皆脚踏实地”,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12]毋庸置疑,五四运动中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比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激进。这种讨论在方法论方面主要表现为追求民主和描绘民主。当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经过社会革命,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没有条件进一步深究民主的实现条件和运作机制的。但是,五四运动对待民主的方法的影响则有着两面性。追求是动力,描绘是憧憬。仅停留此,则难以推动民主进步。这种两面性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民主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建设都有影响。
共产党把科学与民主视为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即纲领和奋斗目标,并在以后的民主革命中接过了这两面旗帜。民主的口号既是党领导革命追求的目标,也是党进行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手段。如把争取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经常会被写进政治斗争的口号中。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抗日根据地发起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也对社会民主进行实验和示范。如实行“三三制”的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召开参议会等。由于战争的环境,这些社会民主实验和示范,在党的根据地并不普及,也没有延续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在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方面的努力是不充分的。长期以来,人民民主的政治机构在运作机制上制度化程度不高,存在着浓厚的不确定性,与理想的人民当家作主存在距离。五四运动追求民主和描绘民主的方法论对党内民主建设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提出在党内外“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P543-544;在理论层面上把民主集中制阐发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作风层面上,强调党内的民主意识,如提倡“听人闲话”,领导者要有胸襟;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反对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反对党内的极端民主化;乃至制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对于民主建设,无论理想的追求还是理论的阐述,无论讲原则还是讲作风,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切都把民主建立在一个或然的基础上。于是党内始终存在“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现象”等不民主的现象。甚至存在鼓吹民主的旗手,强调民主作风最力的领袖和严重的家长制集于一身的矛盾现象。如陈独秀动辄训人的“家长制”,毛泽东情绪化的“家长制”等。邓小平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无论是制度条文,还是制度执行的粗放性和或然性,甚至成为党内潜规则。
(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及其对党建文化的影响
1917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新知识分子领军人物之间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与同时期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一样,同样是出自爱国与救国,探讨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民主与科学是关于理想社会的追求,而“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则是关于改变现实中国路径的讨论。对于中国的现状,胡适主张中国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对不存在的。”[14]他说:“纸上谈兵的各种抽象的主义还可能被政客们利用作他们空虚的口号,来满足自己的野心,根本不用于解决问题。”胡适坚持说,对主义可以加以研究并有选择地作为工具和假设,但不应把它们作为信条和铁律,应当用演进的观点和“历史的态度”来研究各种主义。[15]对此,李大钊持不同的主张:“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16]这场论争虽然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但是,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胡适对“主义”的诟病,发生在“十月革命”影响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后。可以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表明了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分裂。其次,这场论争吸引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知识分子们,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于改造中国的意义和作用。在1920年,毛泽东仍意犹未尽地与同道们表示“主义”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17]“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他说:引进“主义”“这实是进入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18]
“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实际持续时间是很长的,可以说在党90年的成长史中始终存在。就政党政治而言,“问题”是现实的,解决问题是执政者的责任。“问题”不被解决,执政者就不被社会大众认同。“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路径,不同政党可以提出不同“主义”在社会大众面前竞争,供社会大众选择。共产党诞生后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共产主义,并且逐步完善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这种主张多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1925年,戴季陶提出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以反对共产党的唯物史观,排拒国共合作。1930年在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从社会性质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问题。1938年,章乃器发表《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涉及到共产党的“主义”。1939年,国民党当局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后,国民党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搁置一边。”应当注意到,民主革命时期的“主义”之争,是政党竞争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最关键的部分,它激发了共产党对于捍卫自身主义深刻意识,同时也加深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思考。如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方面,既是指导现实的民主革命,又是对未来社会建设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执政以后,“主义”仍然时时遭遇叩问。这不仅是一些政治派别对党的“主义”批评和攻击。如,1957年刮的反社会主义制度风和反对党的领导风,改革开放时期,关于自由化和西化的主张。由于长期遭遇“主义”被批评和攻击的环境,导致党的各级组织认知意识上对“主义”坚持且敏感,而对“问题”相对麻木且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企图以政治方式解决社会伦理道德,在社会上忽视社会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在党内忽视党员的权利和利益。对于社会大众,包括党内的基层党员而言,“主义”是抽象的理论概念,是有距离的,“问题”则是直接的,关乎自身利益的。因而人们是通过感受“问题”来判断党的“主义”。为此,党不仅要重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向社会大众说明“主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要意识到解决问题的重要性,重视通过解决“问题”,说服社会大众接受“主义”建立全党和大众的理想信念。
(三)五四运动的“矫枉过正”行为方式及其对党建文化的影响
五四运动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是“激进主义”或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方式。关于激进主义和矫枉过正,各路史家历来是褒贬不一的。其中,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反传统文化的行为方式的评价。新儒家牟宗三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林毓生较早对五四运动激进反传统提出激烈批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这种态度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19]P1。随后,余英时在1988年所作的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演讲中将五四运动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环节。他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我觉得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的激进主义”,“因为这个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的层面”;他也将“文革”视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文化激进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称“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进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20]。
关于火烧赵家楼,梁漱溟当时针对学生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关系问题,提出先是起诉学生违法然后再根据正义伦理而当场公赦。梁漱溟认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21]五四运动的激进和矫枉过正的行为方式固然由辛亥革命后的尊孔、复辟皇权所激发,也与中华民族一元排他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因而认识五四运动对党建文化的影响,不仅要以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运动历史的影响为视角,更要以本民族几千年历史积淀为视角。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尤其对于具有几千年绵延历史的中国,决不可能经过一场思想革命实现完整意义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革新。因而,在其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交会依然长期存在,甚至会矛盾地存在于同一个生命体中。
共产党人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视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而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启蒙也与革命话语作了链接,被称为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其政治意义被突出地强调,认为“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7]P545。把激进的求新求变、矫枉过正,都是与“革命”和“彻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经过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走向执政党,党对五四运动中激进主义和矫枉过正的行为方式始终持赞扬甚至讴歌的态度。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一文中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特别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样从容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明确地疾呼“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2]P17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采取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方式;在建设时期,强调“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文革中倡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以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造反精神;在改革开放中沉渣泛起的全盘西化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潮。这些都是矫枉过正的行为方式的重要表现,这一行为方式对党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A].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J].中国青年,1925.
[5]瞿秋白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J].每周评论,(第26卷),1919-06-15.
[10]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J].新青年,(第7卷1号).
[11]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2]黄振位.略论五四精神[J].广东社会科学院,1999,(3):5.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卷31).1919-07-20.
[1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及四论问题与主义[J].太平洋,(卷2),1,15-25.
[1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35号).1919-08-17.
[17]毛泽东.致黎锦熙信[A].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18]毛泽东.致罗阶信[A].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19]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0]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卷)[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1]梁漱溟.论学生事件[J].每周评论,1919-05-18.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D2
A
1004-3160(2011)04-0047-05
2011-03-15
1.张忆军,女,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制度建设;2.孙会岩,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制度建设。
责任编辑:谭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