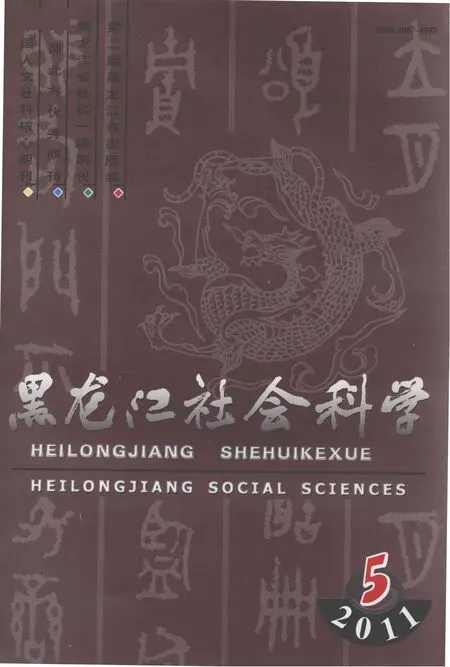论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
2011-04-11李冰梅
李冰梅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北京100089)
论居于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翻译文学
李冰梅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北京100089)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影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文学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产品的“翻译文学”由于其跨界性、复杂性、多变性近些年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多元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系统。”[1]221中国学者乐黛云说:“翻译文学由于其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另一种语言结构中,并通过译者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习惯来表达,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翻译文学。”她进一步指出:“翻译文学应是本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无可置疑。”[2]在国内多位学者对翻译文学的描述中,葛中俊的相对全面,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翻译文学的本质性特征:(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以指一类作品的总集,又可以指一种学科门类;(4)翻译文学价值的承担者和持有者是翻译家;(5)翻译文学在属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分属不同的范畴[3]。翻译文学源于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概念不同。“文学翻译”只是一个普通名词,它存在已久,强调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翻译方法上要符合文学善美要求;而“翻译文学”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文学翻译的结果,是一个集合概念。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被称为一部“译作”。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的群体翻译作品的集合才形成“翻译文学”,如杨义主编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按照阶段将翻译文学划分五四时期翻译文学、三四十年代翻译文学、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翻译文学、新时期翻译文学。近些年翻译文学史的编写,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吴笛的《浙江翻译文学史》等都证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多元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佐哈尔强调的,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对文学多元系统所作的任何描述和阐释都是不充分的[1]221。翻译文学之所以获得独立的学科意义在于它在文学系统中的特殊功能:它对于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译入语。①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本国文学、译入语文学这几个概念使用的范围不同,有时相互重叠。本文在讨论翻译文学问题时,将用“译入语文学”来表述。文学增添新的素材和形式。这些功能在中西翻译史上都得到过证明:意大利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塔尔凯蒂翻译并改写了雪莱的两部哥特式小说,引进了不同于本国文学传统的写作题材,从而促进了意大利文学在一定范围内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巨大改变与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无关系。关于这一学科的特点和研究对象,孙景尧说:“它的原产地是外国,经翻译移植才‘新生’到了本国。从语言来说它相同于本国的语言文学,而不同于原作的外国语言文学;可见它具有‘双栖性’。即既是本国文学,又是外国文学;与此同时,他既不是纯本国文学,又不是纯外国文学。这一跨国、跨语言、跨文学文化的‘两栖性’特点,就决定了翻译活动至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信息转换和沟通相容过程,也就注定了翻译文学本身就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并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4]这个居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之间的学科其地位到底是怎样的,翻译文学与传统的翻译观是怎样的关系,所有的翻译都是翻译文学吗,什么是文学翻译经典化的因素?本文以当代翻译理论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一、翻译文学对忠实翻译观的解构
翻译文学的概念在是解构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就应该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从早期道安的“三失本五不译”、玄奘的“五种不翻”,到近现代马建忠的力求译文与原文不差分毫,译文读者能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感受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无论翻译方法上是“直译”还是“意译”,其基本思想都是以原文为根本,以“忠实”为核心。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也建立在忠实之上,主要有三种模式:早期的贺拉斯模式强调的忠实是可信赖的“忠实译者”对读者的忠实;以《圣经》翻译为中心的圣-杰拉姆模式强调上帝真言的绝对权威,要求对原文的“绝对忠实”;施莱尔马赫模式为代表的诠释主义学派,反对接受在漫长的中世纪教廷加给《圣经》的解释,信奉原作者对其作品有着最权威的解释权,强调翻译对原作者的忠实。18世纪以前的许多翻译理论家以直接实践为基础创立的经验主义翻译思想也提倡对原文的忠实,如泰特勒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5]在三条原则中,第一条是基本原则,即内容忠实。他也承认,做到这三条译者必须具备原作者的才华。到了20个世纪50年代,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研究呈现科学化描写倾向。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是尤金·奈达。作为《圣经》翻译工作的主持人,他的翻译观一直围绕着“忠实”在不同的认识角度上发生着改变,从他词法、句法上对翻译问题的描写,到“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途径以及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从“动态对等”到“功能对等”,他设定最理想的翻译是译作与原作基本相同,以便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用基本相同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至少译文读者可以想象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欣赏原文的。虽然他们对翻译这个古老的话题赋予了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符号学等含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都没有脱离忠实于原文的根本的语言学研究基本框架。语言学派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是它揭示了发生在语言转换层面的事实,对翻译实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翻译的复杂性在很多情况下超出了语言层面。例如,翻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一个源文本会有多种译文本?译文本在译入语中是如何被接受的?文学翻译是怎样一种活动,是模仿还是再创造?文学翻译家真的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隐身”吗?这些问题是无法在语言学研究的层面上回答的。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从翻译的过程来看,翻译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不管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都无法重新唤起作者思维过程中所出现的原始事件,而只能是对文本的再创造。他强调,在翻译时所进行的是解释,而不是复制。不管人们多么强调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都无法消除两种语言之间的本质差异。在翻译中,译者难免会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必然会导致译者为了突出原文的某个重要特征而压制另一些特征[6]。这种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忠实翻译”的观念,终结了翻译家对“忠实翻译”的徒劳追求。
对“忠实观”的解构提高了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在传统的翻译观中,译者只是语言转换的一种工具,被称作“奴仆”、“媒婆”、“舌人”或是“隐形人”,常处于被动地位,具有明显的客体性。现代翻译思想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当代翻译理论家如韦努蒂、罗宾逊、皮姆、霍恩比等都从不同方面强调译者角色的重要。韦努蒂提出译者在译本中在场,译者是文化变革的强有力的介体。郑振铎指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7]文学翻译是各种文类翻译中最复杂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介入的最多。杨武能说:“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而在文学翻译的整个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8]由于翻译文学文本是脱胎于某种外国语言的文本,译者是这个外国文本的读者和翻译者,他的主体性在很多方面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乔治·斯坦纳认为,“任何基于个人以往对语言和文学经验的文本阅读都是解释的多重行为”,“理解即解释和翻译”。以此为基础,他还提出了四个具体的翻译步骤,即信任、侵入、吸纳、补偿,其中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对拟译文本的自身价值进行判断,“相信”它有翻译的价值,在下一步阅读中,译者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之中,再将融合了自己主观因素的阅读结果“吸纳”到翻译之中。对于译者在译入语中无法直接表达的原语文化负载词语,“补偿”就成了许多译者翻译中的重要辅助手段。译者的创造性多表现在“补偿”这一过程中,译者的目的是要在两种文化信息上取得平衡。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由于其对原文理解的差异、文学修养的差异、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每个译者所译文本的差异,这也使得译文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无限延展,造成同一原文有许多译文,使文学翻译活动呈现开放性。“作者负责把词语固定在一个理想的、不变的形式中,译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词语从源语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在译入语中存活下来。”这里巴斯奈特进一步解释了译文本生成的方式和存在的可能性。巴斯奈特的思想解释了德里达重读的本雅明,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交流形式,它更是一种延续,翻译是文本赖以延续的保证,如“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9]译作是一个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来世”和一个新的“原文本”。上述这些新的认识将关注点从文本之间的对等转向对文本生成、文本间权力和地位关系的认识上,改变了传统翻译观赋予原作绝对的权威和居于不可撼动地位的局面,让翻译研究中多种文学文化元素得以释放。
二、翻译文学在二度创作中诞生
英文Translation中的trans-这个词缀总是关联着一个翻译事件发生的两端,即源语和译入语。trans-又隐含着“距离”。钱钟书归纳了translation所包含的三种距离:一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的距离;二是译者的理解和形式之间的距离;三是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由于这些距离的存在,译本的多样化就成为客观现实。在跨越这三个距离中,作为最终产品的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10]78。钱钟书的理想翻译是“化境”,但在他自己看来,“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和‘诱’产生了新的意义”[10]79。“媒”和“诱”就是翻译文学诞生的空间。现代翻译思想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如郭沫若的“翻译创作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茅盾的“艺术创造性翻译论”、傅雷的“神似说”、许渊冲的“三美说”等都把翻译中的创造性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对文学“不可译”观点客观的肯定和积极的否定。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即翻译所失。”他的意思是,诗歌一经翻译便失去了原来的诗意。从诗歌所具有的民族性和意义的独立性上讲,他的观点符合情理,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语言体系自身的严密性,每个词义都被语境所限定。文学家在文本内赋予每个词语独立的意义连接,打破其中的一环,将在某一方面改变原有指向。但“不可译”不一定不译。这个观点无法否定各国翻译文学作品形成的历史长河。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表现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现实,从内容到形式,都融会了与其文化发生交往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元素。翻译是实现文学传播、交流、影响的重要手段。文化交往越密切,文学翻译越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就越大。译作和原作一样,都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任务,它们都是作者和译者平等创造性的产品。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二度创作”或称“再创作”进入译入语文学,成为翻译文学作品。
文学翻译中的二度创作是不可避免的。当代的翻译理论中对于译者有意而为的“创作”称之为“创造性叛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对此明确表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1]给翻译中的“叛逆”性行为以“创造性”修饰,则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地、有意识地越界与发挥以正名。这里强调“积极地、有意识地”以区别随意地和无意识的错误翻译。在实际翻译中两种情况都不可避免,但是对于翻译文学研究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前者。将译作对原作的“叛逆”作为一个值得肯定、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和论题来评析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大塚幸男对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观点给予肯定。他在《比较文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翻译通常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既不是‘断然拒绝’,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同时还指出,创造性叛逆不仅存在于翻译过程中,实际上是存在于文学作品理解的各个环节,“即便是原作本身,读者也往往是‘创造性叛逆’地加以接受的”。由此一来“译作对于读者来说,就存在着双重的‘创造性叛逆’。”他将“创造性叛逆”的提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合法化,为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给予正面的、积极的解释。如果说埃斯卡皮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予以正名和肯定还带有政治色彩和情感色彩的话,罗曼·雅各布森则从符号学的角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各个符号之间取代的可能性,肯定只能“创造性地移植”,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的翻译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移植”。雅各布森所谓的“创造性移植”就是指改变事物的面貌及其相互关系。翻译中的这种“创造性”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也是被认可的,“创造概念”本是哲学家的工作,作为哲学的解释学对概念的创造和讨论有“回溯到历史源头”的特征[12]。有创造性的译者在将源文本带入新的语言文化环境时,也以源文本出现的“历史源头”(原文)为参照,运用译入语的语言材料(词语意义与表现形式)创造出能让译文读者接受的新文本,担负起“创造概念”的责任,译文读者就在“熟悉”与“陌生”的交错间通过“熟悉”的部分去理解“陌生”的部分,不断积累他的认识。中外文学史上成功地完成译本的二度创作,让译本成为译入语文学一部分的译者很多。李奭学举过英国诗人兼翻译家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的例子。《鲁拜集》原本是11世纪波斯诗人奥玛珈音(Omar Khayyam,大陆一般译为“欧玛尔·哈亚姆)的《四行诗集》,经菲茨杰拉德的二度创作,将“珈音的‘三行转’,他易之为‘牧歌体’,又消减原作的‘载酒狂歌’的傲态,代之以个人自由心证所得的愁思。是以所成就的‘英译本’,根本就是‘新著’。”由于菲茨杰拉德的生花妙笔,《鲁拜集》成为英语文学名篇,菲茨杰拉德也因此进入艾文思(Ifor Evans)那个著名的《英国文学史略》。李奭学称菲茨杰拉德不仅是翻译家,“也因所译而受封为‘19世纪出类拔萃的诗人’”。余光中介绍荷马诗歌格律在英国的变化时说:“荷马那种‘当叮叮’的敲打式‘一长二短六步格’,到了18世纪文质彬彬的颇普(Alexander Pope,大陆通译“蒲柏”)笔下,就变成了颇普拿手诗体‘英雄偶句’,而叱咤古战场的英雄,也就驯成了坐在客厅里雅谈的绅士了。”[13]35英美著名汉学家的汉诗翻译在西方很有影响。香港学者钟玲把韦利等人翻译中国诗歌的方法称为“创意英译”。正是韦利的“创意英译”使得其译诗中要表达的主题更明确,更便于西方读者的接受。比如他将白居易的《过天门街》翻译成“Passing Tien-men Street in Ch’ang-an Seeing a Distant View of Chung-nan Mountain”(过长安天门街,远眺终南山),韦利在英译诗题中附带说明天门街和终南山的地理关系。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是历史因素、现实因素与译者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译学界许多学者已经“把翻译文本看做经过变形和改造,融入译者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的一种自足的艺术创造产物”[14]。这就等于承认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的合理性、必然性和独特性。各个民族的文学在表述上的差异和文学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决定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将极具民族和民俗特点的文学表达创造性地转换成能够被译入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以实现翻译的基本交际功能。
二度创作也是创作。与创作母语作品一样,“译者要达到这种自由的艺术境界,完全取决于其高深的文学素养和深厚的语言功力,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情,以及丰富的翻译实践。搞文学翻译不追求境界,只追求‘术’与‘道’是远远不够的。”[15]文学性和文学审美要求译者在二度创作中要有很高的文学感悟力和文学表现力,他熟悉译入语文学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的规定,掌握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审美需求,了解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态度,这些是让他的二度创作能够顺利进入译入语文学大系统中的条件。与原创作品不同的是,翻译文学家有源文本之累,使他难以就一个文学主题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彰显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而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在有限的空间内使外来文本能够最大化地被译入语读者理解并接受。余光中认为,虽然翻译只是一种“有限的创作”,而创作是一种“不拘的翻译”或“自我翻译”,但是翻译的难度不亚于创作。“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将一种经验变成文字,但那种经验已经有人转化成文字,而文字化了的经验已经具有清晰的面貌和确定的含义,不容译者擅加变更。译者的创造性所以有限,是因为一方面他要将那种精确的经验‘传真‘过来;另一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还要保留那种经验赖以表现的原文。这种心智活动,似乎比创作更繁复些。”[13]34就诗歌翻译而言,巴斯奈特承认翻译无法“复制”原诗,她提出“种子移植”的观点,译诗不是复制原文,而是创作出相似的文本,具体做法是将语言材料拆散,再在译入语中“重组”以实现”种子移植”。这个隐喻提出三个问题:(1)这个“种子”是从原语文学中选出来的;(2)“种子”的核是不变的,译文的基本信息要保持;(3)“种子”要适应新的土壤,即译入语文化。如果说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化的移植,那么译者就是这移植者,为了让他选的种子能在异地生长,他要帮助它们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
三、翻译文学的地位与经典化
长期以来,翻译文学一直被视为派生的、模仿的、次要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并且“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16]。一般研究者由此判定翻译文在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边缘地位。佐哈尔在他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给翻译文学独立的学科定位,将“翻译文学”从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一个学科术语,还重点论述了翻译文学的地位与功能以及与国别文学的关系。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特定的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处于中心还是边缘,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与翻译发生的特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他总结翻译文学地位变化的三种情形:一是当译语文学系统自己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形成阶段时;二是当译语文学自身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三是当译语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时。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译入语系统中都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退居边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足以为之佐证:翻译文学在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诞生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基本成型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时我国自身文学正处于一片荒芜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都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表明,译入语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文学的转型都离不开翻译文学的介入。也许译入语文化的社会语境的多变性令这三点不能涵盖所有可能存在的情况,但它足以让人们看到翻译文学对于译入语文学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所起到的积极、推进、改革、创新的意义。
佐哈尔从多角度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地位的变化,不过他没有详尽阐释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翻译文学如何在译入语文学中被经典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由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作出了回答。在他们看来,任何文学都存在于特定社会、特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影响与作用始终会受到一系列相互关联、互为参照的因素制约。因此,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再到译文的编辑、阅读和评论,都是由不同的译入语文化价值决定的。换句话说,翻译是社会文化产物,是文化操控的结果。他们提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所有的改写都反应了某种意识形态、诗学,并因此操控文学使其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对于文学而言,“改写可以介绍新概念、新文类、新的文学手段。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创新史、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权力形成的历史”。勒菲弗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思想意识、文学功能结合起来,强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方面对翻译的决定作用。这三方面不仅是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文学翻译是否能够成为翻译文学的三个主要检测标准。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过滤中成为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的。勒菲弗尔更把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因素分为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所构成的专业人士,有时他们会压下一些公开反抗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时候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改写以使之符合特定时空中的诗学和意识形态。如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俄苏文学翻译的选择,是因为俄苏文学对当时的中国文学所具有“典范”意义,及其在建构“真理话语”和“革命文学”等方面所起到的引导与规范作用。而同时期对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翻译则是“那种将国家、民族、自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赞颂,无疑非常合乎当时人们对于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对于抗战中的中国格外具有吸引力”[17]。这不仅说明这时期中国文学深受来自于苏俄、英美法文学的影响,同时还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模式的需求以及诗学倾向。外因则是赞助力量,按照勒菲弗尔的解释,它是这样一些个人或机构,拥有能够“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文化学派改写即操纵的观点对翻译的积极意义是翻译不再是原作的“派生物”,译作的地位不一定低于原作。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控”特定社会,进而改造、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手段。
与民族文学的经典化一样,一个译本问世后,要进入译入语文学的评价体系,符合这个民族的审美需求,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沉淀下来。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文学为例:严复的“信、达、雅”之“雅”,钱钟书的“化境”之“境”,许渊冲的“三美”,是翻译标准也是中国文学标准,无不凸显中国的审美倾向。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也有一代的翻译文学。文学翻译的发生与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勒菲弗尔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伊特》的几个英译本做了历时研究,认为某些译本的成功与译作的质量好坏关系不大,而与原语文化在译入语读者(英语读者)心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他又以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的三个译本为对象,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文学及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偏见,评论家、翻译家共同为不懂德语的人塑造了英语中的布莱希特形象,实现的是新的文化建构。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指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才会有力量,才能影响一国文学界的将来,因此他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1)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2)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接触。”[7]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在中国的盛行,4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延安的译介等等,都反映了翻译文学与时代的应和关系。赵稀方对此这样解释:“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无不来自于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18]1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中,翻译文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翻译活动本身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并非所有用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会构成翻译文学。只有与译入语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了一定关系的译作,才能纳入翻译文学的叙述范围。冯骥才在《文学翻译的两个传统》一文中,对百年来中国翻译文学的现状作了精辟的总结,指出这些翻译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成为文学经典,是因为翻译文学家们开辟了百年翻译上的两个传统,一个是为了精神而翻译,一个是追求译文的经典性。而这两个传统常常是合二为一。谢天振在《2010年翻译文学一瞥》一文,提出三点:“何谓优秀翻译文学?众所周知,文学翻译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译介在古今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因此,评判一部译作是否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看它所译介的原作是否属于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列。否则,如果原作是一部在世界上属于二三流的作品,甚至是文学垃圾,那么这部译作的质量再高,它也没有资格入选像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国家级别的奖项。其次,评判一部译作是否属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之列,还应该看它是否对译入语国家的文学、文化作出了贡献……而假如一部译作尽管翻译质量也还不错,出版后也广受读者欢迎,发行量还很大,那至多也就是一部畅销书而已,而绝对不够优秀翻译文学的资格。最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当然还应有较高的翻译质量。但这里的质量不应该只是指译文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毫无瑕疵,而还应该指译作能不能给译文读者以原作读者同样的美的享受,同样的心灵感动,同样的思想启迪……换言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译作应该像原作一样,营造起一个优美、生动、丰富、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这样的译作才称得上是优秀的翻译文学。”这三点从选译文本、译文本在译入语的影响以及译入语诗学标准对译文佳作提出了要求。只有被译入语文学接纳的译作才可以存留下来,才能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发挥作用。翻译文学是民族语言和文学与外国语言和文学之间文学相互交流、渗透、吸收、融合的产物,它带给民族文学新题材、新形式、新观念,它能拓宽译入语读者的视野、增加他们的审美情趣、甚至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从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翻译文学一旦成为中文,就成了中国文化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在新时期文化建构中担当着重要作用。”[18]1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各卷封底写得特别清楚:“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以翻译为其重要标志,又以翻译为其由外而内的启发性动力。翻译借助异域文化的外因,又使其内渗而转化为自身文化的内因。同时,翻译文学又提供一种新观世眼光和审美方式,催化着中国文学从传统的情态中脱胎而出,走向世界化好现代化,并充实、丰富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谱系。百余年以来的翻译文学乃重要的文化资源,借此可以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和发展形态,研究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建构的多层性和互动性的文化时空。文学史因翻译文学的介入而变得博大纷繁,从而具有文化论衡的精神史的性质。”翻译文学在这些方面具有普适意义。
翻译文学居间性特点使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翻译文学是基于文学翻译的事实,文学翻译中所有相关的因素都会为翻译文学研究打开一个层面。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说,“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语言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跨文化文学交往的质量,而且译作本身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体系。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方法可分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从共时的维度可以观察两种或者多种文学关系的变化,如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某一国或某几个国家的文学,或者某些作家被大量翻译;从历时的维度可以梳理和勾勒出文学发展的路线图和趋势,以翻译史的形式呈现于世。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与国别文学对话的平台和产物,可以帮助实现双向阐发,研究翻译文学产生的环境和背景、翻译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源文本的传播等不同话题,这些对于认识国别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谢天振.当代我国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3]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16.
[4]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81.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22.
[6]朱建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44-145.
[7]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J].改造,1921,3(11).
[8]许均.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227-228.
[9]周国平.名著在名译之后诞生[N].中华读书报,2003-03-26.
[10]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12]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89.
[13]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14]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02.
[15]王秉钦,王颉.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7-8.
[16]许均,穆雷.翻译学概论[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84.
[17]李宪瑜: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英美法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66.
[18]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011-07-28
李冰梅(1957-),女,吉林长春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译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