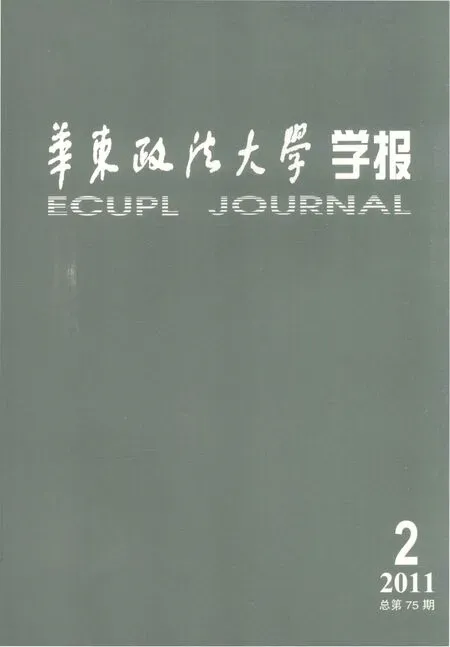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城市地位”理论小结
2011-04-09吴旭阳
吴旭阳
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城市地位”理论小结
吴旭阳*
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是西方文明进步的象征,以帝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一直威胁着城市的自治。罗马法学家是这个时代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城市地位”进行了不同的论述:有的从“法律”上为城市自治进行了理论论证;有的则强调“君权至上”从而断然否定了城市的自治;有的则在二者之间进行妥协,仅在“事实”上承认城市自治。其中,巴尔多鲁尤为突出,他为城市自治进行了系统的合法性论证。
中世纪 城市 自治 帝权 罗马法学家
一、引子
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雏形,它从诞生开始就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必须与其进行斗争或妥协。从中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就出现了自治、半自治城市,甚至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它们对内进行立法活动,并任命官员,实施管理;对外与各种封建势力进行交往。而作为城市自治标志的法律文件——特许状(特许状是确立城市独立地位的基础性法律文件,通常由城市所在地的封建主授予城市),在此前后大量出现。早在1066年,阿尔卑斯山一带就有城市获得了特许状,以确认其事实上的准独立状况。此后,此类文件被大量地授予了城市和大学,其地理范围不仅涉及意大利、法兰西,乃至德意志;甚至王权强大的英格兰也颁发了大量的特许状。〔1〕Mary Bateson,The Laws of Breteuil,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5,No.57,Jan.1900,p.73.这些特许状“引导城市发展成为有法律意义的城市,它在法律上与农村分离开”。〔2〕[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
然而,在封建体制中,自治城市是另类的。它的存在并不能从封建政治理论中合理地推导出来;只能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它时刻受到各种封建势力的威胁,典型事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在1158年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伦加利亚敕令》,试图强行将意大利诸城纳入其强权之中。这激起了城市的反抗,最后他被迫收回成命。1183年,帝国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诸城达成谅解,废止了《伦加利亚敕令》,取而代之的是《康斯坦茨和约》。根据和约,城市在理论上接受皇帝为宗主,而皇帝也承认城市“事实上”的自治地位。斗争之后的妥协,帝国赢得了表面的尊严,而城市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
作为斗争的延续,城市必须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对抗封建强权(尤其是普世的“神圣罗马帝国”强权)。虽然城市不符合封建理论,但在封建势力破碎的“马赛克式”政治版图上,其存在却又是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是城市存在的根基。即使是另类的“事实”,城市依旧有必要在理论上为这种“另类的存在”提供辩护;甚至建构完整的“法律”理论以论证其自治的合法性。
这个时代是罗马法复兴的伟大时代,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罗马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和后注释法学派;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罗马法学大师。这些大师不仅在传统的私法领域有所建树,而且不少人对“城市自治”和帝权等话题也没有回避,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痴迷于罗马法的法学家们,多数能接受《国法大全》对君权的强调,他们把对罗马法的效忠,部分地转移至同时代也有“罗马帝国”头衔(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身上。因此,他们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权威(至少在理论上承认),以及罗马法的普世效力。此外,他们又是城市的显贵,在城市中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又背负着城市对自治的理论要求。因此,罗马法学家们有一定的兴趣来论证城市与帝国等封建势力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能够从罗马法和实证的角度论证城市自治的合法性,部分人信奉“帝权至上”,甚至有人还能调和城市自治与帝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可以归纳为法律确认、否认自治和事实承认三种。
二、法律确认的理论
法律确认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事实上承认城市的自治地位,并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论证。在中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此类观点理论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完备的不同阶段。
注释法学派是罗马法复兴的第一个学派,其创始人是伊纳留斯(Irnerius,约1050或1060-1130年)。但是,作为创始人的伊纳留斯及其主要弟子反对城市自治。所以,最早具备此类观点萌芽的是该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巴塞努斯(Johannes Bassianus,约1190年去世)。他一反之前两代学者支持帝权的传统,转而激进地强调人民的意志。他强调制定法和习惯法的效力都来自于人民的意志,并提出社团理论。根据他的观点,作为人民聚合体的城市,自然就能够获得合法的地位。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论萌芽,没有完整的论证。
作为巴塞努斯的学生,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阿佐(Azo,约1150-1230年),自然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对皇帝的最高权威不以为然;而是继承了巴塞努斯的理论,并进行了深入论述。阿佐认为,“最高权力”(merum imperium,原意为“司法裁判权”)其实就是“司法裁判权”(iurisdictio),但该权力并非皇帝独享;根据罗马法,其他高级官员也拥有此权力。而在古罗马的体制中,虽然自治市的长官不能拥有完整的“司法裁判权”,但他们可以部分拥有。〔3〕Kenneth Pennington,The Prince and the Law,1200-1600 Sovereignty and Rights in the Wester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9.这就暗喻着城市当局也可以部分享有“主权”(司法裁判权)。此外,在罗马法中,“市”是自治的;这也是城市自治获得罗马法奥援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而从最根本的角度,阿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统治权威来源于法律,而法律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即使是君主的权力最终也源自人民的同意。作为最高权威的“司法裁判权”来自于人民“共同体”(universitas)的同意,是一项集体的同意。帝权虽然直接源于王室法(lex regia),其最终来源依旧是人民的同意。在这里,人民以一个“共同体”的身份具有这种权威。据此,城市作为一个“事实上”(de facto)存在的市民“共同体”,也具有最终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帝王权力之外。〔4〕Peter Stein,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0.这样,阿佐就跳出封建传统的“帝国”和“普世统治”的政治理论;而城市则在“人民共同体”这一新的法学理论上有了栖身之地。
阿佐进一步进行论证,他区分了一群“个人”和政治共同体的“集体”之间的区别——作为“个人”的人民必须服从皇帝,而作为“集体”的人民则高于皇帝,人民的“共同体”能够授予皇帝立法权,亦能够保留立法权。从这个角度看,阿佐的理论具有革命性,不仅为城市的自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能为后世的现代国家提供理论支持。虽然阿佐不能更深入地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初步搭起了理论框架,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作为后注释法学派(亦称评注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尔多鲁(Bartolus,1314-1357年)不仅在私法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城市自治以及对抗君权的理论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虽然巴尔多鲁在这方面的论述与阿佐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显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阿佐的理论,使该理论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
巴尔多鲁指出了帝国权力理论上的普世性与实际上的有限性。巴尔多鲁承认帝国的普世权力,他视帝国为普世的政治组织,帝国法为唯一的普世法,各国国王在理论上从属于皇帝,任何对帝国的反叛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并不认为皇帝的权势是无限的;相反,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约。〔5〕J.Neville Figgis,Bartol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tical Idea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19 ,1905,p.156.
巴尔多鲁指出,从世俗的角度看,皇帝是全世界的主人,国王们的统治源自于帝国的许可;但从政治神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国王的统治均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上帝的许可。因此,帝国的普世权力并非绝对的实际意义上的普世所有权(universal propriety);相反,国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有实际管辖权,这种实际管辖权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这种权力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权力:他们可以像皇帝那样制定法律,任命官员,实施统治和裁判。〔6〕Woolf,Cecil Nathan Sidney,Bartolus of Sassoferrato: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pp.110-111.根据这种理论,城市也能够获得自己的实际管辖权。他提出的标志性论断就是“城市自己就是国王”(civitas sibi princeps)——在自己的领地内,城市自己就是皇帝。
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巴尔多鲁双管齐下,在罗马法和基督教中寻找理论依据。从罗马法的立场出发,他宣称帝国人民将统治的权力授予了皇帝,但是也保留了选举和罢免皇帝的权利,这种权利掌握在日耳曼王公和教皇手中。〔7〕Floriano Jonas Cesar,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 of Saxoferrato:An Intrinsic Connec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5,No.3,Jul.2004,pp.375,378.此外他指出,根据基督教理论,世俗的权力虽然来自于上帝,却必须经过教皇的中保,因此皇帝也受制于教皇。〔8〕Magnus Ryan,Bartolus of Sassoferrato and Free Citie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6th Ser.,Vol.10.,2000,p.75.这样,皇帝的权力就不是绝对的,更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不仅受限于封建贵族,更受限于教会。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自然对城市鞭长莫及了。但巴尔多鲁的意思却是更进一步:无论皇帝还是教皇,还是封建诸侯,无论他们之间谁的权威更高,都只是遥远的存在,他们都不能干涉城市实际上的自治。因为,城市在“事实上”是独立自治的。
为此,巴尔多鲁从“法律”与“事实”的角度对城市自治进行了初步的论述。他指出,存在着两种管辖权,即“法律上”(de iure)和“事实上”的管辖权,这二者都是城市自治的合法性基础。从最基本的角度看,城市及其统治是“事实上”存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这显然不够,因为“存在不一定合理”,更何况巴尔多鲁谴责“暴政”,质疑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此,城市还必须获得“法律上”的理论支持。他进一步指出,城市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就是获得了帝国的许可——严格地说是“默许”。〔9〕Floriano Jonas Cesar,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 of Saxoferrato:An Intrinsic Connec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5,No.3,Jul.,2004,pp.376-377.然而,这种理由着实牵强;退一步说,万一帝国收回许可呢,那城市如何自治?更何况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实情却是:城市虽然在“事实上”不容置辩,却在封建理论的“法律上”显得卑微与无力。因此,巴尔多鲁必须在理论上再进一步,以让城市获得“法律上”昂首挺胸的自信,这就是沿着阿佐理论之路继续往前走。
现实地看,城市是民众的共同体,所以要论证城市的地位,尤其是论证其处于封建体系之外的合法性,就不能绕过“君主”与“民众”关系的讨论。在封建政治和法律理论中,在“君民”关系的阴影下,作为民众政治体的城市明显处于劣势;因此,想要逃脱皇帝、国王等封建主的魔爪,逃避其理论上的优越性,就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与阿佐一样,巴尔多鲁另辟蹊径,超越封建理论,提出了民众的终极权威,从最根本之处来最终解决问题。这也是他相关理论中最重要的亮点。
巴尔多鲁首先肯定了民众的最高地位,指出民众的意志可以否定其他权威,这就是城市自治权的基础。巴尔多鲁展开了细致的论证,在他看来,人民的同意是最重要的,是法律约束力的最终合法性来源。他在此建构了一个人民的“共同体”理论:既然政治共同体由人民构成,那么“共同体”的“同意”的最细化、最基础的表现就是——人民的一个个“个体”在“共同体”中表达自己的“同意”。当然,由于个体的多样性,“一致同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通常只能让多数“个体”的意见成为整个“共同体”的意见(否则会导致共同体在实践中的不可能)。多数意见由此可以对整个共同体产生约束力,而不管少数人的反对;这种约束力就是法律强制力的基础。
因此在法源上,他认为:所谓的“成文法”——帝国官方所制定的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具有约束力;而“习惯法”也具有约束力,因为其也源自人民的同意,是人民“默认的同意”(tacitus consensus)。〔10〕Walter Ullmann,A History of Political:The Middle Ages,Penguin,England,1965,p.215.二者都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所以有管辖权。他据此进一步指出,“成文法”和“习惯法”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即“明示的同意”和“默认的同意”之间的区别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民的同意:前者是人民“书写”下来的同意,而后者则是人民“默认的同意”。那么,在习惯法中,人民如何确立自己的“默认的同意”呢?就是人民大众的群体性惯常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习惯法的“人民同意”的性质,也可以推导出习惯法的合法性。〔11〕Walter Ullmann,Bartolus on Customary Law,in Jurisprudence in the Middle Ages(Collected Studies),Variorum Reprints 1980,pp.269-271.也正是基于人民的同意,习惯法才能取得与帝王制定法同等的地位。
法律约束力的本质就是人民的同意;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此之外没有更高的许可;只有人民的同意才是统治和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人民“自我为王”(sibi princeps)。这样,他将人民推到了最根本的地位。〔12〕Floriano Jonas Cesar,Popular Autonomy and Imperial Power in Bartolusof Saxoferrato:An Intrinsic Connect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5,No.3,Jul.,2004,p.378.而作为人民“共同体”的城市呢?既然人民最高,人民可以自我为王,那么作为人民共同体的城市当然也就可以建构自我统治的合法性,无需其他的许可。因此,“城市自己就是国王”的结论就水到渠成。而且在这里,城市自我为王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更具有“法律”基础——其建立在新型宪政理论的基础上。不仅城市的合法性不需要外来的许可,而且除了人民,没有更高的许可。
那么人民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同意”呢?城市“共同体”不能只停留在虚幻中,必须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前面已经指出,多数意见可以成为共同体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产生法律强制力(约束力);因此,城市的多数成员意见就十分重要。在他看来,作为共同体的城市是人民的集合,这种人民不仅包含显贵,更以平民为主。城市的市民通过选举议会和行政官员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议会和政府的权力来源就是人民“共同体”的“同意”,其统治就是合法的,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合法而且具有约束力的。
然而,这样又可能导致另外的问题,即是不是所有的“共同体”都可施行统治呢?当然不是。巴尔多鲁更详细地建构自己的统治理论,指出城市作为统治的“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1)可以被视为一个城邦(respublica,原义为“共和国”);(2)有财政上的国库;(3)拥有统治权(imperium);(4)有立法权。〔13〕Woolf,Cecil Nathan Sidney,Bartolus of Sassoferrato: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p.115.这样,城市的共同体就与一般的经济领域经营性共同体区分开来,就能够具有初步的现代“主权”。
巴尔多鲁的理论建构超越了阿佐,不仅从“事实”,更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建构,从而彻底结束了城市“不明不白”的法律地位,为其争取了雄厚的理论支持。显然,这一理论具有社会契约论的萌芽,在中世纪的西方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因此受到不少法学家的反对。
三、否认城市自治的理论
否认城市自治的罗马法学家阵营也不容小觑,这一理论尤其在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中拥有诸多支持者。该观点的持有者通常也支持皇帝,有人甚至还支持“君权绝对”。
作为罗马法复兴运动的肇始者,伊纳留斯在罗马法复兴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伊纳留斯在晚年明确采取了支持帝权的态度。在他的学说中,帝权是最重要的,民众的习惯法虽然是人民的意志体现,但不能高于君主的制定法,只有在符合制定法的前提下习惯法才具有效力。他甚至宣称,“今天,‘立法’的全部权力都转移到皇帝那儿去了”。〔14〕[英]J.H.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80、581 页。在这种理论下,城市即使自治,也要得益于皇帝的恩赐。
而他的四大弟子继承了他的学问,也基本继承了他的政治立场:“四博士”在著名的1158年伦加利亚会议中,坚定地站在了皇帝一方,支持他对伦巴底诸城征税以及限制城市的自治地位。〔15〕Paul Vinogradoff,Roman Law in Mediaeval Europe,Harper& Brothers,1909,p.51.同时他们还认为,皇帝对城市享有全权,这种全权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及对任何事务都有效的最高权力。〔16〕Arthur P.Monahan,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p.23.当然,他们并非无限度地支持帝权。据说,在一次与巴巴罗萨的巡游中,“四博士”之首的布尔加鲁斯(Bulgarus)就否认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另一个博士马尔提努斯(Martinus)则站在皇帝一边。
在注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阿佐之后,一些法学家虽认同阿佐的前述理论,却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利于帝王的进一步推理,即一旦人民将权力转让给帝王,则他们无权撤销。〔17〕Peter Stein,Roman Law in Europe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60.这种推进,其实就是对阿佐理论的背叛,也限制了在法律上论证城市自治的可能。
而阿佐的继承人——注释法学派另一个代表人物阿库修斯(Accursius,约1182-1260年)显然是城市自治的最大敌人。因为他不仅提出了“君权绝对”理论,而且断然否定了城市自治的重要前提——阿佐的“人民共同体”理论。这种两面夹击对城市自治形成了重大的威胁。〔18〕Brian Tierney,“The Prince is Not Bound by the Laws.”Accursi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No.4,Jul.1963,p.389.
首先,阿库修斯驳斥了阿佐的“人民共同体”理论。阿库修斯认为,这种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他毫不掩饰地亮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团体无非就是作为成员的个体”。〔19〕Joseph P.Canning,Ideas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on the Roman Law,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Vol.33.,1983,p.24.这种对团体人格的否定,也就否定了作为“市民共同体”的城市的独立可能。根据这种理论,分散的个体只能服从帝国的统治;这样,城市的自治地位就被釜底抽薪,无所依靠了。
其次,阿库修斯强调“君权至上”。他认为君主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的制约;为此,他还援引了《学说汇纂》作为论证“君权至上”的依据(如D.4.8.4和D.4.8.51)。阿库修斯的“君权至上”观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对通常被认为是限制王权的D.32.1.23(皇帝宣称,“我们虽然不在法律的制约下,但我们要依法生活”。),他却作如此评论:“法律涉及最高统治权(imperium),在I.1.2.6.中,王室法将最高权力授予了君主。这将他从繁杂的法律细节中解放出来;因为,如果他决心不遵守这些法律细节,则正如D.4.8.4所言,没有其他权力可以使他的行为无效。”〔20〕Brian Tierney,“The Prince is Not Bound by the Laws.”Accursiu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5,No.4,Jul.1963,p.389.因此,阿库修斯支持“君主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est)的论断。但是,他的论证显然存在硬伤,因为他在王室法的范围内来证明帝王的绝对权威,而不能够从法律之外“更高的合法性”角度进行论证。
总体上看,在对待皇权方面,虽然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各有主张,但一部分还是站在了皇帝一边。毕竟,经过查士丁尼筛选之后的罗马法文献,更多地保留了支持皇权的因素。罗马法的一些著名法谚为众君主们所津津乐道——“君主的意愿具有法律的威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和“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也是为何中世纪后期的多数国王,甚至英格兰都铎王朝诸王也不禁要提倡罗马法的原因。相比其他法学派,注释法学派更将《国法大全》视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法律文本,因而这些理念也就深刻地影响了该学派一大部分法学家,使他们成为帝权的支持者。
四、事实承认的理论
后注释法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巴尔多鲁的学生巴尔杜斯(Baldus,1327-1400年)继承了他们老师的立场,却在观点上有所后退。这种后退的结果就是折衷——事实承认的理论;该理论只是在事实上承认城市的自治,又在法律上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威。这种论证更巧妙,也更保险,却无碍于政治现实;与其说是一种妥协,还不如说是高明的策略。但由于他试图在双方之间进行妥协,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的论述。
巴尔杜斯对城市自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他认可法国法学家库内奥(Guilelmus de Cuneo)所提出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理念,即人们可以结成团体(国家)而依法生活。〔21〕Joseph P.Canning,Ideas 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on the Roman Law,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Vol.33.,1983,p.11.受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影响,他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理所当然地结成国家(城邦);国家是拥有政治天性的人们的集合体。〔22〕Arthur P.Monahan,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p.30.因此,他根据自然法理论指出,市民身份就是人本性的一种展现,依法生活是人的主题;也只有如此,“人”才是完满意义上的人。而国家(城邦)就是人们依照自然理性结合成的团体,所以该团体就可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市政当局),可以施行统治。据此理论,城市自治获得了自然法理论的支持。
与巴尔多鲁一样,巴尔杜斯承认“人民的同意”是政治建构和立法的基本要素。对他来说,“人民的同意”也是习惯法和成文法的合法性基础,习惯法是默认的同意,而成文法则是明示的同意;它们之间的区别仅是同意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面对“习惯法是否需要帝国权力认可”的问题时,巴尔杜斯显然认为,人民以自己行为的方式所制定的习惯法,不应当需要其他统治者的认可。〔23〕Joseph P.Canning,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aldus de Ubald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1.城市在事实上独立的情况下,也就能够不服从皇帝的命令。此外,他指出城市在立法时有义务维护“共同的善”,也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判断;在此根本的立法指向上,城市甚至有权抵制来自外界的干扰。〔24〕Arthur P.Monahan,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0.他的理论虽然也是进步的,但他却不能像巴尔多鲁那样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民自我为王,人民高于皇帝;也不能主张作为人民共同体的城市的最高合法性。
为了解决皇帝与其他现实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以论证城市自治的合法性,巴尔杜斯还从万民法的角度进行阐述;这就涉及到皇帝或教皇的普世统治问题。因为万民法作为诸多统治者在法律上的一种共识,一种普世适用的规则,其实与皇帝、教皇的普世法律之间存在着重叠或重合。因此,他就将皇帝的法律当成万民法,而城市的立法则是市民法。他在此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与统一:从“现实”而言,各个统治者实际上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行使着立法权,他们的法律各不相同,可以被认为是不同的市民法。不同统治者的市民法在一些方面存在着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其实就是万民法;而皇帝或教皇从事的普世立法活动就是揭示这种万民法。〔25〕Arthur P.Monahan,From Personal Duties Towards Person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p.27.这样,事实上的“自治”(独立)就与理论上的“一统”统一起来了。因此,基于万民法与市民法的区分,包括城市和王国在内的各种实际统治者都能够拥有实质上的“主权”或“统治权”。
巴尔杜斯还认为,这种实质“主权”的基础就是人民的自治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源自万民法,更源于“共同理性”。但是,巴尔杜斯的立场又摇摆不定,因而他的理性观和万民法在帝权那里却又失效。对他而言,帝权可以破坏万民法,也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理性之上,这就反映了其理论的矛盾性。
所以,巴尔杜斯在大框架上依旧是服从旧秩序的,他的理论出现了一些矛盾。虽然巴尔杜斯十分欣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但是在他笔下“政治天性”的人,并不必然成为“王”;城市和市民也不必然“自我为王”。城市即使是“事实上”的独立,也必须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皇帝依旧是终极的权威。他甚至还认为,“统治权”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城市所能够享有的只是低层级的“统治权”。〔26〕Joseph P.Canning,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aldus de Ubald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98.当然,这种理论也可以适用在封建国王身上,他们与城市一样,也能够享有“事实上”独立于帝国的那种低层次“统治权”。
巴尔杜斯指出,“对上级的否认”是理论上不完满的体现;因此,其只能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换句话说,在完美的“法律”理论中,上级能够完成对下级的控制,下级必须服从上级。〔27〕Joseph P.Canning,Ideasof the Stat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Commentatorson the Roman Law,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Vol.33.,1983,p.9.然而,不完美的政治现实使得上级(皇帝或国王)无力控制包括城市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这种状况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城市,而在居心叵测的大小诸侯、教廷和主教,城市只不过是在势力纷争中才出现并成长的。所以,基于这种现实,城市也无法服从上级(皇帝)。但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帝权或王权能够翦灭群雄时,城市自然也会顺应大一统的时代大局,皈依于统一的帝权(王权)。
他还认为,城市的自治及不服从上级“要么根据法律,要么根据事实”(de iure vel de facto)。〔28〕[英]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下),程志敏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0页。既然封建体制的政治法律秩序不允许城市自治,那么城市的自治只能作为一种事实了。这个基本性论断会导致一系列的连环法律效果,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巴尔多鲁的城市自治理论不稳固了,他的“人民主权”理论也因此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巴尔杜斯的“代理统治者”(vice principis)观。也就是说,城市不能自我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根本就不是统治者,更不是主权者,只能在上级无力进行统治时“代理”进行统治。
从总体上看,巴尔杜斯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城市的自治地位,但在“法律上”并不承认,而是臣服于当时主流的封建统治秩序。由于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妥协,所以其理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矛盾。
五、小结
在后注释法学派之后,罗马法复兴进入了人文主义法学派阶段,历史的车轮驶离了中世纪,来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普世的“神圣罗马帝国”蜕化为德意志帝国;踌躇满志的市民阶层已不满足于城市政权,开始展望国家性的权力。所以,此时的城市自治已不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主权国家、宗教改革等热点问题,因此相关的争议和理论也就渐渐消退了。
通过研究两个学派主要人物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作为意大利人,很大一部分罗马法学家对城市持一种或明或暗的支持态度。巴尔多鲁和阿佐采用的是直接建构式,具有较强的革命性;而巴尔杜斯也并不回避问题,在原有的政治法律理论中论证城市自治的合法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以下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法学家们主要的活动地是城市。众所周知,这两个法学派以意大利北部为基地(包括了法国南部),这恰恰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法学家和大学的活动以城市为中心,而多数城市恰恰是自治的。例如,罗马法复兴的重地——意大利的波伦那,就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在波伦那,执政官被称为“contado”,由城市自己选任;他行使实际管理权,职责范围包括了行政与司法。而波伦那城市的上层,如律师、纺织商人、银行家等等,都拥有大量财富,实际上控制着城市。〔29〕C.M.Ady,A Charter of an Italian Rural Commune,1488,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48,No.190,Apr.1933,p.270.巴尔多鲁的主要活动地佩鲁贾(Perugia)也是一个自治城市。作为著名的法学家和城市自治的最有力支持者,他于1348年获得了佩鲁贾的市民权;城市还授予他大量的荣耀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城市的自治和利益呼号也是顺理成章的。〔30〕William Rattigan,Bartolus(1313-1357 A.D.),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New Series,Vol.5,No.2,1904,pp.230-231.Julius Kirshner,Civitas Sibi Faciat Civem:Bartolus of Sassoferrato’s Doctrine on the Making of a Citizen,Speculum,Vol.48,No.4.,Oct.1973,p.697.
其次,法学家们主要在大学中进行教学研究活动,而大学与城市息息相关,其在法律上与城市有相同之处。大学是自治的,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它们也是通过特许状获得类似于城市的准独立地位。根据特许状,大学不仅能够进行日常的管理活动,甚至能够成立法庭,独立地行使部分司法权。学生组成学生会,对大学进行管理。总体上说,自治的大学与自治的城市有相近的血缘和类似的地位,现代学者这样评判二者:“大学,无论其是教师或学生(控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行会:大学的崛起,只不过是11世纪席卷欧洲各城市的伟大联合运动中的一波。”〔31〕Hastings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Vel.1),The Clarendon Press,1895,p.153.因此,大学中的罗马法学家们自然倾向于城市自治。
再次,我们会发现,后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们更倾向于城市。除了他们那个时代“神圣罗马帝国”日渐式微的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比注释法学派的前辈们更注重现实。后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们多从事实务工作,因此他们必须承认现实生活中实际有效的一切法源。与注释法学派将罗马法抬高到“神圣”的高度不同,他们意识到世界已经改变,虽然罗马法依旧,但是罗马帝国已经不在。罗马法可以是普世的罗马法,但是现实破碎政治格局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不可能具有实际上的普世管理权。
最后,对于希腊古典时代的政治哲学而言(甚至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依旧如此),城邦都是核心的主题;城邦是正常的政体,而帝国则是变态的政体。所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大师的理想政体设计都以城邦为原型,优选不同的政体。虽然,古典学说在中世纪前期的黑暗时代已经被信仰(基督教)与野蛮(日耳曼人)所覆盖;但是随着文化的复兴,这些学说又开始流传开来。到了巴尔多鲁时代,随着阿威罗伊主义的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又成为西欧的显学。他的政治和法律学说,也为学界人士所借鉴。以城市自治理论的集大成者巴尔多鲁为例,他生活的意大利,是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独立的城邦)密布的地区,是欧洲城市化最典型地区。因此,亚里士多德显学中的理论,有了活生生的运用可能。
我们不能够否认,作为法学家的巴尔多鲁很可能拥有那种普世情怀或帝国情怀,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罗马法大师,罗马法赋予法学家们以“帝国精神”和“普世精神”;而《国法大全》更透露着罗马帝王的权威。但是,作为大师的他更应该知道,“理性”才是最重要的:罗马法的真精神不是“帝国”,更不是“皇帝”,而是“理性”!这才是罗马法能够超越传统(拉丁与日耳曼),超越信仰(异教与基督教),超越权力(古罗马帝国与当代权力)而复兴的关键。这也是罗马法能够历经千年(古罗马时代),不断适应人性与社会现实,最终修成正果的关键。因此,“理性”使他现实地承认城市与王国,而不是赞同遥不可及、病入膏肓且让人生疑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城市才能更好地代表“理性”!另外,退一步讲,即使要恢复所谓的“普世帝国”,要将“普世”的“一统”当成遥远的终极目标,残酷的现状也只能让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破碎的政治格局中,王国和城市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长期存在。甚至他们可能还要接受更无奈的思路:这种现实“破碎”或许是达致最终普世统一的必经阶段。一旦接受如此意见,他们就能更坦然地接受城市的事实独立,而不是死死抱住封建正统理论不放。既然普世的帝国还不能够马上实现,既然现实中的城市和王国可能是达致普世帝国的必经之路,那么其存在就是“事实”上合理的;只要其为民众所承认,亦是“合法的”。
当然,从最终角度看,这种现实的政治和法律论证虽然有一定意义,但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各方的实力,只要以帝权为首的封建势力永远孱弱,则城市就可以一直事实独立。然而,只要各方的实力有所消长,则不仅“事实”会变化,“法律”上的理论也会因此变化。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的演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李秀清)
*吴旭阳,厦门大学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