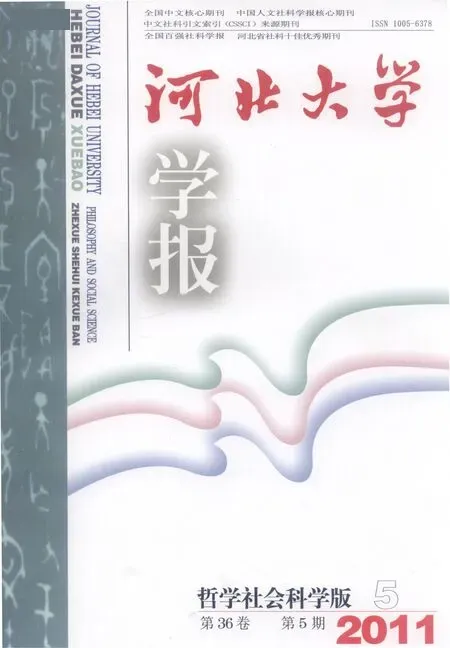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改革的影响——兼与中国高校教师工会比较
2011-04-08杜海燕李克军
杜海燕,李克军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改革的影响
——兼与中国高校教师工会比较
杜海燕,李克军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为了满足战后激增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而又不降低质量,澳大利亚建立了高等教育双轨制,即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侧重研究的大学和侧重教学的高等教育学院两种类型,但双轨制从产生到解体一直充满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之间的争斗,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长期采用维护双轨制的方式来遏制高等教育学院的发展,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虽然联盟最终无法改变道金森废除双轨制的一体化改革方向,但它确实极大影响了双轨制产生、发展以及解体的整个进程。将其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校合并时期的教师工会进行比较,以期有所启示。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教师协会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建立了高等教育“双轨制”,即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两种类型:大学侧重科研,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可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的各级学位;高等教育学院侧重教学,培养本科及大专等层次的学生,最高只能授予普通学士学位。这种划分标准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实践可操作性却很差,也没有考虑到其历史发展性,由此肇始了两类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争斗。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Staff Associations,简称 FAUSA)为了维护大学的自身既得利益,长期采取维护双轨制的立场,遏制高等教育学院的发展。虽然联盟最终无法改变“道金森一体化改革方案”将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合并的大方向,但这种争斗在改革之后嬗变为“新老大学”之争而继续存在。本文拟对此过程进行探讨,并与1990年代以来我国院校合并的高等教育改革相比较,以期有所启发。
一、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与高等教育双轨制的产生与解体
(一)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与高等教育双轨制的产生
1964年莱斯利·马丁(Lesley H.Martin)为主席的“第三级教育之未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Tertiary Education in Australia)在调查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后向联邦政府建议将高等教育分为两种类型,即传统的大学和新增的高等教育学院[1]。“高等教育学院”的创办目的不仅在于满足激增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也是为了在经费有限的前提下能够保持传统大学的科研学术优势。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由此发端。在此之前,成立于1952年的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于1962年给马丁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有力地影响了双轨制的产生。该报告认为当时不只是大学需要提高和扩张,技术教育和教师教育同样需要提高和扩展,而且新建的实施技术教育和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应该采用美国的社区学院等概念,因为“改革的重点不是要建立一个低等级的第三级教育,而是要提供更广泛的和更灵活的选择”[2]。当大学面对日益增长的入学要求时,公众通常都要表达对大学质量问题的关注,“没有任何事实能证明人们头脑中‘越多就意味着越差’这种假想是有根据的”[2]。所以,大学教师协会联盟支持战后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扩张,也支持创办高等教育学院,但报告没有涉及任何社会公平问题如与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方面有关的内容。尽管其本身存在一些被后人追问的瑕疵,但是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际决策力量的全国大学教师组织的报告,其鲜明的态度在战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双轨制改革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
(二)1970年代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对双轨制的深化与维护
高等教育双轨制确立之后,多所实施技术教育侧重教学的高等教育学院建立起来。由于高等教育学院的教师不被大学教师协会联盟认可和接受,高等教育学院的教师们在1968年成立了自己的协会(Federated Staff Associations of Australian Colleges of Advanced Education,简称 FSAACAE)。
1969年,斯文尼调查委员会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进行了调查,该委员会严格遵守马丁委员会提出的高等教育学院与大学“平等但是不同”的原则,认为这种原则应该反映在工资标准上,建议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中从事相同或相似学术工作的人应该享有同样的工资标准[3]。但是,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而且这个问题还进一步成为大学教师和高等教育学院教师之间关系紧张的起源,并在1976年的学术薪金审查会议中达到了斗争的顶点。由于学术薪金审查会议主要由大学教师掌控,一直都和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立场一致,因此斯文尼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1970年代早期,大学教师协会联盟还曾数次呼吁要进一步在政策上明确高等教育学院和大学的区别。但大学教师L.N.肖特教授反对这些建议,认为高等教育双轨制的存在并没有合理的理论基础,而且“如果大学意欲保持其活力而生存下去,它需要有高等教育学院的某些特点;而如果学院想要达到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达到的卓越,它一定要学习传统大学中的某些方法和功能。”[4]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把大学看成“永恒的堡垒”是保守主义的思想。但肖特教授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78年,大学教师协会联盟提交给斯文尼调查委员会的主报告坚持认为“就其基本的教育目的、标准以及整体风气而言,大学和其它的教育机构之间有着内在的根本性不同”[5],报告还态度鲜明地表示要精确界定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之间的差异:“本文可以被认为成是精英主义,而且我们对此毫无歉意。大学从其定义之始就是精英知识分子协会。”[5]事实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一系列没有支持性证据的强硬陈词,大学被描述为与高等教育学院存在着根本性不同的教育机构:大学提供以研究为基础的高水平课程,即使大学提供了职业导向的课程也和高等教育学院的不一样,因为大学鼓励自学而高等教育学院强调教学;大学教师比高等教育学院的教师更有资质而且“知道的更多”,而且更致力于研究;大学中的终身职位是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方式,而在高等教育学院中它只是一种保护饭碗的手段;大学是有着长远目标的教育机构,在国际知识界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而高等教育学院则自治性较弱,目光短浅。
该报告在1979年的教师协会联盟年度大会上引起了麦考瑞大学教师协会的回应。麦考瑞大学的代表反对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和引起分歧不和的各种提议,建议联盟避免制定削弱或损害高等教育学院的政策。但是后来麦考瑞大学的提议被修订了,其中涉及反对精英主义和主张与高等教育学院团结合作的部分被删掉。联盟重新确定了精英主义基调并对高等教育学院加强控制以阻止它们竭力效仿和赶超大学。
(三)1980年代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和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的缓和与合作
到1980年代早期,高等教育学院的发展壮大超出了双轨制成立之初的设想:几所高等教育学院已经和大学合并,而且西澳科技学院即将改名为柯廷科技大学。1982年,针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W.诺波教授建议大学教师协会联盟接受高等教育学院,因为它们“正在努力使自己在研究和自治方面向我们靠近”[6]。形势逼人,W.诺波教授的发言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联盟开始研究把其协会成员扩展到1978年报告所称的那些“异类”的可能性。
促成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与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态度缓和并进行合作的缘由是对自身可能与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Australian Teachers’Federation,简称 ATF) 合并可能性的担忧。1981年,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和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还有澳大利亚学生联盟和后来的澳大利亚教师联邦)成立了高等教育圆桌会议(Higher Education Round Table,简称HERT)。1982年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年会提出:与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合并的问题应该被提上研讨的日程,因为“考虑到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紧张关系,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也许发现自己不得不合并了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这样的一种前景使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非常担忧。”[7]然而,即便如此,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有些分支协会仍然觉得与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是不可接受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师协会坚决认为,合作是可以的,合并是不行的:“对于那些由于大学本身的独特性所产生的事情,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依然应该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协会的责任,因为它是被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代表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个专业协会组织。”[7]
当然,1984年高等教育圆桌会议报告是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和其它教育联盟合作的产物,不可能由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一家说了算,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保持着大学高高在上的地位。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参加高等教育圆桌会议当然可以视为面对危机的一种策略性回旋,而不是否定其“精英主义”立场。然而,在此期间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态度值得注意,它认为高等教育学院的经费需求应该和大学的经费需求具有同样的优先权和重要性,而且高等教育学院的经费应该更多一些[8]。从中可见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关系的微妙变化,因为这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的缓和。
(四)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盟与双轨制的终结
1987年,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秘书总长L.沃利斯在联盟内部刊物上展望了双轨制的未来,提出了合并的可能性。他特别指出:“大学教师协会联盟是双轨制最坚定的守卫者,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我们努力捍卫的制度其实是根本没有任何合理性的。”[9]他提醒联盟不能不考虑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伸过来的橄榄枝,虽然“对于很多人而言,这种想法是对他们现有工作条件的一种严重威胁,尤其就工作量和研究资源使用等方面而言”[9]。
高等教育双轨制由同年的道金斯高等教育改革绿皮书发出了终结的信号。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和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在1988年合作完成了一个联合报告:《未雨绸缪——规划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框架》,它重现和发展了1984年高等教育圆桌会议报告中的许多论点,比如应将大量精力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入学和平等。与1984年高等教育圆桌会议报告一样,它再次认同大学教师协会联盟提交马丁委员会报告中的很多建议,尤其是号召增加高等教育经费、主张高等教育机构应有各自的特色、强调这些教育机构内部的民主决策过程、并支持教育机构的多样性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接受道金斯绿皮书中结束双轨制并在高等教育中用一体化取代双轨制的建议,认为“双轨制是基于教学组织机构中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其逻辑基础早已不复存在了。”[10]
二、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高校教师工会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等院校数量不断增加,但很多单科性院校纷纷改为多科性院校,造成了专业的重复设置等问题,加之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模仿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长期形成了高校的条块分割局面,合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佳形式,是教育资源重组和优化的最高形式。从1992年开始至2003年的十年间,共有275次合并,612所高校被合并组建为250所,其中2000年达到最高峰,一年就有105次合并,由203所合并成79所[11]。这与澳大利亚废除双轨制实行一体化改革既相似但又不同。
首先,两国高等教育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教育成本下降、教育科研质量提高、教育资源改善等。与此同时,两国也面临一些类似问题。例如合并后各校区之间的交流交通,还有校园文化冲突所造成的人际摩擦和合并谈判过程中的协商成本等。还有,就两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而言,澳大利亚双轨制解体后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合并过程较快,可以说是一步到位,而我国的院校合并则是逐步升温,先是一些规模过小和专业过窄的地方院校进行合并,慢慢升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江泽民提出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后才掀起了强强联合的合并高潮[12]。此外,如何确定合并后的最佳规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也是一大问题。支持两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都含有“越大越好”的规模经济成分,但与规模经济并存的是当越过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之后的规模不经济。高校合并的效益和成本难以衡量,导致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也就难以确定,从而无法确定合并后的最佳规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13]。
就笔者的理解和认识而言,在20世纪末澳大利亚和中国进行两场高等教育改革都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全球教育改革趋势所导致的高等教育重新调整和布局。但在政府对高校的改革中,两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代表两国全体教师的第三方组织的态度和观点表达[14]。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改革进程之所以较快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学教师协会联盟的态度转变密切相关,它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阶层,其态度几乎意味着其背后所有大学的态度,所以它与高等教育学院教师联合会由分歧到合作的态度转变清除了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澳大利亚双轨制改革中参与主体为联邦政府和各高校,在这副翘翘板上,作为第三方组织大学教师协会联合会的态度非常重要,而它时刻都坚决地维护着大学教师的利益,有时不惜与政府的态度对立。
我国并非没有和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合会相近似的组织,只有高校教师工会。我国《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在《工会法》指导下工作的高校教师工会,维权也是其存在的前提。在我国高校和教职工关系中,高校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职工处于弱势地位,高校教师工会的建立在于集中教职工的利益和意志成为与学校管理者事实上的平等主体以维护教职工利益。但谁在院校合并中听到过高校教师工会的声音?由于高校的条块分割牵涉了太多的部门和利益,加之我国大学近乎各自为政,仅谈判和协调就损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高校教师工会有足够的时间发言,但它一直沉默,并不关注高等教育改革,甚至其对教职工利益的维护也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小福利发放和组织一些娱乐活动。
三、结 语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双轨制改革之后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当然竞争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它改变了形式,变成了“新大学”和“老大学”之争。当任何一个机构或一种制度更开放的时候,其权力阶层总会建立新的标准来想方设法保持其优势地位。但是,在澳大利亚双轨制高教改革过程中大学教师协会联盟始终作为一个组织代表澳大利亚的大学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思考和参与,而我国院校合并过程中对于政府的意见只有专家或学者等个体声音,没有听到高校教师工会作为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澳大利亚大学教师协会联合会自始至终都在维护大学教师的利益,其态度的变化也都是为了保护成员利益而做出的一种适应,它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中具有实际的影响力,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双轨制的进程。
[1]MARTIN L.ReportoftheCommitteeon the Futureof Tertiray Education in Australia[R].Canberra:Government Printer,1964:3-4.
[2]FCUSAA.Federal Council Sub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Tertiary Education[R].Vestes,1962(2):65-83.
[3]西蒙·马金森.澳大利亚现代教育史[M].沈雅雯,周心红,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7.
[4]MCCOLLOW J.FAUS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nary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alia[J].Australian Universities Review,1994(2):34-40.
[5]FAUSA.Submission to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Education and Training[R].FAUSA AGM paper,1977(6):12-15.
[6]Noble W.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J].FAUSA AGM paper,1982:7-11.
[7]UNSWSA.Comments on the Discussion Paper:Cooperation between FAUSA and the FCA and Relations in the Future[R].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taff Association,1983:13-15.
[8]FAUSA.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Committee of Review o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Higher Education-Submission[R].FAUSA AGM paper,1985:6-8.
[9]Wallis L.Some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J].FAUSA News,1987(3):2-7.
[10]FAUSA/FCA.Thinking Ahead-Planning Growth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A Framework[R].Melbourne:FederationofAustralian University Staff Association,1988:5-6.
[11]徐岚.我国高等院校合并的经济分析[J].理论月刊,2003(9):143-151.
[12]肖海涛.院校合并的历程与反思 ——基于大学理念的视角[J].江西教育研究,2006(9):40-42.
[13]王佳.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培育[J].贵州社会科学,2011(5):113-116.
[14]曾海波,郑日昌.质性评估的职业生涯咨询中的运用[J].贵州社会科学,2011(5):117-119.
The Influences of FAUSA on Binary System Reform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Also a Comparison with University Teachers’Union in China
DU H ai-yan,LI Ke-jun
(College of 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
In orde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higher educ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meanwhile not to decrease its quality,the Binary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alia was built,which divided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into two parts named University track and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 track,but these two tracks battled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Binary System.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FAUSA always suppressed CAEs’development by maintaining the Binary System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 own vested interest.Although Federation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Staff Associations(FAUSA)eventually cannot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named Unified National System by John Dawkins,it did have influnce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Binary System.
Australia;higher education;Binary System;FAUSA
G649.21
A
1005-6378(2011)05-0093-04
2011-05-06
杜海燕(1977-),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体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教育史、体育教育学。
[责任编辑 周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