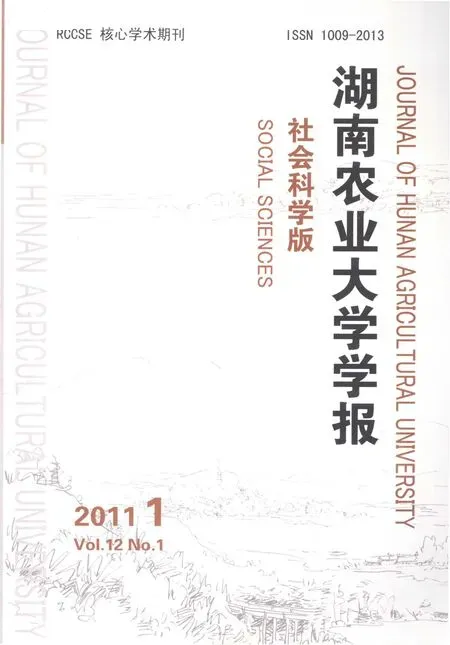“转灯”习俗的审美人类学解析
——基于高台县罗城乡的考察
2011-04-08李惠芬
李惠芬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转灯”习俗的审美人类学解析
——基于高台县罗城乡的考察
李惠芬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审美与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日常的生活场景本身就是某种审美和艺术的表达。高台县罗城乡的“转灯”习俗体现了崇拜与禁忌、仪式与狂欢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又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
转灯习俗;审美人类学;崇拜;禁忌;仪式;狂欢;高台县
Abstract:Aesthetics and art are important parts of human culture. Art and aesthetics are not independent life outside the value system, and many things in daily life itself are aesthetic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The custom of “Changing light” in Luocheng town, in one hand, reflects the worship and taboo, ritual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arnival; In the other hand, carries the values and moral spirit of Han which has existed since its formation.
Key words:custom of changing lights; aesthetic anthropology; worship; taboo; ceremony; carnival; Gaotai county
一、问题的提出
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性学科在国外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在西方,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类学美学”、“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名称出现的研究群体,出现了一些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开拓研究艺术和美学的新方向。用人类学方法关注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的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1]其研究方法是注重实证,从田野调查的方法入手来研究审美和艺术现象。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开发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方面来自古籍文献,是由书面化的语言构成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来自生活和现实,是物态化和观念化的精神,文化存在;再一方面来自出土文物和古代文化遗存,是物态化的古代文化的表征。”[2]
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源于中国美学和中国人类学中对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关注。近年来有关学者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那坡黑衣壮等研究取得了初步成绩。[3]此外,农辉锋以大新昌明壮族的二次葬习俗为例,认为二次葬是壮族通过对先人魂魄聚居于祖坟地的想象来达到整合现实中的家族主义的文化设计。二次葬习俗的形成与壮族的人观、宗教规范以及家族观念密不可分,它有着强大的心理协调功能。[4]王越平应用人类学仪式过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甘肃文县麦贡山、四川平武厄里寨和木座寨三个白马藏族村落“跳曹盖”仪式的对比分析,指出“跳曹盖”仪式是驱鬼敬神与狂欢庆典仪式的耦合,只是在不同的村落中,二者在仪式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寡。并指出“跳曹盖”仪式结构中这种二元性实为不同社会情境下价值观念的产物。[5]雷文彪以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考察了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认为白裤瑶葬礼主要由阴朝报丧、铜鼓造势、开牛送葬、跳猴鼓舞、沙枪送葬、长席宴客六大仪式组成。通过对广西南丹白裤瑶的葬礼仪式规程的梳理和阐述,探讨了其外在流变形式及其内在的生存机制。[6]傅利民、刘沐粟通过对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孟戏”祭祀仪式功能的探析,指出这些仪式的参与者“在一个其本身己经安排好为交流行为提供隐喻关系的领域空间编制出一个有序的隐喻事件系列”,并通过“孟戏”祭祀仪式与他们所供奉的神灵、他们的祖先、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对话和狂欢,从中寻找心灵安慰与生死寄托的基础——精神守望。[7]
正月十五逛花灯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在甘肃高台县罗城乡这一活动又被称之为“转灯”。同样是娱乐,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逛”是沿街悠闲、自在地欣赏,而“转”在玩的同时带有目的性,比如既要按照一定的路线“转进去”,还能“转出来”,类似于一种游戏,融愉悦、兴趣、智力为一体。布置“灯场”用的图纸保存是极为神秘的,除了同姓、同宗的人之外,其他人很难看到。笔者拟在审美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高台县罗城乡“转灯”民间习俗呈现出的对神灵的崇拜与禁忌以及这种仪式所具有的狂欢化特征。
二、罗城乡“转灯”习俗及其嬗变
罗城乡是甘肃省高台县的一个小乡镇。位于高台县城西北39.6公里,古称红寺堡,又称下堡、奉化村。罗城乡南屏巍峨的祁连山,北枕北山山脉,两山之间地势平坦,祁连山区水草丰美。西面与酒泉市(古时称肃州)所属的金塔县接壤,南面与肃南县接壤,黑河贯穿全境。据《高台县志》记载:“商、西周时期,高台一带有羌人部落活动;春秋、战国和秦时期,有乌孙人和月氏人逐水草而居;西汉初年,匈奴崛起北方,占据河西。”[8]可见,该地历为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相互斗争和融合比较复杂的地区。汉代设置的镇夷千户所就在罗城乡,如今古韵犹存,仍可窥见该处人们生活习俗中儒、释、道相互渗透和叠合的迹象。罗城乡以农耕为主,属于高台县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民风古朴。因此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习俗,如正月里“耍型子”造型极为巧妙,将秦腔故事和建筑造型艺术相结合,达到美妙绝伦的境界。这一习俗在甘肃乃至整个河西地区实属一绝;流传于罗城乡的民间小调则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河西各处变异和发展;而正月十五的“灯场”以其布置的神秘性和“转灯”的趣味性吸引着各处的人们争相参与。尤其是“型子”的造型与“元宵灯场”的布置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民俗文化。
“转灯”习俗自明朝万历年间传入罗城乡,如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除文革期间之外,即使在灾荒年代,也从未间断过。关于“转灯”习俗,《高台县志》这样记载:“县城和部分村还盛行‘灯杆会’,即以绳子将灯杆相系,插在平地上,布成迷宫,外层留进、出口,让人们观灯破阵,融娱乐和智力游戏于一体。黑河北岸的五坝、六坝,灯杆会设在黑河之畔,元宵之夜,花灯高悬,冰河辉映,再辅以秧歌、龙灯,热闹异常,令人陶醉。”[8]这里所说的“灯杆会”就是今天的灯会,如今在高台县的其他地方已经失传了。由于罗城乡地理位置特殊,外部环境相对闭塞,文化变迁较为缓慢,至今仍然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具体而言,从灯阵图的说明来看,它是以《封神演义》中的三肖娘娘为报仇而设置的“黄河阵”为依据,以《封神演义》的“三百六十正神”为灯柱,每盏灯代表一位神仙。据说为破此阵,“元始天尊”动用了“三百六十正神”。此阵共设一大阵,八小阵,阵阵相通,阵法各异,变化多端。阵中有“盘龙阵”、“卧虎阵”、“一字长蛇阵”、“连环阵”等,一旦入阵,断其后路,只有奋力杀出,回头必有杀身之祸,不是被马踏,就是逼进死路。此阵阵法极为奇妙,二龙入阵,首尾不能相助,二龙如盘踞相对的两角即是“盘龙阵”,中阵如狮子进场,分卧祭台左右即是“卧虎阵”,末尾一阵乃“一字长蛇阵”。高跷上的人物可扮演古戏“黄河阵”中的各员虎将,手持各自宝物,在紧锣密鼓中快速入场,犹如大破此阵的架势。“马子”入场可伴以唢呐声,形成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游入灯场更似群仙下凡,遨游在灯海之中,其乐无穷。就此灯场,才有“正月十五天子与民同乐”之说。
灯阵入阵时先打四角后打前中阵、右中阵,再打后中阵,最后打其左中阵而出阵。而四中阵都以中央祭台为主。四角四灯柱高挂灯串,四周全用红灯围起,不得随意入内。每阵中央设置黄色灯笼提示你慢行,中央祭台高挂“混元金斗”灯,台上设置赵公明画像或塑像,并放上香表之类的东西,同时放置香炉,还要有专人带入焚香化表,消灾除祸。祝一生平安,富贵长寿,日进万斗。
灯场设彩门,一门两口,右进左出。灯柱五尺许,挂二灯,内燃牛油蜡,灯柱间以绳串之,晚即燃灯,炮声起,锣鼓鸣,二龙入阵,压住阵角,名曰“盘龙阵”,二狮卧于祭台名曰“麒麟阵”,门内设“连环阵”,旁衬“长蛇阵”,合阵八小阵名曰“八阵图”,高跷入阵,姜子牙率众冲入此阵,各自手持法宝力斗三肖;马子入阵,唢呐声起,人喊马叫,有身临其境之感也!游人转入灯场,如入仙宫,眼花缭乱,难辩西东:欲进有路,欲退无门,祭台正坐赵明公,背坐观世音,焚香者恭喜发财,菩萨保佑,四季平安。追逐玩耍任随君便,灯灯见面,无一重复,其乐无穷。”(详见罗城乡“转灯”布置的图纸)
从灯场的布置情况、所用材料及设备的来源看,一般是先找好一块空地,然后按照灯阵图的提示挖好小坑,相邻两个小坑的距离在1米左右,然后在小坑内栽置灯杆,最后在每个灯杆上挂上一到两个灯笼,按照纵行将相邻的灯杆用绳子连起来,整个灯场共栽植360个灯杆,从高处俯视灯场,如同一个方型的“八卦图”。[9]灯杆大多是乡亲们自己捐的,尤其是那些希望来年生儿育女的,为了求子乞福便捐灯杆以示诚心,已经生养了的为了感谢上苍还要多捐几个,那些家里有病或灾的更是自觉,这样便有了材料,大多是自家的树上砍一些枝桠便可,而灯笼也是家家户户各自做的。与以往相比,灯杆和灯的捐献以及灯场内观世音和赵公明的塑像一直未曾改动过,所不同的只是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灯杆和灯比较粗糙些;如今灯杆变得圆润光滑了,灯笼上有了许多图案甚至出现了谜语,灯也不再是牛油点燃,更多时候使用的是电灯甚至霓虹灯,增强了“转灯”习俗的娱乐性。
三、“转灯”习俗的审美文化剖析
1.崇拜与禁忌
(1) “转灯”习俗体现民间宗教的世俗性特点。在灯场内必须将各路神仙高立于灯柱之上点燃,这与村民的宗教神灵的信仰有关。它首先表达了河西人对神灵的崇拜之情。《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就说:“法宝犹如一切明灯。”另外,释迦牟尼认为信众如果能够以灯供养自己,其功德可进一阶。灯阵中间的“赵公明和观世音”雕像的塑立使村民容易将神圣的宗教与现实的功用结合起来。在村民看来,在神的面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平等都会为神的力量和神秘所消解,因此他们烧香拜佛,捐钱捐物,从而完成这种民间宗教意识的世俗转换。
在某种程度上,民间信仰是一种社会化和世俗化很深的宗教,它起源于古代原始信仰的泛灵崇拜,长期的与社会、文化相结合,吸收社会已有的文化资源,自成了神灵崇拜的信仰体系,[10]这种信仰总是带有一定的民间功利性和世俗性。相对于西方宗教来说,中国的民间宗教融合了佛、道以及更古老的许多传统信仰而成,可以说是一种普化宗教(diffuse religion),其信仰的内容经常是与一般的日常生活混合,也可以包括祖先崇拜、神明崇拜、岁时崇拜、生命礼俗、符咒法术等。[11]在“转灯”时,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遵循一定的规则接近神灵,是希望神灵对今世给予关注,他们不要求这种宗教具有严格的教义和浩繁的经典,只希望能够通过随时可行却又不失某种庄严神圣意味的仪式来满足自己的家人和社会的一些要求,比如长命富贵、生儿育女、趋富避祸、消灾去病、升官发财、风调雨顺等。这些往往都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而又为个人、社会的力量所无法把握的方面,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中国的宗教,不管是巫术性的还是祭奠性的,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无论如何,一般而言,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为了长寿、子嗣与财富,以及在很小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祠,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12]所以“转灯”民俗是宗教性的更是世俗的,“转灯”活动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宗教层面的意义,同时新增了表演层面的内容。作为一种“工具”,它突出“传统”和“威严”的作用,用具体形象将抽象的符号意义固化下来,强化了这一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2) “转灯”习俗体现了仪式的审美规定性。“仪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把人与自然划分开来,把日常生活现象与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秘现象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仪式能使日常生活现象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永恒的力量、最高的精神力量。仪式是对自然时间的一种重新体验与表达。”[13]在罗城乡,“转灯”除被民间广泛寓意的“灯”与“丁”的之间的隐喻关系之外,[14]也被村民根据地方性情境设置了地方性的文化政治意义,在游灯场的过程中,严格规定与遵守“转灯”线路,不得逾规,否则就会导致堵路。仪式进行的同时对村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做了一次仪式性的勘定与确认。很显然,“转花灯”中人们共同遵守的“转灯”路线,实际上是村民基于共同生活空间的仪式行为,在仪式的实际表演中,村民对仪式的恪守是对现有神圣秩序的认同,对仪式传统的超越或背离则视为对神灵的挑战。
从审美发生的角度来看,审美形成于并且深深地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在“转灯”活动中,人们在欣赏和拜佛的同时,把灯场的秩序和对神的敬仰所产生的审美情绪当作“自己的法律”而自觉地遵循并成为对其心理和行动给予暗示和支配的内在的文化指令。因此,审美以对人的情感结构的摹仿和再生产保证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性力量而是从内部瓦解理性冲动的统治。在“转灯”活动中,“由于社会集体的每个成员已经不再直接感到这个互渗了,所以它是靠不断增加的宗教或巫术仪式、神圣的和有神的人和物、祭司和秘密社团的成员们举行的仪式、神话等等来获得的。”[15]可见,“他者”与主体意识之确立和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共生、相生相长的关系。“转灯”活动本身因此自然呈现出崇拜与禁忌的功能意识。
2.仪式与狂欢
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仪式属于行为文化,它是由一个群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中进行的。这就使其具有一定的展演性和公开性。与仪式的展演性相对应的则是规范性,仪式本身包涵了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程式。罗城乡的元宵花灯作为一种表演仪式,在内容上有着自己的体系,反映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在形式上有着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仪式的人类学意义。
罗城乡流传着“炀帝玩群花”的故事。据老人讲,黄河灯阵源于隋朝。传说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乘龙舟下江南,路经扬州地界,正值元宵佳节。当地官员根据《封神演义》中三肖娘娘为报仇雪恨而摆下黄河大阵的图样,取九曲黄河之玄机,以三百六十正神设置灯场,以供皇帝欣赏。他们在灯场内挂上各种花灯,灯光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在隋炀帝转灯场的过程中,锣鼓震天,巨龙出入其间,并伴有神光助威以及观世音遣来各色江南女子的嬉戏,形成了万马奔腾、人头攒动的狂欢场面。后隋炀帝将此图带回宫中,每到元宵节必摆黄河阵,灯场成为宫中娱乐点缀。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黄河灯阵来源于民间,是一种既能娱乐又能怡情的习俗,是一种民同乐、大众狂欢的节日盛典。由于民间狂欢精神的文化诉求和生活与表演的合一,以及仪式表演因素和娱乐狂欢因素的融汇、整合等特征,“转灯”便成为罗城乡人民民间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当然载体。或许可以说,“转灯”是罗城乡民间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承载者。正如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说:“在仪式里面,世界是活生生的,同时世界又是想象的……然而它展演的却是同一个世界。”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在井然有序的灯场里,有时行人可以出入自由:小孩子追逐打闹;年轻人谈情说爱;中年人互诉生活的苦与乐;老人奉香化表,祈福平安。有时在锣鼓喧天中,秧歌、马子疾走走如飞,高跷踩着点子徐徐进入,时而巨龙盘旋期间。因此,罗城乡“转灯”活动呈现民众自由狂欢的特点,与娱乐有着本质上的亲缘关系。尽管这种由乡民自行组织的戏剧表演并没有多少审美成分,但是却具有远甚于戏剧审美功能的民间狂欢仪式功能。按照彼得·布鲁克的观点,神圣的戏剧有一种能量,粗俗的戏剧则有其他各种能量,轻松、愉快与欢乐哺育着它。[16]罗城乡的“转灯”正是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边界,一方面,这里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处于同样的文化情境之中;另一方面,灯场所设置的路线和灯笼的悬挂位置、以及灯笼上的装饰,灯场内人们的对神的虔诚、相互的评说、嬉戏,更是以虚拟的情境将游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恼抛却,进入虚幻世界,进而达到自由的审美愉悦中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转灯”习俗的交流和沟通功能。在“转灯”活动中,一方面,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在狂欢的同时,人与神之间进行着宗教意义上的世俗交换;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进行着情感的宣泄与交流,同时,在个体内部也进行着沟通。因为在农村,平时乡民间难免产生摩擦,形成矛盾,灯场犹如村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调节着村庄内部和村庄之间人们的关系,成为全村甚至全乡村民交流的场所。元宵节这天,乡民们总是早早吃过晚饭,约上朋友,带着全家,穿行于熠熠生辉的灯场中;他们一边谈论灯笼的做工,一边平品灯笼的寓意,诉说着过去的收获和未来的希望。在灯场里,在神灵面前,人们尽释前嫌,往日的烦恼、愁苦在这一共同的祁福和游戏中全部化解。在敬神的时候,虽然没有得到现实的物质利益,但将自己的愿望和企求寄托于神灵,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解脱;各自在心中想着自己的对和错,然后跟他人坦率交流,诉说自己的冤屈与不平,聆听别人的劝解与教诲。这样的释放与宣泄可使自己内心得以平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交换”作为审美交流的隐喻,是研究社会制度、文化现象的重要视点,对解决“主体间性”的问题,对于主体如何走出自我的主体性幽闭,实现与“他者”充分的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
克利福德·格尔兹指出:“仪式表演本身,引导人们承认支持着仪式所体现的宗教观的权威。通过借助于单独一套象征符号,引发一套情绪和动机(一种精神气质),确定一个宇宙秩序的图像(一种世界观),这种表演使得宗教信仰的‘对象’模型(models for)和‘归属’模型(models of)仅成为相互之间的转换。”[17]借马尔库塞的话来说,甘肃高台罗城乡“转灯”活动作为艺术,是将感性与理性重新融合从而形成新的和谐关系的“他者”或中介;[18]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又承载着汉民族自形成至今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和道德精神。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均重视的民俗大节,体现了中国民众独有的宗教崇拜和狂欢精神。罗城乡布阵严肃而形式自由的元宵灯场,在千百年的流传中,娱神性渐渐减弱,而娱人性日益增强。人们对历史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充分表明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转灯”的习俗仍然具有其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价值。
[1] 向 丽.国外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动态[J].国外社会科学,2010(2):59-68.
[2] 张利群:论中国古代审美人类学资源的利用[J].东方丛刊,2001(4):68.
[3] 覃德清.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柳州师专学报,2008(2):1-6.
[4] 农辉锋.壮族二次葬的仪式与功能:以大新昌明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97-100.
[5] 王越平.敬神与狂欢——白马藏族三个村落“跳曹盖”仪式的比较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15-20.
[6] 雷文彪.广西南丹白裤瑶葬礼仪式的审美人类学考察[J].广西民族研究,2010(3):100-114.
[7] 傅利民,刘沐粟.行走在对话与狂欢中的守望——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孟戏”祭祀仪式之功能探析[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4):14-18.
[8] 高台县志编纂委员会.高台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9-23、435.
[9] 李惠芬.观灯?转灯——罗城乡民俗趣谈[J].神州民俗,2008(8):54.
[10] 郑志明.台湾神庙的信仰文化初论——神庙发展的危机与转化[C]//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汉学研究中心,1995.
[11] 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274.
[12] 韦 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69-170.
[13] 王 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96.
[14] 周 星.灯与丁:谐音象征、仪式与隐喻[C]//王铭铭、潘忠觉.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5]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32-433.
[16] 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6-48.
[17]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5.
[18]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47.
责任编辑:陈向科
Aesthetic anthropology analysis of “Changing ligh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Luocheng town of Gaotai county
LI Hui-fen(College of Arts, He 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China)
K892.1
A
1009-2013(2011)01-0062-05
2011-01-05
李惠芬(1971—),女,甘肃高台人,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