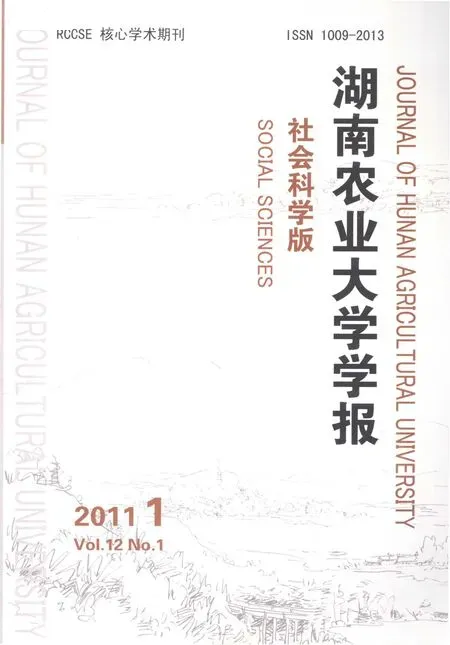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
——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2011-04-08韩国明钟守松
韩国明,钟守松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
——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韩国明,钟守松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税费改革;村级组织;组织职能;国家;农村社会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ural society is opposite and separated before the rural tax reform.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are given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which makes the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s change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and policy in rural areas after the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and consequently the function of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transferred to the service-giving from the resource-gaining. However, due to the one-way government input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areas, an equal partnership did not form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ural society, and the setup of“strong nation, weak rural society” has not basically changed.
Key words:tax reform;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function of organization; state; rural society
税费改革前后的时期划分有其现实的实质意义。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显示出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村级组织,主要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政府职能与权威在农村的延伸,在税费改革前后,其职能和权威的转变,既清晰地显示了国家政策和目标的变化,也从微观层面上反映着国家和农村社会关系的相应变化。
一、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
“国家”一词是作为政府组织层面的国家,主要指各级政权组织及其正式制度组成的政府系统,人们平常所说的国家与社会就是在政府组织层面上区分的。在中国的乡村地域内,在农民看来,党的系统、人大、政协、工会、行政、司法、检察系统、公共卫生文教系统、农村信用合作社、国有企业、镇办企事业单位等都是国家的构成部分。[1]除此之外,则是社会的领域。在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时期,“社会”一词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来定义和理解的。在中世纪,神权和君权(包括封建领主权)笼罩着整个西欧世界,尤其是庄园经济之下,农村地区更是处在领主的严密控制之下,毫无“社会”空间可言。随着工商业的开展,西欧的城镇得以产生和发展,并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体制外力量而存在着,因而,城镇成为当时自由、独立的象征,“社会”也特指具有这种气质和氛围的“市民社会”。[2]本文则关注具有这种自由、独立气质的乡村社会。
国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较早运用“国家—社会”这一框架来解释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和秩序变迁。虽然各自的概念不同,但他们都是站在村庄的立场上,坚持“外部冲击—内部回应”这一理论假设,同时秉持“国家本位观”来解释国家权力对乡村的不断渗透,以及这一过程对村庄秩序的变化和失序的影响。杜赞奇[3]的“盈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黄宗智[4]的“政权内卷化”概念,以及张仲礼[5]的绅士官僚化和萧凤霞[6]的“细胞组织”理论,都是这一框架下的不同分支。这些理论表达了这样一种论断:中国自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政府为了应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任务,或是摆脱民族危机,或是完成民族—国家建构,抑或者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同程度地向乡村地区进行渗透,以便汲取所需的各种资源,虽然渗透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造成了乡村地区秩序的变化和一系列问题。
中国学者则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激进,并且视角更加多元,并不只是以“国家本位”的角度来观察农村社会,他们并不承认国家与社会只是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而认为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其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张乐天[7]和于建嵘[8]的著作通过对一个时代(人民公社时代)和一个村庄(岳村)的描述,考察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并分析其结构化过程中村庄自身的反应,从而把握村庄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孙立平[9]和吴毅[10]通过考察一个时代(人民公社时代)和一个村庄(双村),认为在国家和农村社会关系中,国家无疑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强调了国家对村庄政治的改造和重塑。孙立平更是指出,1949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王铭铭[11]强调村庄内部结构的变革和民间权威的复兴等村庄内部力量对于村庄秩序的影响,与此相反,徐勇则通过“政权下乡”[12]、“政党下乡”[13]、“行政下乡”[14]等六个系列分析了农村体制改革之后现代国家对于乡土社会的整合及其机制。
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微观事件中把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的重心从国家转向农村社区,以对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的把握为基点,来了解国家力量与农村社会力量在村庄中的互动。孙立平、郭于华[15]提出的“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与“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用”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孙立平并且由此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对社会控制范围的缩小;第二,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第三,控制手段的规范化在加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向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在这一领域学者们大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整体上把握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并且这种解读都限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税费改革之前,而关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的论述则不多见。仅见路玉甫分析了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职能定位问题。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如村级组织职能发生错位;村级组织职能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工作重点要由原来的催粮收款转向为群众兴办公共、公益事业,为群众服务在现实情况下非常困难。[16]王乐锦亦指出,村级组织自身收入的减少必然要求对村级组织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村级组织不可能再是一个生产经营性组织,而应是一个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组织,其职能只能定位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即公共品上。[17]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试图以更加微观的角度,即以村级组织的职能和权威转变为切入点,并基于2008年至2010年对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省区部分县乡村级组织、农业技术协会、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方式的调查,重点分析中国村级组织的职能和权威在税费改革前后的转变,一并讨论两个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相应变化。
二、税费改革之前村级组织的职能及相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虽然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和农村基础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国家与农村社会依然是一个“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这种态势在村级组织上的反映,就是政府赋予村级组织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村级组织仍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
1. 村级组织职能的行政化
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开始在农村地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乡政村治”的建立。在这一制度之下,村级组织的组成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方向是以行政区域建制取代生产单位建制。如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公社时期与生产单位相对应的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建制,在改革之后,在行政村一级建立党支部,它的法律定位是领导村民自治的核心;而党委则成为乡镇一级的建制,其法律定位则是领导乡镇政府工作的核心。同时,在原来的生产大队一级,即改制后的行政村一级建立了村民委员会,行使村民自治的法定职能。对于这一时期村级组织的职能定位问题,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即村级组织并没有真正成为为群众自治而服务的组织,反而成为了政府在村庄中的行政代理人,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其履行的主要是行政职能。
首先,从村民自治运动来说,从其产生之初各界就对其性质发生了一定的争议,即究竟是定位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性组织,还是定位于履行乡镇政府行政任务的“一条脚”。农村实行家庭独立经营之后,农村中“分”的因素在不断扩大,而“统”的一面则不断缩小,这在农村的生产和社会管理上产生了许多问题,村民自治也正是作为对体制改革所产生问题的一种反应,由农民自发建立,自我服务。但是,自治运动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包括个人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治意识的觉醒,以及相应的经济力量的发展与社会性组织的大量存在,广言之,即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的存在。然而公社时期无所不包的国家控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独立自主的民间因素遭到国家力量地不断排挤,乃至消失,一个“总体性社会”终于建成,“社会”终于在国家权力的之下湮没了。社会的培育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希冀于一夜之间或者通过一次自治运动就建成一个社会,显然是一个不太切实的幻想。因而,中国的农民自治运动有着先天的不足:没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在这一阶段只能拥有自治形态,而无法拥有自治实质。此后村委会职能的定位与发展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虽然,《村组法》将村委会定位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职能在于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社区服务性职能。可是现实的发展却表明,村委会越来越背离这一规定,而逐渐演化为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承担的也不再是服务群众的职能,而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职能。何海波[18]和张丽琴[19]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的《村组法》对于村委会的职能界定过于模糊不清,加之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村委会的职能摊派,在各种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村委会被赋予了共113项的行政职能,这些职能涉及社会治安、计划生育、乡村建设、公共安全、劳动保障、社会救助等,村委会的行政化程度不断提高,甚至俨然成为了行政机关的一个内部科室。正如何海波所言:“村民委员会制度的目标和功能首先不在于政治民主,甚至不在于乡村民主,而应当被理解为特定政治和社会情势下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18]
其次,从村党支部来说,其与乡镇政府更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中国特殊的政党制度和政权制度,党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的行使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在现实的农村社会管理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的内部管理中奉行“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行政村的党支部要服从上级乡党委的命令和领导,这就使得乡镇政府和村党支部形成了某种利益和目标共同体,其在农村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同时,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村庄的社会管理中,虽然各自有自己的权限范围,但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两个主体,相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中,党支部都发挥着领导村委会工作的角色。199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种关系的存在,也是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实践传统,人民公社实行“党政合一”、“党经合一”的组织体制,其中党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高度重合,党的书记全面负责并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因而在农村改革的新时期,这种关系的保留也在情理之中。现实中的村民自治运动的不完善,更使得党支部在村庄治理中享有更大的权力,在事实上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甚至还能够干预村委会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
最后,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下,国家依然需要将农村纳入整体现代化建设的体系之中,农村在这一体系之中依然扮演一个资源输出的重要角色。因而国家有强烈的控制农村的渴望,这也决定了其行政功能必须在农村中得到实行,其政策措施必须在农村中得到贯彻。因此,政府为了实现其目标,必然会透过村组织实现对农村的控制。而村组织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并不能通过自治来抵抗这种控制,从而,主要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组成的村级组织客观上就有向政府或者国家倾斜的态势,在政府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角色之间,就更倾向于前者。由此,村级组织的职能就演变成完成政府摊派的行政任务,其职能的行政化日益凸显。
在村级组织的行政任务,即由政府所指定担任的工作或担负的责任,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是两大重点,即通常所说的“要钱”和“要命”。根据徐勇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中后期,村级组织的行政任务中,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的比重分别达到了70%、20%。[20-21]
2. 村级组织的权威基础:国家授权的行政强制
行政任务具有行政强制性和行政约束力,村级组织为了实现政府赋予的行政职能,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村组织的两项主要职能,税费征收和计划生育,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村民的直接利益相冲突。这种国家利益与农村社会利益的分离和矛盾,使政府赋予村级组织的行政强制表现得更为突出。
政府在农村税费征收的目的和用途主要有两个,一是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筹集资金,二是用来弥补日益增长的行政事业费用支出。
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划分不匹配,好的税源被上收至中央,导致地方政府财小事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不断地增加行政机构数量、扩充行政人员,使得地方政府开支不断攀升,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增加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收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大要务。同时,当时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种通过税费征收由政府强制农民付费,且由政府官员决定供给内容的模式。许多政府官员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奉行的是是否有益于政绩显示的原则,而非以农民是否需要为其供给逻辑。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以牺牲农村社会利益为代价,强制农民上交本已不多的农业剩余。在税费征收过程中,村委主任和党支部书记需要丈量各户的耕地面积、核算粮食产量等征税标的,然后计算出各家各户该缴纳的“三提五统”,最后再挨家挨户地上门催粮要款,村组织俨然成为了税务部门的一个内部科室。为了应对农民的“瞒税”、“抗税”、“逃税”行为,有的村组织甚至不择手段采取暴力、黑社会方式来强行收缴税费。
在计划生育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多数农民家庭的生育观念还没有转变,政府则对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指标,并在考核中以“一票否决”的严厉方式督促基层干部完成这一指标。这种矛盾使计划生育成为这一时期的“天下第一难”。作为政府在村庄的代理人,村组织也被赋予了结婚年龄控制、生育状况报告、节育措施落实和惩罚措施等大量的行政权力,甚至会配合县乡政府强制没收村民的财产,强行拔房毁地以完成计划生育指标。
这样,为了顺利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硬性任务,保证政府意图在农村社会的贯彻和实施,村组织的权威就通过行政力量被建构起来了。这种建构性的权威在与农村社会的自发性民间权威的较量中,无疑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他们控制乡村的力度和强度是很大的。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期,城镇化尚未全力推进,农村地区总体上分化程度不高,农村中的市场因素还不完全,社会性力量并未得到壮大,尽管有些农村出现了宗族复兴的现象,但总体上农村地区体制外的自发民间力量和民间权威并未形成。相反,以村委会和党支部为代表的村组织作为体制内的一股力量,不仅拥有政治优势,而且那一时期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村组织同时具有相对的经济强势地位和一定的利益分配权力,由此奠定了其在村庄治理中的强势地位。
3. 国家与农村社会:分离和对立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在农村社会的一种制度载体,其产生和功能的演变总是“内嵌”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关系之中的。村级组织的行政化及其依赖行政强制权而建立的建构性权威也是在当时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下产生的。这一环境总的来说,就是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各自发展状况和特殊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建过程。
对于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问题,学界有着比较统一的看法,即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演变是历史连续性与跳跃性的统一。首先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是从人民公社时期演变和发展而来的,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上个阶段的一些特征,即孙立平[21]所说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等多个领域重合的“总体性社会”,其中国家依然主导着整个社会;其次,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较大的调整:一方面,随着“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分化,一个真正的“社会”领域开始形成,[22]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未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社会力量依然薄弱;另一方面,国家主动调整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度和控制方式,虽然在政治组织上国家逐渐撤出农村,允许并鼓励村民自主运动的开展,但国家的行政职能却并没有撤出农村,国家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村社会保持控制。[23]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只是在控制幅度和强度上有所区别于人民公社时期,二者之间的实质并未真正地得到改变。归根到底,国家依然要对农村社会实行一定的行政强制。而这则归结于国家与农村社会在目标和利益追求上的分离甚至对立这一现实并未改变。
虽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地区呈现出国家力量和影响范围逐渐减弱,农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的态势,但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国家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需要农村社会的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而农村社会对于产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则很少得到表达,甚至于被忽略。农村社会在由国家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系中始终扮演的是一个资源输出地的角色,国家甚至以牺牲农村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化。在这样的对立和冲突之下,农村社会的反抗和国家政府的强制控制就成为现实,而在“乡政村治”的背景之下,国家要实现对于乡村的渗透与控制,村级组织就成为一个主要的着力点。由此,一方面政府在事实上并不鼓励村民自治和民间组织的成长;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将村级组织行政化,赋予其行政职能和行政强制权力,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
由此可见,村级组织职能的行政化及其权威的建构性,是与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力量的变化和双方关系的确立。
三、后农业税时期村级组织的职能转变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2002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社会一次影响重大的社会制度变迁,其内容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诸多变化。随着20世纪90年代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国家和农村社会又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农民利益取得一致,但是在“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之下,国家依然主导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并透过村级组织对农村社会进行更加细致和广泛的干预。
1. 村级组织职能的服务性转变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国家政策转型之下,中央从 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并在2006年最终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农民付费转变为政府付费,农村从资源输出地转变为服务输入地。这一重大的农村制度变迁,对于村级组织的职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村级组织的职能由行政性的资源汲取向服务性的资源供给转变。
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农业税和各项预算外收费的取消,原先占村组织大部分工作量的税费征收任务不复存在,国家三令五申严厉禁止地方政府乱摊派、乱收费,从而村级组织丧失了税费征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不仅如此,“十一五”以来,政府持续增加对农村的资源投入,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民培训经费补贴、农田改造、农村电网改造、村庄生活用水设施建设、生态沼气池建设等惠农政策不断出台。笔者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县乡中了解到,税费改革以后,村级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政府的各项政策,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政府项目,对符合国家规定的补贴对象进行登记和发放补贴,发挥着居中协调和辅助实施等服务性功能。
在这一时期,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过前一个阶段的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在生育质量与生育数量之间,农民家庭在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之下也逐渐倾向于前者。同时国家在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重点由人口数量控制转向保证人口质量,因而村级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是优生优育和保健工作。笔者在中西部的村庄中发现,村社组成人员中大约都有2-3名计划生育专干,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受孕妇女提供婴儿保健知识,登记农村计生“两户”(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家庭情况并发放相应的优惠政策奖励,村委会的醒目宣传位置上,张贴较多的就是有关优生优育和国家政策奖励的信息。如此之后,村委会的职能由“要命”转变为“保命”,为村民们提供更多的医疗信息和落实国家对于计生家庭的资金、就业和医疗上的补助,成为了一个服务提供者。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村级组织已经成为新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再需要以“要钱”的姿态强行收取“村提留”,借办公益事业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而是以“给钱”的新角色出现在村庄舞台上。
于是,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政府在农村发展的目标开始契合于农民的利益。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在不存在征地问题,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没有提出要求,甚至将政府对农村的投入看作一种“赐予”而不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政府与农民的根本性的冲突消失。在这样的背景下,村级组织以行政强制为特征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合于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新职能的发挥,政府逐渐收回授权于村级组织的行政强制权力,不再允许村级组织通过行政强制力伤害村民和村庄利益。
2. 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
税费改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化,使得政府在农村的目标与农民的利益诉求相对一致,二者的对立和分离开始减弱。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主导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村级组织的工作内容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作为政府在乡村的延伸的角色则同样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税费改革之后,政府在农村的政策目标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这一政策目标的变化突出体现了国家利益与农村社会利益的融合趋势,政府不再以资源汲取者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服务供给者的新形象出现。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下,对于农村社会的各项事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内容不仅包含了科教文卫等社会生活方面,也包括了农业生产、产业发展等经济生活方面。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重点由先前的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农民手中收取税费,到现在的如何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以增加农民收入。
在新时期,虽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村民付费改变为政府付费,却仍然由政府决定服务内容。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不仅是出资者,也是供给内容的决定者,政府的财政、农业、畜牧、科技、水利、民政等部门决定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而农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仅充当一个被动的受助者角色,是一种单向输入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这种供给模式为政府控制村庄提供了新的手段,具体而言,政府通过村干部的补贴政策,实现了对村级组织的重新控制,透过村级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以完成政府的农村发展目标。
取消税费后,村干部的劳务报酬失去了来源。作为一个配套性的措施,政府将由广西、四川首创的给村干部发放补贴这种地区性、临时性的政策调整为全国性、制度性的政策。这一措施在以后的几年中,引发了一系列的制度性的变化。首先,政府对村干部的补贴逐年上升,作为西部较高补贴标准的云南省, 2006年提高补贴标准后在职村干部达到每人每年4 000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干部无疑具有很大的激励作用。[24]其次,政府为了更准确地发放补贴,对于村干部的“编制”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据作者调查,人口数量超过2 000人的大村享受补贴的村干部可以达到10多人,包括“四职干部”(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委会文书、村计生专干)及计生小组长,有的村庄还设有享受补贴的村委会副主任;人口在1 000人以下的小村也可以有 5-7人享受补贴,包括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兼任文书)、村计生专干及计生小组长。最后,在核定编制的基础上,对应于不同的村庄规模,明确了村级组织的岗位职责。这一切都反映出村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准公务员,村组织进一步科层化,即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形象更为突出,而作为村庄和村民代理人的“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性”[25]并没有明显改善。
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调整,一方面是双方的目标渐趋一致,另一方面是国家依然主导着这一共同目标的实现过程。由于近年来村民自治没有明显的进展,农村社会组织缺失,“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政府凭借农村公共产品的资源供给者和拥有服务内容决定权的家长身份,以村级组织为手段,实现了对村庄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新的更为细致和广泛的干预。而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同时会束缚村庄自治与乡村社会组织的成长。
四、结语
村级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直接载体,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职能和权威的特点与演变,既受到国家政府的制约,也受到农村社会的制约,并根植于二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之中。税费改革之前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虽然通过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化的持续冲击,国家对农村社会不再进行全面覆盖与控制,但“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仍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这一时期,政府赋予了村级组织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村级组织站在与农民冲突的第一线,村民自治进展缓慢,农村社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以“工业反哺农业”并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虽然政府的农村发展目标与农民利益相一致,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种主要由政府付费并由政府决定供给内容的单向输入型模式,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相反,通过对村干部的政府补贴、编制核定和职责分工,即村级组织的进一步科层化,县乡政府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更为细致和广泛的干预,并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村庄自治发展与乡村社会组织成长空间。
[1] 郑卫东.“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5(2):72-79.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6] Sui,Helen F.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 y Press,1989.
[7]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 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47-62.
[10] 吴 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1]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 徐 勇.“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J].贵州社会科学,2007(11):4-9.
[13] 徐 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3-20.
[14] 徐 勇.“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2-9.
[15]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C].厦门:鹭江人民出版社,2000.
[16] 路玉甫.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职能定位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J].地方财政研究,2006(6):36-39.
[17] 王乐锦. 村级组织的职能定位与财务收支范围[J].中国农业会计,2005(6):22-23.
[18] 何海波.通过村民自治的国家治理[C].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论文集,2010.
[19] 张丽琴.村委会职能立法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69-75.
[20] 张 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31-37.
[21] 徐 勇.村民自治、政府任务及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外部行政环境的总体性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1(11):27-34
[22] 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J].社会学研究,1993(1):64-68.
[23] 徐 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2-8.
[24] 王征兵,宁泽逵,Allen Rae.村干部激励因素贡献分析——以陕西省长武县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1):51-58.
[25] 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陈向科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ural society after tax reform
HAN Guo-ming, ZHONG Shou-s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 China)
C912.82
A
1009-2013(2011)01-0033-07
2011-01-26
中国科协重大政策研究项目(2009ZCYJ 20-A)
韩国明(1963—),男,甘肃靖远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