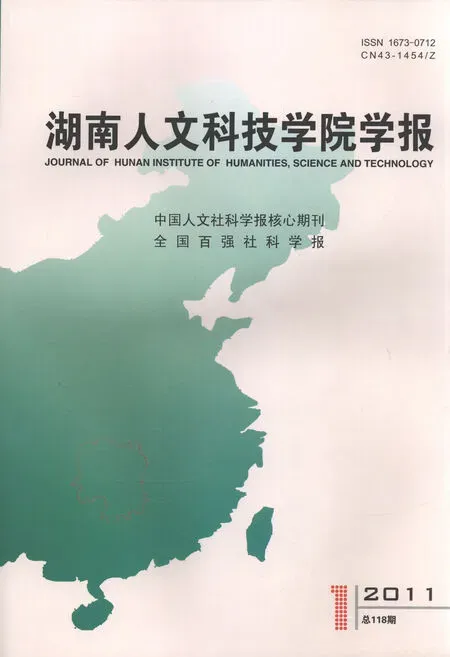火焰、灰烬与精神
——德里达笔下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2011-04-07张计连
张计连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火焰、灰烬与精神
——德里达笔下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
张计连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纳粹问题,是海德格尔的研究者和承继者无法绕过的问题。具有独特眼光的解构大师德里达从精神入手,沿着海德格尔与西方传统精神之间的断裂和欲说还休的牵连,深入海氏思想深处找到火焰和灰烬的纳粹隐喻,用海氏的哲学文本反抗纳粹主义。德里达发现海德格尔的经过沉默和引号净化后的精神是熊熊燃烧的火焰,火既包含了善的因素又包含了恶的因素,火焰燃烧过后带来灰烬,一如纳粹引燃的战火和集中营里的大屠杀。然而,德里达对海氏与纳粹的关系采取的这种既谴责又宽容的态度,在引起我们深思的同时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警惕。
德里达;火焰;灰烬;精神;纳粹主义;海德格尔
在20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中,“纳粹主义”和“海德格尔”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试问苏格拉底以来,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受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主义的遭遇在通常情况下被描述成灾难性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特别是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问世后,在英语世界的作家那里形成了一股潮流,大家都在热切地追随他这个建议,试图在各种主义的主义研究中发现海德格尔的哲学基础上的罪恶性,理查德·沃林、汤姆·罗克摩尔、多梅尼科·洛苏尔多等人最为典型。在德国,反对海德格尔的潮流也是甚嚣尘上,最近以来的作家如哈贝马斯、图根哈特·欧内斯特、尼·德尔图良也将海德格尔的哲学基础置于一种持续不断的敌对批评之中。在法国,形式似乎更加微妙,因为许多领袖级的哲学家如德里达、利奥塔、列维纳斯和福柯都于海德格尔有过很久以前就承认的受惠。对于这些法国哲学家,法里亚斯著作的出现是相当令人尴尬的事,他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和思考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一千个接受者眼中也有一千个海德格尔以及一千种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联形式。
一 重拾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问题的缘起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面对各方面的意见,应该如何判断和辨别?面对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明白的事实是:一方面是海德格尔与纳粹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相似(海德格尔与纳粹都厌恶科学、热爱土地、认同极权),另一方面是欧美政局的推动和各种主义的倡导者各怀目的利用。此外,海德格尔自己的态度,也加剧了这种争议。“战后他缄默不语,对于纳粹,它的男权主义和军事化计划、它排外性的社会运作、它对别国的军事征服、它的种族主义强迫奴役以及种族灭绝政策,海德格尔没有愤怒、没有遗憾、也没有对于此上的关注。”[1]86是的,就像法国学者贝纳尔·亨利·列维所说,“海德格尔不仅拥抱了20世纪最为罪恶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对这一罪恶没有说过悔过或者否认的话,一直到最后(不是一直到战后,而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我们至少可以说他没有表示过丝毫的后悔。”[2]当海德格尔在战后偶尔打破沉默的时候,谈到的是众所周知的对野蛮和残忍的评论,“机械化农业在本质上和毒气室里制造尸体的是同样的东西;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把德国人从波罗的海各国驱逐出去是相同的现象;因饥饿而产生的大量死亡(在中国)是‘是非本真’的死亡;并且,如果战后住房短缺正在导致广泛贫困的话,那么人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真正苦难是正在忘记思考存在。”[1]111
战后的知识分子反思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创伤,对纳粹主义尤其是犹太大屠杀进行了严肃的反省和批判。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纳粹制造犹太大屠杀的集中营,是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最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古典人道主义的彻底失败。奥斯维辛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人类死亡的一次预演,人的身份的死亡,人道主义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精神创伤。而纳粹问题,则是海德格尔的研究者和承继者无法绕过的问题。不管人们怎样欣赏海德格尔的思想、才华和风格,阅读和接受海德格尔都无法摆脱纳粹主义的幽灵。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海德格尔不仅对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心,而且终生都是一个同情纳粹的思想家。德里达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之深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哲学家,正是由于他与海氏遗产的某种“共谋”关系,他的思想和著说也随海氏在某些场合被指责为有法西斯倾向。对此,德里达写了《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作为回应,通过对海德格尔“精神”的解构和建构,德氏对纳粹主义本身作了深刻的思考。他思考了纳粹主义与整个西方思想的关系,尤其是两千多年来所追求的各种不同的精神之间的关系。
二 “火焰”——德里达发现的海德格尔之精神
德里达在他的诸多文本中一再强调他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并一再指出,如果没有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问题,就不会有他的任何研究,“我要做的事,如无海德格尔问题的提出,就不可能发生。”[3]因此,他必然谈海德格尔,事实上,德里达的著作几乎每部都谈到海德格尔,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著作,那些闪耀智慧火花的思与诗无不从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灵感的激发。托马斯·希恩建议:“一个人如果在读海德格尔时不提出政治性的问题,那他根本就不是在读海德格尔。”[4]11对于社会活动丰富,关注世界种种的德里达来说,当然避免不了对海德格尔的政治性言说。但是,德里达作为海德格尔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之一,也当然不会像英、美、德的那些人一样对海氏发起那种有意气用事之嫌的猛烈攻击。具有独特眼光的解构大师德氏从精神入手,沿着海德格尔与西方传统精神之间的断裂和欲说还休的牵连,深入海氏思想深处找到火焰和灰烬的纳粹隐喻,用海氏的哲学文本反抗纳粹主义。但是,一位赞同纳粹主义的哲学家的文本,如何有助于反抗各种纳粹主义的政治斗争?用杰夫·科林斯的话来回答就是,“这里要特别考虑到雅克·德里达的贡献,他对于谴责话语、纳粹主义的界限和政治伦理的讨论,可能是用海德格尔来反对海德格尔自己所主张的政治观点的最为惊人之举。德里达还和其他贡献者一道,对于极权主义和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做出了彻底的反思。”[1]86
德里达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过程中,发现至少在表面上,精神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词语,那么精神是否为海德格尔所弃置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德里达找到了“火焰”作为切入点,他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中找到曾经被避免和搁置了的精神的裂隙和踪迹,然后对准海氏的文本伸出了同样是受惠于海氏而建构起来的解构宝刀。德里达在整体把握海德格尔的全部遗产的情况下,发现精神之于海德格尔,显然没能在存在、时间、世界、历史、存在论差异等宏大主题和词汇旁边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然而他却沿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裂缝,追踪精神在海氏笔下的痕迹,在海氏涂抹不掉的精神裂隙中找到了火焰、灰烬和纳粹的关联。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火元素构成的永恒的活火,它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断燃烧着的。火比其他元素更活跃,更具特征。海德格尔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承继了这种“火”的精神,这是因为“海德格尔经常从赫拉克利特的残片入手,研究其中的短语甚至音节,试图挖掘出失去的原意。他认为,忘记文本的原意已经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而重新找回埋没已久的原意会奇迹般地使西方复兴重生。”[5]纳粹主义者正是带着海德格尔从赫拉克利特的遗产里挖掘出来的火走出德国,冲出欧洲,走向全世界的。希特勒这个“精神性的领导者”带着克拉特利特的活火,燃烧着整个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德里达发现海德格尔的精神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沉默阶段,海德格尔对精神保持沉默,甚至是有意避免。“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正面领会主体、灵魂、意识、精神、人格这类东西的非物质化的存在?……所以,我们避免使用这些名称,就像避免使用‘生命’与‘人’这类词来标识我们自己所示的那种存在者一样,这可不是拘泥于术语。”[6]海德格尔认为,为了言说我们是什么和我们是谁,是必须要避免所有这些属于主体的或主观的系列概念,尤其是精神的概念。沉默不是罪恶,但它掩盖罪恶。而避免是以并不采用的方式采用它,甚至以不再避免的方式避免它,这种迂回的方式在德里达看来隐含了深刻的用意。第二阶段是引号阶段,“精神”这个词回来了,它不再被拒绝、避免,但只是在其被解构的意义上使用。以便指出某种与它相似的他物,精神似乎是这个他物的形而上学的幻影,是另一个精神的精神。正如德里达所说,“海德格尔从使用‘精神’这个词开始。更确切地说,首先是否定地使用它。接着第二步,海德格尔把它作为自己的词语使用,但带着引号,似乎仍是在接替别人的论说,似乎是在引用或借用一个他一心想从中造出另一种用法的词。带着它的引号,一如带着规定这些引号的论说语境,这个句子在呼吸着一个另外的词,一种另外的称呼,除非它对这同一个词、这同一种称呼进行编译,除非它在这这同一底下重新唤回他者。”[4]39引号是海德格尔精神发展第二阶段的标志,“精神”一词在引号里仍命名着的某物因此获得了拯救。精神回来了,“精神”一词开始重新成为可以接受的了。这样,精神似乎超越于解构而指示着任何解构的自然本身,以及任何评价的可能性。第三阶段是去掉引号彰显精神的阶段,引号撤去,帘幕升起,精神本身登台亮相。这种突变带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因为引号的消失,带来了表里如一的精神。
《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是庆祝精神重生的开幕典礼。在这里海德格尔特别提到了精神性的领导者,他认为精神是烙在德意志民族命运上的印记,它铭记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深处,印记的力量加上铭记的力量形之于精神就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与沉默阶段和引号阶段根据笛卡尔、黑格尔或晚期的荷尔德林来谈论精神不同,海德格尔在《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给予了精神以火的特定含义。德里达注意到海德格尔1933年的就职演讲有一项计划,并且如果说它“似乎是邪恶的”,那是因为它同时就具有两重罪恶:一种是对纳粹主义的认可,另一种是仍然保留着形而上学的姿态。而且二者之间呈现某种联结。海德格尔强调精神使命,不断追问精神曾经的堕落、探问如何提升精神的精神性,凸显精神中“土—与—血”的主题,因此《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便表现出强烈的意志主义。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后来的《形而上学导论》为纳粹主义建构了某种“精神化了的”担保。海德格尔在1953年代对精神这个词语的处理,为它提供了一种更富结构性的潜力,在采用关于精神的系列词汇时,海德格尔把说德语者熟悉的“精神”(Geist)、希腊语的“精神”(pneuma)、拉丁语的“精神”(spiritus)以及希伯来语的“精神”(ruah)和“罪恶的精神”(ruahraa)缠绕在一起。承继希腊语的德语和拉丁语之间的对立不允许保持稳定,让海德格尔的精神蕴含着太多不安定的因素。精神性这个词,不久前它还被排除,被“避免”;稍后又处于严密监视中,被压抑、限制在引号中;现在它膨大了,享受着宣告、欢呼、颂扬,毫无疑问,它在所有被强调词语的最前面到来。因此,海德格尔用迂回的方式使精神摆脱了被玷污了的流俗精神,海氏的精神交织灵魂、意识和人格,带着火的善与恶。
德里达通过解读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分析找到了火的主题。荷尔德林是被上帝和光明击中的人,这激起诗人像火一样说话,像火一样吟诗。荷尔德林的精神在火中被烧毁,变为灰烬。《面包和葡萄酒》命名了烧毁、灼伤、火灾、火葬或焚化带来的灵魂。精神是什么?1953年,海德格尔最终的回答是:火,火焰,大火,共燃,精神是那点燃着的火焰。大火,精神的大火,熊熊燃烧的火焰,让人们想起了战争,想起了大屠杀,想起了希特勒在德国燃起而引向世界的战火,在欧洲蔓延,在世界蔓延。精神在燃烧,精神使燃烧,精神是燃烧的火焰。如同荷尔德林的诗句“你的火焰赋予精神以炽热的忧郁”,海德格尔认为恶是精神的一部分,是精神性的,他说“恶在精神本身有其来源。它生自精神,但这种精神恰恰不是形而上学柏拉图式的Geistigkeit。”[4]131恶并不是人们一般讲的与精神相对立的物质或物质的感性之物。恶是精神性的,它也是Geist,在这种Geist中就有那种另外的内在双重性,它使得一个精神成为另一个精神的邪恶幻影。 精神的燃烧带来死亡,带来白色的灰烬,纳粹主义就是一种火的思想,通过把恶铭刻进火焰而引起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希腊语——德语,是火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是一种故事,它不是事后额外地降临到光之火焰上,而是火焰本身。火焰在书写,它自行书写它本身,书写直接就在火焰中。正是在火焰的裂隙中,痛苦席卷,希腊语——德语承载的精神撕裂或撕扯着灵魂,拷问和拷打着世界。
三 在谴责与宽恕之间——德里达面对海德格尔
究竟什么是海德格尔的精神?至此德里达的回答是:火焰。但是精神的火焰经历着动乱,在烈火中燃烧,把自己化作灰烬。1943年夏,在讨论赫拉克利特的讲座上,海德格尔在谈到“存在”的过程中,突然说道,“地球正处在一片熊熊的大火之中,人的本质完全支离破碎了。于是,人面临‘没有路的路’。”[7]应该怎样解构海德格尔的带着火焰的精神呢?在希特勒的战车血洗欧洲的前夜,胡塞尔曾经大声疾呼:欧洲人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处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而海德格尔却一直在解构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传承的西方传统精神。德里达在《论精神》一开始就说,“我将谈论灵魂(revenant)、火焰(flamme)和各种灰烬(cendres)。”[4]1德里达在此,意在再次解构海德格尔解构了的传统西方哲学之理性精神。然而,德里达的“解构”承袭了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克服”,它试图扰乱、瓦解或动摇哲学的基础概念、方法、程序和计划。对于德里达来说,他的这种再解构必须要提出某种动摇性的思考,以对准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用海德格尔的文本来反对按催主义,这是德里达想要在《论精神》中达到的目的。然而,这将如何做到呢?
德里达提出了一种有关谴责和纳粹主义本质的思想。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要被谴责吗?与法利亚斯不同,德里达坚持认为,对纳粹主义的谴责并不是对纳粹主义的思考。如此,在付出了某些代价之后,海德格尔或许会成为一个无罪的话题。因此,德里达以“解构”的方式越过了对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关联的既定谴责。德里达的这种“解构”游戏暗藏着危险,这是一种辩护式的论证线索:纳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事件,那时至少经济得到改善,火车准时运行。另一方面的危险是,把纳粹主义牢固地困在一起,好像它能被固定在一个邪恶的名称下,能被固定在一幅公开展示的形象下面。这或多或少都是一个问题,即德里达如何用海德格尔来解读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既有一种谴责又有一种思考。德里达努力在海德格尔文本中寻找仍然存留着的形而上学残余,并动摇它们。这就是《论精神》一书的阅读轨迹或游戏。能否穿透德里达写作该书的目的和意图,就要看读者能否在字里行间辨析德氏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微言大义”。
精神既是一种力量又不是一种力量,它既有权力又没有权力。德里达注意到,1933年,伴随着某种修辞的力量,海德格尔采纳了“精神”一词。考虑到这是一种使用的和资源的运用,这一术语因而富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特性,不过后来海德格尔对此有所怀疑。因为,正是“精神”一词具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特性限制了海德格尔自己早期的结构倾向,并且让这一术语投入到纳粹的怀抱。灰烬是纳粹肆虐过后留下的残余。灰烬,烟斗中随着呼吸间歇闪亮的烟丝,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就毁灭了自己。但对于火焰与灰烬,德里达在海德格尔这里,再往前追溯,到尼采那里,得出精神创伤是高贵的精神自己创造的,与希特勒无关的结论。至于希特勒如何解读尼采,纳粹主义如何解读和利用海德格尔思想,那是后来的事情。德里达对火焰的思考只能返回,在返回中警醒的精神总是会去做剩下的事。通过火焰和各种灰烬,那是不可避免地作为全然他者的火焰与灰烬,德里达在《论精神》中揭示海德格尔的精神中包含的恶的因素的同时,不免过多地停留在其精神之火焰上,淡然于火焰肆虐过后的灰烬。从德里达在北大的演讲我们知道,德氏是主张有条件的宽恕的,这是他在反思海德格尔精神与纳粹牵连的同时,给予海氏比法里亚斯更多的宽恕的缘由。
“纳粹不是诞生于荒漠。这一点人们都很清楚,但是总需要提醒。即使——在远离任何荒漠之外——它曾像蘑菇一样在一片欧洲森林的宁静中生长,它也会是在一些大树的阴影之下、在其沉默或漠然的遮掩之下生长,但也是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4]150火焰、灰烬与精神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丝丝缕缕地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梳理线索,同时承载着谴责与宽恕。或许以海德格尔思想对抗纳粹主义的复杂难题能够被德里达最为缜密地表达了出来,但对于重读海德格尔来说,这将是一个最富戏剧化的事件。然而,德里达把这种“纳粹精神”幽灵化了,精神不过是显灵而已,灵魂就是被解构的精神,精神中的精神。当时,海德格尔所痛心疾首的是德意志,这个形而上学的民族,正在丧失精神的力量,所以,海德格尔和纳粹一起,要重振精神的力量。新的开始就要经历死亡,要死亡就要毁灭,要毁灭就要有战争烈火。战争制造和治疗精神的创伤,但是有精神创伤的切口,藏着无法体验的微妙感觉。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这种体验,正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精神的体验,也是我们对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的体验:在谴责和宽恕之间,我们是否应该对灰烬给予更多关注,而不应该像德里达一样过多地停留在海德格尔精神的火焰里?
[1]杰夫·科林斯.海德格尔与纳粹[M].越成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贝纳尔·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M].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3.
[3]德里达.多重立场[M].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1.
[4]雅克·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M].朱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莎蒂亚·B·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M].刘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9.
[6]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4-55.
[7]尚杰.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306.
(责任编校:潇晓)
Flames,AshesandSpirit——Derrida’s Heidegger and Nazism
ZHANGJi-lian
(Literature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Nazi problem was the one that the researchers and successors of Heidegger would not be able to bypass. Derrida, a deconstructionist with an unique perspective, had gone into the deepest thought of Heidegger to find Nazi’s metaphor of ash and flame by starting a focus on Heidegger’s writings on spirit. Derrida also explored the break and relates bonds between Heidegger and western tradition. Derrida used Heidegger’s philosophical texts to fight against Nazism. Derrida noticed that for Heidegger, the spirit after silence and purification was a flaming fire, and fire covered both the good elements and evil elements. The ashes that the fire produced resemble holocaust in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fire of war set by the Nazis. However, Derrida’s attitude to Heidegger, which included condemnation and forgiveness, should not only us to think deeply but also make us more dert.
Derrida; flame; ashes; spirit; Nazism; Heidegger
2010-12-08.
张计连(1979— ),女,湖南浏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B086
A
1673-0712(2011)01-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