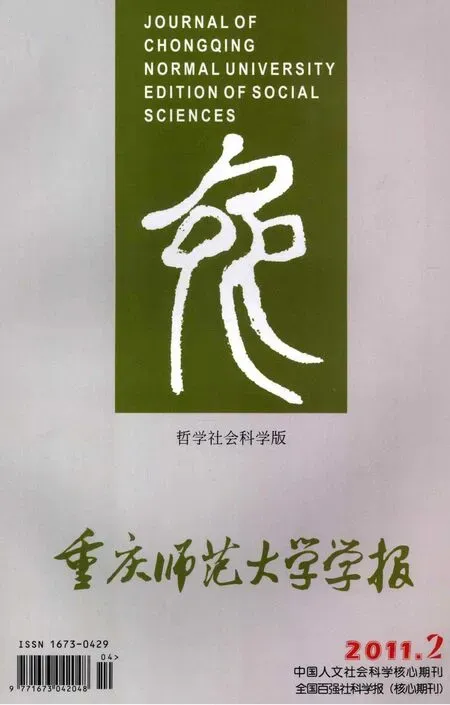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2011-04-02唐红
唐红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唐红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刘勰;诗论;《文心雕龙》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广泛论述了当时存在的各种文体,但他最看重、谈论最多的是诗体。上篇“文体论”的前三篇《明诗》、《乐府》、《诠赋》,加上“文之枢纽”的最后一篇《辨骚》,就今天的文学观点来看都是诗体专论,涉及到诗的含义、作用、内容和渊源流变等;而下篇的《比兴》、《时序》、《物色》、《才略》等篇也都是以诗赋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论及诗歌的创作活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这些共同构成了刘勰丰富、完整的诗论内容。在刘勰论及诗体的篇目中,《明诗》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不仅因为诗这类文体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在于该篇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诗的含义: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65)
诗是什么?这是刘勰“明诗”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段文字句意连贯、逻辑清晰,整个都是在解释诗的含义,刘勰自己也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一对诗的解释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诗者,持也”四字虽然出自纬书《诗·含神雾》,但“持人情性”四字则经书、纬书和各类典籍都不见,是刘勰自创的新语。可在刘勰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诗言志”和“诗缘情”两个经典的论断,他为什么还要花费心思从纬书中觅一个“持”字出来呢?况且六朝时期谶纬之学已经处在禁绝之中,刘勰本人也写了《正纬》一篇放进“文之枢纽”,并指出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原本“无益经典”的东西,如何在文体论的首篇开篇就出现,而且变成与经典“有符”了呢?对于非常讲究“为文之用心”的刘勰来说,此反常举措也许暗藏着丰富的意涵,不能以常理度之。但现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文心雕龙》的注解,认为这段文字讲了两个问题:“大舜”九句是在讲诗的含义,“诗者”七句则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2](57)。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刘勰对诗的界定全是采用经典里的陈词,毫无己见;其次,“持人情性”虽是新语,却也脱不开诗教的窠臼,同样没有己见;最后,刘勰为什么要从《诗纬》中找个持字来训诗,并且将之与“思无邪”相提并论,得不到满意的解答。这样解读的最终结果,是把刘勰变成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儒家诗教观的推崇者,可事实不尽如此,熟悉《文心雕龙》的人都清楚,刘勰虽然强调“宗经”,但绝不保守,他的整部著作论述精辟,新意迭出,更何况“宗经”与创新并不相悖。所以,对于刘勰新创的诗“持人情性”之说,我们如果用新思维去解读,也许更能把握他诗论的真实面貌,了解他的“用心”之所在。
一、“持人情性”是讲诗的含义,而非诗的政治教化作用
刘勰论及各种文体,基本上都遵循自己在《序志》篇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论述模式。其中,“释名以章义”就是对文体的含义进行界定,这在《文心雕龙》里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者……也”判断句式,如“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诠赋》)。据笔者统计,在《文心雕龙》20篇文体论所详细论述的34类文体中,有27类文体用了“者……也”句式来“释名以章义”,它们分别是:诗、乐府、赋、颂、赞、铭、箴、盟、诔、碑、哀、吊、讔、史、传、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对、书;另有谐、诸子、议、记这4类文体用了“者”或“也”的句式,如“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议之言宜,审事宜也”,“记之言志,进己志也”;惟有祝、杂文、封禅3类文体没有用这种判断句式,当然刘勰也没有对它们进行明确的界定。此外,《书记》篇所附带提到的24种文体,刘勰亦全部采用了“者……也”句式界定文体含义。这种叙述话语形式上的准确、凝练和一致,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时比较重视的,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推断:刘勰在论述各种文体时,有意识地采用了“者……也”的判断句式来对文体含义进行简明扼要的界定,虽然这一句式不是刘勰对文体“释名以章义”的全部,但却是他概念界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独特意义。那么在《明诗》中,“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应该是刘勰对诗这种文体下的定义。
另外,单从《明诗》开篇这段文字来看,刘勰也采用了一种规范化的论说方式来对诗进行界定:在对一个问题作出新的判断之前,论说者需要先引述已有的重要观点并作出评价,以此展示自己对该问题的把握程度。在引了“诗言志,歌永言”之后,刘勰即说圣人对“诗”、“歌”所作的分析,含义已经很明确了,意思是这两句话按字面意思理解即可,无须作过多阐释;而对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刘勰用“舒文载实”对其作出评价,认为诗就是人的心理情感舒发成“文”的自然过程。经过这两个铺垫,刘勰抛出了自己对诗的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不是标新立异,除了前面的铺垫,刘勰还将孔子的“思无邪”拉来作靠山,“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因此,《明诗》开篇这整段文字都在讲解诗的含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是刘勰释诗的核心内容,并非是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
现在通行的《明诗》注解大致都把“持人情性”解释为把持、扶正、“扶持人的性情,使不偏邪”[3](51),并引申为“引导、劝诫、教育”[4](56)等儒家诗教观。王运熙先生曾明确说过:“刘勰比较重视教化、美刺讽谏作用,重视诗的政治内容……《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就是强调诗歌的教育感化作用。”[5]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詹英《文心雕龙义证》、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等,也都持这种观点。对“诗缘情”颇不满的清代纪昀对刘勰“持人情性”的提法推崇备至:“此虽习见之语,其实诗之本源,莫逾于斯;后人纷纷高论,皆是枝叶工夫。‘大舜’九句是发乎情,‘诗者’七句是止乎礼义。”[6](27)朱自清也认为“诗者,持也”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7](152)这些对诗“持人情性”的解读之所以会走入政治教化功用论的误区,除了没有认识到刘勰“释名以章义”的独特论说方式外,还在于他们误入了刘勰“宗经”的逻辑圈套。刘勰在《序志》篇中讲明了自己写作的理论逻辑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而《明诗》开篇这段话的叙述方式恰好又局部地符合这一逻辑:“诗言志”为舜之言,是“师乎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出自《毛诗序》,是“体乎经”;“诗者,持也”引自纬书《诗·含神雾》,是“酌乎纬”;用《论语》“思无邪”之说来肯定《诗·含神雾》对诗的训释,是“按经验纬”(《正纬》),刘勰就这样在形式上完成了一个标准的“宗经”模式。受此影响,刘勰很容易被认为是非常保守的儒家诗论观的持有者,即注重诗的政治教化功用。但事实却不尽如此,综观《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及《明诗》篇对诗的详细分析,诗教在刘勰诗论中的地位是不突出的,儒家诗教内容虽被刘勰提及,却被他作了新的解读,用来为其“自然”文学观服务。
二、“持人情性”与“思无邪”相符新辨
刘勰说“持人情性”与孔子“思无邪”之说是相一致的,所以很多人就据此反过来用“思无邪”解释“持人情性”。可是孔子这句话也颇为难解,一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这类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是比较常见的,如清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诗经》中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8]后世对“思无邪”三个字的解读又何尝不是如此。本文无意对此进行详尽的梳理与阐发,仅举一二例子。《朱子语类·论语五·诗三百章》记载了许多朱熹对“思无邪”的解释,但多有矛盾之处,其中有两处比较有代表性:
李兄问:“‘思无邪’,伊川说作‘诚’,是否?”曰:“诚是在思上发出。诗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于正,岂有假伪得来底!思,便是情性;无邪,便是正。以此观之,《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9](545)
(朱子)曰:“便是三百篇之诗,不皆出于情性之正。如《关雎》《二南》诗,《四牡》《鹿鸣》诗,《文王》《大明》诗,是出于情性之正。《桑中》《鹑之奔奔》等诗岂是出于情性之正!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往往只是刊定。圣人当来刊定,好底诗,便吟咏,兴发人之善心;不好底诗,便要起人羞恶之心。”[9](541-542)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更是“纠缠不清”:
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10](1541)
由于无法跳出儒家诗教观的思维定势,这些“臆说”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近人郑振铎干脆说孔子“思无邪”之说“其意义却是不甚明了的”。[11](218)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知孔子删去的《诗经》内容,而现存的《诗经》又无法用“情性中正无邪”的诗教观来“一言以蔽之”,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抛开汉代成型的儒家诗教观,重新解释“思无邪”。在这方面,宋代袁燮在《题魏丞相诗》中的一段话倒可作为参考:
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已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纯,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12]
按照袁燮的理解,《诗》三百无不是先民情性之“自鸣”,一言一句,都是内在心理情感的自然舒发,“岂有假伪得来底”!如此看来,这个“邪”解作“伪”也许更为可取,“无邪”便是“无伪”,古人“感物吟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情”此“志”无论是“乐”还是“哀”,是“正”还是“淫”,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自然自鸣,没有虚假伪饰。其实程子说的“思无邪,诚也”已有“无伪”的意思,朱熹也说“惟其表里皆然,故谓之诚”[9](543),但宋代这批理学家始终跳不出诗教的框框,非要把“思无邪”和善恶邪正等伦理内容连在一起,所以形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阐释状态。如果将“无邪”解释为“无伪”,那么无论“思无邪”之“思”是指心志、情性,还是发语助词,无论《诗经》里的诗篇是“正”还是“淫”,都能解释得通,这或许才是孔子“思无邪”的本来面目。刘勰诗“持人情性”的新提法正是在这个理解维度上与“思无邪”“相符焉尓”,这是其“自然”文学观的有机组成,而不是对“止乎礼义”之类儒家诗教观的反映。
三、从《明诗》篇论说结构解读“持人情性”
以刘勰思维之精细严密,行文之字斟句酌来看,每一篇文章中必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和逻辑转承的过渡语句。如果说真如纪昀所言,《明诗》首段文字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结构,那么其后的文字也应该以诗教为中心,按照类似的结构进行阐述,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儒家诗教来看,刘勰在其后并没有提到过“温柔敦厚”、“主文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的诗教核心内容,也没有表露出“诗”把持、扶正、“扶持人的性情,使不偏邪”的意思,惟有提到“顺美匡恶”、“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等“美刺”内容,这点零散的论据如果要用来论证篇首即提出的诗教观,似乎显得太过无力了。
就论说结构来说,《明诗》篇第二部分开头“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四句话在整篇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释诗”转到“论诗”,这样才能“明诗”。因此,这四句话是我们理解刘勰诗论的关键点,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贯通上下文,完整地把握刘勰“明诗”的过程。而这四句话几乎是大白话,意思完整明了,明代曹学佺点评为:“诗以自然为宗,即此之谓。”[6](27)崇尚文之“自然”是《文心雕龙》的重要思想,《原道》篇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纪晓岚认为:“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6](14)明了此四句话的含义和结构地位后,我们就可以对下文作出正确的理解了。无论是“葛天乐辞”、“黄帝云门”,还是尧的“大唐之歌”、舜的“南风之诗”,都是“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的自发之作,虽然仅是“辞达而已”,可也“莫非自然”。无论是对“大禹成功”的“顺美”,还是对“太康败德”的“匡恶”,同样是情性的自然感发,绝无虚伪矫饰。“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文学体裁的完备,经典作品的出现,创作方法的兴起,文采得到重视,“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因此孔子谈诗,也看重“绚素之章”、“琢磨之句”。尽管“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但人们还是喜欢用诵诗来传情达志,哪怕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还是请人作诗。这表明无论外物和人的心理情感如何变化,诗始终是人“吟咏情性”的载体。所以,历史的发展,人的情感体验的变化,同样促成了诗体的自然变化,只是到了六朝时代,玄学清谈和轻浮绮丽的文风矫揉造作,违背了自然之态,所以亟需批评与救弊。这也正是《文心雕龙》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
“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这是和“人秉七情”四句同样重要的转承语句,从“论诗”转入总结,在论说结构上照应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从历史来看,人的情性的发展变化与诗体的发展变化之间的自然对应关系是清晰可鉴的。刘勰虽只是“撮举同异”,但他在篇首对诗的解释可以说已经很清楚了,特别是他的新观点——诗“持人情性”之说。
四、诗“持人情性”新解
按照前面所作的分析,刘勰认为诗是人的情性的自然舒发,那这个“持”该作何解呢?“诗者,持也”在纬书《诗·含神雾》中完整的原文是这样的:“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13](464)从原文可以看出,这里并非以“持”来解释文学意义上的“诗”,而是在训释“诗”这一“持”的假借字。据饶宗颐先生考证,“诗与持同训,互相假借”,《诗·含神雾》“诗者,持也”就是如此。[14](9)这种情形在《礼记》和《仪礼》中共出现过三次。《礼记·内则》云:“(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斋。朝服寢门外,诗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郑玄注:“诗之言承也。”[15](1469)《仪礼·特牲馈食礼》:“主人左执角,再拜稽首,受,复位,诗怀之。”郑玄注:“诗犹承也,谓奉纳之怀中。”[15](1185)《仪礼·少牢馈食礼》:“主人坐奠爵,兴,再拜稽首,兴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怀之。”郑玄注:“诗犹承也”[15](1202)。也许正是由于诗与持同训假借,汉代的纬书制作者便直接把“诗者,持也”放入《诗纬》中,试图以此解《诗》。但即使如此,我们在理解刘勰诗“持人情性”时,也该用“持”的本义,即“承负”之义,而不该想当然地根据儒家诗教观作引申,把“持”解释为“扶正”“扶持”等。根据前文对《明诗》篇的解读,刘勰以持训诗,也应是用的持的本义——承负,“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就是说诗承载着人的情性。
“诗言志”与诗“持人情性”在语法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志”形于“言”为诗,诗即是“志”的载体;人的“情性”的自然舒发成为诗,诗即是“情性”的载体。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诗言志”的“言”重在一种表达、抒发之意,是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待诗,包括赋诗、诵诗和献诗,都是这样,所以诗能观志;诗而“持人情性”的“持”重在一种客观的描述,揭示出诗和人的情性之间所存在的自然而然的“承负”关系,情性的发展变化,必然带动诗体的发展变化,无论是情性还是诗的单方面发展,如“为情而造文”、“为文而造情”,都违背了诗与情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失去了自然之本。所以刘勰在《明诗》的后面部分总结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不同的诗体代表着不同的情感形式,人的才气(情性)不同,对诗体形式的选择、风格的展示自然有别。“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诗要随情性之自然成形,而人各有情性,要想在诗歌创作上各体兼备,确是很难做到。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册)[M].齐鲁书社,1981.
[3]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 王运熙.钟嵘诗论与刘勰诗论的比较[J].文学评论,1988,(4).
[6]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朱自清.诗言志辨[A].朱自清全集(第六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8] 皮锡瑞.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A].经学通论[M].中华书局,1954.
[9]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册)[M].中华书局,1986.
[1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八)[M].中华书局,1986.
[11]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2] 袁燮.题魏丞相诗[A].絜斋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14] 饶宗颐.诗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简资料为中心[A].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湖北人民书社,2000.
[15]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
An Analysis of Liu Xie’s On Poetics
Tang 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hihezi University,Xinjiang Shihezi 832003,China)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we can find Liu Xie’s ideas everywhere.Liu Xie defined poetry as a media of disposition.Most scholars regards that Liu Xie did not give definition to poetry but explained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 of poetry.This misunderstand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attern of stylistics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also it neglects Liu Xie’s natural views in literature.
Liu Xie;On Poetics;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I206.2
A
1673-0429(2011)02—0066—05
2010-09-28
唐红(1977-),女,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