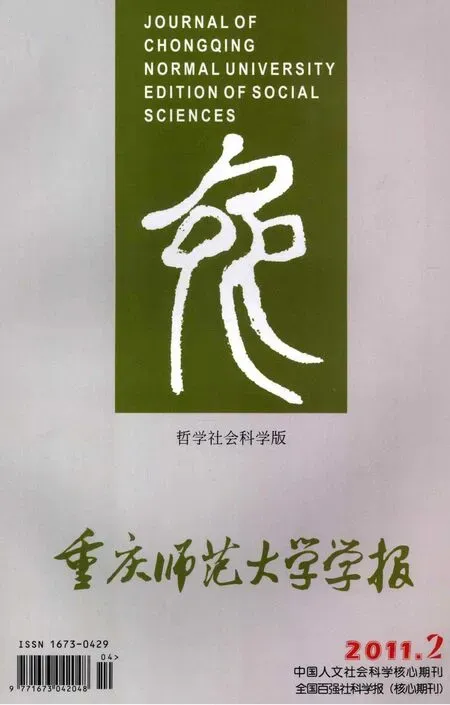“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2011-04-02罗丹阳
罗丹阳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歌花”与“歌骨”
——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罗丹阳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苗族古歌;口头传统;“歌花”;“歌骨”;变异性;稳定性
苗族古歌苗语称为“HXak Bangx”,也称大歌,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优秀古歌代表,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是研究苗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马学良称赞苗族古歌是“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是“形象化的民族发展史”,“鼓舞着世世代代的苗族人民,继承祖先艰苦创业的宝贵传统,创造今天的幸福生活。”[1]苗族古歌涉及到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透过苗族古歌,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苗族人民的生活、劳动场景以及宗教信仰、图腾崇拜、风俗习惯与传统的心理机制等,对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来说也很具参照价值。
苗族古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重视。特别是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一书中,对苗族古歌内容、形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在书中总体性介绍了苗族歌手阐述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使人们对苗族古歌中“歌花”与“歌骨”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提出“歌骨”是表现一支歌主题的部分,在古歌演述时具体指问和答的内容。“歌花”是游离于“歌骨”之外的部分,内容与主题无关,主要以营造气氛、激发情感为目的,以邀请、赞美、自谦等为内容,也可以包括那些表示交代、承接的套语。“歌骨”重在叙事,“歌花”偏于抒情;“歌骨”严肃庄重,“歌花”活泼风趣;“歌骨”以传授知识为主,“歌花”以娱乐身心为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伴而行。此后,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歌花”(bangx hxak)与“歌骨”(hsongd hxak)现象,但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更没有作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本文选取苗族古歌传承中的本土语汇“歌花”与“歌骨”作为重点探讨的对象,通过解读《苗族古歌》中《溯河西迁》相关章节,对传唱古歌的苗族歌手所述“歌花”与“歌骨”现象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旨在通过剖析《苗族古歌》这样一部宏篇巨著,对它进行全方位窥测与研究,通过论述“花”与“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一、“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的传承方式
苗族古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至今仍然还在苗族民间口头流传。苗族古歌属于口头传统范畴,在传承方式上主要依靠口头教授,师徒传承。歌手在长期传唱过程中,依据自己的相关经验,总结了古歌中存在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形式对它进行形象表述。著名学者马学良曾对此有一段论述,他说:
记录诗歌与记录故事是不同的。记录故事可以一字一句地记,而诗歌最好是从歌唱中记录。因为诗歌有的是传统的古歌,有的却是即兴的诗歌。诗歌句式短,格律性强,而且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若要记下诗歌的全貌,必须从现场对歌中记录。据歌手讲,如果教唱诗歌,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骨”是比较定型的,是歌的基本部分,即设问和解答叙述部分;“花”虽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即兴之作,或为赞美对歌的人,或为个人的谦词,或为挑战性的,往往与诗歌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显而易见,不是那种特定的对歌环境,就很难迸放出那样的“花”来。[1](10)
这里反映出了一个问题:民间在教唱诗歌的过程中,艺人教唱诗歌,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就其原因来说,是由于“骨”较定型,是歌的基本部分,而“花”虽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民间传唱者的即兴之作,它的变异性比较大,这些都是民间口头传唱艺人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民间艺人对苗族古歌中的具体内容选择“教”与“不教”,实质上是由古歌中存在的“花”与“骨”这一现象的分类来决定的。“花”与“骨”的发现在苗族古歌的研究中,是一个新的突破口,具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从2006年至今,笔者在黔东南施秉县双井村开展了六次田野调查,并就苗族古歌的当地术语表述问题,对当地的古歌师龙光祥老人进行了田野访谈。龙光祥老人说,“歌花”用当地方言术语表述为“称呼”,指双方在对唱的时候,临时编的一些唱词;“歌骨”用当地方言术语表述为“路数”,唱歌时,每问一个问题,每解答一次,唱词内容和格式有一定的套路,特别是主题思想,都是一致的。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参照了民间的表达形式来进行文本誊写。苗族歌手在演唱时,十分重视对“歌骨”的传承与对“歌花”的自由发挥。“歌骨”的部分在古歌中出现频率相当高,重复出现,即程式化的部分,具有稳定性。而名为“花”的仅是叙事点缀的部分。在苗族民间口语化中,有时也形象化地称之为“打结”、“作结”等。
二、“歌花”与“歌骨”:口头传承的变与不变
苗族古歌的传承与演唱中存在着程式化的叙事结构、故事线索与句法手段,歌手只有记住了这些“歌骨”才能将这么长篇累牍的古歌演唱下来而不至于遗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古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歌手的创造与发挥,融入一些新的“歌花”,在传统的继承之中也有创造、变新之处。民间所说的“歌骨”与“歌花”,从实质上来分析,就是一种稳固性与变异性的形象表述。在民间文艺理论的归纳上,我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阐释观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苗族古歌中,“骨”正好体现出古歌传唱的程式化风格,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叙事主题、故事范型和句法程式。叙事主题,如创世和迁移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叙事类型,在《苗族古歌》中主要体现在《开天辟地》、《跋山涉水》这两章,它们在古歌传唱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故事范型则主要体现在“古枫歌”与“蝴蝶歌”的传唱中;句法程式则表现为“特性形容修饰语”,如“六对西迁的先祖”、“五对爹娘”等,在前述的古歌叙唱中,它们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分别为九次与七次,这是“骨头”出现的地方。它们的句法单位虽然呈现为片语,但具有程式化的稳定性特征。苗族人民用“六对西迁”修饰“先祖”,用“五对”修饰爹娘,“六对”、“五对”这些词被称为“特性形容修饰语”。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先祖”是“六对”而不是其他的数字,为什么爹娘是“五对”而不是其他的呢?在传唱中,能不能表述为“七对西迁的先祖”、“八对爹娘”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特性形容修饰语与古歌的传唱内容,是绝对不能随便变动的,即古歌传唱中的稳定性部分,它长期作为固定的程式保存下来,并一代代在民间流传。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凭借着这几个概念和相关的文本分析模型,帕里和洛德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够表演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流畅的现场创作能力的问题。[2](10)
“歌花”是不断变化的,即兴演唱的,属于歌手个人自由发挥的部分,可列为古歌或古歌传唱中的枝节部分。而“歌骨”却具有变化较小、比较固定的特性。“歌花”与“盘歌”这一艺术传统存在着内部的关系,从上段“歌花”的内容记叙中,我们能够发现变异之处。一般分为几种情况: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等。首先,苗族古歌的演唱是因人而异的。演唱苗族古歌的歌手经常不是同一人,在演述过程中,歌手一般都会加入个人的见解、看法等,这些都是属于歌手思想意识领域的主观化的东西。这导致了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歌师卓越的编唱才能,使苗族古歌得以不断丰富、完善;另一方面,歌手在创造过程中,古歌也在不自觉地发生着变异。我们的学术界以前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即过分注重对异文的解读,忽略了对民间艺人的研究,更没有看到他们在民间文化保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古歌主干部分形成以后,在一代一代的传唱过程中后人会不断增补后期社会的内容,或者在民族文字出现以后,祭司、巫师、歌师在记录整理时也会进行加工修改,使古歌内容不断扩展,形式也逐渐趋于完善。所以,我们应该从关注异文转换到关注人。在民间,苗族人民对歌师和古歌充满了爱戴之情,民众的支持则是苗族古歌得以流传的群众基础。对于这一点,钟敬文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我们作研究要善于从民间来,不可离开民间这个大环境,更不可忽略民间歌手在民间文学的传承与民族文化的保存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然而不太乐观的情况是,一些学者在从事田野过程中,搜集、整理民间传唱等形式时,往往只注重了对传唱的篇目内容的记录,而忽略了对演述人、演述场景、演述情形等补充材料的记录。导致我们今天在参照古歌的版本时,只能看到文本的主要情节、内容的记录,看是怎么发展与进行阐述的,却不知道当时是哪几位歌手在何时、何地、何场景中进行演述的。看版本的书面编排时,在“第一作者”的位置上,往往出现的是学者的名字,而不是以“XXX歌手演述”等形式。在田兵的《苗族古歌》中,也只有每一章的最后,有一小段讲述者的姓名记录,如“演唱者XXX”、“搜集者XXX”、“整理者XXX”,而对当时演唱时具体情形、演述的进程、周围的观者反映、歌手之间的应和对答等等,则缺少相关的补充记录,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搜集、整理民间演述文学时,应该作好详尽、充分的记录,要充分尊重民间艺人的演述,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对他们的姓名予以记录,这对于后人研究记录的材料,是大有裨益的。第二,苗族古歌的演唱也是因地而异的。苗族对歌、赛歌和学歌的习俗,为苗族古歌的继承发展提供了场所。在演唱苗族古歌时,如果所在的场合不一样,演唱的具体内容也肯定会不一样,在婚礼上与在祭祀仪式上,在牯脏节、芦笙节等不同的场合,苗族古歌演述的内容也是不同的。第三,苗族古歌的演唱还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异。在各个不同时期苗族历史向前发展,古歌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世世代代苗族人民以不老的古歌歌唱生命,歌唱生活,传承着他们的历史,演绎着他们的故事。总之,因为种种因素的变异所致,苗族古歌的“歌花”部分,在不断发生着流传、变异,较之“歌骨”更具备凝固性的特点而言,“歌花”更具备流动性的特点。
苗族古歌作为苗族民间口头传承作品,既具有变异性的特征,也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因为苗族古歌至今仍以口头传唱形式在民间口头流传着。在这种长期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会发生流传变异,后代的社会生活内容与思想意识形态等,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古歌的内容与情节诸多方面,浸渍、渗透到这部长篇古歌中,这给我们后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哪些是“原生”的古歌的部分,哪些是一代代传唱中添加进去的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对古歌进行新的考察与分析。尽管一时不能做到泾渭分明,但是古歌各章还是有章可循的。古歌在流传中受到后代的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内容的渗透,但这不会改变古歌的核心与主体部分,即古歌具有稳定性的程式化部分;后世的某些新的形式的浸渍,无法取代先民原生状态下的生活、思维方式。苗族先民的世界观、思维意识等,已经有了当时的社会的印记,这些已经反映在整部古歌中去了。试想,如果后一代的社会生活让整部古歌产生根本的大变动,那这部古歌与后代的幻想文学作品也就没有两样了。从苗族古歌的《溯河西迁》这一章节来看,它的主要情节和核心内容不可能是后人加入进去的。它反映的苗族当时西迁的路线,尽管后来有一些添入的情节部分,但整体来看,是跟当时苗族的社会生活状态紧密相连的,后世改编的可能性极小。与西迁相连的主要是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的那种思维中的传统与集体范式。
稳定性与变异性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部篇帙繁浩的苗族“创世古歌”,在苗族民间传唱了千百年的岁月,经历了苗族历史长河中几个发展阶段。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所致,在苗族当地,现在能够完整演唱古歌的民间艺人已经不多了,而且它在流传中已经发生了变异,已经不是产生之初的原貌了。然而,由于这个口承传统有稳定性的一方面,所以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没有因为苗族没有文字的记录而无法保留,至今仍在苗族人民的口头传唱着,并且为苗族群众所喜闻乐见。苗族有句古话叫“说者记不全”,即古歌是用来“唱”而不是用来“说”的,苗族古歌是一种带韵律的、口头的演唱方式,它必须在合乎自己本民族传统的环境中、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去演唱,这样才能把它传承下来。
三、“歌花”与“歌骨”的重要理论意义
民间文学由于是口语相传,在流传过程中,不能像作家文学由文字写定,而是随着时空流转和情境改换会有变异,因此,变异性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不论中外,有关民间文学的介绍之作,在谈到民间文学的特质时,一般都免不了会谈到“变异”性,然而要真正解说清楚“变异”的内涵,却并非易事。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如果“变异”是民间文学的一个基本特质,那么“变异”的原因与结果,也就是“变异”的本质又是什么?民间文学是不是永远在变动之中而无从捉摸?永远“变异”而无所定准的东西,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它有固定的认识?作家文学的作品是以文字传达,以文字定位,因为作品一经写定发表就有一个定本流传,即使作者本人有所改作,也是据一个文本再作另一个文本。文字是书写在固定材质的符号,基本上是稳定而不流动的。
民间文学则是口语相传,相对于文字来说,语言是流动而非固定的。因此流传过程当中,难免会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多有变异。可以说民间文学变异的根源就在于:口传。不论是神话或民间故事、传说以及歌谣,在传统社会中,都不是普遍一般人能讲能唱的。按往常的调查和理解,每一个社会中能讲善唱的多半只是少数的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都只是听众或者说是参与者。这也就是说,真正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及其所承载的传统传扬出去、传承下去的,实际上是那些专门负责讲述的人(如仪式中讲述神话的祭司、长老),或特别善于讲述的人(有些人很会讲故事或念唱歌谣,有时可能是兴趣与特长,有时可能是某种职业上的需要)。我们可以概略了解到,因为民间文学的流传是随时变异的。变的另一端应当就是不变,变异的另一面应当就是统一或稳定的东西。
民间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能够成为各地学者比较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有其稳定不变的一面。否则若只有“变”而无“不变”,则作品便无传统可循,研究者也难以对作品作广泛的跨文化研究。苗族古歌中的“歌花”是由歌手即兴表演时演述的,具有不稳定性,随着演述的时间、场合、语境等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是歌手演述时变化不定的部分。“歌骨”是古歌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变化较小,可列为古歌传唱中的主干部分,是整部古歌的主要情节与内容。长期以来,一代代歌手之所以能够记住长篇累牍的古歌,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记住了整部古歌的主干部分即“歌骨”部分,它体现出的是民间口传文学的稳定性特点,而“歌花”则更多体现出口传文学的变异性特点。因此,在论民间文学之变的时候,对于相对稳定不变的一面,就不能全然的疏忽。这就如人的两面,只看一面,不能知道全貌。专就民间文学的变与不变这一问题来说,国外早已不乏专论的文章,但是因为立论重点各有不同,所见未免各有偏向,求一多面顾全之作,似仍罕见。
古歌的艺术传唱形式,至今还在许多民族地区口头流传着,从南到北,存活于民众的口头之中。少数民族民众对本民族的古歌,缺少理解与认识,处于一种比较自然与初级的状态。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汲取和保留一份民族民间口头艺术的优秀基因,而且需要深入民间,在扎实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对古歌传统自身的价值与功能进行挖掘。我们在对苗族古歌进行研究时,切忌把它视作一种僵化的形式,就文本分析文本,脱离开古歌传承的文化语境作孤立的文本审视。相反,应该把古歌视作流动的、发展的“活”形态的民间传唱形式来加以考察,对它的方方面面加以研究,尤其是把握住“歌骨”与“歌花”之间的内部联系,也即“稳定性”与“变异性”的辩证关系。对苗族古歌的研究,我们不能脱离苗族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有深入当地,在这些附带的背景的大情境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古歌的流传、变异等具体情况,才能更好地领会古歌内部的深层含意,以便更好地对这部古歌的文化学价值作合理的衡量,使我们最终认识到:任何一种民间文化“传统”的形成、维系与发展的内部运作机制正是建立在“稳定性”的基础上的。
变异性与稳定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同时存在于苗族口头传唱之中,我们不能厚此薄彼,任何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综观民间文学发展史,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过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往往过于强调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特征,在总结“民间文学基本特征”时,或是把稳定性特征忽略不计,或是提到了这点,也只是简略的论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忽略了对口头传承的稳定性研究。我们要以辩证的二元观念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纠正以前认识中存在的种种偏颇,以弥补民间文学稳定性研究的缺失。民间歌手所总结的“歌骨”与“歌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角度,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民间口承文学的研究,引导我们步入一个新的轨道。
[1] 马学良,今旦.苗族史诗[Z].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
[2] [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Bangx Hxak and Hsongd Hxak:——On the Variation and Stability of Miao Epics
Luo Dany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Miao epic is very important for Miao people in the history.Scholars ever noticed the Bangx Hxak and Hsongd Hxak existing in Miao epics.However,scholars just described the Bangx Hxak and Hsongd Hxak,few people analyzed the environment,laws and patterns for spread.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Bangx Hxak and Hsongd Hxak in Miao epics and argues that there are variation and stability of Miao epics.
Miao epics;oral tradition;Bangx Hxak and Hsongd Hxak;Variation;Stability
I206.2
A
1673—0429(2011)02—0061—05
2010-12-30
罗丹阳,女,苗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