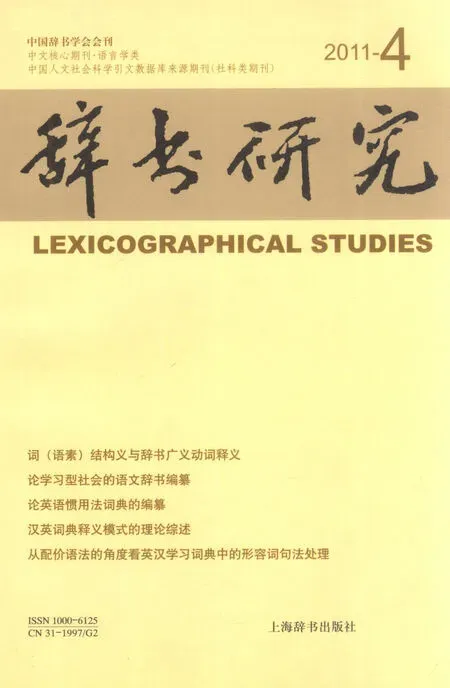从国学研究看中国古代辞典文化*
2011-04-02雍和明
雍和明
(广东商学院 广州 510320)
“国学”作为汉语词汇可以追溯到周代。经过漫长的社会文化演变,“国学”由最初指代国家创办的服务于贵族子弟的学校转变为在当代特指专门的学问。在古代,字书辞典列入“小学”,在国学文献中则归属“经部”。中国第一部百科性质的义类辞典《尔雅》就辑录于《四库全书》“经部”中。《尔雅》本来属于教学参考书,但是,在汉文帝时期被列为教材,到唐代因科举取士而升格为经,自然获得了其在国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在《朱自清讲国学》中,国学大师朱自清将其列为首篇予以说解。这充分说明《说文解字》在朱自清的国学体系构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学术价值。诸如《尔雅》《说文解字》之类的古代字书辞典本身就是国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国学著作(尤其是儒家经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此渗彼透的互动关联。这种关联延绵不断,内涵丰富而又厚重。国学的发展和国学著作的繁荣影响并引领了中国古代字(辞)典编纂,成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产生、发展、传承和兴盛的主要学术动力。
一、古代识字课本是国学之源,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
识字课本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无足轻重,不过是儿童练习识字的教科书,但是,任何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识字课本却是初始人类文明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智力源。它们记录了古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语言符号,承载着人类文明中经久不灭的文化印记。古今中外,任何文明的起源和演进都与这些古代识字课本所发挥的教导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古代识字课本是中华文明和汉语文字至关重要的传承载体,是中国国学最具传播价值的源起,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
语言符号的开启为文献的出现准备了先决条件。中国文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夏代。现存的最早文献是商朝后期殷代帝王占卜时留下的甲骨卜辞。公元前6世纪,孔子依据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等千古不朽的典籍,是中国古代文献的滥觞,也是中国国学文献真正的始祖。而早在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时期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识字课本,对国学文献的出现自然有着催化和推进的作用。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辞典都源自该语言的最古老的识字课本,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关系。Edmund Coote的《英语识字本》(The English Schoole-Maister,1596)、John Palgrave的《法语基础识字本》(Lesclarc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coyse,1530)、Claudius Hollyband的《法语识字本》(The FrencheSchoole-maister,1573)、John Florio的《启蒙识字本》(Firste Fruites,1578)以及William Stepney的《西班牙语识字本》(The Spanish Schoolemaster,1591)都在各自的民族辞典文化中发挥过源头的作用。中国辞典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第一部有文献辑录的蒙童识字课本——《史籀篇》。从周时史官教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到秦统一后李斯撰《仓颉篇》、赵高撰《爰历篇》和胡母敬撰《博学篇》;从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撰《凡将篇》、元帝时史游撰《急就篇》和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到扬雄续《仓颉篇》作《训纂篇》以及东汉贾鲂再续《训纂篇》作《滂喜篇》;从汉儒汇辑古代经书训诂编纂《尔雅》到许慎综括“六书”编成《说文解字》,扬雄博考各地方言、遍采周秦旧籍撰《方言》以及刘熙专用声训撰《释名》,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汉语辞典文化从蒙童识字课本、古代字书到字典辞典的演化轨迹,以及它们与社会文明、文字教育、语言演变、文字改革相互交织、互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整个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汉语辞典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国学是以古代经典著作为根基的,而古代字书辞典主要是为诠释经典文献服务的。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阅读时在字行间或页边注解词语的做法,这种传统一直为后代人所沿袭。世界辞典基本源自古代智者在名篇经典的字行间和页边留下的阅注或释解素材,它们主要是名篇经典中的难词汇集,当然也有为了满足特定时期传经颂教、军事征服等的特别之需而专门编纂的字表或词集,如古代苏美尔语词集。最早期的希腊语词集就是为了解释经典作品,特别是为了解读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用难词而编纂的,通常以在经典文稿中晦涩难懂语词的上方添加解释性翻译或辑词成集的形式出现。印度的辞典编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现存最早的是一部为诠释梵语经典语词而编撰的名为Vaidika Nighatu的梵语词集。可见,早期的字表和词集大多源自古典名篇经文用语注释汇编。
中国古代字(词)书同样源自经典诠释。世界语言只要有使用者就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古代经典文献经历时空的变化使前人的语言成为后人的阅读障碍。《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和《春秋》这五种儒家经书成为当时的法定教科书,解释五经音义成为非常必要和相当严肃的任务。中国人对远古时代文化典籍的注释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已偶尔出现在一种典籍中对另一种典籍的字词句篇的解释,包括对儒家以外诸子著作的注释。系统的注释一般认为源自子夏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萌芽于春秋后期。到了西汉,经学的兴起推动了注释的发展,使其开始成为有组织、有系统的学术活动。西汉末至东汉初,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汉字为主体的考据在经学注释中渐成风气。“训诂”正式成形。经典注释便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训诂注释书和纂集书。古代字书和辞典的某些特征在这种训诂专书中已有显现,所以,对国学经典的训释直接催生了古代的字书和辞典。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一大批释解儒家经典语词的古代字书辞典。如果将儒家经典名目与古代字书辞典做比照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字书辞典基本上是从那些经典名目中汲取语料素材用以对语词进行解释,或者是直接训释那些经典名目的派生作品。有些字书辞典本身就是经典名目,所以到了后期自己也成为被诠解的对象。西汉时期,纂集类训诂成就集中体现在《尔雅》中,到了西汉末至东汉时期,训诂的纂集著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服虔的《通俗文》等可谓是代表之作。光从《尔雅》收录字词的结构情况便可说明古代字书辞典对国学经典的训释功用。作为法定的识字教科书,《尔雅》“共收集各类词语四千三百多个,各种释条二千多个,集中收录并解释那些陌生的古语词和方言词”,“共有十一大(词)类”(赵伯义1997)。这些语词除方言和俗语以外,大多出自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论语》等先秦经典文献。
国学经典中的语词不仅是古代字书辞典训解的对象,国学经典本身也是古代字书辞典引例的主要来源。再以《尔雅》为例。《尔雅》的例证一般都隐含在释义中,大多取材于教育者非常熟悉的先秦典籍,如《诗经》《尸子》《楚辞》《庄子》《列子》《国语》《淮南子》等。《尔雅》单从《诗经》中引用的语句大约就占到全书例证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后代学者能够借助古代字书辞典中所引用的语料来研究早已失传的经典名篇,探求社会历史文化真知的原因。
三、国学是中华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的精髓,古代字书辞典是中华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成果的高度浓缩和集约体现。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人文需求和精神价值成果。国学经典是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核心成果,而主流人文需求引导着这个时代辞典文化的走向,使辞典高度浓缩和集约化地体现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精神价值。
佛教源自印度,东汉时期正式传入中国。当时的佛经翻译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参与,所以,佛经语言从一开始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佛教文化的日渐扩张使之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诘难碰撞和交映融通,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与儒教、道教形成了文化功能分工,即“佛学修心、儒学修身、道学修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完成了经典翻译和向中国传输的任务,并出现佛学经典注疏和学术著述。历史学也摆脱了儒家经学而成为专门学问。到了隋唐时期,实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独自演化的格局,使南北之学统一于经学。唐代科举制度使儒家经典成为文化教导的总纲,又是科举应试的范本。“五经定本”及《经典释文》《五经正义》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参见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2010:161)。它们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唐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经学成果。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国僧人开始注意总结佛教语汇,固化音义,编撰音义辞典,使佛教语汇渐渐走向定型化与汉语化。已知的最早的这类辞书是北齐僧人道慧所编的《一切经音》。继《一切经音》之后,唐玄应编撰了25卷的《一切经音义》,由慧苑增补两卷,再由慧琳历时25年,集唐朝及唐朝之前编纂的所有佛经辞典之大成,汇聚1300余部佛教经典的语词,编成鸿篇巨著《一切经音义》100卷,最后由辽希麟续编出《续一切经音义》10卷。佛教文化和佛经音义辞典编纂的互动是唐代文明的又一显著特点,佛经音义辞典成为佛学文化成果的代表。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宋学以讲求义理和注重实用为主要特征。语言文字是宋元学者阐发义理的最实用、最直接的工具,这不仅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也带动了字书辞典的编纂(参见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2010:163-164)。宋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字书辞典,如王洙、胡宿等的《类编》,戴侗的《六书故》,娄机的《班马字类》,陆佃的《埤雅》等。从辞典史的角度考察,宋代类书中最有影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属于宋学研究背景下的产物,都是宋代精神文化成果的集约体现。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在唐代得到逐步完善,到了宋元时期进行了改革。进入明朝,科举制度进入其鼎盛时期。明朝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制度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规定“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范围,并且指定《四书》以朱熹集注为准绳。“官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之后,学术精神开始以朱学为主流思想,官方儒学由此自经学时代走向理学时代。”(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 2010:242)明代不仅复兴了理学,确立了朱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在中后期推行实学,使其在明末清初达到极盛。实学讲究“真实”,提倡“实用”,主张“实心”,注重国计民生。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从空谈义理转变到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这直接导致汉学的复兴和考据学的兴起。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统治地位,其影响涉及到经学、史学、文献学以及相关的领域,对中国辞典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综而观之,明清是各种思潮融合碰撞的综合时期,也是向近现代文明演进的过渡时期。正因为如此,如果从文明演进的脉络看,明清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进入文明成果的总结期,也是中国古代辞典编纂的总结期。经过官方与私家两股力量的共同努力,明清总结性成果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高峰,其辞典编纂成果尤为辉煌。一般来说,官方的学术活动往往代表并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清朝官方的学术活动主要发生在康乾时期,而编纂辞典是康熙年间官方学术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任何朝代都会有自己的标志性文明成果,辞典是其代表性文化成果之一。盛世修典是中国辞典文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汉魏、唐宋、明清都是中国辞典演进的高峰期。中国辞典的主要类型都源发于汉魏时代,到了唐宋,不仅类型更加齐全,而且结构基本成型,规模逐渐扩充。明清两朝调动大量人力和物力,编纂了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型工具书,规模可以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而且呈现出系列化的势态。出现了像“集字学之大成”(《正字通·自序》)的《正字通》,“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康熙字典·序》)的《康熙字典》,汇辑经传子史的引证于一书的大型训诂辞典《经籍纂诂》,汇释词藻典故的大型辞书《佩文韵府》,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清文鉴》《五体清文鉴》一类双语和多语系列辞典。它们都是集前世成果编纂而成的不朽之作,是中国传统辞典文化的总汇和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的实实在在的体现。
四、国学的衍生演进与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发展是互为促进的,集中反映了辞典与社会、辞典与文化、辞典与文明的互动关联。
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发展与国学的发展和衍生是相辅相成的。国学研究的推进是古代字书辞典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中国辞典文化的源头看,文字教育催生了《史籀篇》《仓颉篇》等儿童识字课本,训诂学的迅速发展衍生了《尔雅》之类的辞典,秦时小篆的流行催生了对其进行整理规范的《说文解字》,魏晋时楷体取代小篆使《玉篇》应运而生。这种字书辞典与文字教育、语言演变、文字改革、社会发展相互交织、互动演进的关系贯穿于古代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学尤其是先秦经典的出现及对其的诠释是中国古代字书辞典发展的原动力,而古代字书辞典的演进又推动了国学的深化发展。
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与国学的这种互动关联不仅在古代汉语字书辞典的演进中得到集中体现,而且在古代外汉和汉外双语辞典的萌发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佛教在西汉末期传入中国,东汉大月氐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中国第一批佛教经典。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到唐开元十八年这664年中,共翻译大小二乘、三藏圣教等释典达2278部。这些佛教释典成为中国国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佛经释典正是源自用梵语写成的佛教经典著作的翻译,如北齐僧人道慧编制的《一切经音》、唐玄应编撰的《一切经音义》25卷、慧琳汇编而成的《一切经音义》100卷和辽希麟续编出的《续一切经音义》。这些辞典不仅弘扬了佛教教义,更丰富了国学文献和国学研究的内涵。佛教传播和译注催生了古代双语辞典,促进了古代汉语辞典的发展。古代佛经释典又为传播佛经教义和规范佛教用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种互动关联在中国辞典史上延续近半个世纪。
古代佛经释典在佛教用语诠释中引用了大量古代经典文献。就拿玄应所著《一切经音义》为例。它不但训释佛典中难字难词的音形义,而且搜采广博,在词目的释文中征引了自秦汉迄唐问世的数十种古籍,其中最多的是字书、韵书、训诂书,其次是经史注释。所引古代字书和语言辞典,除《尔雅》《说文解字》《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玉篇》等少数著作流传至今外,其他大多早已亡佚。仅以卷一所引为例,这类佚著就有《字书》《字林》《字略》《三仓》《字诂》《通俗文》《仓颉篇》《韵集》《三仓解诂》《埤苍》《字苑》《声类》《字统》《尔雅音义》《广仓》等。这些难得的引证为后来学者研究古代辞书和汉语言文字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对促进国学研究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献支撑功能。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萌发和兴起不仅伴随着中国国学演进的脚步,更是反映了与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与中国国学的互为推动和互相关联的演进轨迹。
中国辞典文化历史悠久厚重,曾一度领先于世界辞典编纂和理论研究。从国学研究的高度认识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探寻中国古代辞典文化轨迹、特点和规律,必将有助于突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辞典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辐射西方学界,必将有助于在更大背景中探究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更高层次上领悟和把握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价值,必将有助于丰富国学研究的内涵,大力挖掘、弘扬和开发利用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更加具体地展现东方文明古国的风采。
1.李学勤.中国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2.王淄尘.国学讲话.北京:世界书局,1935.
3.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中国辞典3000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5.赵伯义.论《尔雅》的学术成就.河北师院学报.1997(2).
6.朱自清.朱自清讲国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7.Yong,Heming and Jing Peng.Chinese Lexicography: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