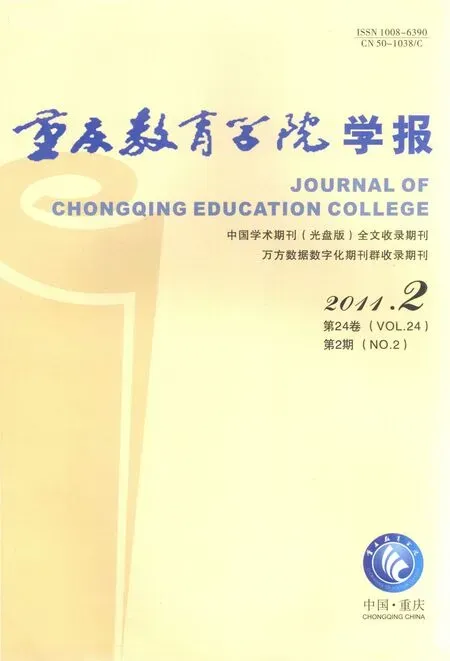渝东南酉水流域方言土语中的某些古音及其区域色彩研究
——以“瓦乡话”、汉语方言、土家语、苗语等为例
2011-04-01白俊奎
白俊奎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
渝东南酉水流域方言土语中的某些古音及其区域色彩研究
——以“瓦乡话”、汉语方言、土家语、苗语等为例
白俊奎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
本文例举“西”[ɕi55](看,看到,仔细看)、“息”[ɕi35](孙之子,泛称子孙后代)、“耶”[ʑe35](父)、[tia55](爹)、间 (房屋计量单位)[kan55]、“龚”[ʨiɔŋ55]、“老革革”[lau51ke214ke214]、 牙桠 [ʑa35ʑa44]、“达搭”[ta35ta55](哥哥)、 颟颟[maŋ55maŋ55](饭)、“满忙”[man51man35](父之弟, 叔叔)、“喷香”[pɔŋ55ɕian55]、“攀臭”[p'aŋ55ʦ'əu214]、“倒”[tau51]、“起”[ʨ'i51]等方言土语的内涵,有些是笔者第一次提出,有些是对前人旧说加以补充。这些方言土语中有古音保存,特别是“瓦乡话”在渝东南酉水流域的保存更显珍贵,其区域色彩愈显浓厚。上述现象的成因是:渝东南在四省边界处,与湘西北、黔东北、鄂西南交界,山川地理相连,水系复杂但互相连通,人文相通,汉语方言或民族语基本相同或相近,这些方言土语有许多古音和有特色的方言口语保存下来,与重庆市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与成都市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与贵州省大方县等地相同或相近,有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的必要。
渝东南;酉水流域;汉语;民族语;方言土语;古音
渝东南是中国著名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这里有乌江、酉水、郁江、阿蓬江等河流纵横交错,哺育着这个地盘上数量庞大的人口和民族。在历史上,这些河流流域生息着许多民族,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产生着较大的影响,现在这里仍然有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在此生产和生活,这里的方言组成成份比较复杂,有古汉语,有土家语,有苗族语等,土家语、苗语是古代巴人、楚人等古族语言的遗留与更新。从如下例证可看出渝东南酉水流域“瓦乡话”、汉语、土家语、苗语等保存了很多古音,有浓厚的区域色彩。
“西”[ɕi55]:在中国,一般人说到“看”这一字眼时,总是当作现代汉语来读音和理解,但在渝东南特别是乡村,人们总有“西”这一字眼的使用与理解,如“等我去‘西’一眼”(让我去看一眼吧)、“我今天在街上‘西’到他了”(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他了)、“请你不要在那里‘西’一‘西’的啊!”(请你不要在那里看一看的啊!)、“你在那里 ‘西’到耸蒙了?”(你在那里看到什么东西了?)“我的眼睛‘西’不倒”(我的眼睛看不见)……渝东南方言“西”与古代汉语“觑”一脉相承,至今仍在广大城乡使用,作为一种古代汉语读音的语言活态,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调”,[tiau35]:基本义项为“看”。渝东南如酉阳、秀山等地特别是酉水流域有一个特殊的方言语音[tiau35],这一方言词的语音很特别,有特殊含义:“看,仔细看,偷窥,侦察”等等,义项很多,与另一方言语音[ʨ'uɔ51]一样都有“偷窥”、“悄悄地看”、“侦察”等义项,这些方言语音在重庆市主城区及附近地区、成都市主城区及附近地区、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川东北、川北等地都有相应的使用群体。
“息”[ɕi35]:渝东南很多地方如酉水流域保存着一些古代汉语的词汇,如“息”在渝东南特别是酉水流域酉阳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乡都有“孙孙息息”的说法,意为“孙子和孙子的子孙后代”,在渝东南许多地方如酉水流域酉阳、秀山等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广大地方的碑刻中往往这样进行书写:“孝男:……,孝孙:……,曾孙:……玄孙:……,重孙:……”酉阳、秀山人迁移到与紧邻的贵州省思南县土家族苗族地区后则在家族仙盒(神龛)写上:“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辈、子、孙”辈的姓名。“息”,相当于家族墓碑上的 “曾孙”,“玄孙”、“重孙”也归于“息”之行列。在这些的民众口头语言中,儿、孙、息,三者界限分明,指称清楚。息,是“孙的儿子”,“息”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重孙,也统称为“息”,这就相当于泛称了。那些受过一些教育或见闻稍多的人,能准确地知道或说出“曾孙、玄孙、重孙”之类的称呼。没有受过教育、见闻狭窄、孤陋寡闻者,很难知道或无法知道、很难说出或无法说出这些称谓,这些人有时即使知道一些或能说出一些,也是不全面的或者自己内心也不知道其准确的含义。在亲属称谓中,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太祖父,在书面语中界限分明,指称不模糊,但在渝东南亲属称谓的口头语当中,父亲、公(祖父)、祖(曾祖父)、太(高祖父)、祖太(高祖父的父亲)、老祖太(高祖父的爷爷),有时指称清楚,但很多时候也可能指称并不清楚,自“太(高祖父)”开始,一律统称“太”或“老太”。“息”既有准确无误、界限分明、毫不模糊的指称对象,如果从另外的角度(主要是再往“孙的孙”及其更靠后的世系)来讲,也有相对模糊的内容与含义。在群众的口头语中,无法准确地给出太多的称谓。民间传统有“五福”的说法与心理习惯,出了“五福”或五个世代(五辈人)就不怎么重视了。在亲属称谓和态度疏远或亲密程度等方面有许多相应的表现,在此不加以展开进行阐述。“息”在此充当特殊的角色,有特殊含义。毛远明先生认为:“息:本义是呼吸,引申为生息,再引申,则泛指儿女。”[1]笔者由此再引申为“子孙后代”。如此,渝东南、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至今流行的方言“孙孙息息”,意思当为“孙孙及孙孙的子孙后代”, 其例证是 《诗经》、《仪礼》、《三国志》、《魏书》、《北魏墓志》、《太平广记》、《括异志》、 宋代史料、《元史》等历史材料,反复研究、辗转论证“息”作为纵向发展的文字,发展历程复杂,其读音应当归属于古代汉语书面语,其使用频率高,使用范围大,由此可见一斑!
“老革革”[lau51ke214ke214]是专有名称,巴蜀大地、湖南省、湖北省、贵州省等地都在平时口语交际中广泛地使用,西南大学毛远明先生认为“老革革”是“老革”后一个语素的重叠,重叠后表示强调意义与描绘色彩,是形容词,用来描绘人,表示人年纪大,用来描绘植物,表示植物不嫩,不茂盛,可作定语,如“老革革的芹菜咬不动”,可作谓语,后面要加助词“的”,毛远明教授还列举“麻革革”[ma35ke51ke51]、“粗革革”[2]等例证加以论述,“粗革革”[ma55ke51ke51]、“青革革”[ʨin55ke51ke51]等在巴蜀大地城乡特别是乡村使用的范围很广,是区域色彩浓厚的方言土语。
“喷香”[pɔŋ55cian55]、“攀臭”[p'aŋ55ʦ'əu214] 毛远明教授在同一文章中列举出大量的生动活泼的例证,有说服力。这是至今渝东南仍在使用的方言。
“倒”[tau51]、“起”[ʨ'i51]。渝东南方言“倒”、“起”连用,产生许多不同含义如“你走倒起”,意为“你先走吧”;你吃倒起,意为“你先吃吧”;我拿倒起了,意为“我拿到手了”;你拿倒起,意为“你拿着吧”;我拿倒起了,意为“我已拿到手了”……这与重庆市、成都市方言相同或相近,喻遂生教授认为[3]:重庆话用在谓词后的“□倒”[tau51]和“起”[tau51]是两个口语常用字。……重庆话谓词后的“倒”和“起”可以表示动作、性状处于某种状态或动作正在进行,也可表示动作的完成和趋向,或动作、性状的延续。本文把这些不同的“倒”和“起”分别记作“倒 _1,倒 _2,倒 _3”和“起 _1,起 _2,起 _3”。“起”还可连接述语和补语,本文将其记作 “起_4”。……文章中列举大量语例,说服力强。李蓝1996年[4]、1998 年[5]先后撰文论述贵州省大方县“倒”和“起”的用法,笔者比较发现:它们与重庆、成都、渝东南等地“倒”和“起”的用法、含义基本相同或相近。李蓝把“倒”和“起”与江西省南昌话进行比较,发现它们的用法和含义基本相同,而贵州省毕节、遵义等地很多居民普遍强调(口头传说、族谱及碑刻)其祖先来自于江西省,可知历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方言上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耶”[ʑe35]: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有“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句,杜甫《兵车行》有“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结合上下文理解,“阿耶”意为“阿爸”。至今渝东南酉水流域群众还把“父亲”称为“耶耶”[ʑe35ʑe55]。一般来说,至今在渝东南酉水流域城乡“耶耶”[ʑe35ʑe55]这一称呼与“父亲”这一含义还紧紧相扣。在文化程度较高单位的人群中,许多人有意识到放弃方言土语的影响,向现代汉语普通话靠拢,这些“企业、事业单位”等享受国家工资等,被人们称为“正规化的单位”,有正规、稳定的职业和待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特别注意亲属称谓的现代读音,逐渐放弃古音古义、土音土义,理解成现代汉语“爷爷”的含义。但作为一种区域方言,更多的人们(甚至是那些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生活和工作在县城的为数不少的现代知识分子都更愿意、更自觉自愿地把“耶耶”含义当作“父亲”来理解和接受,是他们世代相传的古老称谓,有朴素而坚实的伦理道德特质,是与血缘紧密联系、扎根于心灵深处的古老精神信仰)愿把 “耶耶”[ʑe35ʑe55]当作“父亲”来理解和接受。一些学者如西南大学文献研究所何山认为“耶耶”的“爷爷”含义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在魏晋南北朝民歌中,在诗圣杜甫诗歌中,“耶”、“耶娘”的含义都是“父亲”、“父母亲”,这中间的连贯性、连续性、不可分割性、意思紧密性、继承性等脉络分明,是主流,在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或碑石中“耶”有“爷爷”的含义,缺乏代表性,没有典型性,不是当时汉语方言或书面语的主流。不能以此就推断“耶耶”在魏晋南北朝时就以“爷爷”为主要含义、主要表达功能。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主体当以平民百姓为最主要,贵族阶层、文化界的语用也应当加以留心。何山认为[6]:“爷”字原写作“耶”或“邪”,《篇海类编·人物类·父部》:“爷, 俗呼父为爷。通作耶。”最早用于父称,故在“耶”的字形上加“父”,造出“爺”字,后简化作“爷”。称父亲为“耶”或“爷”在明代已很普遍,题(明)宋濂撰;(明)屠隆订正,《篇海类编·人物类·父部》的材料当是出自明代宋濂和屠隆正,笔者认为,这一含义的词语出现时间应早于书面语,更早于碑刻语,称呼父亲为“耶耶”当是在宋濂、屠隆正前。
中古汉语读音、土家语读音与称呼在渝东南地名中有遗留,如秀山县“石耶”[şi35ʑe51]是古代长期在此定居的古代巴人语言的遗留,意为 “拿长刀打猎的地方”。[ʑa35ʑa44]含义为“父亲”,与称“父”为“耶”基本相同。“爹”[tia55]与“瓦乡话”读音相同,“瓦乡话”是中古汉语读音的遗留,至今渝东南称“爹”为“[tia55]是汉语古音的遗留。笔者在渝东南酉阳县后溪镇茶园村发现周姓群众称“爷爷”为[tia55tia55],与紧邻的其它姓氏大多数民众称“爹”为[tia55]不同,这是语言使用中的异化。
“达搭”:[ta35ta55]。渝东南酉水流域称呼“哥哥”为“达搭”,是渝鄂湘黔交界处广大群众长期以来使用的方言古音的遗留,土家族语称呼“兄长”为“阿可”,称呼“弟弟”为“阿波”,苗族语称呼“哥哥”为“阿那”,其它语种无此类含义与用途。“搭答”[ta35ta55]广泛地使用于汉族中,是古老汉语的一种,在其它语种间找不出构词理据,找不出其它使用义项、场合和价值。
“间”[kaŋ55]和“龚”[ʨiɔŋ55]。间”[kaŋ55]:古代汉语读音[kaŋ55],现代汉语读音“间”[ʨian55],其古代汉语读音至今仍保存在渝东南等地,五“间”[kan55]房子,与广东等省保留近古乃至中古汉语读音相同,李白《朝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以现代汉语读音来读,不押韵,但在李白所处的唐代,“间”读音[kan55],其诗押韵,符合语言实际。至今渝东南读“大江溪”、“小江溪”为“大干溪”、“小干溪”,读“豇豆”为“干豆”等,都是古音保留。“龚”[ʨiɔŋ55],渝东南方言读音为[ʨiɔŋ55],渝东南人把“弓”([kɔŋ55])读为[ʨiɔŋ55]。弓,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 gōng、国际音标[kŋ55],渝东南读音 jiōng、国际音标[ʨɔŋ55]等都是对古音的保留。“间”[kaŋ55]、“龚”[ʨiɔŋ55]体现了古代汉语声母分化情况,j、q、x、g、k、h的关系获得更多证据,为古代汉语演变提供了活生生的事例,是语言学实证材料,很珍贵。
“满”[mɔŋ214],意为“东西‘装满’”,与湘西北、渝东南“瓦乡话”读音相同,是汉语方言古音的保留,渝东南酉水流域很多民族的祖先都来自湖广省辰州府沅陵县,沅陵是“瓦乡话”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根源地,至今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等地大量“瓦乡话”都与沅陵“瓦乡话”有渊源关系。
“等”[teŋ51]: 渝东南广大城乡至今仍然在使用的“等”,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当中是“谦让”的意思,表示客气和委婉,用于表示谦和的祈使句中,语气较平和;有时有命令、祈使之意,用于祈使句中,语气较生硬。“等”[teŋ51]另一层含义是“听之任之”,语气生硬。
“搞”[kau51]含义有“打、杀、害、做、获取、得到、赠送”等,感情色彩有褒、贬、中性,使用范围较宽,不分阶层和职业都可使用,粗鲁色彩更多一些,随意性较强一些,在知识分子中使用机率低得多,“搞”的读音及用法在渝东南、湘西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乃至四川省广大城乡都是这样。
渝东南酉水流域还保存着另外一些古音,如:我:ŋɔ51。傲:ŋaɔ214。矮:ŋai51。爱:ŋai214。岩:ŋai35。按 :ŋan214。晏:ŋan214。安:ŋan55。爪:ʦua51。硬:ŋen214。停:t'en35。盐:yin35。仰 :ʑan51。 拈 :ʑ'ian55。 面 :min214。(饭 )“满 满 ”[maŋ55maŋ55]:吃“饭”为吃“满满”[ʦ'i35maŋ55maŋ55],秀山县苗族语称“吃饭”为[nɔŋ51li51],“瓦乡话”称“吃饭”为[rəu214mɔŋ55],今天渝东南酉水流域称“吃饭”为[tşi35maŋ55maŋ55],是“瓦乡话”的遗留与演化,“瓦乡话”是中古汉语的遗留,渝东南至今称 “吃饭”为[maŋ55maŋ55],是古代汉语音的遗留。“抬”[t'ai35]:含义为“拿”,也是古代汉语意义的衍伸。
“奶娘”[nai55'ʑiaŋ35]:含义为“妈妈”。渝东南“瓦乡话”称“奶奶”为[ai55'ʑiɔŋ55],可与互相映证。“奶耶”[nai55ʑe35]:含义为“父亲”,可与前述“耶”的用法与含义互相映证,也说明 “奶娘”[nai55ʑ'iaŋ35] 与 “奶耶”[nai55ʑe35]中的[nai55]是词根,含义是“父辈”或“长辈”,有“生身”和“哺育”等渊源关系。“满忙”[maŋ51man23]:含义为“叔叔”。“满娘”[maŋ51ʑ'iaŋ34]:含义为“婶娘”。“娘”[ʑ'iaŋ35]:含义为“母亲”。“孃孃”[ʑ'iaŋ55ʑ'iaŋ44]:含义为“姑妈”或“婶娘”。“年”[ʑ'ian35]:含义即为“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吃”[tşi35]:在湘西北、渝东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乃至四川省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至今还有很多人把“吃”读成“骑”[ʨ'i35]。[ʦ'i35]与[ʨ'i35]一音之转,z、j的演化可见一班,它们的韵母没有变化,它们的声母[ʦ][ʨ]在读音清浊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能准确理解和接受。把“盐巴”读成“银巴”[ʑin35ba55],把“黄苞谷子”读成“完保谷子”[waŋ35bau55ku35ʦi51],把“风”读成“丰”[hŋ],把“自己”读成“共人”[kɔŋ35ren35],也是古音“各人”[kuɔ35ren35]的遗留。
以上若干字的古音及区域色彩十分浓厚,至今在湘渝等地特别是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自然经济较多、外出人口相对较少的边远地区使用较多,与湘西北、渝东南酉水流域的“瓦乡话”及广东客家话都大量地保留着古音,使用范围较大,使用频率较高,“瓦乡话”和广东客家话是区域特色浓厚的汉语方言,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读音,是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古代汉语读音的遗留,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不同,在语调上有明显的区别,这是不同地区同一语言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步伐不同造成的,是语言文化领域里的现象。当今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的土家族和苗族、汉族、侗族等很多民族民间传说、家族谱和地方史资料记载都说他们的祖先都由江西省等地迁移来,此前,他们的祖先是从江淮闽浙一带迁移来,当今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黔东北的汉语方言读音渊源当与华东地区和江淮地区有联系,而江淮通语来源于更古的中国古代中原及陕西、甘肃、山西等地,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后溪镇(如田、彭、白三大姓)、兴隆镇(如李姓、梁姓)、酉酬镇(如赵姓、张姓、田姓、杨姓等)、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石堤镇等地的土家语、苗语、口语、碑刻等的记载相似,这是其文化价值之所在。
[1]毛远明.字词考释两篇从“息”、“媳”二字看形旁类化对词义的影响[J].中国语文,2006,(4):377-379.
[2]毛远明.四川方言词语杂释——兼及方言词语的文学记录[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2):72-75.
[3]喻遂生.重庆方言的“倒”和“起”[J].方言,1990,(3).
[4]李蓝.大方话中的“倒”和“起”[J].毕节师专学报,1996,(4):44-52.
[5]李蓝.贵州大方话中的“倒”和“起”[J].中国语文,1998,(2):113-122.
[6]何山.词语札记两题[J].中国语文,2009,(5):474.
[责任编辑 于 湘]
Research on some ancient accents and their regional colors of the local dialects in the Youshui River basin of Southeast Chongqing——with“Waxiang dialect”,Chinese dialects,Tujia Dialect and Miao Dialect as examples
BAI Jun-kui
(Literature and News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ongqing 400067, China)
This paper lists the connotations of some local words such as “西”[ɕi55](look, look carefully), “息”[ɕi35] (grandchildren’s children, general reference for future generations),“耶”[ʑe35](father),爹[tia55](dad),“间”[kan55](unit of house measure),“龚”[ʨiɔŋ55],“老革革”[lau51ke214ke214],牙桠[ʑa35ʑa44],“达搭”[ta35ta55](elder brother),颟颟[maŋ55maŋ55] (eat), “满忙”[man51man35] (father’s younger brother, uncle),“喷香”[pɔŋ55cian55],“攀臭”[p'aŋ55ʦ'əu214],“倒”[tau51],“起”[ʨ'i51], etc.Some of the connota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by us, while some are supplementary to the old expressions of our ancestors.These local dialects preserve some old accents.The preservation of“Waxiang Dialect” in the Youshui River basin of Southeast Chongqing is especially precious for its stronger regional color.The causes of these phenomena are that Southeast Chonqing is bounded on the northwest of Hunan, northeast of Guizhou and southwest of Hubei with mountains and rivers connected, water systems complicated but interlinked, and people and culture often interacting.The Chinese and ethnic dialects in these areas are similar or almost the same.These dialects have preserved many ancient accents and typical oral expressions which are similar to or the same as those of Chongqing proper and its surroundings, Chengdu proper and its surroundings and Dafang County of Guizhou.It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outheast Chongqing; Youshui basin; Chinese language; ethnic dialect; local dialect; ancient accent
H01
A
1008-6390(2011)02-0082-04
2010-11-18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酉水流域“瓦乡话”的调查研究与抢救保护》,项目批准号(编号):10SKH07。项目主持人:白俊奎;项目成员:毛远明、钟维克、陈碧娥、万卫卿等。
白俊奎(1969-),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南大学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巴渝古代文化与文学、民间文学和语言学(汉语词汇与土家语、苗语和“瓦乡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