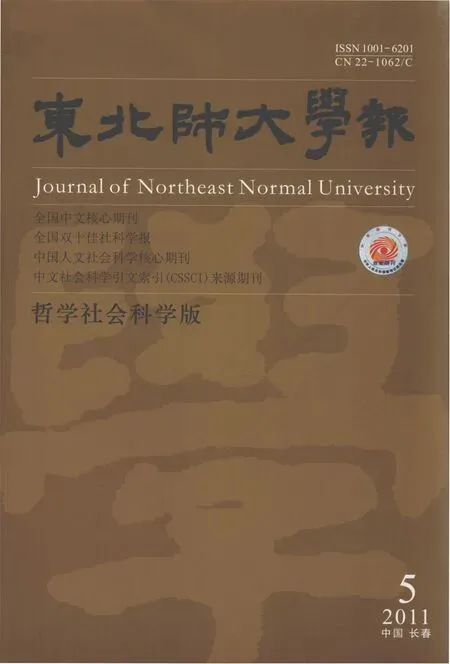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11-03-31王晓梦
王晓梦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王晓梦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现代文学;闺秀派;自由解放;诗意伤感
在“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女作家。她们多是出身于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的名媛闺秀,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文风清秀婉约,文字工整细腻,字里行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风范。鉴于她们名门大家的出身、高等教育的学历和独特的古典审美情怀,因而我们将这一女作家群体称之为闺秀派作家。所谓“闺秀”,原为长久以来中国古典文学中书写风格的一种类别,自唐诗宋词以来,成为雅正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本文所论之“闺秀”文学,将其范围再缩小一些,以出自李清照、朱淑贞等人之手的有深厚文学素养为基础,表现怨而不悱、哀而不伤、含蓄渊雅传统的诗文,作为民初以来闺秀派作家白话创作的精神与风格的源头,并将冰心、苏雪林、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陆晶清等作家作为传承和发展这一文学类别的翘楚典型。她们在具体创作中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张扬,不能一概而论,但鉴于她们在创作中的较多相近之处以及她们的亲密朋友圈子,所以将她们集合在一起,划为“五四”时期的相对统一的闺秀派作家群体。本文力图从整体上把握闺秀派作家的形成氛围、创作指向、创作风格、审美情怀,进一步挖掘她们在艺术上的相互密切关联,以此来丰富我们对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认识和理解。
一、兼具传统文化与欧风西雨的背景
闺秀派作家在家庭背景方面较为相似,大都出身于官宦或文学世家。富裕优越的家境使得她们可以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传统教育,这也是她们能够成为第一批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进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女性作家的首要原因,是“五四”时期闺秀派作家的一大优势。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她们在知书达理的同时,重视人的感情,注重自身的修养及其内涵;而在高等学府中深造的过程中,她们又受到了西方先进文化思潮的洗礼,在接受西方新思想的启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思想对人尤其是对女人的束缚和压制,作为新一代的女性她们不应甘心躲在家庭这小小的庭院里,应该积极争取为人的自由,实现自我的价值,为新时代的到来积极献上自己的力量。可以说,她们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经受了现代文化的浸染,这使她们获得了现代性的知识和人生观念。现代文化激活了她们身上本来就有的传统文化的情愫,在不同文化的对接中建构了现代闺秀型的女性文化人格。所以说传统文化与欧风西雨的文化对接构成了“闺秀派”这一别具风采的作家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
与新文学第一代男性作家现代意识的产生更多地受益于留学海外的教育背景不同,绝大多数闺秀派作家的思想观念、文化心态乃至审美方式的现代性变迁都是在当时并不成熟的国内女子高等教育的文化语境中完成的。例如冰心曾在燕京大学就读;苏雪林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等都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而且她们所学的科系也几乎全是中文系,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多半学养深厚富有诗词根底。由于这个原因她们也都参加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研究会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一个专门由女性成员组成的文艺社团,社团的组建对于闺秀派作家群的形成意义重大。在女高师读书期间,石评梅、冯沅君、苏雪林、庐隐、陆晶清等结为至交。在“五四”高潮的岁月里,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1]。深厚的友谊,彼此的欣赏,是她们在创作中产生共鸣,进而走到一起的重要机缘。另外,她们当中大部分又从事过教师职业,像庐隐在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安徽宣城中学、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等几所学校任教,苏雪林更是勤恳执教五十余年,是位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这一点对整个流派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闺秀派作家从传统的家庭教育中走出来,她们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仍恪守着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在她们身上保留着传统女性的端庄典雅、温和多情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不满足女红,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甚至走出国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沐浴,带上了现代女性冲出家庭后的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2],这一切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创作集体的形成。
二、女性自由解放与“道济天下”的追求
同为一个流派的作家并不意味着大家的创作思想完全一致,闺秀派作家群因其各自独特的女性意识影响更是如此。尽管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影响下,她们的创作仍整体上体现出了一种共同的创作追求:拿起笔来庆贺自己的新生,表达和实现作为女性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探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在“五四”运动大潮中,女性解放的第一步就是要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由婚恋。从闺秀派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女性争取自由爱情的激情呐喊,看到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新女性故事。比如石评梅的两篇小说《匹马嘶风录》和《偶然来临的贵妇人》,主要探讨了女子冲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后的出路,前者表现的是献身革命的女英雄,后者刻画的是过着纸醉金迷放荡生活的所谓“贵妇人”形象。凌叔华的小说《春天》、《花之寺》等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的描摹,也深深烙有女性意识的萌动与觉醒的痕迹。《春天》这部小说让人深思的并非在于霄音的行动是否成功,而在于作为一个人的而不仅仅是女人的正常情感的独立表露,在于她内心沉睡的独立意识的萌动。尽管结婚即意味着失去爱别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去信安慰一下生命垂危的友人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已婚女性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情感天地和人性自由权利。在这篇小说的叙说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体会到了“女人也应该是人,而且应该是自主的人”[3]的深情呼唤。陈衡哲的《鸟》,则传达出了挣脱千丝万缕的封建桎梏对女性个体的挤压、追寻心灵自由的呼唤。对于一个被封建家庭重重束缚下的女性,为了能“做一个自由的飞鸟”,“在自由的空气”展翅翱翔,“不管他天西地东,也不管他恶雨狂风”,勇敢地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在这鸟儿身上,寄托着现代女性的未来理想,跃动着觉醒的一代女性对自由与解放的渴望。
但是在“五四”落潮以后,闺秀女作家们的生活和理想出现了激烈的动荡。因为她们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数人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已觉醒,已经走在追求解放与自由的路途中,但黑暗的重压又使她们手足无措,表现出了梦醒了又无路可以走的徘徊。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她们笔下的女性命运就出现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反映女性苦闷、彷徨的“时代病”,以庐隐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庐隐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大都深深刻着“五四”时代的烙印,她们所热情追求的人生理想与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其理想幻灭,而这幻灭便形成了她们空虚、厌世的病态心理。庐隐恰是用她哀伤的笔调叙写了她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反映“五四”时期一部分知识女性的时代苦闷,尤其表现了她们热情地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困惑。二是继续表现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同时,表现出肩负社会“道济天下”追求。庐隐的小说总是在悲哀中寻求着人生的本质,她从自我的人生际遇出发,去关注身边的人生悲剧,因此庐隐的“问题小说”都表现出如她所说的以她所能扩大的悲观的范围,为一切不幸者同情:如被封建礼教扼杀了爱情的青年男女(《月夜里的箫声》);被洪水夺去家园的乡民(《水灾》);被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断送了生命的农家少女(《一封信》);处于烽火连天的军阀混战之中的无辜百姓(《王阿大之死》)等等;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以男女青年的爱情为题材,塑造了一个向封建婚姻制度大胆挑战的“新女性”形象,为知识女性继续争取“个性解放”树立了精神榜样。冰心则公开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是要感化社会,所以她试图在小说中借她所极力描写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去开列治疗社会症结的方剂。她的“问题小说”也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关注社会问题,如爱国青年与封建家庭的矛盾所映射出的父与子之间的思想冲突(《斯人独憔悴》);空怀报国之心的青年由于失望而远走异邦的人才闲置的问题(《去国》)等等。陈衡哲的《波儿》、《老夫妻》等作品则从东方伦理观念出发,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个体的人孤独命运等问题。而石评梅剧本——《这是谁的罪?》描写一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派”恋人,由于封建家庭的粗暴干涉被迫分手,酿成一幕社会惨剧。当即有人撰文指出,作者的用意“是要编问题剧”,“罪在其父,罪在社会习惯”[4]。这类反映民生疾苦、质询社会时弊、呈现黑暗现实的“问题小说”,表明了闺秀派作家的创作视野并不再只是关注女性的徘徊自怜的深闺情怨和庭院深处的身边琐事,而是有着感时忧国的社会责任和鲜明的时代气息。从女性解放与自由的追求进而反映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表征警世济世的写作意图,确实是闺秀派作家早期创作的共同心愿和思想宗旨。
闺秀派作家常常借描述人物心理在作品中展开大段的人生哲理讨论,造成“五四”女性文学普遍的议论化、抒情化倾向。如庐隐的《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便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大量抒写生命不自由的形而上感受,充分证明了中国女性在受封建男权压抑数千年后已经渐渐苏醒,并初步获得了独立的主体人格,能够以人的自觉来审视自身存在[5]。但另一方面,初步觉醒时期的青春稚嫩往往又限制了“五四”女作家的理性思辨力度,使她们和笔下的人物普遍都无法将充满灵性的生命感悟当作理性思辨的起点,由此出发建构起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由于她们的富家出身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她们的视野始终未能完全打开,无论在正视绝望的深度上,还是在反抗绝望的力度上,均没能达到鲁迅等作家的理性高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终有欠缺。
三、诗意与感伤的古典审美情怀
闺秀派作家个个才华横溢,拥有各自独特鲜明的个性气质,但受到时代的召唤,新思潮的洗礼,她们在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地追求着相同或相似的目标,因而作品中也就透露出她们相同或相似的审美风范。她们在审美意识上较之古代女性发生了较大变化,古代女性那种凄凄惨惨的哀吟已经被时代的放歌所代替,风花雪月、绿肥红瘦式的诗句也被富有时代性的个性解放、大胆的爱情宣言所代替。但是,就女性创作的审美风格而言,闺秀派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古代女性作家的精神血脉。无论是创作立意,还是风格呈现,都极力表现着一种古典的诗意美和感伤美。
(一)对诗意氛围的营造
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传统以“诗言志”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审美功能,但又因为诗的“思无邪”,所以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缘情而绮靡”。由之,“诗文并茂”中国的文学传统至“五四”前,不论是诗的抒情与言志,还是散文的抒情与言志,其在审美上一直都是重抒情的。“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虽以小说这一叙事文体为主,但因为她们接受教育的环境对她们文风的深刻影响而继续秉承这一传统,情为行文,以事记情。而传统诗文中对情感的含蓄抒写,也使她们在叙写的过程中少了炽热的倾泻。含蓄节制使这一派女作家的作品更见风致。冯沅君的作品以表现男女情爱最为大胆而著称,但那些细腻的情感也只是停留在如她的《旅行》中所写到的“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的节制。庐隐在作品中描写的自然风物,除了能铺叙环境衬托氛围,还兼具以景物设喻比兴的妙用。石评梅《只有梅花知此恨》的结尾则用盛开的红梅来烘托灼热的爱情,用“秋野荒冢一样的沉寂”来象征爱情的被扼杀。她们以清隽文笔赋以自己的作品朦胧的色彩和象征的诗情。这种诗意的人生思考方式,带给我们真切的心灵触动,也能感受到这一时期女性作品特有的诗意氛围。
与西方美学因其叙事文学传统的重写实不同,中国美学则因诗与散文的抒情文学传统而重写意。古代文论者在品评作品时,常常用意境的有无作为文章高下的标准,而闺秀派作家在创作时,也自觉地吸取了古典文学中常用的融情入景的笔法,注意作品优美意境的营设。如石评梅《红鬃马》中,“我”异乡求学八年后回家时的感想:“黄昏的灯光虽然还燃着,但是酒杯里的酒空了,梦中的人去了,战云依然飞扬着,奔忙的依然奔忙,徘徊的依然徘徊,我忽然踯躅于崎岖荆棘的天地中,感到了倦旅。”行文间有古典诗词的青灯孤影、滴酒成愁的人在天涯之感,“灯光”、“酒”“战云”等古典意象作为情的载体,情中见景,虚实相生,艺术境界较为幽深。同样地以婉约文风凝铸其文的意境营设也常常呈现在陈衡哲、冰心、庐隐、凌叔华的笔下。闺秀女作家笔下那些以婉约之笔所叙之事也许并不具有抵达社会内在本质的深度,所写情节也许并未达到古典传奇小说的曲折跌宕,但字里行间所营设的包容这些故事与情节的“境”却无不动人心扉。
闺秀派作家对诗意氛围的营造不仅体现在她们的抒情记事上,也充分表现在她们诗化的语言文字上。冰心雅丽清新的文字,是她对于古典文学深厚功底的映现,其他女作家的叙事语言也同样或典雅而自由,或有白描而秀丽。如凌叔华《酒后》中“那穴里有几百株芙蓉,此时开得正盛。芙蓉林里有一张石床,床的四周栽着菊花和秋海棠,床上却厚厚的铺了一层丹桂花”的素雅,如陈衡哲《西风》中描绘装扮“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素;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的秾丽;如石评梅《白云庵》“廿余年中我像怒潮狂飙,任忧愁腐蚀,任心灵燃烧,到如今灵焰成灰烬,热血化白云,我觉已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和人间一切的愿望事业都撒手告别”的浓郁。这些闺秀女作家们的诗情弥漫的语言,充溢着古典意韵隽永意味。庐隐算是“五四”时期风格较为朴直、健劲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却受到古典诗词的深刻影响,也充满了诗意的文字。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女主人公手握一卷诗词,漫步低吟,从中寻找些情感慰藉的情形。陆晶清散文的意境美不仅在于将情感融入其中,也表现在她刻意化用古典诗歌的语言意象,特别是在描写自然田园景色时,很有些古代诗歌风格,借助诗中的语言勾勒出新鲜动人的艺术情境。[6]
(二)对感伤情怀的独到体现
阅读闺秀派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始终渗透着或浓或淡的感伤色调。这种浓厚的感伤色调的产生,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同时还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五四”之后,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文化的激荡流变,使她们深感失望吞噬着她们奋斗的热情,悲哀咬啮着她们脆弱的心灵。加之个人感情生活所受时代的影响,闺秀女作家在她们的许多作品中悲叹人生之不幸、倾诉内心的失意。石评梅的散文随处可见的是“夜幕下是何等的寂寞萧森啊!幢幢的黑影,伴着那荒冢里的孤魂。”(《京汉途中的残痕》)字里行间透出“花下映出我影儿的彷徨,黯淡的月光,照出我心中的凄凉。”(《残夜的雨声》)于是其散文总是透出凄清、冷寂的意境。社会与人生的矛盾,使她有着强烈的悲观思想,除了顾影自怜,长吁短叹之外,她只能在作品中任意泼染着灰黯的颜料,低回吟叹着哀伤的词曲,为自己凄惨的命运吟唱永无休止的挽歌[7]。陆晶清散文始终浸透着一股淡淡的伤感和哀愁,悲凄的身世是她永远无法走出的阴影,尽管在现实中她不断地革命、奋斗,可这一切多以失败而告终,在深深的迷惘里,她更加哀怜自己的不幸,因此伤感成了她散文的主要情愫。在她看来,“人生就是一束大梦!一个一个的惊醒,就是一个一个的抽去,在梦中忌说是—梦境。我们且自骗着混下去吧!”其中透着的悲凉是没有经历过不幸的人们难以体味的。庐隐的感伤,是悲凉哀伤的,笼罩着梦幻般温柔缠绵的浪漫色彩,好像郁积着数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沉重压抑感。庐隐笔下没有追求者与旧势力正面冲突的激烈场面,然而人们分明处处感到那“看不见”的历史因袭是怎样如梦魇般左右她们的命运,使这些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不住地低泣徘徊,甚至觉得“那一天我住到深山穷崖时,便是被赦的日子。”(《云鸥情书集》)这种隐伏的压抑更显示出作家的悲凉。凌叔华的名篇《绣枕》写的是爱情悲剧,细细读来,没有气壮山河的慷慨之情,没有义愤填膺的悲歌之调,没有痛不欲生却于平静中隐藏着悲凉,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愁滋味,让人不由得悲从中来。作品是作家心灵的反映,透过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凌叔华对于那个年代爱的无奈伤感。正由于女性的细腻、柔情、多感,加之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所赋予的压力构成的女性压抑,所以在她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埋藏于心灵深处抒情性背后的伤感和悲凉。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闺秀派作家,作为登上中国新文学文坛的第一代女性作家,作为中国女性文坛的翘楚典型,她们的贡献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在“五四”新文学的恩泽和滋润下,时代和个人的悲情,触动和震撼着她们女性易感的心灵,切身的对于战乱的感受,加上成熟的艺术表现力,使她们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的各种领域上展示大时代的主题,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她们一方面秉承了中国古代“闺秀”文学的含蓄典雅,给“五四”文坛带来了唯美的温馨、古典的回味;一方面又开创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先河,带来了清新向上的风气,为中国文学的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可以这样说,她们的作品以古典韵致传递并融入现代探寻,架构了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既有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承继,同时也是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丰富。她们对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的女性生存境况做了深刻的思索和质询,努力摆脱对男权的依附,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进行着独立的创作,为第二代、第三代女作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石评梅.石评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8.
[2]冰心.从“五四”到“四五”[A].冰心文集:第七卷[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9.
[3]陈学勇.论凌叔华小说创作[J].中国文化研究,2000(3):78.
[4]钱虹.黎明时分的三支响箭——论“五四”女作家的杂文、新诗和“问题小说”[J].学术研究,1999(10):37.
[5]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研究[J].文学评论,1998(1):52.
[6]吴丽亚.陆晶清早期散文浅析[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12):41.
[7]农迎春.独特的艺术追究——评石评梅的创作[J].河池师专学报,2001(1):79.
On the Feminist Writer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China
WANG Xiao-m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Media,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 255049,China)
In the 1920sand 1930sin China there was impressive literary emergence of a group of women writers.They retained a dignified and graceful womanho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times made them accept the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which brought them liberation,the modern female charact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e thinking.The impacts of two educational ideas from East and West con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of independent groups of feminist writers.
modern literature;feminist writers;freedom and liberation;sad poetry
I206.6
A
1001-6201(2011)05-0129-04
2011-03-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W050)
王晓梦(1969-),男,河南南召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