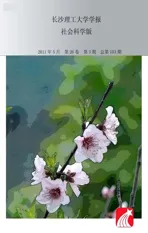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2011-03-31伍明春
伍明春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一、引言
中国新诗进入1930年代后期,“现实”与“现代”之间的龃龉越来越深,对于现代诗歌艺术的种种探索与实验被日渐排拒在主流之外。1920年代后期以来由梁宗岱、戴望舒、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发起和初步发展的汉语诗歌的现代性建构从此被局限在一个不断缩小的范围之内。诚然,在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这样一个内乱与外患交困的特殊时代,诗人以他们的创作介入现实是无可厚非的。这既与诗人们内心的责任感相关,也和中国社会的特点分不开:“中国社会不允许这种诗脱离社会的‘纯化’。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诗只能不纯化。因为社会从来要求诗为它分担忧患与追求。传统儒家的入世诗观也潜入了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是中国诗人一厢情愿地为社会代言,并对之做出承诺。”[1](P188)此论是针对1930年代进行的诗的纯化运动——唯美的和形式主义的诗建设而发的。它既道出了中现实社会问题对本土诗歌创作隐潜的暧昧规定性,又揭示了中国诗人身处的一种不无无奈的表达困境。进入1930年代后半期以后,这种规定性和表达困境显得更为突出。因此,当我们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时,不可忽略这些因素对延宕现代汉诗成熟的影响。
事实上,抗战开始以后,由于时代语境的强大整合力的作用,七月诗派一度成为中国诗坛的主角。这是一个创作上以艾青、田间为精神领袖,诗歌美学追求上与胡风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两个刊物——《七月》和《希望》的时间跨度为1937年10月至1946年10月,七月诗派诗人们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诗作实际上代表着这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主流方向。七月诗派的创作实践基本遵循胡风所主张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融合”的文艺思想,他们的作品对于当时那场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而言,无疑形成一种有效的鼓呼。然而,当我们以冷静的艺术分析的眼光去面对这些诗歌作品时,会发现在充满激情的铺张抒写之下,诗歌所必需的艺术质素普遍匮乏。与其说这是一个民族遭受苦难时,她的诗人关注现实与表达现实难以避免的代价,毋宁说是诗歌在介入现实时的艺术方式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可谓适逢其时。
二、西南联大的“新诗圈”
当然,在主流之外还有不少诗歌的支流坚持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探索从未停止过。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活跃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西南联大诗人群”证明,中国现代诗歌依然“在路上”。这群诗人中,不仅早负盛名的冯至、卞之琳、闻一多,也有一批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王佐良等。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三所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南开的联合体,在当时被称为“民主的堡垒”。在这里诗歌的民主也得到极大的发挥。两代诗人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他们的创作与诗歌活动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上代诗人不仅自己创作诗歌,如冯至在联大期间创作出版《十四行集》的同时,也注重对下一代诗人的鼓励与培养,如闻一多主编的《现代诗钞》选入穆旦、杜运燮、王佐良学生辈的诗,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一文中给予杜运燮的诗《滇缅公路》较高的评价;而下代诗人既从上代诗人那里直接得到创作实践上的启示,又通过他们开设的一些课程(如冯至的德国文学课)和译介的诗人作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现代派诗歌。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后辈诗人无疑比前辈诗人来得重要,但他们的诗是对前辈诗人的继续与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诗人、学者燕卜逊在联大执教的短短时间里,对青年一代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燕卜逊讲授的那门当代英诗课程,“内容充实,选材新颖,从霍普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前者是以‘跳跃节奏’出名的宗教诗人,后者刚刚写了充满激情的《西班牙,1937》,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燕卜逊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也非一般学院派的一套,而是书上找不到的内情、实况,加上他对语言的精细分析”,[2](P8)深受学生的喜爱。燕卜逊的到来,不仅带来了西方现代诗,特别是当代英国诗的清新气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言传身教促成了诗人穆旦等人诗歌观念的转变。
在西南联大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西南联大诗人群,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是新诗的探险队”。[3](P19)他们在当时以及以后的诗歌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现代汉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话语据点。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西南联大诗人群主体部分的青年一代诗人们,实际上是后来的“九叶”诗人群体的雏形。这个观点基于如下两个理由:首先,后来形成的“九叶诗群”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其现代性的追求、诗歌精神的向度是承袭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其次,在联大时期,南方(主要集中于上海)的那些诗人辛笛、陈敬容、唐湜等人尚未结成一个群体。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后来被称为上海诗人群的陈敬容、唐湜、辛笛等诗人在“九叶诗群”形成之前,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西方现代派诗歌。如陈敬容不仅翻译过里尔克的一些诗作,诗歌创作也深受里尔克的影响。在此期间,唐湜“读到卞之琳的《西窗集》与冯至、梁宗岱、戴望舒们的译诗,更在课室里念到T·S·艾略特、R·M·里尔克的作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试作了一些新的探索”。[4](P193)我们或许可以将他们的这些活动看作是西南联大诗人群集结前的“热身”。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联大诗人群并非只躺在大学的象牙塔内玩弄一些现代技巧,作几声无病呻吟。他们的诗同样是介入现实的,只不过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通过诗歌语码的陌生化等原则坚持一种现代品格。他们中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被认为是位于“四十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前列”[5](P158)的诗人穆旦,对于西方现代派的诗歌技巧的借鉴是较为成功的。他的诗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等也有着丰富的现实的血肉,穆旦甚至还被当时的现实主义诗刊《新诗歌》的编者认为是“战斗的文艺战士”。[6]与当时的主流诗人抒写现实题材不同的是,穆旦的诗歌语言是较为节制、内敛和冷静的,这就避免了那种滑行在现实表面之上的空洞的叫喊。然而,作为一个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的诗人群体,西南联大诗人群却受到排拒。见证者之一的老诗人郑敏在几十年后写到:“现代派又在三四十年代返回它的祖先的故乡:中国诗坛。尤为可笑的是,在它祖辈的故乡,它受到了种种嘲讽、咒骂甚至禁止。”[7]正如前文提到的追求汉语诗歌的现代性的诗人被放逐到边缘地带。西南联大诗人群、唐湜、陈敬容们都概莫能外。因此,这些“同路人”的集结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诗创造》上的集结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并没有顺利地向和平与民主过渡,而依然充满忧患。当抵抗外敌的斗争一旦转化为国内两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时,主流诗歌就很自然地充当其简单的传声筒的角色。这就是1946年至1949年间政治抒情诗大量涌现的原因。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也间接造就了文坛上个派别之间的对垒,而对垒的各派系纷纷创办刊物作为自己的阵地。1947年7月《诗创造》的创刊也不能排除有这样的意图。作为当时该刊物主要编者之一的唐湜曾写道:“臧先生到头办这个诗刊也可能是想团结一些青年诗人与阿垅们对垒。”[8]《诗创造》是上海星群出版社(原名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诗刊,它的编辑工作一开始由出版社的创始人、诗人、画家曹辛之(杭约赫)主持,并得到了臧克家的大力支持,臧克家凭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影响和各种关系为《诗创造》的诞生创造了不少条件。他除了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作外,还“经常在大方向上给予指导”,并且“在决定办《诗创造》时,他提出要注意两点:一、刊物一定要搞现实主义;二、不要大暴露,否则出不了两期就会出问题”。[9]由此可见,臧克家与《诗创造》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作为这个刊物的指导性的参与者,他的诗歌观念不可能不影响《诗创造》的整体风格倾向。因此,虽然在《诗创造》上发表的诗“风格多种多样,有十四行诗,也有山歌民谣;有政治讽刺诗,也有抒情小唱”,[10](P321)似乎形成一种兼容并包之势,但是,其中的主流派仍然是主张现实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如袁水拍、臧克家、陈侣白等人的诗)。
《诗创造》对于“九叶诗群”形成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促成了上海诗人们的首次集结,从而为后来的“九叶”诗人们的会合埋下伏笔。通过参与《诗创造》的编辑工作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作,辛笛、陈敬容、唐湜、杭约赫等人既得到相互结识的机会,同时又以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指向——诗歌现代性的追求(关于后者,又以唐湜、陈敬容最为自觉,此处不赘述)。唐湜在后来回忆道:“在《诗创造》中,我与敬容、唐祁关系较好,在辛之的支持下,初步形成了一个四人核心。”[11]事实上,作为《诗创造》的实际负责人的曹辛之,是倾向于主张多作现代诗艺探索的,所以他与几位现代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诗人,如陈敬容、唐湜、唐祁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时代氛围里,他们的诗歌艺术主张很快就遭到来自对立面的反驳。后来接受《诗创造》编辑工作的林宏、赫天航回忆说:“1948年春,林宏、康定、燧伯从外地相继来到上海,开始参加《诗创造》的编辑工作。逐渐在刊物的选稿标准上,林宏、康定等人的意见与辛之、唐湜等人不时发生矛盾,前者认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下,要多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诗作充斥版面;后者则强调诗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之作,主张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的探索。”[9]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持不同艺术主张者之间隐藏的深刻矛盾,甚至还有相互否定。此时的《诗创造》,对于一心想推动一场新的诗歌运动的唐湜等诗人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阻力。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阵地来亮出自己的艺术旗帜。而在另一方面,林宏等人的意见由于与臧克家的诗歌保持一致而得到臧克家的大力支持(关于这点可参阅上引林宏、赫天航文章)。臧克家在这场争论中做出立场上倾斜,无疑加速了《诗创造》内部诗人的分裂和《中国新诗》的诞生。
1948年6月,《诗创造》改由林宏、康定、田地等人主持编务;在当时时任上海金城银行信托部主任的诗人辛笛的贷款支持下,曹辛之等人另行创办一个诗刊《中国新诗》,由方敬、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湜、唐祈任编委。在《中国新诗》创刊号上,有两篇文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一篇是《中国新诗》的“代序”《我们呼唤》。这篇文章在极其尖锐地批判了当时诗坛空洞和贫乏的病态现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的诗人们对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经验活动传达等现代诗艺的追求,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个喧嚣动荡的年代里坚韧的挣扎与坚持,并与苦难的生活、诗歌艺术难题顽强搏斗的精神。另一篇是登在同一期刊物上改版后的《诗创造》的一则广告。它这样写道:“从第二年的第一辑起,我们对原有的编辑方针将有所变更,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明快、朴素、健康、有力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与欢乐呼吸在一起,并使诗的艺术性和社会性紧密地配合起来,有一个更高的统一和发展。”[12]改版后的《诗创造》的确忠实于新的编辑方针,发表的诗作有明显的反映现实和追求大众化的倾向,提倡深入浅出、一般读者能够接受的用语和形式。两篇文章明显地体现出诗歌艺术追求上的分野。
三、《中国新诗》的整合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年轻一代诗人都先后毕业,分散在各地。虽然被称为“联大三星”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但当他们一旦脱离西南联大那样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语境,不免有一种更深切的边缘感与漂泊感。他们也经常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文艺复兴》、《大公报》副刊等报刊,但缺少一个能够充分展示他们对于现代诗歌艺术创作的种种探索的舞台。《中国新诗》作为一个大力提倡现代诗歌探索的诗歌刊物,它的创刊无疑吸引穆旦等诗人投入它的怀抱中去。总之,“九叶诗群”的真正会合终于在《中国新诗》上得以实现。来自南方与北方的诗人们不仅以各自的作品在这个诗刊上争奇斗艳、相互辉映,而且在内在的诗歌精神上也取得了统一与融合。特别是袁可嘉、唐湜都曾在诗歌理论方面付出积极而有效的努力:“……逐渐出现自觉的理论提倡:北方的袁可嘉,在1946-1948年间,连续发表文章探讨‘新诗现代化’,南方的唐湜也陆续写下了他的颇有影响的对‘现代派色彩十分浓郁之作’的评论。”[13]袁可嘉、唐湜两人的理论倡导激活了这些诗人诗歌写作某些共同因素与内在激情,使他们终于走在一起,结成中国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探险队,“一齐向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奔流,相互激扬,相互渗透,形成一片阔大的诗的高潮”。[14]
如果说南方诗人杭约赫等人为“九叶”诗人群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阵地和宽容的舞台——《中国新诗》,那么,穆旦等北方诗人的诗歌作品为这个诗歌刊物带来了浓厚的现代气息。特别是穆旦,这位以他的诗歌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15]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以成为这个诗人群体的精神领袖。他对那种彻底的现代诗歌精神的探求代表着“九叶诗人”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穆旦《赞美》一诗对于其他诗人如辛笛、唐湜、唐祈等的创作所产生的或隐或现的影响中窥见一斑。穆旦共在《中国新诗》上发表8首诗(据《穆旦诗全集》统计)。这些诗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现代品格。所谓现代品格的呈现,主要指这些诗并不仅仅停留于对现代生活表面之上的简单摹写,而是注重对现代生活中的意义进行一种提升。《城市的舞》(原载《中国新诗》第四集)一诗便向我们展示了在现代生活最重要的场景——城市的面前,个体生命正在逐渐丧失其主体性。人们还来不及追问一声“为什么”,就被毫不客气地卷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中。人们在建设城市的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变异的命运:“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城市之舞”实际上就是人们为自己进一步堕落加速的狂欢之舞。而《我想要走》(原载《中国新诗》第三集)一诗是穆旦考取赴美自费留学(1947年10月)之后写的。这首诗表现了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个人在无力改变社会现实时师徒从中超脱出来,换个新的环境,却发现被一股无形的引力拉回原来的地面。在诗中,诗人使用了他惯用的设置矛盾场的手法来表现这种纠缠牵扯的状态:“我想要走出地方,然而却反抗:/一颗被绞痛的心当它指导脱逃,/它是买到了沉睡的敌情,/和这一片土地的曲折的伤痕,/我想要走,但我的钱还没有花完,/有这么多高楼拉着我赌博,/有这么多无耻,就要现原形,/我想要走,但等我花完我的心愿。”其他几首:《暴力》、《甘地之死》、《绅士和淑女》等,或倾向于形而上的玄思,或倾向于对现实切入,都体现了诗人穆旦在当时已经显得较为成熟的现代主义风格。当然,穆旦发表在《中国新诗》上的诗作只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纵观他的整个诗歌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代诗歌的各种可能性的更多探索,也可以发现其诗歌构建的更大艺术空间。
不惟穆旦,其他的“九叶”诗人也都以自己辛勤的创作和艰辛的探索加入到中国现代诗歌的建设中来。杜运燮在《中国新诗》上发表的几首诗《闪电》、《雷》、《善诉苦者》等,不仅继续和发展了他那独特的机智、诙谐和轻快的特点,而且在诗歌中物我关系的重建、形式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反讽手法的改进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如《山》一诗将平凡的司空见惯的山写成追求崇高者的化身:“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根植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茫茫平原的升华,它幻梦的形象,/大家自豪有他,他却永远不满。”但“他”是孤独的,常常“梦着流水流着梦,/回到平原上唯一甜蜜的童年记忆”,“他永远寂寞”。诗人似乎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写山,其实诗中却暗中流露出自己的某种人生自况。郑敏在会合后发表的一些诗作,如《最后的晚祷》、《求知》、《噢,中国》等,追求一种较为整齐的形式(十四行诗或四行诗节体),并且使用颇具气势的长句,从而是这些诗具有较强的容纳庞大主题的能力(如《最后的晚祷》的主题是甘地之死的人类意义;《噢,中国》的主题则是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走向的思考)。郑敏的这些诗作虽然加入了不好现实的元素,但仍然体现出诗人一贯喜爱的在事物和事件面前保持一种沉思默想的姿态这一特点。而原先在南方的诗人陈敬容、辛笛、唐湜等也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歌文本,壮大了“九叶诗群”的声音。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来,他们诗中体现的先锋性和现代性可能不及穆旦们那么激进,但在他们的诗中,特别是陈敬容、辛笛的诗,由于古典诗词优秀传统这一营养成分的加入,使得他们诗歌中所包含的意义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翻新和丰富。此外,唐湜、杭约赫、唐湜、袁可嘉的诗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现实生活某些侧面的切进,使他们的诗歌语言节制而内敛,从而较好地保持了现代诗的品格。这里,必须提及唐湜创作于1948年的《交错集》。这本集子所收的诗作具有较强的形式感,最能代表诗人在40年代风格的转变。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一个较为自觉的现代诗人形象。《交错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以西方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作为表现对象的诗,如《雪莱》、《弥尔顿》、《罗丹》、《巴尔扎克》等。这些诗并非只是对所表现对象的一味赞颂或对他们的作品作空泛赞美,诗人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而不是被动地受牵制。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诗人在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时的心路历程。
四、结语
值得再次提起的是,“九叶诗人”群之所以能够在1940年代得以会合,并肩在现代汉诗的艺术探险的路途上越走越远,是和他们中的两位理论家的极力鼓呼与热情呐喊分不开的。这两位理论家就是袁可嘉和唐湜。袁、唐两人分别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和浙江大学外文系,科班出身无疑为他们借鉴学习西方诗歌理论提供了“近水楼台”之便利。袁可嘉1946年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文学杂志》等报刊上的论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文章,即批评了当时诗坛上存在的“对于诗的迷信”、政治感伤性对现代诗质的损伤等各种问题和病症,认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诗歌的真正的艺术价值,也为新诗现代化这一迫切的历史性课题勾画出一个理论框架的大致轮廓:“无论从理论原则或技术分析着眼,它都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16]这一系列文章既总结了以前新诗现代性探索所取得的成效,也指出了此后新诗现代化的走向。
如果说袁可嘉的以系列理论文章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为“九叶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理论背景的话,那么,唐湜对各位诗人的具体而微的评论文章,如《搏求者穆旦》、《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辛笛的手掌集》、《陈敬容的星雨集》、《郑敏静夜里的祈祷》等,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喝彩”之声。当然,这里所说的“喝彩”并非空洞无物的无聊捧场,而是在对这些诗人的创作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分析之后发出的感叹与鼓呼。唐湜也并不满足于那种序言式的印象主义批评,而是运用了许多相关的现代诗歌理论作深入的、颇具说服力的解读与剖析。此外,唐湜的这些文章对“九叶”诗人创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直言不讳,如在《辛笛的手掌集》一文中,他就很中肯地指出了辛笛诗歌中出现的某些失败之处。
“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尽管并未最终形成一股个鲜明的流派现象(事实上,对这一诗人群体的命名就带有明显的“后设”意味),但他们这种略显松散的组合,却无疑为推进新诗艺术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新诗的接受史上,九叶诗派的形成及其意义必须经过40多年的时间才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认可。而这种现象的产生,无疑又为今天研究九叶诗派提供了学理的依据与理论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谢冕.新世纪的太阳[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188.
[2]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A].一个民族已经起来[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3]张同道.探险的风旗[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4]唐湜.我的诗艺探索[A].新意度集[M].三联书店,1990.
[5]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A].半个世纪的脚印[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3).
[8]唐湜.九叶在闪光[J].新文学史料,1989(4).
[9]林宏,赫天航[A].关于星群出版社与诗创造的始末[C].新文学史料,1991(3).
[10]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星辰[A].“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C].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11]唐湜.九叶在闪光[J].新文学史料,1989(4).
[12]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星辰[J].“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322.
[13]钱理群.一九四八年:诗人的分化[J].文艺理论研究》,1996(4).
[14]唐湜.诗的新生代[J].诗创造,1948,8(1).
[15]袁可.诗人穆旦的位置[J].半个世纪的脚印,153.
[16]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J].半个世纪的脚印,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