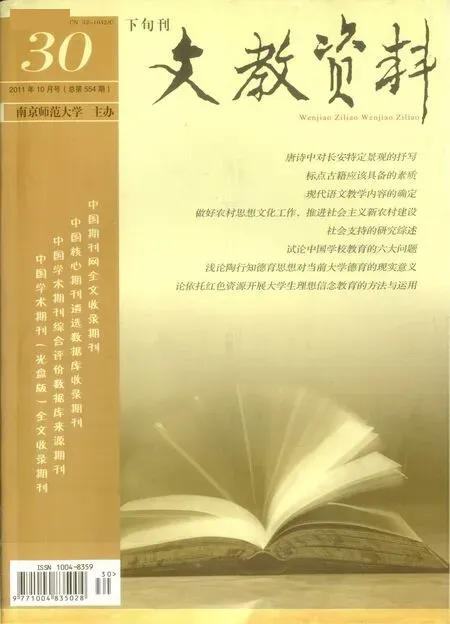浅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2011-03-20胡洪兴
胡洪兴
(邳州市土山高级中学,江苏 邳州 221300)
李商隐(公元813—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从高祖至其父亲,都只做过县令一级的小官。九岁丧父后,李商隐跟母亲回到郑州,之后家境极为艰难。不久,跟随堂叔学习古文、诗歌和书法。十六岁时著《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十七岁时,被太平节度使令狐楚辟为巡官。牛党人令狐楚爱其才,教授骈文奏章,并令子令狐绹与李商隐同游。此后八年,除有短暂时间的宦游外,李商隐一直在令狐楚幕中。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前后,李商隐赴玉阳山、王屋山一带隐居学道。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应举,经令狐绹引荐登进士第。次年,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了仕途依托,便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茂元爱其才,以女相嫁。牛党人因此骂他“背恩”。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李商隐被选为秘书省正字。同年,其母去世,他离职服孝三年。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受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潦倒至死。
李商隐素有大志,无意卷入了牛李党争倾轧的漩涡,为他仕途失意埋下了伏笔。在婚娶茂元之女后,李商隐虽曾有任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上)的经历,但大部分时间却浪迹于幕府。顿挫中总想奋起,一次次希望伴随着一次次失望,政治上的落拓与不甘寂寞的情怀缠绕在一起,使李商隐的诗有强烈的政治要求,欲罢不能而欲言又止的结合,又使李商隐的诗曲折、隐晦、多典、难懂。
咏史诗作为一种特定的诗歌形式,既有特定的内容,又有特定的表现方式。在晚唐,政治衰败,党争加剧,有理想有才华的士人追慕盛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社会原因与文学因素的结合,为伤今悼古之作的蔚为大观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在众多的咏史诗人中,李商隐在咏史诗的发展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李商隐的咏史诗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且直指时事
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人,他的咏史诗是政治诗的特殊表现形式。诗人因事兴感,以历史上盛衰兴亡的往事作为吟咏的题材,选取封建帝王们因生活上的荒淫奢侈、政治上的昏愦腐朽而造成亡国的惨痛教训作为集中表现的主题,讽喻当代的帝王,抒发自己理智、冷峻而感伤的亡国之忧,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诗人辛辣地嘲讽和暴露了封建帝王色荒淫昏的各种丑态,揭露其因溺声色而导致乱政亡国的罪行。
李商隐咏史诗观照现实是以历史作为参照的。诗人在咏史诗中借楚灵王、吴王夫差、北齐后主、南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乃至唐玄宗等荒淫误国的典型托古讽时,深寓历史教训,具有强烈的鉴戒意义。显然,李商隐如此的创作实践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昔的形式,反映现实社会的新问题,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统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容量。
作家的创作总要受某一思想的指导,咏史诗也要受诗人历史观的制约。从李商隐的诗中,我们可以总结指导其创作的历史观点。在其咏史诗中,李商隐大都指责是帝王本人败乱了国家,“系人不系天”的思想贯穿于李商隐的全部咏史诗中。比如:“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南埭”是南朝帝王经常在那里游宴玩乐的玄武湖和鸡鸣埭,可同样在这里能频繁地看到降旗一片。有人说:“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但三百年间每一个皇帝梦都那样短促,显然,兴亡之道,不关天也。他又说:“只要君流盼,君倾国自倾。 ”(《歌舞》)
2.李商隐咏史诗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新的创造
李商隐通过咏史向当时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鉴戒时,并不是全面地阐释某一历史事实,而是尽可能选择富于包孕效应、暗示作用的典型历史人事细节,如寄慨的微物、寓意的片断、合理的图景等加以着力描写,借题发挥,生发、引申出历史故事、历史素材中人们不易发现的现实意蕴,翻旧为新,出奇制胜,小中见大,扩展、延伸咏史的内涵。在李商隐的作品集中,古体诗已很少,甚至连五律也为数有限,而大多采取七律、七绝的形式,特别是七绝的大量运用,是此时咏史诗变化的标志。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习用的体裁。
我们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常常要看他相比前代作家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而以咏史形式写爱情、恋情正是李商隐的新创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在运用历史材料时,往往能跳出史料的限制,在符合当时生活逻辑的范围内,设想未必实有却有可能有的感情活动,这是咏史方法在诗歌领域的新发展。这样就把具体的抒情对象和具体的情感抽象升华得具有无限的超越性,往往一种具体的情感穿越于无限的艺术时空中,一波三折,甚至千回百转,变得幽恨深远。
李商隐的咏史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用典多,几乎句句有出处。如《井络》一诗中连续使用了“井络”、“阵图”、“杜宇”、“金牛”等典。用典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的新鲜,另一方面却使了解诗意颇费周折,以至晦涩难懂。李商隐的咏史诗当属后一种。
李诗的多典当然与他早年习受骈文有关,但不应是主要因素。例如作者有感于“甘露之变”而写的《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以诗人之才,写两首律诗并非难事,然而诗却隔年而成,可见诗人是有感于衷,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事关朝政,写作时怕意显招难,唯恐隐之不深,即成之后,又怕无人领略,有负苦心,便不觉附以短注,提供一扇解诂的窗户。咏史诗是李氏特殊需要的政治诗,李商隐写此类诗时应属同样的这一心态。这一心态直接的表现就是“多典”。
3.注意议论与形象或感情的结合
如《北齐》诗:“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再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沈德潜评此诗:“纯用议论矣。然以喟叹出之,故佳。”这种议论寓于形象之中的做法很高明,故《诗薮》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宋人议论之祖。……然书情,则怆恻而易动人;用事,则巧切而工脱俗。”指出了李商隐咏史诗议论的好处及对后世的影响。
4.常见题材的创造性使用
文学创作是具有独创性的活动,它总要求作家采用新手法,进行新构思,表现新内容。而咏史诗题材的因袭却是常见的现象,这是由于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文学性较强,从其特殊性能反映出普遍性,故易吸引作家的目光,成为咏史诗中的传统题材。如商山四皓的故事,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都有题咏。创新既是文学活动的普遍要求,咏史诗也不例外,虽然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在基本内容一致的条件下,诗人们便要寻找新的角度及表现手法。温庭筠的《四皓》诗是这样写的:“商於六里便成功,一寸沈机万古同。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真有紫芝翁。”诗意与李商隐的“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同,然而细读后,便会觉得二诗焦点仍有不同。温诗羡慕四皓生逢其时,得以脱颖而出,言外有自叹自惜意,而李诗特别是后两句:“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则不过是说用对人方可安天下。此诗其实是有感而发:晚唐的皇帝多为宦官拥立,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皇帝在位时都没有立太子,即使立了太子也是时立时废,因为这样的缘故,朝庭变乱不已,乃至于立储一事成为人们时常议论的话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诗人各方面的条件不同,只要善于挖掘,那么一个习见的题材仍可以写出有新意的作品来。
总之,李商隐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丰富了咏史诗的内容及表现手法,成为晚唐咏史诗的集大成者。他的创作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印行,1988.12.
[2]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
[3]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0.
[4]钟铭均.李商隐诗传.中州书画社,1982.7.
[5]叶葱奇疏注.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