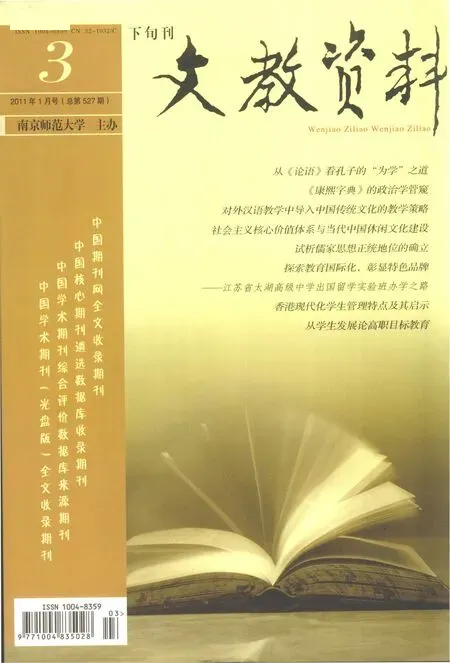痛苦的历程,辉煌的心路——《寒风吹彻》解读
2011-03-20李金松
李金松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江苏 南京 210012)
每读散文《寒风吹彻》,常从字里行间读出丝丝凉意,种种况味,牵引出诸多感慨唏嘘。而又每每于感慨唏嘘之时,从那丝丝凉意、种种况味之中,品咂出痛极而成的旷达、悲极而生的博爱和冷极而涌的炽热来。现就以下两大方面,试着加以阐释。
一、自我、他人、亲人——悲悯情怀的三重超越
经过十四岁经历的那个冬天之后,作者对寒冷的认识逐渐深入。而也正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我懂得了隐藏温暖”。在凛冽的寒风中,在纷飞的大雪下,作者“放下一年的事情”,“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对自我、他人、亲人的三重超越。
作者经过那个十四岁经历的冬天之后,摆脱了曾经的年少无知、张狂不羁,而对自己鲜活而伤痛的生命产生了深深的悲悯之情。然而作者并未仅停留于对一己生命惺惺自怜的小境界中,而是由己及人地进行了可贵的超越。
十四岁冬天的那个夜晚,由于是独自一人赶着牛车进沙漠去打柴,因此作者有了一次以自己赤裸的生命和严酷的自然直接对话的经历。而正是这次经历,使他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种殷实的生命体验,使作者对生命的悲悯之情超越了自我,把爱之触角伸向了更为广大的空间,包括一个陌生的路人,完成了由己及人的可贵飞跃。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作者主动“把一个浑身结满冰霜的路人让进屋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希望把自己的友好和热情,变成一个冬天的火把,去温暖对方身上带着的“许多冬天的寒冷”。然而作者的热情帮助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那个路人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朝我点了一下头,开门走了”,最后冻死在村西头。
这次经历,又促使作者对冬天作更深层次的思索。作者沉痛地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作者沉痛地进入了内省式的批判式反思。他在十四岁的那个冬天冻坏了一条腿,是因为他没吭声,没向家里说腿冻坏的事,而耽误了补救措施的施行;那个陌生路人最后被冻死,也是因为“他一句话不说”,而未寻求同类的热情帮助。那么,姑妈呢?
姑妈由于年老多病、孤苦伶仃,特别需要亲情的温暖。她在许多年前的冬天,在作者兄弟几个去看望她后临别前,总平淡地说一句:“天热了让你妈过来喧喧。”作者对姑妈的处境也怀有深深的悲悯之情,不但自己常去看望姑妈,而且一直没有忘记姑妈这句话,且也不止一次地把它转告给母亲。但是由于母亲“有五六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要拉着他们度过冬天,不让一个孩子受冷”,竟直到姑妈去世,也没能满足她这个微薄的愿望。
这件事,使作者对悲悯之情又有了一层更深的体认:即使主动说出自己需要的帮助,也会因为冬天对所有人的普遍挤压,而使求助者未必就能得到她要的帮助,尽管对方也很想提供帮助。
这样,作者面对双鬓斑白的母亲,把自己的悲悯之情又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作者写道:“我告诉自己,不管天冷天热,我们都要过来和母亲坐坐。”因为“每当儿女们回到家里,母亲都会特别高兴,家里也顿时平添热闹的气氛”。作者希望“我们长高长大的七个儿女,或许能为母亲挡住一丝的寒冷”。
至此,作者把自己对生命的悲悯之情通过三重提升,如地底岩浆般炽热地奉献于读者的面前。
二、痛心、坚信、呼唤——人间真情的三阶提升
品读《寒风吹彻》,是一次艰苦而温馨的旅行。
在作者素淡、明澈的语言中,我们迎风冒雪,踏冰而行。有冰凌扎刺之痛,有冰裂氺冷之苦。曾经之伤,遗留之痛,无法修复和挽回,层层叠加,累积着寒冬的阴冷。然而在一番冰雨浸漫、霜雪侵肌之后,我们却又时时感到了丝丝暖意,阵阵热流。在一片冰天雪地的文字林中,地老天荒的话语场里,我们虽然读出了作者对自己遭遇的叹息,对路人结局的悲悯,对自己亲人光景的伤感,却也读出了他遭遇坎坷后的淡定从容,历经磨难后的顽强执着,遍尝辛酸后的深沉博爱。
我们看到作者经过风雪洗礼后的生命变得越发丰润而饱满,不谙世事的心脏变得更加博大而悲悯。他痛心于父母的粗心和自己的年幼无知的倔强,而使自己冻坏了一条腿。他痛心于那个陌生老者的拒绝吐露心声而冻死于村头,他痛心于年老多病的姑妈至死也未能实现的微薄愿望,他痛心于母亲因忙于拉扯子女而未能在姑妈死前满足她的微薄愿望,并在忙碌中也进入了“伤心寒冷”的“一个人的冬天”。他更痛心于目睹自己最亲的人“独自在冬天的透心寒冷”,却无能为力。他一边劈好过冬的柴火,围抱火炉,吃咸菜啃馍馍,“用自己那只冰手,从头到尾抚摸自己的一生”,一边用如雪般干净线粋的文字抒写心情,为自己也为我们“创造一种绝处逢生”[1]。
于是我们看到年仅十四岁就被冻坏一条腿的作者,并没有就此怨天尤人,自伤自怜,进而冷眼看世界、看人生。而是从这次遭遇中,懂得了隐藏温暖,并把“这温暖”节约地用于此后多余的爱情生活,把自己仅有的温暖全给了自己的亲人们。
在亲历路人被冻死在村头的悲剧后,他也没有从消极的层面来看待这些人,而是坚信“他的生命中肯定还深藏着一点温暖,只是我们看不见”。在这里,我们读出了冻死者的另一种坚信。他认为老者的择死而去,未必是心中无爱,反倒很可能是因为他心中有爱,甚或是心有至爱,心有大爱(即如殉情和牺牲)。从他对冻死的路人的唏嘘叹息和悲悯同情之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人心之暖、人情之美的坚信与守望。
最后作者悲怆沉痛地写道:“我围抱着火炉,烤热着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在这里,作者不仅写出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的生存况味,而且完成了“个人成为全体,刘亮程成为我们”的角色转化。他痛得悲怆,爱得彻底。
至于作者的虚怀之辞,也只是期望生养于和平盛世、日渐小康的孩子们能早日成熟,也即作者所谓:“当然,把这样的文字呈现到中学生面前,说明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长大了。 ”[2]
至此,我们从作者痛苦的历程中,可隐约揣摩出作者辉煌的心路、良苦的用心。
[1][2]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寒风吹彻中,我们还有春天的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8:189,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