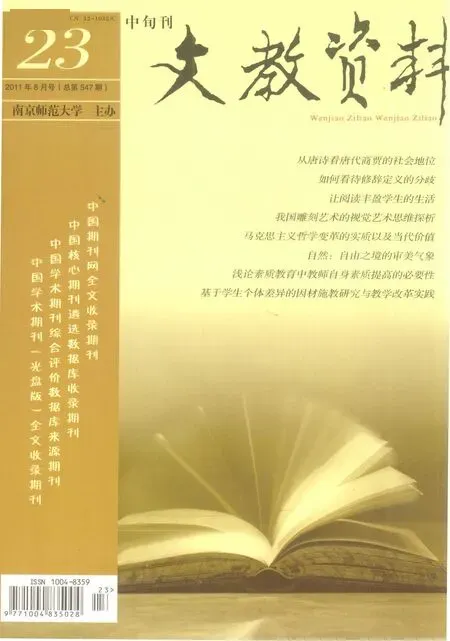由儒观释,以释鉴儒——金元之际释儒互动文化视野下的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
2011-03-20王萌筱
王萌筱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2009级硕士研究生)
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思想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学者们的探讨多数集中于其儒家的精神底色、对佛道二教排斥与并包的矛盾态度上。元好问的儒者身份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然而在全集中亦有多篇诗文谈论佛教,《威德院功德记》一文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文中,元好问一方面对易代之际佛教大兴的缘由进行追问,一方面由佛教之兴盛反观儒学之衰颓并对其进行深层的反思,我们正可借此略窥作者谈论佛教的基本动机。
一、“好僧”之标准:由儒观释
《威德院功德记》一文开篇便直抒对“浮屠氏之力”的慨叹:“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塔庙处视他郡为尤多。宣、政之季,废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砾之场金碧相望,初若未尝毁者。浮屠氏之力为可见矣!”“浮屠氏之入中国千百年,其间才废而旋兴,稍微而更炽”一句便总结了此前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整体走向。元好问进而据此追问释氏大兴之因:“天下凡几寺,寺凡几僧,以乡观乡,未必皆超然可以为人天师也。唯其(指威德院的僧玘等人)死生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据此,元好问是将佛教“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的品质视作了佛法大兴的原因。
既将“僧”的品质作为释氏大兴的基石,元好问所持的评判“好僧”的标准便十分重要。就其文中的“死生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几句观之,正与儒家亚圣孟子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境界相谐。而对这篇记中所盛赞的威德院建成者——僧玘,元好问又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予尝见其持律严,入理深,护念所业如捍头目,盖人又不可及者,每窃叹焉。”以“执著一念”作为评判“好和尚”的标准,却与中国宋以来大兴的禅家反抗知识论的“破执”理念不符,亦不同于法相唯识宗等所主的“万法唯识”论,反倒更接近于正统儒者的价值衡量标准。
儒士们对寺僧或儒中喜佛者学养、品行高下的评判,在金元之际似乎形成了一股风潮。同样身处金元易代之际、融汇儒释二家的耶律楚材在其《楞严外解序》批判儒者喜佛之谬种种,同时大赞其友屏山居士(即金末文人李纯甫):“若夫征心辨见,证悟穷魔,明三界之根,探七趣之本,原始要终,广大悉备,与禅理相为表里,虽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绎之(指《首楞严经》)也。余故人屏山居士牵引《易》、《论语》、《孟子》、《老氏》、《庄》、《列》之书,与此经相和者,辑成一编,谓之《外解》,实渐诱吾儒不信佛书之饵也。吾儒中喜佛者固亦多矣,具全信者鲜焉。或信其理而弃其事者,或信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经论而诬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经,或讥其建寺。尘沙之世界,以为迂阔之言;成坏之劫波,反疑驾驭之说。亦何异信吾夫子之仁义,诋其礼乐,取吾夫子之整合四,舍其文学者耶!或有攘窃相似之语,以为皆出于吾书中,何必读经然后为佛,此辈尤可笑也。……我屏山则不然,深究其理,不废其事。”①耶律楚材所赞的李纯甫,据《金史》载:“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藁’,其余应物文字为‘外藁’。……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以故为名教所贬云。”②虽为名教所贬,却被耶律楚材视作儒中喜佛者之翘楚加以盛誉,与元好问所持的“好僧”标准相似,皆是对佛法唯一的执著信奉及践行。
整个社会对佛教的关注,这是金元两朝佛教在北方大为兴盛的文化氛围之产物,亦与入元以后世祖为怀柔藏民而立藏传佛教为国教以致藏僧气焰炽盛引发民愤有关。③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有金一代的宗教生活却基本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占主流地位的是汉地佛教,最繁荣的教派是禅宗和净土宗——而在中国佛教领域,这二者长期作为正统的和可以接受的教派而为官方所承认。④由金入元的元好问文集中所载涉及佛家之文亦多是其为汉地禅宗佛寺所作之记,与其交游往来之僧友如英禅师、汴禅师等亦多为汉地禅僧;⑤而耶律楚材之释门师友乃是汉地曹洞宗万松行秀禅师,与其交往唱和极多。在传统的经学领域内,儒士们一贯有着宗经崇古的传统;这一传统经由儒士对释教的介入而渗透影响了佛教的评价体系,在宋金元之际,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无疑成为汉地正统儒士所认可的佛门之正统经典,面对异族统治之下藏传佛教之流毒危害,浸润于儒家文化的士人们必然会以此来进行文化上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形式的内里却又纯然是儒家本位的。在元好问的这篇文章乃至同时代其他儒士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种“由儒观释”的倾向,也即以儒家准则为佛门立法。
二、他者的观照:以释鉴儒
元好问在文末感叹道:“噫!使吾圣人之门,有若信、若果、若因、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于一亩之宫,亦何遽有鞠为园蔬之叹乎?吾于是乎有感。”固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文章的文体问题——既是为寺院作功德记,自然以歌功颂德为主,对寺僧如此称颂并无足怪;然而,再联系元好问的两首诗作,我们当能发掘出文末这一声浩叹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现将二诗录于下:《曲阜纪行十首》(之八)节录:“白塔表佛屋,万瓦青粼粼。何年胜果寺,西与姬公邻。塔庙恣汝为,岂合鲁城闉?鲁人惑异教,吾道宜湮沦。许行学神农,耒耜手自亲。当时子孟子,直以为匪民。况彼桑门家,粪壤待其身。一朝断生化,万国随荆榛。”《应州宝宫寺大殿》:“缥缈层檐凤翼张,南山相望郁苍苍。七重宝树围金界,十色雯华拥画梁。竭国想从辽盛日,阅人真是鲁灵光。请看孔释谁消长,林庙而今草又荒。”⑥
在诗文中,元好问一再感叹释氏之兴盛与儒家之没落,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首先需要明确金元之际尤其是元初儒学的文化定位和儒生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传统说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一,即认为知识分子地位极其低下的“九儒十丐”说,其二,认为蒙古人作为文化浅薄的游牧民族对先进博大的汉文化存有天然崇拜的“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所征服”说。针对第一点,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一文根据对“儒户”的研究,认为元初的“儒户制度”乃援引僧道赋役优免之例而来,三教地位实际上大体相当;而针对第二点,如何客观看待元初的文化政策,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牟复礼认为:“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人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蒙古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对他们征服的所有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古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只是蒙古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大限度地为蒙古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⑦
其次还须细察元初统治政策下儒释二家的地位消长状况。可以发现,元初统治者的这种“实用主义”统治方略,其实与佛教“契理契机”之思维模式有相当的类似度,故而才能适应不同地域的风俗文化。如同佛教可以借其不同面目“现身说法”而融入异域并一度极为深远地影响了东亚及南亚各国的思想文化一样,来自蒙古的骑士们亦以其多变的统治术实现如此广袤区域的一统。身兼儒学和佛学双重学养的元初股肱之臣耶律楚材,其治国之道便正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明显地让儒学在心性论领域停留在旧儒学(理学之前)而退居佛学之次。在儒士们积极争取文化发言权的同时(文坛领袖赵复、元好问等对后进的大力引荐,参观元好问《与耶律公书》),佛门子弟亦不甘落后。元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万松行秀禅师为耶律楚材的文集作序云:“世谓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国,证之于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国治之明效,吾门显诀,何愧于《大学》之篇哉!”⑧以此宣传佛法所具有的强大社会政治功能。乃马真后称制元年(公元1242年),海云禅师亦以佛教的治国方略开示 “安天下之法”:“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备于佛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尘许,况一四海乎?若论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离心。”并且推崇佛法僧三宝为至高无上:“诸圣之中,吾佛最胜。诸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⑨佛门弟子对新兴政权中统治权力的争取,丝毫不落于向来入世的儒者之后。
通过对元初历史之探查,我们不难发现儒释道三教的高层人士均试图以新王朝的建立为机会,重建其学之统绪。而现实社会的状况又是如何?金元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大量的佛寺、孔庙均毁于战火。政局稍定之后,僧徒忠心护道,修扩寺庙,多处僧寺均得重兴,而儒士则远不如之,致使儒学废顿。甚至如元好问在此文中所写:“道则异术也,教则异习也,梯空接虚,入神出天,与吾姬孔氏至列为三家。儒衣冠之子孙,有奔走而从之者,况乎诱庸俗而役之,以为区区之塔庙,岂不謦咳颦呻之顷而得之?”元好问如此痛切书写,盖因彼时不乏其例。其见著者如屏山居士李纯甫,《金史》载:其“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无仕进意……日与禅僧士子游,以文酒为事……晚年喜佛,力探其奥义”。⑩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一向以儒士身份自居的元好问更加为儒家的命运担忧。而新朝统治者的政策亦让儒士们心寒,虽然儒户制度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然而科举进士制的废除、儒教被当做宗教的一种而与佛道并列甚至不如佛家,相对于自两汉“独尊儒术”以来到宋金文官政治的儒学至尊传统,僧侣、儒士的地位颇有此消彼长之势,儒士的地位可以说“相对”下降了。
将其人其文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便可以理解元好问在《威德院功德记》这样一篇为佛门所作之文的末尾如此抒怀的深层原因了。同处于易代之际,儒家之没落引发了元好问的痛切之思,进而从佛教这个“文化的他者”出发来观照自身所处的儒家文化传统,由释之兴而反思儒之颓,并试图力振之——元好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链条中的一环,其心路历程却可视为整个文化发展进程的一种隐喻:儒家作为思想之本体而引导着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道家作为本土文化的别枝时时对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世俗性倾向进行制衡,释家作为一种渐渐融入本土的外来文化传统而得以为其提供反观自身的载体;若没有这种文化制衡与反思的机制,儒家的所谓正统当亦无从昌盛百代,所谓经典当亦无从流传千载。
注释:
①《全元文》第一册,第223-224页。
②《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艺下。
③参考:《元史·释老传》第4521页:藏传佛教“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以及门岿.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张践.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孙悟湖.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等文。
④参考:《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三章《金朝》,第365页。
⑤参考: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见《元好问全集》(下册)附录五至七。
⑥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上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6、207页。
⑦《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九章《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第714页。
⑧《全元文》第一册,第22页。
⑨《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十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5a-b。
⑩《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文艺下。
[1]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3]李正民.元好问研究论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元]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萧启庆.元代史新探[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8][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三百五十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0]杨曾文.宋元禅宗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2]门岿.从佛道之争看元代宗教的宽容政策[J].殷都学刊,2001,(1).
[13]张践.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J].世界宗教研究,1996,(4).
[14]孙悟湖.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15]孙悟湖.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16]佟洵.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17]魏崇武.略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佛关系[J].兰州学刊,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