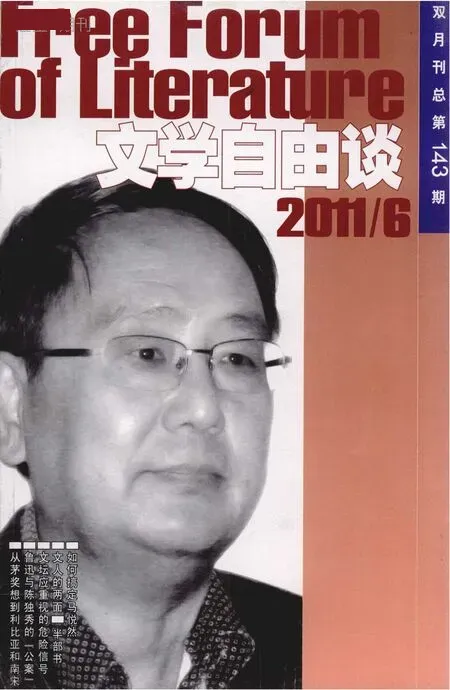捕捉世俗的碎片
2011-03-20文许辉汪杨
●文许辉汪杨
汪杨(文学博士):你常称自己是“淮北佬”,在你的作品中,也的确随处可见淮北的方言,地域化是你创作的自我守则吗?
许辉(一级作家):有一段时间,我很受地理决定论的影响。所谓地理决定论,就是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这并非当时我看了什么相关的书籍的原因,而主要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侧重。我前期的生活环境主要在被农村包围的城市和农村(插队),那是离自然地理最近的地方:麦收时在城市的木窗内就能闻到大地成熟的香气,在初夏有露水的车辙边,更易于看见因翅膀被洇湿而停留在蔚蓝色野花上的蜻蜓。农耕文明与自然地理保持着密切的近乎零距离的关系。农村是地域文化的一个源头。在农业文明的视阈里,地域文化的元素以农村——乡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大都市这样的方式链接并递减。这是以农耕文明的方式扫描的结果。对我而言,这个“地域文化”的时期,可能已逐渐过去。
汪:的确,区域地理和区域文化对于每个人的性格、语言乃至生活方式,都起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任何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不自觉地烙下了地域的印迹,也许你在不自觉中仍然会受到它的制约,比如,在你的作品中,第一人称代词经常是“俺”,这是淮北的方言吧。
许:在我小说里,人称代词从第一篇小说开始,就有一个“原则”:如果作品人物是农民,自称就是“俺”,如果是城市人,就自称“我”。虽然在社会交流已然十分充分的今天,社会生活间的日常话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还有一些调侃的语言环境。“俺”字的使用原则是要对城乡、时代(1980年代)、地域和文化背景进行区分。“俺”是传统官话区的方言,过了淮河,特别是过了长江,民间不会以“俺”自称。公家人也不会用“俺”来自称。所以,从这种人称代词,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小说的地理和北方文化背景。
汪:也就是说,你用“俺”这个称呼目的并不仅仅是强调地域特色,而是想通过“俺”与“我”的区别,来突出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
许:的确如此,比如《焚烧的春天》,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我绝不会让小瓦等人的口中蹦出“我“这样的自称,虽然在真实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和例外,对城里人,在我的小说里,他们的自称就一定是“我”、“我们”,不会用“俺”来自称,这既是要以此来进行城乡的区分,也是要以此来塑造作品个性。
汪:那小说中人物的命名呢?也有类似遵循城乡区别的原则吗?
许:我对小说人物的起名,是有我自己的想法和原则的。在我的小说中,如果是当代题材的(写于2000年以前),人物姓名一定非常通俗、易懂、平实。例如《尘世》中的陈军,《夏天的公事》中的李中,《幸福的王仁》中的王仁,《漂荡的人儿》中的刘康,《没有结局的爱情》(原名《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中的刘康,都是最普通,最简单,最没有特色的。这样做,一是从宏观视野体现“芸芸众生”;个人无法游离于时代之外,既使最有特点的个体,宏观看也只是“芸芸众生”;二是为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政权在新世纪前的意识形态特色:绝对的平等、大众意识、底层观念,摒弃中国文化中的文人传统。这不是表示我的臧否,而是试图以这种方式匹配我生活的时代,隐晦地传递时代的价值评判信息。此外,我在这些具体的小说氛围中打算提倡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平民意识,而非自上而上的精英体验,这也导致我会给2000年前写作的当代题材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如此起名。
汪:我还发现,在你的小说中,人物经常出现重名的情况,比如《夏天的公事》中有李中,长篇小说《王》里也有李中,《漂荡的人儿》中有刘康,《没有结局的爱情》中有刘康,《王》里也有刘康。
许: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有频繁的重名现象,这是我有意而为的。这样的安排,是想传达这样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情报:换一个角度看,姓名又仅仅是一种符号,不同年代、不同生活情境中的人,都是同等的、可以互换互通的,他们之间总有关联及某种延续。《夏天的公事》等写于上世纪80年代,《王》写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互文”这样的说词。相同的姓名隐含着不同文本、不同话语系统间的关联,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的证明、相互的补充、相互的阐释,是一种“互文”。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得不把西方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指标性的参照的话,这样的 “合拍”,也多少说明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曾经有意无意受到的西方的影响。
汪:但是,在很多人眼里,你的作品是最东方的,或者说在你的作品中,几乎是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因素的。比如你的作品《碑》。
许:《碑》其实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上世纪90年代初,我打算写长篇小说,那一两年里有许多个长篇小说的构想,有的仅有书名和构思,有的写出来了,比如《王》和《乡村里的秀梅》(《尘世》),有的仅尝试着写了开头的一部分。《碑》就是那些开头之一。后来《芒种》杂志约稿,而我又正在给《小说家》写一部中篇,于是就想到了这个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开头。把稿子找出来,简单修改一下,很快就在《芒种》上以头题发表出来,紧接着被《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当年又获得《芒种》的文学奖,被收入多种选集中。
汪:你选择了“洗碑”这个意象,入土为安是最具东方文化的情结。
许:《碑》写的就是宽义的人生。人生有悲,有情,有喜。在这篇小说里,似乎只看得着“悲”。但这个悲,与情,与喜,都是有逻辑、因果关系的。看见这样的悲,能想象得到当初的情,当年的喜,能体味到人生的留恋。这个小说的感觉,我认为的确完全是东方式的,是天人合一的感觉,和写作时自己的文化体验、背景噪声完全契合。这个“天”,不是天子的“天”,而是大自然的“天”。它的文化内涵完全是东方式的,中国式的。
汪:你很擅长捕捉这些世俗生活中的片言鳞爪,你作品中的人物很多都颇似《碑》中的麻脸匠人,“像是不知,也像是不觉,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一锤一錾,洗了几十年,也还是不急不躁”,抓住每一刻的生活感受加以放大。《幸福的王仁》中的王仁也是如此。
许:这部小说牵涉到我自己在某一时期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部小说。与其说是喜欢自己的这部小说,倒不如说是喜欢自己这部小说中的那种生活方式,喜欢一种世俗生活的况味。从某种角度看,最腐蚀人斗志的那种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温润的家庭气氛、甚至无关生存大局底线的勾心斗角,都能获取特殊的享受和滋味,使人流连。一部小说不是生活的全部,它只能以偏概全地放大和欣赏一种社会价值观。这正是我们容易受到小说感染的原因。
汪:我想到了你那篇颇具争议的长篇小说《王》,对于这部作品存在着近乎两级式的评价,一类觉得它是东方古典文学中的“圣经”,另一类则认为它在分段处理以及人物塑造上有缺陷,晦涩难懂。
许:《王》也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编辑的评语说它“以平朴、简约的叙述话语复活了一个遥远的历史时刻,剥展开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形式与内核”。网上的一个评论则称它为“东方的圣经”。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我十分认同这两段评语中“东方”和“封建政治文化”这样的词语。在我看来,《王》散发出来的气息,是彻头彻尾东方式的。封建政治文化几千年,在中国已经发展得淋漓尽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熟悉它,哪怕你没念过几年书,不识几个大字,但你每天米饭馒头地吃,吃下去的都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它包含了所有使中国强盛的元素,同时,也包含了所有使中国屈辱的种子。《王》要讨论的不是是与非,不是正确和错误,也不是价值体系,而是试图复活“一个遥远的历史时刻”,一个并不一模一样存在的历史时期:一个虚构的历史时期。它的寄情山水式的淡然,也是吻合于这种东方式的文化情绪的。
汪:《王》其实并不难读,但它很显然是需要读者静下心去阅读的,这篇看似是历史的小说,其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觉得它吸引不了读者的很大原因,不在于你创作的内在理念有何脱离时节之处,而是由于它先锋化的行文风格。
许:我的小说初看可能较“写实”,其实是浸透着“先锋”元素的。这些“先锋”的元素,主要不体现在技术上,而体现在文学观念和思想认知上。
汪:《夏天的公事》一直有一个隐而未现的人物——老夏,这个人物一直被提起,“老夏不去心中还真没有底,不过他是肯定要来的”,读者和李中一样一直都在等待老夏的出现,等待这个全知全能的人,来把故事推向高潮,可是,一直到最后,老夏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学处理,颇有些类似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许:《夏天的公事》这个小说里写的是最通常的中国社会环境中的普通故事和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未尝不可,同时也是合适的。但小说毕竟未仅仅停留在生活真实的层面,而是整体隐含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这并非通过是非选择就能厘清的道德观念,也非运用社会学或政治学原理能够说明的事件,它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迷境,是多路径的一个场面,这不是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所能涵括的。
汪:李中的“公事”实际上就是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作为公务员的他,必然要经历出差开会这一工作流程,而这样的严肃甚至有些崇高的命题,在你平静舒缓的叙述中,再次被简化成了生活本身。
许:《夏天的公事》,最初的名字是《单词》,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我的某种“学院派”倾向。所谓“单词”,就是只包含一个词素的词,也叫单纯词,是相对于合成词而言的。对一个句子,或者一段话来说,它是最单纯、最简单、最基本的成份。用它来暗喻写作目的和小说内容的单纯,是我的本意。游玩、享受世俗人生、从内心里欣赏成熟和丰富的饮食、休闲文化,都是我最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是我写《夏天的公事》的初衷。
汪:你对世俗生活的执着,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蜚声文坛的“新写实小说”。
许:我自己没感觉新写实对我有什么突出的影响,但当时的评论都把我的作品归入其中。也许那是一种巧合。我的小说只是在单独走自己的路。它很边缘。
汪:在文化与商业及权力相比处于不平衡的环境下更加如是,在这样高节奏的生活时代,你是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个人风格,以其文本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就经典,还是准备适当地向公众的品味妥协,以获得公众文化观的认同呢?
许:我的小说的确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较大反响。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无奈。谁不想名利双收?!但在一个时期,却只能有一个选择。自个种的庄稼都有感情,做成饭吃起来也都香。但毕竟它们会有差别,有些还有较大的差别。由于创作状态、即时背景、短暂但一时强烈的文化影响等等的支配,有些作品发表以后,自己也会在心中淘汰掉。但多年后偶尔再次读到时,心中的亲切、亲近感,仍然是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