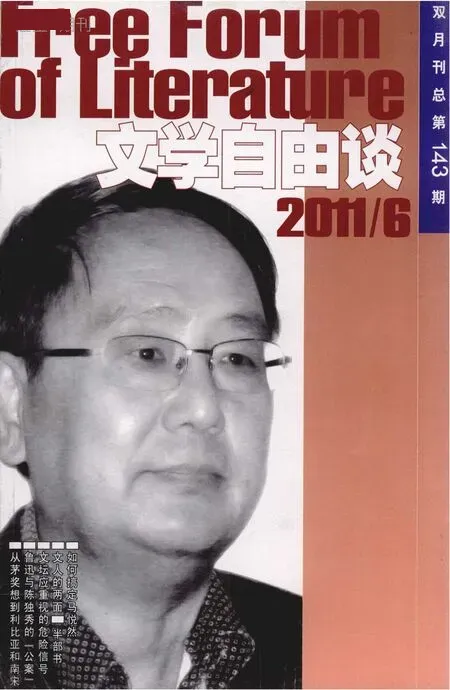不自诩作家的 作家
2011-03-20文高深
●文 高 深
上些年纪的人,对“徐懋庸”这个名字大多是熟悉的。他写过大量的杂文,解放前出版过《不惊人集》、《打杂集》和《街头文谈》,解放后发表了近30万字的杂文、小品文。1957年他把这些散见在各报刊上的短文,结集为《新打杂集》,北京出版社已经排版,后来因为当年那场运动,徐懋庸也因杂文罹祸,《新打杂集》夭折。
徐懋庸写杂文是学习鲁迅的,尽管后来他与鲁迅闹过一些误会,但是他仍然热爱鲁迅的作品,特别是杂文。徐的杂文不论气魄、风格或章法、笔调,都颇似鲁迅。有一段佳话可作佐证。1934年元旦,《申报》副刊编辑黎烈文邀请鲁迅、郁达夫、曹聚仁、林语堂、陈子展和徐懋庸小聚,席间林语堂问鲁迅:“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吧?”(鲁迅当时写杂文换过许多笔名)鲁迅反问:“何以见得?”林语堂语气肯定地回答:“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的名字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猜错了,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
徐懋庸绝对是一流的杂文家。尽管杂文归类为散文,是文学的重要一枝,可徐懋庸最多说自己是个文人,却从不自称作家。徐懋庸不仅自幼熟读古文、诗词,也读了托尔斯泰、莫泊桑、契诃夫等世界级的名著。他从十三四岁开始,本来是志在文学的,由于一位教师的影响,最初是作古诗,学骈文,吟风弄月,雕章琢句。后来他认识了一位朋友,他们一起做事,做的是为大众的事情,徐懋庸对这位朋友的思想和行动都非常佩服,他还送给徐懋庸一本关于苏俄文艺论战的书。过了不久,那位朋友死于敌人手下,他的另外几位朋友,知道徐懋庸也是他的至友,又喜爱写作,就为徐提供了许多素材,拜托徐懋庸为这位友人写一篇详细的传记。
这位朋友的人生经历是个伟大的悲剧,徐懋庸认为是一部很好的小说题材,朋友给他心头刻下的印象又极深,动笔之初,徐懋庸自信一定是写得好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他改写了十多遍,没有一次不让人失望,其他几位朋友总说传记没有表现出那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这件事对徐懋庸的“作家梦”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曾仔细地自我检讨,是哪一句写得不好呢?是哪个形容词用得不当呢,?在结构上有什么毛病?自以为看出了一些破绽,改了多遍,可是那传记到底还是一篇失败的作品。当时,徐懋庸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的才华不够。
直至1929年,“壁下丛书”出版,刊载了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篇短文《以生命写成的文章》,徐懋庸顿开茅塞。那短文说:
“想一想称为世界三圣的释迦、基督、苏格拉底的一生,就发现了奇特的一致。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有自己执笔所写的东西遗给后世的。而这些人遗留后世的所谓说教,和我们现今之所谓说教者也不同,他们似乎不过对自己邻近所发生的事件呀,或者与人的质问等类,说些随时随地的意见罢了,并无组织地将那大哲学发表出来。日常茶饭的谈话,即是留给我们的大说教。
“倘说是暗合罢,那现象却太特殊。这十分使人反省,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像做戏,尤其是我们的以文笔为生活的大部分的人们。”
徐懋庸在《我在文学方面的失败》一文中说,有岛武郎的文章是对他的“当头棒喝”,自己写传记所以失败,读了此文才恍然大悟。他说:“我的失败,原因是生活的空虚。自己的生活空虚的人,对于他人的充实的生活,也是不能深刻地认识的,既无深刻的认识,当然不能深刻地表现。我对于那个人的思想行动虽然了解一二,但因自己不曾像他那样地思想行动,故所了解的不过是皮相,那么如何能够用我的文字来表现他的生命呢?”
他以为,世界最伟大的人将生命献给了人类社会,并不执笔写文章。认识他人的生命之伟大而将这表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者,已在其次,而也必须自己有相当伟大的心,相当充实的生活。倘若游离了生活,把文章或他种艺术当作孤立的东西来制作,那势必会成为“雕虫小技”的。
自从有了这种觉悟之后,又没有直接投入火热斗争的机会,徐懋庸对于小说、传记一类文学更其疏远了。后来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有诸多不满与失望,则以“不吐不快”的心情写些杂文。他在《自由谈》上发表最早的杂文《见得多》,也是说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生活。他对高尔基的《秋天的一日》法译本有一行“一个见得多的人的记述”的附注特别感兴趣。他认为“见得多”是高尔基的伟大的成因。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作家一般都没有“行万里路”的条件,所以见得少却要硬写,就往往“画虎类狗”,只成就些“风花雪月,恋爱,接吻”而已。在《见得多》这篇只有600多字的短文结尾时,他提到鲁迅,“不过,我们曾有在农村见得多的几位作家,例如鲁迅,因此,我们还能有《呐喊》和《彷徨》等作品”。
徐懋庸给见得少又想当作家的人开了一个不必耗巨资行万里路,也可以“见得多”的药方,那就是农村。他善意地劝告一些作家,“切莫永远自己禁锢在都会的亭子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