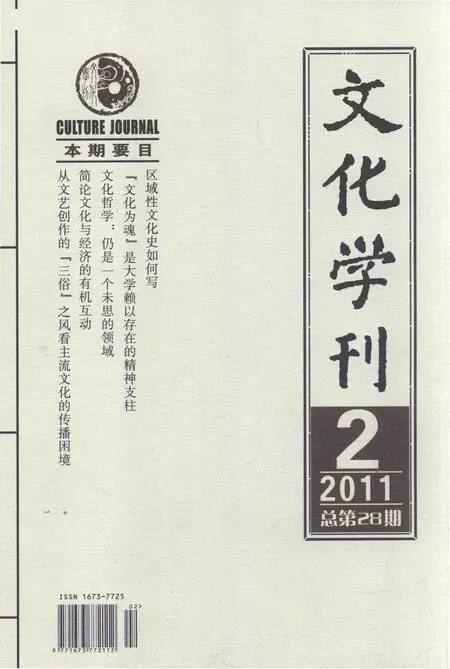自述与文学想象的建构
——以王小波的文本为例
2011-03-20刘芊玥
刘芊玥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自述与文学想象的建构
——以王小波的文本为例
刘芊玥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不仅仅是对某个族群民族事项的记载,也是关于小型社会中的边缘人群、大都市小型社群的边缘人群的描写。本文主要选取王小波的三个同性恋文本——社会文本、小说文本、电影文本——来进行分析,以“纪实与想象”为视角切入,建立起三个文本之间的关联,并试图从中得出有关不同文本之间“想象再生产”的初步探讨。
民族志;文本;纪实与想象;自述;想象的再生产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1]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2]因此,民族志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不仅是对某个族群民族事项的记载,也是关于小型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或大都市小型社群的边缘人群的描写。而同性恋,即属于这种边缘人群之一。具体到民族志的“纪实与想象”上来时,笔者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民族志纪实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任何纪实都是想象的一种,这种想象本身形成自己的一个世界,其间的每一个目标都力图指向真实,以达到纪实的效果。
本文主要选取王小波的三个文本——《同性恋亚文化》、《似水柔情》和《东宫西宫》来进行分析,以“纪实与想象”为视角切入,建立起三个文本之间的关联度,并试图从中得出有关不同文本之间“想象再生产”的初步探讨。其中,《同性恋亚文化》是李银河、王小波合著的社会调查报告,《似水柔情》是王小波在调查报告主人公原型基础上再想象完成的小说,《东宫西宫》是根据《似水柔情》为蓝本改编的电影。
一、自述中的有目的的想象
《同性恋亚文化》是李银河在1993年出版的《他们的世界》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后者是王小波与李银河在1989年至1991年完成的对中国男同性恋现状的调查报告。全书共分为九章,其中算上前言,有四篇文章为王小波所作。
在《同性恋亚文化》的序言里,王小波说,此书首次发现了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体,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也正是在这项调查中获得的关于同性恋大量的感性认识直接激发了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热情,在完成小说《似水柔情》以后,他又和导演张元合作,创作了以前者为蓝本的电影《东宫西宫》。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里,我们不难找到小说和电影的大量原生态情节。根据王小波夫妇的调查,“东宫”、“西宫”指的是北京两处著名的同性恋聚会场所——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王小波直接以此为电影命名,其书写用意已非常明显。在《小A的感情生活》一节中,小说和电影的主人公阿兰的形象已隐约可见,尤其是与小学教师相识和相恋的生活事实,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小说和电影的情节中。阿兰被司务长侮辱及敲诈的情节则是来源于王小波调查过程中一位同性恋者被熟人凌辱的口叙实录,而整个小说和电影的核心情节基本是出自于一位被访问者的亲身经历——被警察抓住反而成功地将后者勾引。
王小波的调查报告和李银河的很大的一点不同是他完全采用写小说的叙述方式来写调查报告,比如记者采访、第三人称描述与“我”的现身说法的三位一体,王小波特有的苦中作乐的戏谑,沉默与狂欢的相对,复调结构的回旋等。在这篇访谈中,王小波先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替使用的方式,用半页纸的篇幅来交代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及和B的初识。然后笔锋一转,以“A的故事又可以这样叙述”[3]为开头,用全知视角加“我”的现身说法的方式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王小波这种叙述本身即完成了对社会文本的一种想象,而且在访谈A的过程中他有意识的问题引导导致了A对B及自己单线叙事的分流。在有关同性恋的调查报告中,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研究者,应该怎样解释自身的情感?当研究者不是同性恋者时,他或她如何去了解同性恋者真正关注和侧重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缝隙,研究者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因为其中一定会包含调查者自身的判断。作为旁观者,在问题和目标的设定上已经预先包含了想象的成分。王小波的这篇调查报告和小说故事之间的关联,只是他的小说创作中比较明显的一例,在他的其他有关两性小说题材的创作中,亦深受这个阶段同性恋调查的影响。当然这个问题属于作家经历和文学创作探讨的范畴,在此就不加深入了。
二、“想象的再生产”
从社会文本《同性恋亚文化》,到文学再现的《似水柔情》,再到电影改编的《东宫西宫》,在这个文本不断被书写的过程中出现了“四重想象”,即同性恋自述者本身的想象、访谈文本的想象、文学再现的想象以及电影改编的想象。在此,一个个“想象”不断介入其中,且不断进行生产的循环悄然隐匿于其中。
就同性恋自述者本身的想象而言,《同性恋亚文化》主要是以访谈的方式呈现的,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于王小波夫妇调查所搜集的资料多来源于调查对象本身的自述和自我感觉,因此这些由当事人的感觉建立起来的因果模式是否可以成立,是否是错觉,是否有在无意识中为自己的状况找寻合理性的因素都要打上一个问号。正如王小波在《关于同性恋问题》(笔者注:原名为《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所说,“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没有按统计学的要求来抽样,故而所得的结果不能做定量的推论。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们只是全部同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们转述的,所以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多少有些偏差”。[4]
而就文学文本而言,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主要讲的是一个同性恋者引诱一个非同性恋者成为他们群体一员的故事。前面已对小说和调查文本的不同作了初步勘测,这里笔者把小说和电影放在一起来对比,重点分析它们的差异,以及《东宫西宫》对《似水柔情》的再想象。电影因为叙事媒介的不同,注定和小说的表述方式不一样,在《东宫西宫》中,对小说进行的再想象凭借以下三个“零部件”而最终得以完成:一是同性恋者的自我讲述。小史以窥视者的眼睛去“偷看”以阿兰为代表的同性恋人群以及他们的行为和经历,这双眼睛背后暗含的是所有观众的目光。二是附加的同类叙述——女贼和衙役的情节。若干年后阿兰寄给小史一本自己写的小说,阿兰的回忆和幻想以此为契机被嵌入了小史的倒叙的框架中。女贼和衙役是阿兰和小史的影射,这种有关古代女贼和衙役的情感纠缠的想象暗示了在前一种叙事中没有讲出的东西——衙役爱上了女贼,他最后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实现对爱的成全。这在反面暗示了小史的游移和矛盾,面对阿兰的诱导,他的情感不断地出现波动。两段控制与被控制、捉与被捉充满对位色彩的情节相互对话阐释和延伸,造成一种交错杂糅的结构,王小波对权力的叙述悄然地游走于其中。三则是来自于张元,在主人公小史的游移背后包孕了作为导演的张元的想象,暗示了他为同性恋者呐喊的姿态。这个电影的主题在笔者看来,张元是想表达一种惶惑,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同性恋者,都具有同性的潜能,这种相爱只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道德禁忌无关。
这同王小波多年前的那篇调查报告相比,多出很多意味来。原初的故事文本在其不断的转换、迁移的书写姿态中折射出参差掩映的文化内涵以及此消彼长的话语权力。欲望的诡异流动,不仅使故事所要诉说的情感主题更加复杂含混,也凸显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多重变奏。同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从调查文本、文学创作到电影改编,在这其中出现了一个想象的不断生产的过程,未来还会产生新的想象方式,把这样一个想象的生产不断地进行下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模仿和表现不单单是描摹性的复现,而且也是对本质的认识。因为模仿和表现不只是复现,而且也是‘展现’”。因此,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中,只在于作为戏剧的表现活动中,虽然在其中得以表现的东西乃是它自身的存在”。[5]从王小波不断书写的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只有在不断被展现的过程中才具有生命力,再创造的艺术具有这样的独特性,即它所要从事的那些作品对于这种再塑造是明显地开放的,并且因此使艺术作品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显而易见地向着未来敞开了。
三、被建构的同性恋世界
通过对“四重想象”的分析,笔者企盼达到两个目标:
一是通过“四重想象”,笔者试图对格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中的观点作出回应,即是说,在文化研究中,随着分析逐渐切入研究对象的内部,作为生活事实的同性恋文化和作为研究文本存在的同性恋文化之间的界限现在已经变得模糊。格尔兹曾引用自己田野日志中“模拟抢劫羊群”的事件为例来阐述“深描”的概念,并分析道“有关柏柏尔人、犹太人和法国人文化的描述,必须依照我们想象的柏柏尔人、犹太人和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构建,以及他们用来明确说明其经历的方案”,“这种策略要否认的是,这种描述本身就是柏柏尔人、犹太人或法国人——即它们表面描述的是事实的一部分;它们是人类学的描述——即科学分析的发展体系的一部分”。再加上研究者采用了角色的眼光,从而使得民族志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此外还有第二层和第三层阐释”。[6]因此,研究者的调查著述也是小说,是“虚构的事情”和“被制造出来的东西”。本文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揭示,对共同构成同性恋亚文化一部分的不同文本进行分析,把文中涉猎的社会调查文本、文学文本以及电影文本都视为“故事”,不同的文本从其他话语吸取养分,也对其他话语作出贡献,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故事,它本身都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一种特殊的参与世界的模式。
二是笔者在这几个文本想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想象的再生产”的建构过程。伽达默尔提出过所谓“视域融合”和“解释学循环”的概念,他认为文本的作者总是含有一种“原初视域”,而解释者在解释文本和作者时,由于那种理解的历史性,会产生一种“当前视域”。这种“当前视域”与“原初视域”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由历史情景的改变所引起的差距是任何解释者都不可能消除的,这就给传统解释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所谓“视域融合”概念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理解的过程和实质不是对文本的一种简单的复制,而是把作者和文本的“原初视域”和解释者的“当前视域”交织融合在一起,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域,达到一种新的视域。而这种新的视域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又作为一种前理解成为进一步理解的起点。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理解依赖于前理解,前理解又依赖于理解的循环。正如他所说的,“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7]同理,在各种不同的同性恋文本的构建生成中,想象一旦介入再生产同性恋的建构,就不会停止,而尤其在小说和电影等文学艺术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每一次的新叙述,基本都会附加新的含义。这种想象的结果促进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接纳,也改变了同性恋的自述和社会文本的生产。
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专门讨论过的,他说文本的意义是被构成的,是通过社会历史的进程构成的,经验对象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而是在认知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我以上的篇幅的叙述也主要是想突出实际和被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我们认知的同性恋世界不过是被建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想象再生产”上的一个环节。
[1]陈向明.社会科学质的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2.33.
[2]Wolc tt,F.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R.M.Jaeger(Ed)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M].Washington,DC.1997.328.
[3]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151.
[4]王小波.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1994,(1).
[5][7]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5.416.
[6]C.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7.
【责任编辑:王 妍】
I247
A
1673-7725(2011)02-0161-04
2010-01-18
刘芊 (1987-),女,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