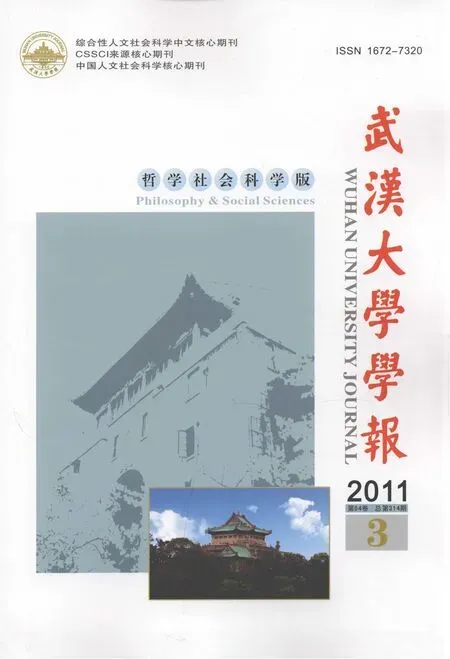行政法学视角下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初探
2011-03-19肖登辉
肖登辉
我们正生活于一个信息无比发达的时代,正行进在一个权利高度张扬的世纪。在五彩斑斓的信息大观园中,个人信息独树一帜、异常夺目,因为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密不可分,可谓“息息相关”。个人信息无处不在,我们几乎成为“透明人”。随着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自身个人信息的保护。
因此,对行政法学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首先,行政法学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可以拓展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领域;其次,行政法学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可以深化行政信息公开理论研究和完善相关立法;再次,行政法学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研究,可以为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试图从行政法学视角围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植根于民法,而且深切关涉行政法。“个人数据法的制定应当说在我国信息安全的保证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兼跨民事和行政两个法律领域。电子商务、电子税务、电子银行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均有待于个人数据法的制定和完善。”①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在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发生于1983年的“人口普查案”是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该案的起因是德国联邦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人口普查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公民进行全面的信息收集,拟定收集的信息范围包括人口、职业、住所和工作等几乎全部个人信息。德国联邦政府的《人口普查法》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在其4月1日生效前,有人提起宪法诉讼要求宣告《人口普查法》违宪。1983年12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后做出判决,认定该法有违宪情况,并做出具体处理:违宪部分无效,其余部分修改后施行。“存储与修补个人信息的技术手段目前掌握在政府手中,注意到这种‘在实践中不受限制的’技术手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一次联邦人口普查延后了近四年之久,原因是人们在1983年《人口普查法》中的某些条款中感到了其滥用的潜在可能。”①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该案直接涉及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虽然是由德国宪法法院审理的案件,但它所反映的正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也就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行政法正是调整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部门法,因此,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法关系密切。
“自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其渗入公民生活的企图就从未停止过。国家权力渗入公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就是对个人信息的收集。”②齐爱民《: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0页。出于履行职责的需要,政府大量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随着电脑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人类跨入信息社会,社会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个人信息成为信息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政府为了各种行政目的,开始利用计算机等现代科技对个人信息进行大规模地自动化收集与处理。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更是如此。因此,行政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控制。行政法的宗旨在于通过控制行政权力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控制行政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具体而言,行政机关在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以及公开行政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不仅包括财产权,也包括人身权。个人信息权是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一种人身权,更具体地说,属于人格权。行政相对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可以分为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两类,个人信息权属于精神性人格权。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名称之遴选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与个人信息具有基本相同含义的其他概念主要有“个人资料”、“个人数据”、“个人隐私”。有的国家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例如,韩国1999年《公共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日本2003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保护行政机关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关于保护独立行政法人等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等;有的国家采用“个人资料”的称谓,例如,瑞典1973年《资料法》,法国1978年《资料保护法》、挪威1978年《个人资料保护法》、冰岛1981年《有关个人资料处理法》、芬兰1987年《资料保护法》、英国1998年《个人资料法》等;有的国家采用“个人数据”的称谓,例如,奥地利1999年《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德国2003年《联邦数据保护法》;有的国家采用“个人隐私”的称谓,例如,美国1974年《隐私权法》、以色列1981年《隐私保护法》、加拿大1987年《隐私权法》、澳大利亚1988年《隐私权法》、比利时1992年《个人资料处理时保护隐私法》等。通观这些国家的立法,虽然在立法名称上有所差异,但其立法意旨基本一致。
在我国,除了个人信息的提法以外,还同时存在着个人资料、个人数据、信息隐私等其他一些类似提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文义先生在其个人专著《个人资料保护法论》中一直采用的是个人资料的提法。大陆地区学者齐爱民先生也曾经一直主张采用个人资料的概念,并明确反对称之为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其观点颇具代表性。其理由主要是:个人信息是个人资料的内容,个人资料是个人信息的物化形式。个人信息的表现和存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一定表现为个人资料,没有物化成个人资料的信息大量存在,比如一个人自然表现出的个人属性。对个人资料进行立法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以个人资料形式存在的个人信息,而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③齐爱民《:论个人资料》,载《法学》2003年第8期,第81页。。
概念其实也只是事物的一个符号,但选择一个恰当的符号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有利于准确表达一定的内涵,正所谓名正言顺。对于上述几种提法而言,笔者倾向于“个人信息”的提法。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从词的本义上看,信息和资料之间是有差别的。首先,资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信息则是资料经过处理后可以提供为人所用的内容,能够直接起到识别的功能,是有价值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人资料都能够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只有具有价值的能够为人所用的资料,也就是信息,才能够成为被保护的对象。个人信息这一概念准确地表达了所要保护对象的特点,具有识别效果和资源价值。个人信息必然是个人资料,但个人资料未必是个人信息。其次,个人资料的财产属性较为明显,而个人信息主要体现的则是人格属性。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护的正是个人信息权这一人格权。
第二,在我国法律中,较少出现数据的概念,它主要在技术领域使用,比如数据交换、数据库。“个人数据”称谓的专业技术性过强,不利于指代一个普通的法律概念,也不利于为人们所了解与使用。
第三,采用个人信息的称谓与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更为契合。我们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信息社会,信息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信息的作用较之以前愈发重要,其价值日益提升。在现实生活中,“信息”一词的使用如同铺天盖地一般,大至国家机关设置,小至市民生活,涉及面也非常之广,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例如,国务院设有信息化领导小组,国家部委中专门设有工业和信息产业部,国务院和地方设有信息化办公室。我们可以使用搜索引擎予以验证:使用google搜索“个人信息”,约有224,00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而使用google搜索“个人资料”,约有141,000,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显而易见,前者的使用数量是后者的1.5倍有余,其使用频率更高。
第四,“信息”概念已经为立法机关所初步接受,正式成为了一个法定术语。许多现行法规中都在使用这一名词。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又如,全国不少地方都已经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已经颁布实施。我国刑事立法已经先行一步。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如下: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这应该是“个人信息”的提法首次进入国家法律之中。从法制统一的角度而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采用“个人信息”的提法更为适宜。
第五,信息隐私或者资讯隐私的提法固然揭示了个人信息与隐私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它没有突出个人信息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言之,它没有揭示个人信息是可以识别出个人的信息这一根本特征,因而,它们都不如个人信息恰当。
三、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关系之厘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的立法宗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而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宗旨则在于保障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立法宗旨迥异,但是,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行政机关所持有的个人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关系紧密。“仅就政府机关而言,个人信息保护与政府信息公开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①周汉华:《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64页。在一般情形下,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并行不悖。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即某种信息(如个人房地产登记信息)既属于个人信息又属于行政信息时,如果一方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公开,此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就容易发生冲突。
随着电子政务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冲突更加激烈。这种冲突实际上是行政知情权与个人信息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两种不同权利之间,是一种权利冲突。正如我国大陆地区学者胡建淼、马良骥所言:“行政机关在保障公众知情权,促进政府管理透明化的同时,可能侵害到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公民的隐私权。”①胡建淼、马良骥《: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法律新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法〉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790页。台湾地区学者李震山也提出:“政府机关管理庞大个人资讯,在要求‘政府资讯公开’与‘知的权利’的民主认知下,是否会侵及个人资讯隐私权,值得重视。”②《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672页。
在处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行政信息公开法之间的关系上,各国立法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分别立法,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此类做法。例如,美国不仅制定了《信息自由法》,也制定了《隐私权法》。又如,日本不仅有《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而且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保护行政机关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与《关于保护独立行政法人等所持有之个人信息的法律》。美国与日本虽然没有采取两法合一的立法模式,但在执法机关上实现了两个制度之间的统一和整合,由一个共同的机关来负责两个制度的实施。在美国,承担该职责的机关是司法部信息与隐私办公室。在日本,承担该职责的机关则是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另一种是统一立法,即在同一部法律中同时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例如,匈牙利的《个人数据保护与公共利益数据公开法》,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与信息保护法》,南非的《信息公开促进法》,泰国的《官方信息法》,都同时规定了行政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现了两法合一。
笔者认为,尽管两法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立法资源,但是,由于两部法律在宗旨上实在是大异其趣,不适宜共存于一体。就现实而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颁布实施,因此,我国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分别立法的做法。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第4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个人信息”或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字眼,但该条规定事实上已经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上做出了一定规范。这一规范还比较模糊,将来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该与行政信息公开法律制度有更好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