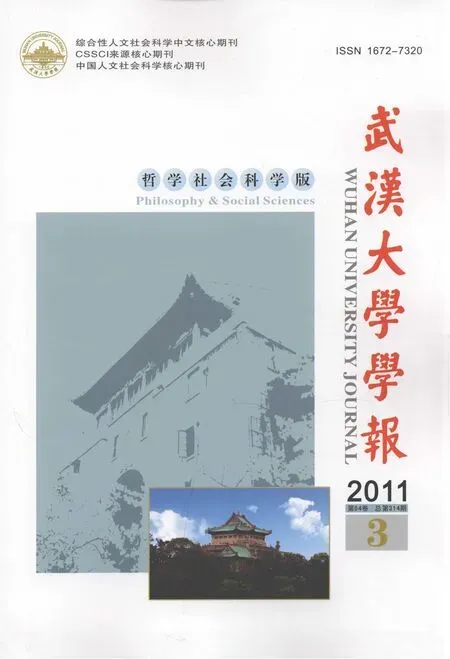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审视
2011-03-19郭锐
郭 锐
批判理论①批判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批判理论是指除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说;狭义的批判理论专指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哲学影响的罗伯特·考克斯、安德鲁·林克莱特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专指狭义的批判理论。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合流,“新—新综合”的理性主义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背景下,率先举起理论批判的旗帜,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多个面向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发起冲击,从而揭开了“第四次大辩论”(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的序幕。这是哲学领域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延伸。批判理论以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对科学主义主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和历史观等诸多哲学范畴中,引导了对于主流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革新或转向,使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走向多元化。
一、哲学基础审视:理论思维的革新
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最具基础意义的哲学范畴。批判理论对主流理论的反思与超越,首先表现为哲学基础上的彻底转向。在本体论领域,它以实践本体论取代了物质本体论,对现实世界的本质进行了重新认知;在认识论领域,它以后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取代了实证主义认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属性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方法论领域,它以历史主义方法取代了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对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构成了批判理论整体理论思维的革新。
(一)本体论的革新:现实本质的重新认知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on)和存在物(ontos)及其本质与规律的学说,其研究的是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和基础②张志伟等《:西方哲学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关于本体论的基本理念,构成了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基底,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例外。国际关系学者在面对所研究的问题时,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观念,即对现实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或倾向于存在第一性,或倾向于思维第一性,抑或倾向于康德式的二元论,不一而足。这些本体论观念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理论思维的基础。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秉持科学主义色彩的物质本体论①崇 尚科学主义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拒斥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但这不意味着理性主义本身没有特定的本体论基础,对其本体论的探讨仍是必要的。。新现实主义把国际政治理解为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强调的权力和国家利益等概念,都以国家间的物质互动(特别是政治军事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为基础,是典型的物质主义。新自由主义以非物质的“制度”为理论核心,但制度的产生仍然是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相互依赖的结果,是国家间硬权力安排的结果,制度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物质性权力的博弈和物质性利益的回报,因而新自由主义在本体论上也是物质主义的。
批判理论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实践本体论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改变了物质本体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践本体论植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以实践来解释存在、揭示本体,认为人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其通过自身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不断改造世界,促进历史的发展②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它超越了物质主义忽视主观能动性的缺陷,将人的实践视为世界一元的本体,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以此为哲学基底的批判理论,把世界政治的三个层次——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均视为由物质、观念和制度三大范畴构成的“历史结构”④罗 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1~204页。,它们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上的,最终来自于人的实践,“是由人的集体行动所造成的,也可以由人的集体行动来改变”⑤罗伯特·W.科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85页。,从而赋予了实践以本体地位。
批判理论在本体论上的革新,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一方面,它否定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把现实世界的本质视为“外在客观”的共同基础假设,突破了主流理论把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范畴视为“给定”因素的机械唯物论思维,从而动摇了物质本体论,揭开了本体论革命的序幕。另一方面,它对现实世界的本质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认知,使国际关系理论界意识到人的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人的主观意识对本体具有建构作用,从而为奥努夫、温特等提出建构主义铺平了道路。
(二)认识论的革新:理论属性的重新思考
认识论是指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以及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而言,它涉及的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批判理论不仅在本体论领域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本质和基础进行了重新认识,还在认识论范畴中对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主体认识和解释客体的经由途径进行了重新定位,由此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属性进行了重新思考。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日渐盛行,实证主义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认识论基石。它把认识对象限制在“经验世界”和“科学问题”上,否定近代哲学上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它秉持科学主义以主客体二元对立为前提的认识论传统,认定主体与客体可以分离,主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现“价值中立”。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义学派,对实证主义推崇至极,试图建立一种实证的、符合“科学”要求的、“硬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和体系⑥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而后行为主义革命时代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都接受了实证主义的理念,在认识论上把现实世界视为某种外在于理论的东西,强调把主体与客体严格分开,认为在对客体的认识中,主体的立场、态度和情感等因素可以完全排除,主张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去探索客观规律或者如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
批判理论并未追随主流接受实证主义认识论,而是基于人本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从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出发,批判理论秉持一种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理论并非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作为主体的人是认识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出发点,任何所谓的客观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都必然受到认识主体的影响和限制。批判理论以此质疑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并非产生于主体对于客观现实的中立观察,而是反映了此前既已存在的社会目标和利益”①Andrew Linklater.“The Achievement of Critical Theory”,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 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sm and Beyon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9.。批判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都包含着预先设定的利益,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批判理论尖锐地指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即考克斯所谓的“问题解决理论”)都是服务于符合既定秩序的国家、部门或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其目标是保守的,其宗旨更与“价值中立”说辞自相抵触②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第192页。。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只是维护现有世界秩序中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
批判理论在认识论上的革新,不仅是基于人本主义立场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否弃,还是对科学主义影响下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性质疑。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属性进行了重新思考,为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成为一系列认同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反思主义理论的先驱。同时,它也促使主流理论逐渐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并在一定限度内开始与非主流理论进行对话,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
(三)方法论的革新: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位
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论。就理论研究而言,它解决的是理论创作通过何种途径、从何种角度体现和反映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③张吉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考——兼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3期,第73页。。具体到国际政治研究中,它体现为实证主义方法和后实证主义方法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解释”(exp lanation),主要使用实证主义方法。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它们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把国家视为“经济人”,认为国家在外在客观结构下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进行博弈,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高度科学主义化的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方法,以市场结构类比国际体系,以公司类比国家;新自由主义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强调制度对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制约作用。
批判理论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治,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tanding),提出了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考克斯将这种国际关系研究的新方法称为“历史主义方法”。与实证主义截然相反,历史主义认为描述是不能离开阐释和理解的④罗伯特·W.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第226页。,它在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中,不寻求创立普遍适用的理论来说明客观规律,也不追求(理性主义强调的)理论的简约性,而是以理解和诠释为目标,关注政治和社会斗争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⑤See J.George and D.Campbell.“Patterns of Dissent and the Celebration:Critical Social Theo 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0,34,pp.289.,从而揭示以具体时代为特征的历史结构。批判理论正是以这种诠释性方法为工具,对世界秩序加以解析,对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和世界政治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揭示。
批判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重新定位导致了研究议程的整体变化,它构建了以批判为取向的理论研究视角,否弃了建立在实证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问题解决”的理论研究视角。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历史主义方法的出现打破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此后一系列反思主义理论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的涌现开辟了一条道路。
二、价值观审视:价值主题的嬗变
批判理论在价值观领域的变革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彰显了人本主义理念,将已被主流理论所剔除的人文关怀重新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中;二是以世界主义价值理念取代了主流理论的社群主义价值理念,使理论研究的价值主体由作为政治性社群的国家转换为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
(一)人文关怀的回归
国际关系学在诞生之初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在一战的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理想主义学派,以探求更和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为宗旨,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试图通过自身的讲授对人们进行启蒙,以克服阻碍人类进步的无知和偏见。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缺陷,国际关系理论的人文气息被成为绝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学派所逐步剔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更使得忽视人文关怀的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国际关系学界日渐盛行。以技术旨趣为取向、推崇实证主义的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以探求国际政治客观规律为宗旨,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诉求。这些被考克斯称为“问题解决理论”的研究范式,充斥着机械的、冷冰冰的利益言说,而缺乏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以深具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思想资源的批判理论,将丧失已久的人文关怀重新引入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中。“人的实在是价值来到世界上的原因”①转引自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2页。,价值不仅与客体的属性相关,更与主体的目的、意愿与需要相关,只有作为主体的人才能赋予客体以意义和价值。基于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批判理论将理论研究的价值关注由客体的效用价值转向主体本身的内在价值。它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作衡量客体的尺度。它以解放旨趣为取向,深入反思既存世界秩序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力图寻找更为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国际政治实践模式,希望把人类从自己塑造的现实困境中解放出来,摆脱压抑人类的异化与不公正。它内在地蕴含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以及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
在批判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国际问题研究,有着主流理论所缺失的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它“触及到全球生活的各个角落:富有与贫困,生命与死亡,变革的渴望与被理解的奋斗”②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677页。。林克莱特主张批判理论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普遍自由、解放的道德诉求,解释和回答人类如何才能建成以人的解放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使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革命的基础的根本问题③陆 昕、白云真《:试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以林克莱特的学术思想为个案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89页。。考克斯的理论也不乏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关注现存秩序中的“浪费、不公正和危险”,包括核毁灭的威胁、常规战争、环境破坏、失业、饥馑等④罗伯特·W.科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290页。,并希望通过世界进步力量的团结和长期努力来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这都体现着批判理论对人本身的关注与重视。
(二)价值主体的转换
传统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是以国家为基本价值主体的。这些理论范式在价值理念上多认同社群主义。社群主义以社群为道德思考的最终价值来源,认为个体的意义与自我实现依赖于所处的社群。在国际关系领域,这种具有价值优先性的社群自然只能是国家。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具有强烈的国家中心论色彩。它们不仅把国家视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还把国家视为国际行为的价值主体,以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为理论研究的实际导向,积极为国家利益的实现建言献策。同为主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虽然避免了现实主义式的强烈的国家中心论色彩,但也是为国家的现实利益代言的。这些主流理论虽然标榜“价值中立”,但它们实际上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作为政治性社群的国家才是它们实际的道德立场。
批判理论在价值观上实现了彻底转向,其理论研究的价值主体由民族国家转换为个人和人类社会。批判理论在价值理念上认同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反对社群主义将国家置于道德优先位置的假设,相对于国家,它更重视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价值。由此,批判理论将个体与人类整体的利益诉求置于作为政治性社群的国家利益诉求之上,将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作为道德价值的基本载体。这种价值主体的转换,促使批判理论重新思考全球政治的规范基础,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持批判态度,并谋求构建更合乎人类利益的新的世界秩序。批判理论认为,它们所确立的一系列世界主义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更好地促进全球范围的自由、正义与平等⑤See Scott Burchill,Andrew Linklat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2005,pp.160.。
批判理论在深层理念上对价值主体的转换,对其经验研究有着显著影响。以安全研究为例,质疑传统安全观,反对像主流的理性主义那样将主权国家视为安全这一国际政治核心价值的主体,认为安全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非国家,“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①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67(3),p.537.。批判理论使安全研究的重心由国家安全向世界安全和人的安全转移,以人为中心,将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世界视为安全价值的主体,促进了安全研究的范式转变。这种研究范式体现了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三、历史观审视:历史哲学的重构
国际关系理论中明示或默示的历史观构成了各理论流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底,批判理论也不例外。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相对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它将历史唯物论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否弃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史观;重新彰显了已被主流的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反对的历史进步论,否弃了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史观。
(一)引入历史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的主要创造,批判理论产生之前,这种引发了对人类历史认知的革命性变化的历史哲学范式,没能进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历史问题上多持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的立场。理想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在探究战争与和平的根本性问题时,言必诉诸“人性”这一形而上命题,就其本质而言仍未脱于唯心史观的窠臼。而后行为主义革命时代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摆脱了唯心论倾向,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界定为体系结构或国际制度等物质性因素,但这种高度简约的科学主义化的理论将上述存在物视为给定因素,忽视了人类实践的能动作用和生产方式的基础性地位,因此从本质上讲只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批判理论否定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唯心史观和机械唯物论史观,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4~705页。。批判理论以这种历史观为其学理底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等理论方法研究国际问题。一方面,它强调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地位,认为在塑造历史结构的人类实践中,生产实践最为基础、最具有决定意义。据此,批判理论“以权力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来研究诠释目前的历史变化”③罗伯特·W.科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主题1。,认为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世界生产分工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国际关系只是特定世界生产秩序中的政治关系,服从于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批判理论虽然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不再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但仍然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想,并把建立在生产结构基础上的阶级结构视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基础,并以霸权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结构(即历史集团)④See Robert Cox.“Gramsci,Hegemon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eds.).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1~133.。此外,它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法、帝国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思想。
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建。它在重视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意义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物质性因素之外的道德、文化与认同等因素,对比经济生产方式广泛得多的人类生活进行更为全景式的分析。它关注政治共同体建构与演进的动态过程,并由此展开了对于世界政治结构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它秉持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理念,强调对话与沟通的重要意义,实现了理论研究中技术工具理性向道德实践理性的转移。这种历史理念上的重建,使得批判理论相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二)彰显历史进步论
关于国际政治是否存在进步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界历来有很大分歧。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将不断向着更好的、更倾向于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这种理念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但残酷的二战使这种思潮跌入低谷。二战后盛极一时的经典现实主义认为进步在国际政治领域并不存在。马丁·怀特声称:“国际政治是一个事件不断再现和重复的领域。”①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载詹姆斯·德·代元《: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页。新现实主义继承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理念,认为国际关系的系统与结构从长时段来看是稳定不变的,并从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视角,将国家和国际体系视为机械的难以变化的物质结构,从而进一步否定了“进步”的可能性。继承理想主义衣钵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论倾向,但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旨趣使其刻意回避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哲学问题,使得历史进步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几近偃旗息鼓。
批判理论的出现使沉寂多时的历史进步论重新回归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域中。批判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体系是社会历史的动态结构,而非纯粹物质力量决定的静态结构;世界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非静止不变的。林克莱特在对政治共同体的研究中,把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共同体视为一个历史变化过程,认为现存政治共同体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会永恒存在。他着力分析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和转型,“探索国际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预测超越边界主权国家局限性之后政治共同体的形态。”②Andrew Linklater“,The Achievement of Critical Theory”,pp.280.考克斯关于国际关系进化的思想则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他认为生产关系的结构会因再生产和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先从起源于简单再生产的社会的最古老的方式开始,然后进步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社会关系方式,最后是在分配型发展产生的方式。”③罗伯特·W.科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第17页。
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批判理论不是像主流理论那样把对既存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而是积极关注体系与秩序的变革。它深入反思国际关系中的不合理因素及其根源,要求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修正甚至革命。它寻求以一种更具善与德性、更有利于人类自身解放的新的世界秩序,以取代充满剥削与压迫,导致人的异化、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理论的意旨是谋求反抗现实、超越异化,引导和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构建更公正、更合理的新的国际公共生活。
四、结 语
批判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和历史观等哲学范畴中,引导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转向。这种变革将人本主义思潮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政治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和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它动摇了理性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为建构主义等新兴学派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由此,批判理论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和里程碑。不过,审视其思想建树的同时,批判理论所固有的理论缺陷也应当引起注意,最突出的一点是其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批判理论不是采取与现存秩序相调和的态度,而是批判、否定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它在本质上认同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认为思维的根本特性是否定性,肯定性思维违反意识本性,因此它对现实不做肯定的理解,只做否定的诠释。批判理论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现实两个层面展开其否定性解读。它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却未能具备成为主流理论的充分解释力;它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了激烈批判,却未能提出改变现状的可行性方案。这意味着批判理论只能是一种处于边缘位置的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