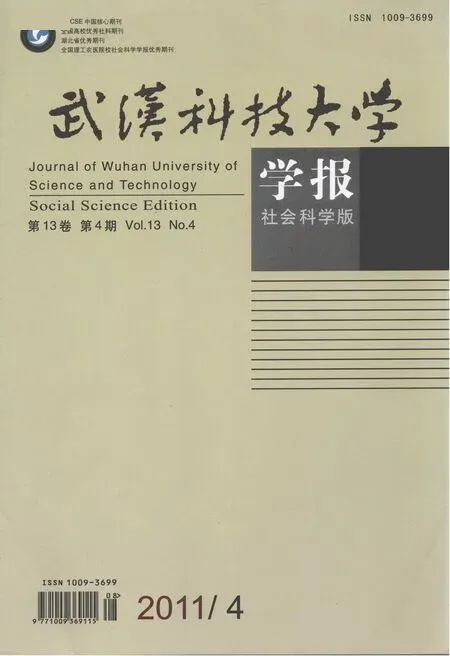空间、语言与生存——福柯生存美学的一个视角
2011-03-19张中
张 中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从空间到异质空间
米歇尔·福柯在考察西方传统空间与时间观时说:“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1]如其所言,与时间备受重视相比,西方古典空间观念在伽利略之前确实较为落寞和孤单。即使是在柏格森那里,空间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然而,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地理空间的“时空压缩”(大卫·哈维语)以及人们思想的解放,使得空间不仅获得解放,而且取得了超越性地位。于是,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开始重视空间的这种地位变迁,也开始重新读解空间的意义。而且洛克、梅洛-庞蒂、列斐伏尔、哈维等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立场,重新赋予了空间以新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福柯不仅在其早期研究中就非常重视空间问题,而且在其中后期著作中,也依然关注这一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福柯不仅发现了“活的”、动态的空间,而且还提出了一种所谓“异质空间”的思想①一般认为,“异质空间”的思想是福柯1967年在巴黎所发表的演讲《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首次提出的。其实,“异质”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应该是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乔治·巴塔耶。作为福柯的精神导师之一,他自然会给福柯带来很多思想资源。。所谓“异质空间”是指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具有差异性、异质性和颠覆性的空间。这一概念既可指现实空间,也可针对虚幻的空间——它特别关注的是那现实性和虚幻性,同时包含体验和想象的空间及其文化实践。事实上,从福柯的早期著作来看,他对空间的重视就潜藏在知识、话语与权力的批判里。比如,在考察欧洲疯癫史和医疗史等问题时,他就发现了对于疯人和病人的控制或“规训”,实际都是与空间密切关联的:早期的对于疯人的流放之“愚人船”,后来的隔离所,甚至晚近的监狱、医院、工厂、学校以及军营等,都是空间分割与规训的场所。所以,他说:“规训涉及空间的划分。”[2]158不过,“规训只存在于多样性存在的地方,基于多样性可达成某种目的、某种目标或结果”[2]158。所以,对于福柯而言,空间的重要意义显然是要发现差异性、异质性,甚至是某种超越性的东西。而这些也将必然逃脱“规训”的力量,颠覆传统秩序,撕裂延续的历史。事实上,福柯凭借空间的转折,也突出了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和“异托邦”②所谓“异托邦”,其实就是“异质空间”的不同译名而已,只是它更强调那种“可能的不可能性”。想象。不过,福柯并不否认历史:“福柯对历史的‘谋杀’也并非真正‘取消’了历史话语,而是使历史具有了更为本真、更为浑整的、空间化的话语形式,促使历史话语从传统的线性‘时间化’形式向后现代的非线性‘空间化’形式的转移”[3]。
虽然福柯的研究大都是剑走偏锋或偏激的,但他十分关注那些长期被遮蔽的事物,尤其是通过对这些事物的“重新发现”,他希望获得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方式。显然空间问题就是福柯的一个研究基点。同时,“福柯这种由‘异位拓扑学’开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促生了后现代的空间政治文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后现代哲学、文学与批评对于实际空间的书写形式”[3]。而且,福柯自己甚至专门写过《论书写》、《论作者》之类的文章,还由此延伸出“越界”与“外部思想”①前者有《僭越序言》,主要谈巴塔耶;后者有长文《外部思想》,主要论布朗肖。等重要的概念和思想——而这些,其实更可以被看作是其“异质空间”思想的拓展和延宕。
现在,回到福柯空间问题本身,我们来看看福柯到底是怎样解释现代空间的。福柯说:“我们生活在空间之中,由此我们自身得到了伸展。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消逝于其中的空间,我们的时间和历史发生于其中的空间,吞噬和磨平我们的空间,也是一个自在的异质空间。换言之,我们并不是生存于某种个体或事物也许置于其中的虚空之中,我们也不是生存于染上了闪亮色彩的虚空之中,我们是生存于一种关系整体之中,这些关系决定了彼此不可还原和绝对不可重叠的位所。”[4]21在这里,人们首先看到,福柯试图转变人们的观念。他认为,现代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的空间。这当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其“异化”;二是指空间的“拓展”。即是说,古典空间的安静、恬适感早已被迅速变动的时代所打破,而人们的心理空间也已经被“异化”。同时,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科技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被一再缩短,那么人的生存空间也就必然遭受挤压与胁迫。由此,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空间或位所的关切和争夺也就愈加重要或明目张胆。
对此,福柯解释说:“在我们今天,位所正在取代绵延,绵延本身已经取代了局域化。位所是通过点与点或要素与要素之间的临近关系来确定的。用正规的术语来说,这些可以描述为系列、树状和格子。”[4]20这就是说,现代人实际仅仅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点状位所里。人们看似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场所,实际上,他只是在“异己”的空间里“漫游”——他没有自己确定性的、稳定性的空间。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这里依然存在着权力:“现代人所追求的理想空间,就是显示自己资本和权力的空间,显示自己占有和排挤他人生活空间的权能的空间。”[5]314由此扩展来说,现代都市空间也都是权力和利益的位所。比如,现代都市努力打造的,那些将交通、环境、商场、审美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社区或广场,实际上它根本并不属于每一个人。可是,它又好像属于每一个人。人们在这里只能获得“此刻”的存在感,而并不能获致稳定的心理空间感。根据福柯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出,其实这些也都是权力的象征、规训的象征;也就是说,现代空间并不能从根本上给予人以自由和解放——至多,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即如福柯所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场地日益代替空间。这首先是因为场地是权力斗争的阵地,而其分布状况及结构是权力斗争的结果”[5]315。
在福柯看来,现代空间并不能从根本上给人带来崭新的生存和自由。于是,人们需要重新发现“异质性”空间,从而将自己的生存引领至新的场域和境地。所以,福柯认为,人们需要寻找“异位”②福柯为此还专门做了”异质拓扑学”式的考察分析,并列出了6个原理,具体参见其文《不同的空间》。即异质性“位所”。虽然他的这种“异质空间”可能只是一种幻想即“异托邦”,但福柯却在将空间进行延伸的同时,也将人们的生存进行了可能性的探讨。而这,显然是一种试图超越的努力。
二、在言语与沉默之间
在福柯的思想中,对于主体的解构和对于理性的批判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也是措辞严厉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僵死的、主流的观念的批判,福柯更是不留情面。比如,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福柯却反其道而行之③虽然福柯前期作品借用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但福柯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并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这一点。:他努力批判传统的、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试图发现语言本身或语言背后的秘密。
相对于萨特“语言是透明的”观点,福柯则认为,语言是含混的、模糊的④这一点倒是与梅洛-庞蒂的观点相同——虽然福柯对其持批判的态度。。语言内部隐藏了无限的秘密和神圣,也暗藏了无尽的压制、暴力和权力。在福柯看来,语言与物质的关系实际上很成问题;也就是说,语言就像马拉美和布朗肖所认为的那样:语言超越于实存之物(虽然是否定的看法);物质具有“不可命名性”。语言是那种“可见之不可见”、“不可能的可能性”之物;它仅仅反映为冰山的一角。即是说,无尽的秘密都在语言之下暗流涌动,同时也孤独而沉默。福柯偏要揭开这个秘密,偏要为沉默而游说。因此,他说:“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6]这样,他也就有理由首先批判道:“一切在物(诚如被表象的)与词(具有其表象价值)之间的关系维度中起作用的东西,已被置于语言内并负责确保语言的内在合法性。”[7]440事实上,福柯在其早期极为关注语言问题,但不久之后,他就用“话语”概念代替了“语言”概念。不过,这些依然都是他批判与解构现代理性霸权和权力的理路。所以,无论是在《词与物》中,还是在《知识考古学》里,概念的转换并没有使福柯调转方向和目标。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的批判依然是其重点——而在其间,福柯尤其注重那些被压制的、处于“沉默”状态的事物。因为,“对福柯来说,理性话语总是扎根于独白理性的不同层面上。这些意义基础处于默默无闻状态,但奠定的是西方理性的大厦,不过,它们自身毫无意义。假如理性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往或冲突来显示自身的话,就必须把这些意义基础挖掘出来,如同对待史前沉默的文物一样”[8]。所以,福柯一直认为自己从事的并非“翻案”的工作,而是一种描述性的“系谱学”。
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摧毁理性,而只是对理性化的策略与程序进行了攻击和颠覆。比如,在对疯癫史和性经验史的分析中,福柯从历史中发现了“断裂”和“间断性”,但也发现了权力和理性的踪迹。所以,布朗肖认为:“福柯没有质疑理性(reason)本身;他只是对一些理性(rationaltities)观点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s)程序的危险性进行了反思。”[9]由是观之,对于福柯而言,语言就是这样的一个批判核心与基准点。事实上,福柯迷恋尼采和巴塔耶——不仅指他们的思想,也包括他们的语言、文风;同时,福柯还对布朗肖、马拉美、萨德的文学作品极为赞赏。换句话说,福柯从他们那里发现了语言的秘密,也发现了语言的断裂。甚至,“福柯同意马拉美的看法,认为寓言的模糊结构使寓言可以表示一切,但又无所表示”[5]470。而这“寓言”,在福柯看来既使人着迷,又使人慌乱。“因为在认识到‘语词’与‘事物’的必然分裂之后,人们既可以抛弃对终极自然之‘物’的幻想,由此走向与‘物’的分裂的、空洞的、无序的‘语言’;也可以揭示出隐藏在任何一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规则,放弃对自然的、无偏见的线性‘话语’的幻想,由此走向无法被语言真正表象的、沉默的、混沌的‘物’的领域’”[3]。可是,做到这些实际上很困难,尤其是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那里,语言是自明的、透明的①福柯对二者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但是,福柯一直试图瓦解传统的(包括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他希望给“沉默”以发言权。甚至在对疯人的沉默进行描述的时候,福柯这种愿望也依然强烈。不过,福柯这种在理性之内批判理性的做法,遭到了德里达的激烈批判。德里达曾嘲笑道:“当人们想去表达疯子的沉默时,他已站到敌对面去了,他已站在秩序一边了。”[10]这就是说,对于语言的批判也必将囿于语言之窠臼,必将回到理性话语本身。当然,这也许是一种“无法之法”,也许是一种策略②德里达的批判文章为《我思与疯狂史》(见《书写与差异》)。面对德里达的批判,福柯极为震怒,并直接导致二位大师开始交恶——但他却在5年后才写出回应文字《我的身体,这纸,这火》。。
但是,福柯却依然试图努力表达这种“沉默”。因为在福柯看来,语言本身就代表理性和权力。若想逃脱语言的牢笼,必须要向外在空间和异质的场域行进。而这种对于“外部”的想象其实既是福柯“越界”的渴望,也是其激进美学意志的表现。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发现了萨德。福柯说:“萨德抵达了古典话语和思想的终点。他恰恰统治着它们的边界。”[7]280在福柯看来,萨德对于欲望、性、色情的近乎疯狂的描写和表达,既是一种“越界”,更是一种探险。而这些既是一种激进的开拓和冒险的姿态,也更是一种对秩序和理性的批判姿态。尤其重要的是,福柯发现了萨德作品中语言的秘密。在他看来,“萨德透过不断重复的语言结构,对细节所作的精细描述,则将他的语言推向了不可感知、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境界。”[11]于是,语言就处于言说与沉默的裂隙处,存在于那些可见与不可见的、可说与不可说的“褶皱”③这(指“褶皱”)是德勒兹著名的《福柯》一书中的重要观点。里。而这也等于是说,语言也就在生存于自身与人的生存的尴尬和期望里,生存于确定与不确定、中心与边缘之间……只是,这样一来,语言愈加神秘、隐晦和含混;可是也愈加迷人。于是,福柯最终抒情地写到:“词默默地和小心谨慎地在纸张的空白处排列开来,在这个空白处,词既不能拥有声音,也不能拥有对话者,在那里,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所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7]393然而,语言的寂寞并不代表其理想即是如此,语言渴望得以表现和稳定——只是,这在后现代显然是一种不必要的幻想。
所以,福柯通过对于语言的关注,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语言关系到人们的生存,也关系到自我的实现。不过,语言所潜藏的无尽秘密永远无法彻底显明。因此,福柯说:“我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简易、我们的自由是如此的受束缚、我们的话语是如此的反复,以至于我们说明,实际上,下面的阴影区必定是无底的大海。”[7]280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那无限的深渊,但语言却以其含混的姿态不断向我们招手;也许,我们永远不能探明语言的秘密,但我们却能通过有限的语言通达那无限的世界……而“人们的命运正是在表象、词和空间这一交叉点上(词表象的空间,并接着在时间中表象自身)默默地形成”[7]154。
三、自我及其生存
由上可见,福柯在人的生存问题上,实际上采用了两种分析策略:对于人的外在生存,他希望从“外部”或“异质空间”来开拓;而对于人的内在生存,福柯则着重从语言来关注和分析。而这二者显然都是事关人的生存,也都是事关自我之构建的问题。因为,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福柯也宣布了“人之死”。而这个大写的“人”、理性的“人”之死,也等于宣告了传统的主体将是破碎的、无处安放的。所以,福柯需要在摧毁它的同时,重新而且合理地置放人的生存。如此一来,福柯也自然就注意到了自我的创造或自我的构建之重要性①这主要反映在福柯后期的美学中,尤其是在《性经验史》和《主体解释学》中表现极为明显。。而这个问题,显然也和他前期的努力即对于空间和语言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事实上,福柯的全部努力,均可看作是其对主体的解构,以及对于新的“自我”的构想。所以,福柯的哲学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生存美学”;而他的“‘生存美学’关心的是实践中的自我,不是神、理念、群体、意志。对于福柯而言,自我不是普遍的,而是具体的;自我作为成熟的个体,是具有启蒙态度和自律精神的个体,自我可以在‘生存美学’实践中不断地深化、构成自己”[12]172。事实上,自我若需自由而自在地生存,必然需要空间和语言;那么,这就需要重新审视福柯对于空间和语言的探讨及与自我生存的关系。
其实,福柯对于空间的关注始终是潜藏于其思想和文本之中的。如前所述,空间对于福柯而言,需要强调其差异性、异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异质空间既能显示人的新异性生存,也能提升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意义。现代意义上的空间实际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孤立和静止的了,毋宁说,它已经成为事关人的生存的重要的、外在的和心里的“位所”。人在空间中的任何行为,都关系到自我的建构和梦想。福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十分重视对于空间的思考和批判。比如,他从边沁所创设的所谓“圆形监狱”考察分析中,发现了权力和规训、空间及其异化。他认为,从监狱、医院、学校、军营,到现代都市、广场等,现代空间的霸权无处不在。那么,在其中,有形的权力和规训形式早已淡化或潜藏,而无形的却在根深蒂固地控制着人们。因此,人们需要打破这种无形的权力和规训;需要向“外部”索解和创造。那么,异质空间就被福柯看作是一种探索,也被看作是一种关于自身的创造。
进入现代以来,语言问题成为了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无论是皮亚杰、弗雷格,还是本雅明、伽达默尔,他们都开始重新思考语言问题——至于维特根斯坦,则更是彻底颠覆了西方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然而,福柯依然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人的存在和语言的存在从未能共存和相互连接。它们的不相容性是我们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7]442。在福柯看来,语言和人的生存关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此,早期福柯试图从文学那里寻找资源,以求解决方案。他一度十分迷恋和赞赏马拉美、布朗肖、萨德、巴塔耶的作品,当然也就十分注意他们对于语言与生存关系的探讨。如前所述,这些作家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从新异的角度嘲笑了传统的语言观:他们强调的是物质与语言的分离性、语言的独立性和模糊性,以及语言与自我生存的关系。事实上,他们这些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异质空间”的探索性努力——只是以语言作为外衣而已。
关于语言,本雅明曾经说:“对人类思维活动的任何一种表达均可理解为一种语言,而这样的理解处处是以一种真正的方法提出新的问题。”[13]所以,本雅明看到了语言的重要意义,但也看到了现代社会中语言的堕落和缺场。同时,本雅明将语言分为上帝的语言、自然的语言和人的语言②按照本雅明的看法,以重要性和源起性而言,这三种语言为递减次序——且人的语言已经堕落。,并认为上帝的语言才是神圣的。他说:“真正的语言是上帝的道的载体,是理性和真理的中介。语言具有内在性,它的本质与人的世俗功利无关。”[14]对于解释学和伽达默尔而言,语言却是作为诠释学经验的媒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取得一致,而“这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理解的真正问题以及那种巧妙地控制理解的尝试——正是诠释学的主题……语言是谈话双方得以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中心点”[15]。不过,维特根斯坦却不这么看,他更强调语言的应用:语言即应用,语言就是生活的全部。因之,他说:“语言游戏存在着——如我们的生命。”“一切都在语言中出现”[16]。维特根斯坦还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17]12-17这就是说,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想象一种语言——包括语言游戏——也就是想象一种空间,想象一种文化。这样,维特根斯坦事实上已经通过语言游戏将生命与他者联结在一起了。当然,这些关于语言的探讨必然会给福柯带来鲜明的启示。
正因为这样,福柯对于语言和人的生存问题的探讨,也就显然并非是形单影只和孤独无依的了。只是与这些哲学家相比,福柯关于语言的探讨往往更加注重语言本身。也就是说,福柯是从语言本身出发的。并且,他从中解读出了权力和压制,也解读出了超越和差异。而这种超越、异质或“越界”的思想,也正是福柯给予现代主体所开的药方与安慰剂。如果说空间关涉自我外在生存;那么,语言就关涉内在生存。而这些却在晚期福柯那里走向了合流,即它们共同融汇在“自我”问题域之内。
晚期的福柯从古希腊和斯多葛派那里看到了新的超越性空间,以及自我构造的可能性。相对于早期对于主体的强烈批判和解构,晚期福柯却有保留地给予主体以一定的位置——尤其是当他看到了“关心自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后。福柯认为,“关心自己包含有改变他的注意力的意思,而且把注意力由外转向‘内’”[18]10。福柯从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之箴言“认识你自己”出发,发现了苏格拉底“关心自己”的极端重要性。因为前者是人对“外部”的探索和思考;而后者才真正回到人本身、生存本身。如果说,早期福柯主要进行的是一种解构性工作,而晚期福柯的工作,则可以说是一种建构性的。即是说,对于“自我”的关注,不仅使人重新认识自己,也使人重新安置自我,重新置放他人与世界——而这些显然就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所以,福柯说:“‘关心自己’就是一种态度: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世界的态度。”[18]10这样,福柯的哲学就逐渐具有了伦理化倾向,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美学”的特征。尤其是晚期福柯开始关注自我的技艺、生命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一种伦理化美学的价值质素之表征。故而,福柯的“自我”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化或美学化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既关系到自身,也关系到他人;既与空间密切联系,也与语言相互缠绕……也正因为这样,晚期的福柯才说:“我们需要将自己创造为艺术品。”[19]
当然,福柯对于大写的主体始终是持解构的态度的。所以,“在自我问题上,福柯与现代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对‘先验’的否定。……他认为,自我根本不是实体,而是一个被构成和自我构成的东西”[12]151。于是,对于现象学和胡塞尔,福柯是批评的。即便是对于梅洛-庞蒂改造之后的主体,福柯依然不满意。至于萨特,他则是嘲笑的。事实上,在福柯那里,先验主体根本不存在,大写的、理性主体更是必须抛弃的。也就是说,虽然晚期福柯重提主体和自我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已经不同于以往——它不再是先验的,而是实证的、历史的。这样,福柯实际上就是开始了新主体(或“自我”)的构建工作。而这一构想既与异质空间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其中,福柯最重视的乃是人的生命和生存问题。这也就是说,“福柯关注的是对生命的策划,这种策划相当于一种艺术和技术;福柯称它们为‘生存的艺术’或‘自我的技艺’”[20]67。而这种生存的技术,也是福柯重新创造自我的策略和路径:“福柯的‘生存美学’基于个体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的‘自我’不是现代哲学中理性‘自我’,而是具体的、实践中的、不可替代的‘自我’”[12]154。在福柯看来,自我是实践性的、具体的和可操作的。他从斯多葛派的自我训练或“苦行”中,发现了自我生存的技术和艺术,也发现了“关心自己”才是首要性事件。福柯说:“关心自己是一种刺激,应该被置入人体内,放入人的生存中,它是一种行动原则,一种活动原则,一种在生存过程中不断担忧的原则。因此,我认为,这个‘关心自己’的问题也许应该摆脱‘认识自己’的权威,它让后者退居其次。”[18]8可以说,福柯的生存美学实际上并非要寻找一种放纵,而是要寻找自由自在的自我生存。在这一生存中,自我既是自由、解放的,又是向异质场域开放、开拓和延展的。
福柯曾经十分赞赏马拉美的诗歌和文学探索,认为马拉美的“寓言”结构其实正是实现他所谓生存美学的路径。在福柯看来,“真正地实现生存美学,就意味着以寓言为模式建构自身的生活,展现自身在复杂的生存过程中的含蓄迂回的艺术技巧,恰当处理非常恼人的‘自身与他人’的相互关系”[5]470。因为马拉美的寓言结构是指,寓言是模糊的——它既可以表示一切,又可以毫无表示。即是说,寓言(也可说是“语言”)既是可见的,又是隐晦的;既能够显示意义,又能够隐藏意义。它就像人的生存一样,既需要直接展现,也需要迂回曲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他人之时:因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决定了人与他者的关系”[20]67。当然,福柯的“关心自己”也并非是要强调自我的霸权和中心主义,或回到理性话语本身,他只是想要提醒人们:像古典生存一样,我们需要回到生存的原初状态。事实上,现代社会的道德将人们囿于条条框框和规范之下,同时也就将人的个性、风格完全阻隔和悬置了。也就是说,现代道德规范实际上将人的生存完全客观化和理性化。问题是,福柯现在想要提请人们注意,我们本不该如此——正像一位美学家所质疑的那样:为什么我们出生时是原创,怎么到最后都变成了拷贝的了?
然而,福柯也并非想要重新确立什么道德或伦理规范——他的生存美学实际上最多能够被看作是一种“境遇伦理学”。也就是说,福柯的自我及其生存,经由空间和语言,经由个体自我的训练、节制和塑造,最终将使自我构建为一种具有开拓性和延展性的生存主体,一种风格化的主体。而这种自我及其生存,其实就像福柯自己所说的那样,“大致说来,古代对快感的道德反思不是旨在把行为规范化,也不是形成一种主体的解释学,而是达到一种态度的风格化和一种生存美学”[21]。
[1]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6.
[2] 米歇尔·福柯.安全机制、空间与环境[M]//汪民安.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8.
[3] 赵奎英.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与本质性写作[J].天津社会科学,2010(6).
[4] 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M]//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
[7]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
[8]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82.
[9] 莫里斯·布朗肖.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26.
[10]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9.
[11] 赖军维.福柯论萨德侯爵之情色语言:古典时期语言的终结?[M]//黄瑞琪.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273.
[12] 李晓林.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3] 瓦尔特·本雅明.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M]//陈永国,马海良.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3.
[14] 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6.
[15] 洪汉鼎.理解的真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281-282.
[16] 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93.
[17]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8]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9] M Foucault.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an overview of work in p rogress[M]∥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New York:New Press,1997:262.
[20] 马库斯·S·克莱纳.愉悦的享用——福柯关于实践的生存美学[M]//马文·克拉达,格尔德·登博夫斯基.福柯的迷宫.朱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1]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