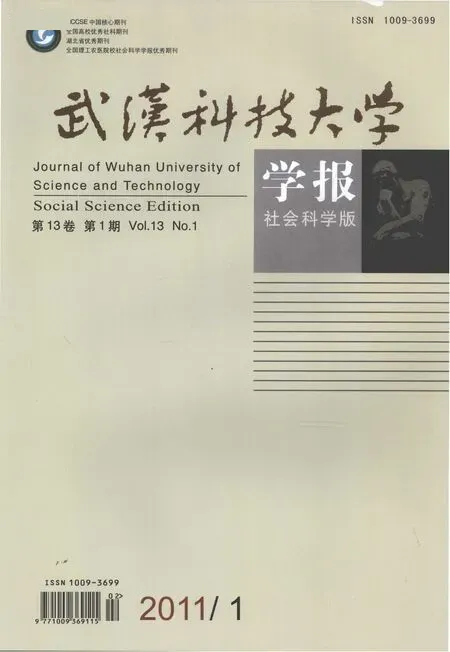论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及其超越
2011-03-19张彦
张 彦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浙江杭州310013)
论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及其超越
张 彦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浙江杭州310013)
近年来,“风险”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风险社会”理论为人们把握当代社会的形态和特征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然而,风险的治理问题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如风险事实与风险判断的困境、风险治理当下与未来的困境、风险主体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困境等。因此,必然要求风险的治理者能正确面对这些困境,从而超越风险本身,超越经济利益本身,超越狭隘个体本身,实现对风险社会的道德治理。
现代风险;治理困境;休谟难题;道德治理;
一、现代风险的特征转向
现代风险的概念,已不同于以往的风险含义和范围。从词源上考察,风险(risk)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 Risicare一词,其词意为“在山崖中航行”,故风险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有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遭受损失、不利、伤害乃至毁灭的可能性”。据考证,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的risque,是在早期的航海贸易和保险业中出现的。因此,在比较早的用法中,风险被理解为客观的危险,体现为自然现象或者航海遇到礁石、风暴等事件。然而,现代风险跟以往的风险界定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人为的、主观的风险大大增加;二是有组织的、体制性的风险来源也明显出现,三是对风险的治理手段也从以往单纯依靠技术进步而倾向于多维度的治理系统。
现代风险的出现与发展跟现代性的自反性理论息息相关。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把整个现代化过程都纳入思考视域,把其结构性断裂解释为现代化自身的后果。在这里,自反性包含双重含义:一是自我反对(self-refutation),二是自我反思(reflection)。自我反对是指以科学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所招致的却是非理性甚至反理性后果,不断地消解着自身存在的基础;自我反思表征的是追求自知和确定性的理性对自身性质的反思,从而具有了破坏其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可能。因此,现代风险的研究既有现代性的本质,又有后现代的指向。现代性的本质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在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寻求价值合理性,表现在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寻求依据;后现代的指向表现为对现代性、现代化的困惑质疑和价值反思,表现为对现代伦理学方法的批判和扬弃。现代风险的研究面临诸多困境:风险事实与风险判断的困境、风险的当下与未来的困境、风险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困境等。由此,必然要求风险治理者作出有效而合理的伦理决策,从而超越风险本身,实现对现代风险的道德治理。
二、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
(一)困境一:风险判断的“是”与“应当”
“是”与“应当”的问题是伦理学的经典难题之一。赫德森说:“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乃是那著名的‘是’——应该问题。”[1]当然 ,最先完整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大卫·休谟。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是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指出理由加以说明。”[2]这就是著名的“休谟法则”或“休谟难题”:“应该”能否由“是”(事实)产生和推导出来?休谟难题的实质就是:在看待事物时,如何从“是”与“不是”的知识判断引发出“应该”与“不应该”(或“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休谟问题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二者是分离的,一开始它们之间并无联系,只是后来由于某种动机才有了联系;二是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二者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知识判断在前,价值判断在后。休谟问题的难度之大,从他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末,没有一个人能对其进行系统论述和解答。1903年,摩尔发表元伦理学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但他只是揭示了以往伦理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自然主义谬误”,并没有真正从正面解析这个难题。
“是—应当”问题落实到现代风险的治理问题上,就是风险事实、风险存在与风险识别、风险评价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由现代风险的存在事实的“是”(是什么)能否推出风险治理的“应该”(怎么做)。同时,由现代风险的这个“是”与“应当”的困境,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困境就是,作为风险主体的人类,是针对风险事实的纯粹解释者?还是作为风险治理的立法者和道德代言人?
其实,关于风险的陈述区别于其他陈述,它既不是单纯的事实主张,也不是惟一的评价主张。风险陈述既是一种事实陈述,又是一种评价陈述。作为一种理性计算的程序和技术时代的产物,风险直接或间接地与文化定义以及与各种生活标准密切相关。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我们必须问自己:生活是什么?我们想如何生活?我们该如何生活?所以,这就意味着,风险的陈述本来就是可以用涉及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解释的陈述。
因此,对于风险的治理来说,应该如何做(ought to be)不能说明自身,它只是意向性的,而意向活动必须以存在论事实为前提,意向性问题的意义受制于存在论问题的意义[3]。如果说,只局限于“应该”这一层次必定从根本上削弱伦理问题的意义,而且最终使伦理学失去根据。所以,就像贝克所说,风险只是指明了什么“不应该”做,而不是“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如何处理现代风险治理中的“是—应当”的困境难题呢?王海明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完全断裂的,可以进行这样的逻辑推理[4]:
前提1:行为事实如何
前提2:道德目的如何
两前提之关系:行为事实符合(或不符合)道德目的
结论:行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因此,关乎到现代风险的治理,我们可以这样推演:
前提1:风险事实如何
前提2:治理风险的目的如何
两前提之关系:风险事实符合(或不符合)治理行为目的
结论:行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
对于风险治理的这一困境,我们在看到“是”与“应该”之间的区别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两者并不是截然不可跨越的,任何的道德判断都是基于事实,就像石里克所言:“最终的评价是在人类意识中真实地存在的事实。即使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科学,它也不会因此就不再是一门关于事实的科学。它的研究完全是实际的东西。”[5]因此,不论我们是现代风险的解释者还是评价者,区分和对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我们所要追问的是无论何种角色它的依据以及合法性何在的根本问题。
(二)困境二:风险治理的“当下”与“未来”
风险概念是一种表述可能性和潜在性的概念,潜在性、可能性是风险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可以是危险形成灾难的可能性,或者是偏离决策目标的可能性,或者是个人或团体反叛社会行为引起的社会失序和不稳定的可能性,等等。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它作为今天经验和行为的归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取代了。我们所讨论的虽然“不是”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进程却“可能”发生。因此,现代风险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和面对未知的未来的努力,是与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紧密相连的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所以,风险治理的第二个困境就在于它的“当下”与“未来”,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预测与混沌之间的矛盾。
“不再——但——还没有”这种独特的现实状态 ——“不再信任/安全,但还没有毁灭/灾难”——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也是风险成为一种公共参照的框架。根据这个参照框架,风险主体对于风险的“当下”与“未来”困境的把握,主要有以下两个认识论的进路:一是认识的有限性。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能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有限的,已有的认识是无限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且是对有限事物的有限认识,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全部认识,因此,人的认识和理性都是不能穷尽的和无限扩展的。这种认识的有限性导致了不确定性的产生。自然科学提供了认识有限性解释进路的样本。二是理解的差异性。同一个“文本”,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诠释,因而诠释具有相对性,这赋予了“文本”不确定性。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必须以“前理解”为前提,它是“前有”、“前见”、“前设”的总合。理解和诠释始终是视域的融合过程,视域融合构成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中介,使两者沟通起来。解释学的“视域融合”为理解的差异性提供了进路的样本。因此,与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的现代风险概念,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道与不知道的合成”。这里可以表述为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在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预测或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由现代风险治理的“当下”与“未来”的困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风险是关注未知、面向未来的。风险意识的确立,表明人类的反省意识和未来意识开始真正觉醒。这种意识来自于人类的自我反省和拯救,来自于将可预测的安全呈现于日益开放的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来自对人类社会的良好愿望,对爱、安全、和谐的希望和追求。第二,风险是向未来开放的、敞开的。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人类新的发展能力的空间,由此也决定了这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和预警性反思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说,现代风险的研究是一个个潜在开放的空间,其疆界是一个个现实的、动态的、“无边界”的过程。它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意义关系,也蕴涵着一种力量,蕴涵着变化与改革。第三,超越传统的时间不可逆的观念。从过去不能决定未来以及未来也不可能受过去控制的时间不可逆性来反思现代风险,我们应以足够丰富的想象力去设想未来,使人的此在性不再仅仅取决于由“过去”已经完成了的状态所决定的现实既定模式,更取决于由“未来”的可能状态所引导而做出抉择的将来发展模式。学会以“未来反观”的思维方式来关注未来和积极地塑造未来的心态,去构建一个适合自己生活和发展的生存空间。这些无论对于社会还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困境三:伦理主体的“个体性”与“公共性”差异
现代风险从产生、形成、爆发直至弱化或者消除都无不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如何应对与处理社会风险问题,最根本的是必须从人自身着手,从人的实践活动是否合理出发。但由于人自身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他们的欲望、偏好和价值取向,使他们以不同的态度、观点和方式看待同一个事物,反映在不同时代、社会、民族、群体中,形成不同风俗、时尚、目标、思潮、流派乃至时代精神和发展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的“内在尺度”往往会与公共的“外在标准”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用另外一种表达,就是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中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道德生活的悲剧性和悖论性:悲剧性表现为“一个善和另外一个善的冲突,一种价值和另外一种价值的冲突”[6]205;悖论性表现为社会至善与道德价值的矛盾——“完善的社会制度自动地塑造着完善的人,在这个社会制度里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任何非道德的行为”[6]212。所以,反映到风险主体的人身上,现代风险还存在着“个体性”与“公共性”差异的困境。
尼布尔在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揭示出了这样一种冲突:“社会需要和敏感的良心命令之间的冲突。”[7]由此可见,社会与个体的道德冲突主要表现在前者立足于“公正”,是对社会群体的外在安排,意在用强制性的规范制度来维护整个社会群体的秩序与发展,有牺牲个体道德需求的可能;后者则立足于“良心”,是对个体自觉的内在要求,意在依照个体独有的品性、人格处理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张扬有可能会侵犯社会整体的道德规范。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这一困境的诠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命题: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能自发地提升社会效用,公共物品的产生要靠强制性的或选择性的方式,即要么强制执行,要么以奖惩机制来使外部性内化。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这一理性体现在为产生集体利益所作的投入(成本)和集体利益能够给个人带来的效益的比较中。这种比较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个人获益度、效益独占的可能性和组织成本,而这都和团体的规模、团体的异质性有关[8]。所以,集团利益作为公共物品之所以能产生,在于生产者对其成本-效益的比较分析中,后者大于前者,集体效用就会被生产出来。但对每一成员而言,为集体公共物品生产的付费只有在团体的边际收益超过个人的边际成本时才是“经济的”。因此,这种集体行动包含了巨大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制度成本等,因而难以真正实行,往往会由“集体行动的逻辑”变成“集体行动的困境”。
其实,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不能单纯用经济与否来衡量,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伦理学或政治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语境里,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对每一社会成员给定偏好的尊重;其次,由于社会尊重每一给定的偏好是“自由”所要求的条件,故“正义”更要求社会对每一给定偏好的尊重与社会对其他给定偏好的尊重相容[9]。但是,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尊重和相容是存在困境的,存在着“个体性”与“公共性”、“个人善”与“公共善”之间的矛盾。其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风险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有助于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现代社会机构在肯定了解灾祸的真实性的同时,却否认其发生、隐藏其根源、阻止赔偿或管理。换一种说法就是,风险治理被越来越多的难题所困扰,使人想到必须加强相应法规和管理;但同时,没有人或组织对这些事承担特定的责任。
对这种状态的解释和解决,在风险研究中有两种明确的立场和方法。贝克和吉登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公共性”的制度主义倾向,即要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把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突出出来并给予恰当的定位。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在全社会对激进的思想进行控制,而是怎样用改革和改良的方法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吉登斯、贝克等人的理想是能够在制度失范、道德失效的风险社会建立起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既能增加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与贝克、吉登斯等人相反,玛丽·道格拉斯、威尔德韦斯则立足于“个体性”的主观主义立场,从“风险文化”出发来寻求应对风险的方法。在他们的理论中,实实在在的风险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是谁在认知并强化了风险意识与观念。他们认为,风险意识只是由相对社会中心来说漫游于社会边缘的社团群落引入的,这些社团群落的特定的文化观念促进了风险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认为用“风险文化”来描述当代社会的风险现象更为恰当,风险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因此,在风险应对问题上,他们并不像贝克等人那样强调制度主义主张,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有效地控制风险,而是努力用诸如环境保护运动、绿色运动之类的亚政治运动去防范和化解风险。
当然,现代风险治理的困境还不只以上三个,还存在着许多困境与悖论:诸如作为主体的人是风险治理规范的立法者和道德代言人还是作为风险事实的解释者?这个主体是个体,还是群体,抑或是某个主体?风险主体与伦理主体在这里是否相异?能否融合?风险治理过程中公正原则、自主原则、自由原则、不伤害原则之间的排序问题,等等。如果以上风险的治理困境不能合理地予以解决,那么,风险防范和治理行为就不能切实地实现,就会相应地产生一系列代价:如侵犯主体人性的伦理代价、损害社会公正的伦理代价、破坏生态平衡的伦理代价、践踏制度文明的伦理代价等。因此,人类控制风险行为的实现有赖于现实冲突的合理解决,现代风险的有效治理依赖于道德困境的合理解释,依赖于道德治理的全面实现。
三、现代风险的道德治理
柏格森说:“若认为把道德压力和道德渴望仅仅作为一种事实来考虑,而不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他们的最终解释,那就错了。”的确,作为现实中一种两难选择的风险治理,必须有一整套与这种困境选择相关联的治理系统,这就是道德治理。从风险治理的宏观角度看,“经过长期的经验和理性选择,人类社会对于风险的抵御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组织化结构和与之紧密相连的责任框架,这就是以官僚体系为载体的国家、以股份公司和行业协会为载体的市场和以各种民间组织为载体的公民社会共同构成的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10]121。而道德治理机制内生于公共治理理论之中,是公共治理结构稳定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风险规避的特殊规定。道德治理机制是指通过一系列道德标准及独特的实现方式,对各个层次的治理活动进行伦理约束,以促进其他治理目标的实现。
道德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基本层次,它与公共治理的边界相一致,也是降低治理风险的有效手段。因此,所谓道德治理,就是治理理论在伦理上的拓展,它是一种“非正规约束”的制度体系,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职能,以道德性的善规定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规则等方面,防范和管理伦理风险,制定并达到组织希望的道德目标,以尽可能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各相关者利益的过程。这里的道德治理是广义的,“用一个福柯式的定义:治理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组织或地方,控制、规范、塑造、掌握他者或对其施用权威所采用的各种战略、策略、过程、程序或计划”[11]。
道德治理是超越现代风险的治理困境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风险是伴随着人们的选择和决策存在的,“治理不过是一套实现特定选择和决策的制度安排,它的功能不是消除风险,而是辨别和应对风险”[10]47。风险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判断共同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形式来实现一种理想的秩序,以规避和减小风险。就现代企业的风险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从公司制的所有权分散化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结构特征出发,建构了一套委托代理条件下的公司治理理论。传统的治理理论研究大多偏重从治理结构和为法律、行政系统所认可的正式制度的角度来探讨公司治理问题。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规模的扩大,逐步出现了公司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趋势,并且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剧和具体环境下的制度缺陷,使得单纯依靠正式制度来约束利益主体的行为难免出现不完全性、滞后性,某些主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对处于公司治理活动中的个体来说,其活动的出发点只有与制度的一般原则相适应,才是道德的,才能促进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实现,成熟的道德治理机制能给企业带来长久的稳定”[12]。所以,有人认为公司治理理论的关键词有两个:“信息不对称”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风险”[13]。
道德治理是一种对伦理风险的复合型整体性的治理模式。复合治理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风险的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个人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都是风险治理的参与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过程之外,更不能被剥夺享受治理结果的权利。其次,风险的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这既体现为地理意义上的纵向多层次,从村庄、部落到国家、区域乃至全球范围;也表现为治理领域横向的多样性,人类活动存在的地方都具有风险问题,这些领域都需要治理。第三,现代风险的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全方位的。风险的空间扩张性和时间延展性,使得风险的应对必须从时时处处人人入手,避免风险的扩散,由可能性风险转化成后果严重的风险。因此,现代风险的道德治理不仅仅是民族国家内部的,还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
现代社会,人类多重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各种道德价值观相互碰撞与激荡,经济金融贸易的跨越地区和国界、人类对大自然的无限索取和疯狂征服、科技理性的急剧膨胀和评价霸权等最终将会使人类社会风险重重、岌岌可危。现代风险渗透进了一切领域与行业,每一个个体、组织和政府都应该为现时代的风险负责,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风险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难题,重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重大危害,重视现代风险的伦理决策和道德治理。
[1]W D Hudson.The is-ought question:a collection of papetrs on the central problem in moral philosophy[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69 :11.
[2]大卫·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509.
[3]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上海:三联书店,1994:4.
[4]王海明.休谟难题:能否从“是”推出“应该”[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35.
[5]莫里茨·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孙美堂,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
[6]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7]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蒋庆 ,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201.
[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67.
[9]阿马蒂亚·森.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M].应奇,编.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13.
[10]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1]Nikolas Rose.Powers of freedom: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5.
[12]王克勤.论公司治理中的道德机制[J].思想战线,2005(6):133-136.
[13]王蓓蓓.治理伦理: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J].上海经济研究,2005(10):65.
Modern risk management:dilemmas and transcendence
Zhang Yan
(Divis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3,China)
These years,“risk”has become a key concept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world,and“risk society”theory has offer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apprehending modern society.Yet,risk management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dilemmas,such as the gap between actual risk and risk assessment,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esent risk management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future,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ublic involved in risk.These dilemmas demand that risk managers should transcend economic interest and narrow-minded concern for individual interest,realizing the morally-correct management of modern risks.
modern risk;management dilemma;Hume’s puzzle;morally-correct management
D63
:A
:1009-3699(2011)01-0042-06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0-11-01
张 彦(1979-),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