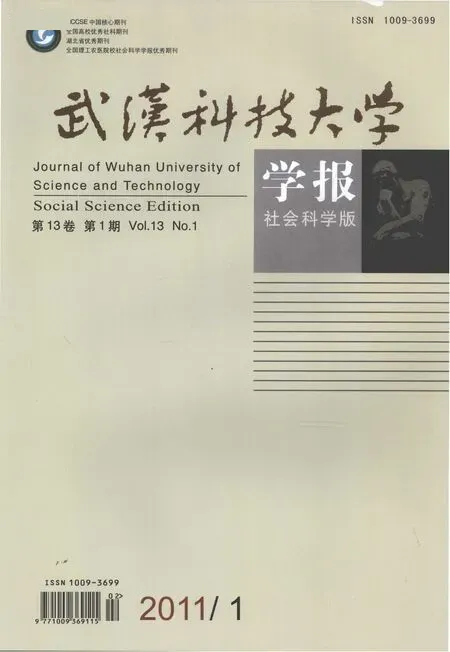转型社会中律师业的结构变迁
2011-11-02郭国坚
郭国坚
(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转型社会中律师业的结构变迁
郭国坚
(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转型时期,社会处在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各种矛盾日益凸现。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重要一环,律师在平衡和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业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同时也因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中国律师业的结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律师业社会结构的调整,促进法律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社会转型;中国律师业;职业理论;知识结构;管理模式;客户取向
一、社会转型与中国律师业
转型是每个社会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社会转型往往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相继产生、激化,因此,有关社会转型的国家治理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政府,同时也对社会如何应对这种急剧变化提出了难题。一般意义上,社会转型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其实质就是传统与现代张力作用下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内,社会结构发生变革,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发生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分化,体现为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及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在经济领域分化的推动下,政治、思想、文化及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相继出现了分化过程,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变化[1]288。社会分化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后果:“积极后果是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功效,社会正是通过内部结构的不断分化来适应环境,求得自身发展的,因此,社会分化程度可以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判定标准;消极后果是社会分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并非任何形式的分化都必然伴随着各个结构要素的功能互补和耦合,都能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有些社会分化会造成冲突、降低社会整合性、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1]288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和防止转型的中断、社会的断裂和失衡,就必须进行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指运用政策、法律法规等手段调整或协调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重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体系的过程,其前提是社会各利益群体的相互依赖性。社会整合的作用就在于使这些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能够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在同一个社会中和睦相处、共存共荣,其实质是异中求同,使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在某种一致基础上结合成一个整体。因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整合是“借以调整和协调系统内部的各套结构,防止任何严重的紧张关系和不一致对系统的瓦解的过程”①转引自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董云虎、李云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一个社会要成功实现整合,关键取决于该社会的成员是否具有参与和合作的精神而达成社会共识,也取决于该社会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能够运用政策和法律等强制性手段对社会进行调控和整合。社会整合最有力的方式便是制度和规范。可见,法制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诉求。
然而,法律系统是如何发挥其整合功能的呢?这就需要对法律系统中的子系统做进一步地考察和研究,即法律的整合功能尚需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人身上。帕森斯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和律师)的活动,不仅使法律体系的功能得以落实,也使法律体系的权威和自主性得到维护;也就是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但是法律系统对整个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要承载者,而且在法律系统内部,它本身就是一个执行整合功能的子系统。作为执行社会控制功能的法律职业,负有使社会成员纳入社会的使命。在法治观念成为社会共同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图景下,法律职业发挥其功能的特有方式表现为:他(她)们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意见,防范不法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或者防范容易引起诉讼的事件于未然;纠纷产生后,可以帮助解决法律争端,或者引导罪犯重新进入社会。从精神病理的角度看,律师对当事人的倾听和帮助,法官的听讼解纷,时常使当事人精神上的压力缓解或减轻;更确切地说,法律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一种间质,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普通公众之间的缓冲器[2]。
问题到这里似乎画上了一个句号,它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进路:社会转型产生社会分化——社会分化需要法律系统来实现社会系统的有效整合——法律的整合功能尚需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人身上即通过法律职业来实现社会系统的整合。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因为人们忽视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在社会转型中,法律职业也处于分化之中。这种分化本身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调控,从而导致法律职业发展出现失范,那么无疑会弱化法律职业在社会整合中应有的功能。西方国家出现的律师业过度商业化、律师职业伦理丧失、律师分布不均衡以及律师间贫富差距拉大等种种现象,都预示了中国律师业发展可能出现的图景。这些现象,有些已经发生,有些正在发生,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变化,并深刻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设法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鉴于此,笔者以法律职业中的律师业为研究对象,就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及结构变迁展开分析。
二、律师业职业化发展与结构变迁的成因
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法律开始从以习惯为主的自然生成法,进化为日益浩繁的成文法,法典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大陆法系国家尤其如此。成文法的发展、体系的完善,推动了民主、法制的发展,也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得以继承。法律形式主义规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当现代社会开始由统一走向分化和利益多元时,管理社会的职能也分化为精细而严密的专业分工,于是职业化的群体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中维系庞大国家和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社会整合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3]。韦伯指出:“在交易活跃的社会中,用以调整有关利害关系人关系的法律日益增加和复杂,因而对法律专业知识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为此能够把当事人的主张准确无误地翻译成法庭标准用语的律师,能够以创造性的合同形式和法律概念并使之得到审判官承认的法律顾问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职业法律家也是加强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条件。”①转引自季卫东:《法律职业化定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我国律师职业获得了发展的良好契机。首先,商品经济孕育了发达的法权经济,其所需的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必备条件;其次,中国社会转型期对民主和权利的呼吁与追求,也为律师职业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权利型社会中,任何权利主体的正当利益,都必须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时代的发展呼唤律师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的法律素养,为社会主体的权利诉求提供保障[4]。与此同时,中国律师业也经历了深刻的结构变迁,它是社会变迁的一个产物,同时也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从逻辑上看,中国律师业的结构变迁是一个递归的过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
西方职业社会学对美国、英国的律师职业的研究表明,法律工作的分化是导致律师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美国律师业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显示出强烈的市场控制倾向。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律师都是独立的私营执业者。到了20世纪后期,私营执业者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在大型律师事务所里工作。美国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律师协会大都创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美国律师基金会 1975年对芝加哥律师业的大型问卷调查,海因茨和劳曼完成了《芝加哥律师——律师业的社会结构》一书。他们在书中指出,芝加哥律师在收入、组织资源、流动性与声望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分化,而决定这种种分化的一个根本性分化,则是律师的客户类型,即为大型企业服务的律师与为个人服务的律师之间的分化。对中国律师业的第一项大型实证研究是由美国学者麦宜完成的,他在2000年对我国25个城市980名律师进行了一次大型问卷调查,并在1999~2001年间对67名律师、法律学者、政府官员以及记者进行了访谈,还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详细观察了48个案件的处理情况。他的研究表明,在从国有制、合作制向合伙制的“脱钩”改制过程中,中国律师业的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类似的分化;然而,这一分化的基础并非不同的客户类型或者不同的法律领域,而是律师与国家的关系[5]。
诚然,中国律师职业的结构变迁并非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其中国家的调控作用十分明显,但无法排除市场化因素对律师业结构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加快和加入WTO的影响,这种作用也日渐凸现出来。此外,律师职业的结构变迁与法律教育的发展密切关联,律师的数量、知识结构、职业技能都与法律教育的发展分不开,这也是由法律职业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变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表现在:推动律师考试制度的建立;推进国办所向合伙所、个人所的转变;推进公职律师、政府律师、公益律师的发展;推进律师行业自治的发展,等等。最后,作为市场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律师工作分工、诉讼类型、律师收入、律师数量等环节。因此,有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在任何一个语境下,律师业的社会结构都将是分化的,客户类型、国家权力、法律工作分工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决定这一社会结构分化的关键。”[5]当然,这种概括只是一种大致的总结,影响律师职业社会结构变迁的还有其他因素,如社会大众的舆论趋向、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等,这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研究。尚需强调的是,律师职业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各种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律师职业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三、律师业结构变迁的现实考察
(一)法律教育发展背景下律师业知识结构的变迁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设有法学院的高校共有389所,占全国2003年所有普通高校的25.06%。从设立时间上看,中国法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并无均匀、连续、渐进的特征;相反,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见表1)。

表1 全国法学教育机构的发展变化表
21世纪以来,全国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截至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法学专业在校生449 295名,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生总数的2.88%。通过对1994~2004年法学院实际毕业生人数和全国律师工作人员数相关性计算,发现这两组数据的相关性即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926 2,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此外,截至2004年,全国共有在读法学博士生6 515人,在读法学硕士生49 060人。1990~2004年间,法学类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21.53%,其中法学类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8.43%[6];同期全国各学科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年均增长率为16.82%。与此相关,律师的人数也经历了结构的变迁,这种变化表现为律师工作人员绝对数的增长和律师工作人员学历水平的提高(见表2)。

表2 1994~2004年全国律师工作人员①律师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专职律师、兼职律师以及律师行政助理、特邀律师、实习律师、其他工作人员。到2000以后律师年鉴取消了这种划分,律师工作人员由律师和律师行政助理组成。另外,由于1994~1999年之间没有关于律师学历的相关资料统计,故而统计的年份从2000年开始计算。数量及不同学历人员数量表
(二)国家推动下的律师事务所管理方式转变
国家的推动作用对律师业结构变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作用通过特定政策的实施、法律法规的制定来影响律师业,这在律师事务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84年8月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后,一些法律顾问处改名为律师事务所,并在经营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的尝试,打破了收入和支出由国家包办的框框。1988年初,广东省深圳市三名青年律师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个体律师事务所;同年3月,河北省保定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随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亦相继办起了合作制律师事务所。1988年5月,司法部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对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设立、组织形式、经营管理分别作出了规定。1993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不再使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行政管理模式来界定律师机构的性质,大力发展经过主管机关资格认定、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的自律型律师事务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对外经济往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律师事业也开始走向国际化。1991年5月,司法部在给江西省司法厅的批复中就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建立业务协作关系一事作出了原则规定。1992年司法部开始进行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试点工作,确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口为首批试点城市。司法部于1992年10月20日首批批准了12家外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律师事务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办事处。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逐步开放。2001年12月19日国务院第51次常务会议通过《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对外国律师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范围、法律责任分别作出了规定。2007年《律师法》通过修改使个人律师事务所得到了法律的“正名”。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律师业社会结构的调整。
(三)市场条件下律师业结构的变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由市场来完成,这种配置是通过法律服务的提供方与需求方的相互关系来实现的。从宏观上看,法律服务的需求促使提供方按照市场需求的方向进行合理地流动;从微观上看,法律服务的需求也促使法律提供方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这种调整表现为针对不同的法律需求的各种内部分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不同的客户对象对律师业务、收入的影响。
1.经济因素、人口、案件数量和律师的有效需求
根据国家“七五”计划对全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同时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调整,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全国被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区。根据《中国律师年鉴》(2004年)所公布的有关律师统计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所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三大经济区域律师分布情况,东部沿海地区律师人数最多,中部和西部地区律师人数比较接近,其中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具体而言:①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所占比率为37.9%,却集中了54%的律师,高于其人口所占比率;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所占比率分别为 33.1%和 28.6%,而律师所占比率分别只有 23.7%和 22.3%,显著地低于其人口所占比率。②以“每10万人口拥有律师数”这个指标进行考察,东部沿海地区为12.4,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6.3和 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合起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律师人数(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大约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两倍[7]。
全国律师分布的非均衡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由于特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形成了经济、资源的优势,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民众和企业的法律需求则促使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而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经济交易量小,法律服务需求的类型少,因而律师服务的收益比较小,于是律师数量比较少。这样一种假设固然有其道理,但这种论述并不充分,因为这种分析只是一种经验的假设,它需要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加以证成。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证成这一推论的意义何在,它能够为实践提供何种理论上的指导。基于此,我们通过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人员数量、案件数量、人口数量、年人均经济总量、律师人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量进行考察(见表3),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律师人员数量和案件数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748 695;律师人员数量和人口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3 081;每10万人拥有的律师数和年人均经济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47 736。这一组数据表明,律师的数量和人口数量、案件数量、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从趋势上看,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案件数量会相应地增多,与之相应,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人员数量也会随之增长。另外,我们还发现,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和年人均经济数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851,两者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律师年人均受理的案件数量会有所减少。这一数据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一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案件数量会随之增多,律师代理的案件数也会有所增加,然而情况恰好相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经济发达地区律师数量一般较大,而较大的律师基数必然会对人均受理案件数起到一种摊平效应。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并不会导致案件数量的无限制增长。西方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社会需要法律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增长将伴随诉讼率的上升;但现代化进程完成后,诉讼的增长将会变得平缓,甚至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到律师代理的案件。

表3 全国律师工作人员数量①之所以没有采用“律师数量”而是采用“律师工作人员数量”来计算,是基于现实环境下律师行政助理在律师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帮助律师完成任务,其作用不可小觑;另外,律师行政助理在律师工作人员中的比重不大,因此论及法律服务,如若不把律师助理也算上的话,未免显得厚此薄彼,因此,笔者将他们也纳入到法律服务队伍中同执业律师一起来进行计算。与律师代理案件数量以及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
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2004年人口1 493万,年人均经济量37 058元,律师人员数11 565人,律师人员受理的案件总数407 058件;上海2004年人口1 742万,年人均经济量55 307元,律师人员数9 917人,律师人员受理的案件总数258 869件。通过比较发现,虽然上海的人口数和经济量都超过了北京,但上海律师受理的案件数并没有多于北京,相反却远远低于北京的案件数,其中非诉案件和其他案件类型低于北京,诉讼案件受理数高于北京。因此,我们不能以上海每10万人拥有的律师人员数量低于北京,就简单地认为上海的律师太少了,应该增加。这种推论没有意识到律师人员的数量还与案件数量相关,律师人员数量的增长如果超过案件数量的增长,那么势必会降低律师年均受理的案件数量,这就有可能降低律师的收入,并且导致律师的过度竞争,危及到律师市场的平衡。
从全国来看,律师人员年均案件受理数超过110件的省(自治区)分别为甘肃 (110.8041件)、河南 (108.0077件)、宁夏(148.3835件)、西藏(525.2949件)。从人均经济量上看,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明显较低,其中河南为人口大省,人口数为9 717万,其他三个省(自治区)则表现出经济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双少现象。由于律师人员需求在这些省份存在较大缺口,必然导致律师年均受理案件数量的上升。此外,各省律师缺口的类型不同。河南省的缺口在非诉案件和其他类案件的需求上,而其他三省(自治区)的缺口主要是在诉讼案件和其他类案件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藏律师人员的数量在全国是最少的,西藏人口共780万,而全省仅有律师人员78人,年均律师人员受理诉讼案件数为423.5513件,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53件)的30倍。这一数据让人们惊叹西藏律师人员匮乏和律师负担之重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解决律师分布不均衡问题的思考。一般而言,律师的分布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有其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源于经济、人口、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得到较快的改变。从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上看,市场的调节具有趋利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特点。这样一些特点和客观性造成了目前律师分布不平衡的现实。应该看到,这种现实虽具有合理性却并不具备正当性。从价值分析的角度上,我们无法回答为何法治成果不能惠及全民?为什么有人在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时其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在少数人那里律师却成为他们的专属品?遗憾的是价值判断只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指导,提供一种理想的状态;它为人们指出了奋斗的目标,却未给人们提供一个途径。因此,对于律师分布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之道,实在需要人们采用一种反思建构的态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2.律师业务结构与客户类型
在律师业务结构与客户类型的考察上,笔者引用了日本神户大学市场化社会法动态学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调查中的相关资料。这份调查以中国北京等8省市的4 312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50 881位律师为调查对象,按照客户分类的每个律师平均民事案件数和所占的百分比做出了系统的列举(见表4),并通过棒线图进行了对比。通过分析这些资料发现,就民事案件而言,中小企业、大企业成为了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客户;其次,个人客户和行政机关客户在客户构成中的比重相当:个人客户的平均值为6.02%,行政机关客户的平均值为9.36%。同时,各省市的客户结构呈现出与经济发展和省情相关的特殊性,如浙江省大企业、中小企业的业务比重就大大超过其他省市。从总体上看,各省市指标反映出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都转向了企业业务,而个人和行政机关的业务则呈现出并驾齐驱的特点。另外,从每个律师平均代理的案件数量上看,最低者为北京和上海,律师平均代理的数量仅为0.638件和0.660件;最高者为浙江和山东,分别为2.146件和1.881件。青海省的平均代理案件数为1.133件,超过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数据,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律师业务的构成;另一方面也为人们研究律师业结构提出了问题:究竟经济发展与民事案件中律师平均代理数量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经济越发达这种数量就越低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浙江、山东的人均代理数量会高于青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北京、上海的人均代理数量会如此之低。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是简单的是或否;换言之,律师的平均代理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关关系,但不是绝对相关,其中还涉及其他一些变量,如:案件总数量,诉讼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比率关系,律师的总数量、其他代替律师功能的个人或团体的数量,等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而是要通过变量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我们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计算出经济的发展与律师的有效需求之间的合理的比率关系。这一结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可以避免律师的过度竞争,指导律师业的流向,乃至对中国法律教育的产出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表4 按照客户分类的每个律师平均民事案件数
四、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得出在市场化的浪潮下中国的律师业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市场化取向,而是指出现今的律师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发生的初步转变。这种转变对律师业的管理与角色的定位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制定律师业的政策之时无疑需要正视这种转变,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回应转变中产生的诸多问题,诸如如何实现律师业的管理?如何弥合市场化取向下律师向大城市的流入以及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需求的普遍不足?律师作为私人在法律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到个人权利的实现问题,更关乎着社会的正义问题,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显著。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此仅仅是提出问题,对于问题的回答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我们期待着在中国律师业结构转型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化解这些问题,并促成法律服务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正义。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学尧.法律职业主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65-71.
[3]陈卫东,韩红兴.2003:法官职业化若干问题思考[G]//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2).
[4]谢佑平.1999:律师职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J].现代法学,1999(1).
[5]刘思达.2005:分化的律师业与职业主义的建构[J].中外法学,2005(4).
[6]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20.
[7]冉井富.2007:律师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一个描述和解释[J].法哲学与社会学论丛,2007(1).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bar system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China
Guo Guojian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In this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China,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come forth one after another due to the polar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ociety.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the bar syste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ettling disputes.Being the product of social changes,the bar system changes as society develops.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bar system in China is a dynamic process.An improved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push forward the adjustment of the bar system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law service market in a healthy and ordered manner.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bar system in China;occupational theory;knowledge structure;management mode;clients’orientation
D926.5
:A
:1009-3699(2011)01-0068-07
[责任编辑 李丹葵]
2010-06-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编号:03AFX002).
郭国坚(1983-),男,福建福安人,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