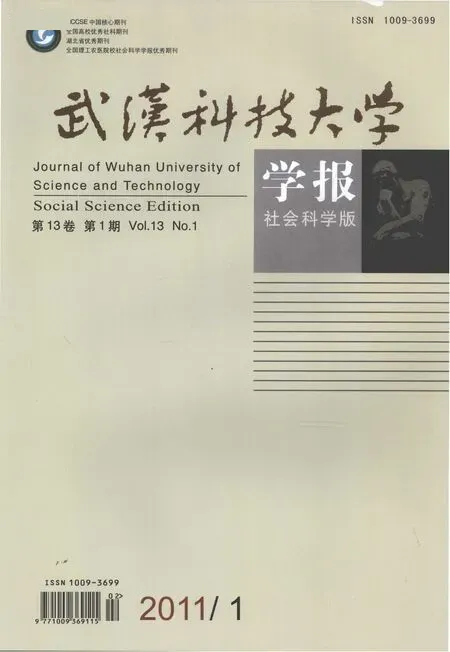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2011-03-19臣刘水静
梁 臣刘水静
(1.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贺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西贺州542800)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梁 臣1,2刘水静1
(1.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2.贺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西贺州542800)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亚里士多德;德性;实践智慧;伽达默尔;道德知识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被认为是对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进行说明的目的论伦理学。对于这种目的论伦理学,传统学者主要从幸福论和德性论这两种视角来进行阐释,而尤以从德性论这一视角展开解释的人居多。然而,这两种解读都难有新意,如果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有所创新,便必须突破原有的解读范式。20世纪以来,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阐释富有新意的哲学家中,伽达默尔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读出了常人所不能读出的东西。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主要体现在其1930年撰写的《实践知识》及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的“亚里士多德诠释学的现实意义”这一节中。笔者认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知识论意义上的解读,即主要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问题。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并未专门探讨道德知识问题;那么,为什么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行知识论解读呢?笔者拟对此加以分析。
一
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学的现实意义”这一节晦涩难懂,因为他并没有说明自己基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什么内容进行探讨,所以要了解他的知识论解读,首先必须了解他所探讨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相关内容是什么。
笔者认为,伽达默尔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阐述的德性品质尤其是实践智慧在道德活动中的作用来进行解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善的概念抽象空洞,既有违于他的思想逻辑,也无助于实践,其本人要追求的是可实践的善,属人的善。而属人的善与德性密不可分,德性从属于善,是善的一个子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德性的人,因此他的伦理学主要是研究德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有两种,即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它们分别是灵魂的有逻各斯部分的德性和灵魂的无逻各斯的即欲望的部分的德性。理智德性由教导而生成,道德德性则由习惯养成。道德德性作为一种品质,意味着在先的考虑和主动的选择,是针对人们自身、选择适度的品质。为了获得勇敢、节制、慷慨和大度等德性品质,成为有德性的人,人们就必须出于自愿和选择地进行道德实践活动,使之合乎德性行为。因此,道德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违反自然,它既可以生成于实践活动也会毁于实践活动,并且只能在实践活动中实现。所以,人们如果研究道德德性,就不能不研究实践;同时,因为实践活动本身并没有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所以人们对德性的研究也只能是概略性的。
但是,道德德性——作为灵魂的无逻各斯的即欲望的部分的德性——离不开实践智慧(即明智)。实践智慧作为理智德性,一方面可以由教导生成;另一方面,它又与道德德性不可分离。亚里士多德说,自然德性离开了实践智慧就不能成为道德德性;同样,离开了道德德性,就不可能有明智。实践智慧同道德德性一起完善着实践活动,所以,实践智慧在德性及其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实践智慧是考虑总体上对于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的品质,它涉及的是实践活动,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173。实践智慧和普遍的东西有关,但实践智慧又考虑具体的事情,“因为实践智慧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处理具体的事情”[1]177。因此,有时不知道普遍的人比知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既然实践智慧涉及具体的事情,那么实践智慧就必然需要经验,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年轻人可以在数学和几何学上学得很好,但他们并不一定有实践智慧,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实践智慧把握具体的事情时需要感知,这种感知不同于对具体事物的感觉,实践智慧的这种感知类似于人们判断眼前的图形是三角形时的这种感知,这表明实践智慧的感知包含理智的成分,接近于数学的感知。
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因为实践智慧的研究对象是实践题材,是可变化的东西,人不会考虑不变的事物,也不会考虑他能力之外的事物。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变的、必然的和永恒的事物。它可以通过演绎获得可证明的知识,因而是可传授的和可学习的。实践智慧也不同于技艺,技艺的对象虽然也是可变的事物,但技艺涉及的是制作活动,而制作不同于实践,它的目的是使某事物生成。因此技艺的始因在制作活动之外,如在制作某个东西时,与技艺相关的制作活动就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与实践智慧相关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做得好就是目的,实践智慧始终将始因即人自身的善把握住,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是能够分辨出善事物的人。技艺不是德性,但有德性,技艺可以有好有坏;实践智慧中没有德性,因为实践智慧本身就是德性,实践智慧就是好的,它指导的行动总是正确的。此外,在技艺方面,出于意愿的错误比违反意愿的错误好;而在实践智慧方面,出于意愿的错误更坏。
实践智慧包含好的考虑和体谅,也与理解相关。好的考虑不是科学式的判断和意见,是“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正确的考虑,这就是明智观念之所在”[1]182。体谅就是对同公道相关的事情做出正确的理解。理解的对象是引起怀疑和困难的事物,所以理解和实践智慧与同一些事物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理解只作判断,而实践智慧则向人们发出一种指令即人们应当做与不做的命令。
二
正是基于上述所探讨的内容,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了知识论的解读。伽达默尔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涉及了正确评价理性在道德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但使伽达默尔感兴趣的东西在于“他在那里所讨论的并不是与某个存在相脱离的理性和知识。而是被这个存在所规定并对这个存在进行规定的理性和知识”[2]404。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知识和道德存在是不可分离的。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抽象而又空洞的善的理念,并用人的具体行为来说明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批判表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德性学说基础——他们把德性和知识、善和知等同起来的基本观点——是片面的和夸大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证明“人的道德知识的基础是‘orexis’,即努力,及其向某种固定态度的发展”[2]405;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试图把道德知识建立在伦理和习行之上。这样,他把德性学说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现在的问题是,道德知识究竟是关于什么的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存在脱离实践的道德知识,如果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不能运用于具体实践,那就是无意义的,并且这种“知识”忽略了具体情况的特殊要求,从而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危险性。如果人总是在他所处的个别情况中遇到善的问题,对于道德知识而言,它就有一个任务,即考察具体情况对人所要求的东西,或者说行动的人要按照一般要求去考察具体情况。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不具有数学家所达到的那种高度的精确性,因此人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概略地呈现事物,从而给德性提供某种帮助。因为伦理学的本质标志之一就是,人是作为行动者来认识自身和决定自身的,并且他的这种职责是不可剥夺的。对于某种正确的伦理学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是“通过概略性解释帮助道德意识达到对于自身的清晰性”[2]406。这就是说,接受这种帮助的人,比如听亚里士多德演讲的人,他总是希望,他自身通过教育和训练所造就的态度,能在生活的具体情况中去保持并通过正当行为去证明。所以道德知识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道德知识显然不是任何客观知识,求知者并不是立足于他所观察的对立面,而是直接被他所认识的东西所影响。道德知识就是某种他必须做的东西”[2]407。
显然,道德知识不是科学知识。古希腊科学知识(如数学)是一种关于不可改变事物的知识,它依赖于证明并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而道德知识是一种关于人及其行动的知识,它既不依赖证明也不可通过学习而获得。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作为行动者认识自己,他在某种场所同某种东西打交道时,他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知识并不是为了发现什么东西而存在,而是指导他的行动。
道德知识更接近于技艺知识,它们都有指导行动的要求。技艺知识是能够创造某种特殊事物的手艺人的知识。虽然一个曾经学过手艺的人所具有的实际知识,并不比那个只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所具有的知识在实践效果上更优越,却不能表明技艺知识是理论知识,因为他在使用这种知识时,经验是自动被获得的,并且技艺知识总是指向一种活动。在道德实践中,人要做出正确的道德决定,经验从来不可能是充分的,道德知识是必须的。道德意识所要求对一种行动的实际指导并不满足那种在技艺知识和每次成功之间的不确定关系。道德意识所要求的完美性同技艺的完美性虽然存在类似的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种东西,而且它们的区别是明显的。“很清楚,人不能像手艺人支配他用来工作的材料那样支配自身。人显然不能像他能生产某种其他东西那样生产自身。人在其道德存在里关于自身所具有的知识一定是另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将不同于那种人用来指导生产某种东西的知识”[2]409。亚里士多德称这种知识为自我知识,即自为知识,它既明显地区别于理论知识,又区别于技艺知识。
但是,如果人们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本体论上只把自我知识的对象规定为某种能够是别样的个别东西,那么它同技艺知识的区别就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们似乎在实行一种完全类似的任务:做出道德决定的人,在具体情况中去观察正当的东西并把握这一正当的东西。他要做出道德决定,必须先选取正确的材料,并且行动像手艺人的行动那样得到卓越的指导。为了把道德知识区别于技艺知识,伽达默尔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的分析中引出一些对他的讨论有意义的观点。
首先,人们既能学习一种技艺也能忘记这种技艺。然而人们却不能学习道德知识,也不能忘记道德知识。人们并不是站在道德知识的对立面——像选择或不选择一种技艺一样——来吸收或不吸收它,而是总处于那种应当行动的人的情况中,并总是必须具有和应用道德知识。这就说明,人们只能应用某种人们事先自为具有的知识于具体情况中。因此,“道德知识就是人关于他应当成为什么以及什么是正当或不正当的观念。它们表现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德性范畴中,如勇敢、节制、诚实和大方等”[3]48。这种道德的理想观念同那种制作对象的计划对手艺人所表现的理想观念是有区别的。例如,属正当的东西并不可以独立于那种需要人们判定什么是正当的情况而规定的,因为情况本身部分地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而手艺人所要制作的事物观念则完全可以事先被规定,并受它所使用的目的规定。
在一种绝对意义上,属正当的东西也是被规定的。因为它能用法律表述并包含伦理行为规则同时被精确地规定,从而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在司法管理中,“应用”法律的人也需要某种知识和技能,但它们不是技艺。手艺人在进行制作活动时被迫改变计划,以便适应于具体的情况和所与的条件,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关于他想做的事情就更加完善,他只是在执行过程中省略了一些东西,这里涉及的是手艺人的知识的应用及其应用的不完善问题。而“应用”法律的人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中必须松懈法律的严厉性,他要是不这样做就不是正当的;而他这样做是为了发现更好的法律,因为法律本身虽不一定有缺陷,但却是不完善的,因为在“法律所认为的秩序来说,人的实在必然总是不完善的,因而不允许有任何单纯的法律应用”[2]413。
伽达默尔也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法的探讨,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符合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用自然法问题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它不只是适合于法律的问题,而且也适合于人对自己应当是什么的一切概念。虽然道德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存在差异,但在这种差异之中依然存有某种像事物本性这样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承认一般适合于人的东西也完全适合于伦理学教师,因为伦理学教师总是处于某种伦理政治的束缚中,从中获得他关于事物的观念。这些理想观念不是可学的知识,它们只具有图式的有效性并总是首先具体化于行动者的具体情境中。同时这些理想观念不是单纯的约定,而是重新给出事物的本性,“只不过事物的本性本身经常是由道德意识对它们进行的应用所规定的”[2]416。
其次,这里人们看到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概念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根本的变化使得道德知识区别于技艺知识。每种技艺知识都是某种个别东西并服务于某个目的,它不需要自我协商,人们学习了技艺知识就能取得正确的手段。所以在制作活动中,目的和手段都是可以预先被规定的,技艺知识只是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道德知识不是服务于某个单纯的目的,而是关系到整个正确生活的大事;它要求自我协商,是行为者与自身商讨的完成,这种自我协商使得道德知识不具有像技艺知识那样预先获得的属性。所以在道德实践中,手段和目的的知识都不能预先获得,它们都不是某种知识的单纯对象。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既与目的有关,也和手段有关。它不仅是正确选择手段的能力,而且在选择手段的时候指向目的,手段和目的都在应用中融合在一起。对手段的考虑不是单纯服务于所要达到的目的,手段的考虑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考虑,并且使目的正确性得以具体化。
亚里士多德的自我知识也是具体情况的知识,它不是一种被感官所看见的知识,而是努斯(Nous)的看的知识,这意味着人们学会了把道德知识看成行动的情况,同时根据正当的东西去看,这种观看即精神的觉察。“道德知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知识,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掌握手段和知识,并因而使自己区别于技艺知识”[2]418。在技艺方面可以区分知识和经验,但在道德知识里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因为道德知识本身包含某种经验,并且这种知识或许就是经验的基本形式。
最后,事实上,道德考虑的自我知识同自身有一种独特的关系,这使道德知识区别于技艺知识。伽达默尔认为从实践智慧的一些变形中可以知道这一点。比如,理解作为一种道德判断的能力,是作为一种道德知识的德性被引入,它并没有关系到行动的自我本身。人们在作判断时只有置身于某人行动的具体情况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所以这里需要的知识也是关于某个具体情况的知识。具有理解的人,只有他想做正当的行动,并同其他人一起被结合到这个共同关系中,他才对某个行动的人有正确的理解。“具有理解的人并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对面去认识和判断,而是从一种特殊的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隶属关系去一起思考,好像他与那人休戚相关”[2]419。所以理解也不是一种技艺知识。另外,伽达默尔用洞见(Einsicht)和宽容(Nachsicht)来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体谅和原谅。有洞见的人就是愿意公正对待他人的特殊情况,因而更倾向于宽容别人的人。这里也不涉及技艺知识。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伽达默尔并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进行一种单纯的阐述,而是有他自己的眼光,这就是他的解释学理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学的现实意义”这一标题正说明了这一点。他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知识论解读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使这种解读服务于他的解释学基本问题,使之成为解释学应用的一个典范,正如他所说的:“解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流传物必定总是以不同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和特殊东西的关系的问题。因此理解乃是把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2]414其实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并没有涉及解释学的历史向度,只是涉及到了理性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正是基于理性与道德行为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伽达默尔从中发掘出了解释学的基本问题。这才是伽达默尔解读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关键所在。
另外,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学解读也有助于认清和避免那种受现代科学的客观化所支配的精神科学方法论的错误。因为19世纪的解释学和历史学的受现代科学客观方法所支配,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某种错误客观化的结果,伦理学、解释学和历史学都属精神科学,而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则可以揭示出精神科学所具有的不同于那种受客观方法所支配的自然科学的性质。
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进行知识论解读,使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解进一步深化。这种解读并未曲解亚里士多德的原意,而是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文本的基本意义为基础的。道德知识确实包含着应用或实践,它总是规定和指向行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文本中,人的道德德性和实践智慧,并非先天具有的,而是在习俗或教导中形成。人在做道德决定时,德性及其观念同具体的境况和活动是分不开的,这些德性及其观念就可以解释为道徳知识,它们离不开道德活动,并体现于道德活动中。
伽达默尔还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的描述同他自己的探究联系起来,从而表现出了一种从属于解释学任务的问题模式。文本应用于个别情况,不是先有了理解而后应用,而是一开始理解就伴随着应用。在应用中不仅“一般”规定“特殊”,“特殊”也规定“一般”,解释者总是把他应用于文本,同时文本也应用于解释者,这种应用是双向的。所以解释者要想根本理解文本,他就必须把文本同自己的解释学处境结合起来。伽达默尔就是从这种解释学理论的立场出发,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邵华.解释学视域中的实践智慧[D].武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08.
G adamer’s interpretation of Aristotle’s moral knowledge
Liang Chen1,2Liu Shuijing1
(1.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Teaching Divi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Hezhou University,Hezhou 542800,China)
Being practical is fairly characteristic of Aristotelian ethics,and thus practical wisdom has a prominent role in Aristotelian virtue system.By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wisdom,Hans-Georg Gadamer illustrates his theory of moral knowledge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mor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in detail in his works.Based on his fundamental theory of hermeneutics,Gadamer’s approach i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horizon of studies on Aristotle,which serves as a constant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es on Aristotelian virtue ethics.
Aristotle;virtue;practical wisdom;Hans-Georg Gadamer;moral knowledge
B82
:A
:1009-3699(2011)01-0014-05
[责任编辑 李丹葵]
2010-09-19
梁 臣(1977-),男,广西桂林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广西贺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