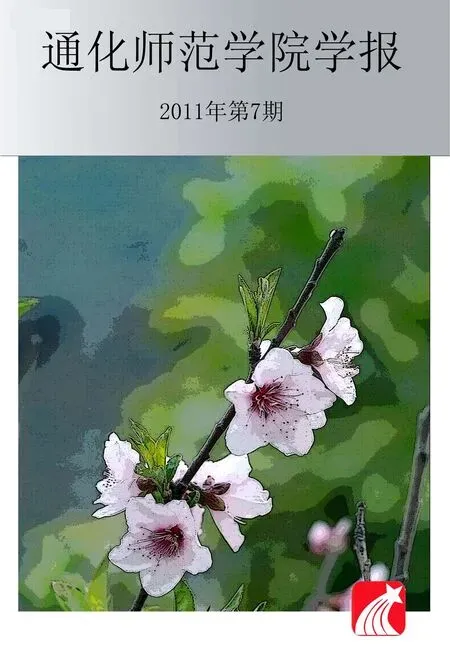歌咏宣传与“抗战建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歌咏宣传目的分析
2011-03-18陈惠惠
陈惠惠
(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江苏南京210003)
歌咏宣传与“抗战建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歌咏宣传目的分析
陈惠惠
(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江苏南京210003)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开展歌咏宣传活动,歌咏宣传的背后有着特殊的政治目的。从歌咏大会和歌曲文本入手,探讨民族主义背景下,国民政府歌咏宣传与“抗战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彰显国民政府开展歌咏宣传活动的目的,充分展示宣传与政治的关系。
歌咏宣传;抗战建国;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重视歌咏宣传,积极开展各种歌咏宣传活动。为进一步探讨国民政府歌咏宣传开展之目的及成效,本文主要从具体微观的层面,选取歌咏活动举办中常用形式——歌咏大会及歌咏宣传的内容凭借——歌曲文本,从歌咏活动的具体操作过程及歌咏活动的宣传内容角度剖析国民政府开展歌咏宣传的深层目的,探讨在民族救亡背景之下,国民政府歌咏宣传与“抗战建国”的关系。
一、歌咏活动分析——以歌咏大会为例
1935年2月22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干事刘良模组织上海“民众歌咏会”。该组织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是为民族解放而唱歌”,并要求会员“学会了抗日救亡歌曲要去教别人”。[1]“民众歌咏会”成立之后以多种形式开展歌咏活动,传播救亡歌曲,并在全国各地设立有众多分会,发展较快。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歌咏大会,这是歌咏运动史上出现较早、规模及影响均较大的一次民众歌咏宣传活动。此次歌咏大会有近千人歌唱、5000多群众到会,其间包括男女电影明星、学生、工人、商民及士兵,各阶层人士因歌咏演唱而空前聚集。
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使歌咏大会逐渐成为一种比较典型的歌咏活动举办形式,国民政府对此也常予以运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所举办的歌咏大会次数颇多,大多与抗战动员相联系。这里所指之“歌咏大会”,取广泛概念上之意义,其具体开展形式不固定于单纯的歌咏演唱,结合其他形式的宣传亦包括在内。一般来说,歌咏大会参加人数众多,以集体唱歌作为主要活动方式,由歌咏团体与民众广泛参与。其目的在于唤起民众意识,宣传与抗战动员有关之思想。
从仪式上来讲,尽管歌咏大会举办形式不固定,但大规模的歌咏大会仍具有一定的程序。歌咏大会开始后,一般先由领导或与会者讲话,阐明举办歌咏大会的目的,而后才是歌咏表演节目,分为“开会”和“歌咏”两个部分。如1938年7月31日武汉举行儿童联合歌咏大会,大会先由主席吴新稼报告歌咏大会的意义,“使大家明白当前的时局,和听了这些歌以后要作到的事;担负起保卫武汉的责任,出钱出力来救国”[2]等等,接着是卫戍总部政治部代表讲演,儿童代表亦上台报告流亡经过,此后进入正式的歌咏表演。
1942年3月29日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由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及白沙教育推进委员会主办音乐月万人大合唱。此次大合唱于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操场举行,有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等13所院校参加节目。大会会场布置极为隆重,据此次大会参加者回忆:大会司令台正中,悬挂着古琴形的大会会标,会标上书写着‘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白沙音乐教育推进委员会主办,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司令台的两边贴着一付对联,上联是:百鸟争鸣群山翠,下联是:万人齐唱满江红。大会场的进口处扎有高大的牌楼,场中向四方拉线悬挂着无数三角形的五色旗,宛如欢庆佳节。近五千名学生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场中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会场四周围集着约二、三千群众。白沙私立三楚小学的童子军,手持军棍,负责维持秩序。[3]79
由会场布置仪式可见,歌咏大会极为重视气氛的烘托。在此种气氛之中,民众的情绪易于受到感染而被调动起来。此次歌咏大会同样由“开会”与“歌咏”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先由大会司仪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游世华先生宣布开会。全场肃立,唱国歌,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行最敬礼,主席敬读国父遗嘱后,大会主席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谢循初先生致开会词,教育部音教会代表和来宾代表分别讲话,此后歌咏合唱节目正式开始。
歌咏大会举行过程中,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常有互动。与戏剧等其他表演形式不同,歌咏大会中的观众所扮演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观众角色,他(她)的身份在歌咏活动的具体进行中会发生转换。受演出气氛的感染,观众往往会被带动而与表演者一起表演,从而兼具观众与表演者的双重身份。此外,由于底层民众智识水平普遍较低,为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歌咏大会的表演者重视讲求技巧性,他们往往在演出之前向民众解释演唱歌曲的内容,使得民众能大概了解表演的内容及目的。在演出休息间隙或者表演结束后,大会的表演者通常会教授民众学唱易于记忆的曲目,从而使得现场之民众能真正参与到仪式表演中,也进一步扩大了歌咏大会的影响力。如1940年2月13、15两日晚,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赴筑市民教馆为征属军人子弟学校开征募基金音乐会各一次,听众约千人,情绪热烈,尤以《满江红》、《游击队》、《赴战》等歌最为听众所欣赏,当正团长说明歌词音节大意,“听众致有随声合唱者,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歌声之雄伟,为从来所未能有之记录。
从场域来分析,由于参加的人数众多,歌咏大会突破了在狭小的剧院、戏院、会堂等空间举办的常规,将举行的场地扩大到露天的广场、体育场、操场等广阔空间中来。虽说仍有不少歌咏大会于剧院、戏院、会堂等室内空间举行,但更为多数的歌咏大会,尤其是有大量民众参加的歌咏大会多于室外举行。保卫大武汉时期,政治部所组织施行的歌咏大会即多于室外广阔之处举行,如1938年4月9日抗战宣传周歌咏日,由武汉三镇所有歌咏团体于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广场歌咏;1938年7月28日政治部孩子剧团于武汉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武汉各儿童团体联合露天歌咏大会……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之后,于室外举行的歌咏大会也不少。如1941年3月12日教育部所举办之千人大合唱则于渝市夫子池新运模范区广场举行。歌咏大会由室内转向室外广阔的场域,使得歌咏大会的举办更加易于操作,举办的成本也更为低廉。戏院、剧院等举行的歌咏大会,大多有人数的限制,需要凭票入场,而底层民众能进入戏院或者剧院观看歌咏节目者甚少,在广场等公共场域所举办的歌咏活动则免除了这些繁琐的手续,只要有兴趣民众即可加入到歌咏宣传的活动现场中,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距离也更为接近,易于宣传之开展。此外,由于空间限制的打破,民众也会因为歌声的吸引而加入到围观者的行列,由此有利于歌咏宣传的进一步扩散。受空间的开阔,声音传播范围的限制等等,歌咏大会举行过程中往往还需借助扩音器、喇叭等现代设备,这些现代工具有利于召集民众,如1942年2月8日下午,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为响应国家总动员文化宣传周举办露天音乐会,地点定于夫子池广场,为召集民众,“两点多钟的时候,从扩音器里放送出的歌声,飘扬在广场和附近的街道上,招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听众”[4]。
就歌咏大会举办成效来看,它所取得的动员效果比较显著。歌咏大会往往能吸引多数民众参与,民众在观看表演的同时常常受到歌声的感染,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抗日救亡的思想教育。此外,歌咏大会往往具有特定的政治主题,有直接现实的目标,如筹款劳军、献机救国、慰劳伤兵、救济难民等。这些现实的目标,通过歌咏大会这样的民众号召形式,一般都能较为顺利地实现。如1938年7月19日晚,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会主办献金音乐大会。此次大会在光明戏院举行,以售票方式筹款。“晚上八点钟,光明影戏院比平时更热闹,听众们慷慨地买票,他们怀着一个信念:今天的钱不是给老板,而是奉献给伟大的抗战,打退我们的敌人。”[5]1938年8月9日为节约运动最后一天,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号召歌咏漫画火炬大会游行,“数不尽的团体,数不清的群众,大路上拥挤着听歌看画的群众,狂热的歌声和激奋的口号,刺激得每一个人都兴奋起来,《义勇军进行曲》完了,又是《大刀进行曲》,又是《保卫大武汉》,拍拍拍群众鼓掌,再唱一次《保卫大武汉》……”,此次歌咏大会在民众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围观群众被吸引,高举火炬参加到队伍中,“老年人,儿童们,都能随着大队高唱《时局已到最后关头》了……”,歌咏与火炬所到之处,“群众在不知不觉中便接受了宣传,深受到影响,没有喧嚣,没有讽笑,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每个人都能用严肃的态度来拥护这一个运动的开展了。”[6]又如1938年12月10日在社交会堂所举行的劳军募捐歌咏大会,尽管从技术上来讲,歌咏团体的表演并不成熟,“除行营军乐队,中国电影制片厂和华北歌咏队技术较为纯熟外,其余的都可说十分粗糙。如果照平常的尺度来测量,他们的水准都十分低”,但从动员效果上来看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当儿童保育院的小朋友演唱之时,观众的反应更是强烈,“当他们唱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的时候,许多对小小的眼眶已含着热泪。一位小朋友独唱《松花江》的时候,竟哭不成声,全场除这小孩的悲惨微弱的歌声外听不到旁的声音”。[7]儿童的表演与听众的感观形成了共鸣,许多观众默默地跟着这位小孩流泪。在这样悲壮的歌声中,听众情绪受到感染,因此捐款劳军极为踊跃。除了捐款的现实目的达到了之外,听众通过亲身参与这样的表演,情绪被调动起来,当散场的时候,听众和表演者已打成一片,都引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为自由和平而战》。
歌咏大会通过仪式气氛的烘托,充分调动起参加大众之情绪,使民众充分参与到抗战救国的行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歌咏大会举行的直接现实目的。除此之外,通过具有一定意义之抗战爱国歌曲的演唱,歌咏大会传达了抗日救亡的声音,激昂雄壮的歌声取代了社会上的靡靡之音,民众的抗日情绪被激发,民族精神得到张扬,有利于抗建大业的完成。
二、战时歌曲文本分析
歌曲文本作为歌咏宣传及推广的凭借,它的产生往往烙下了时代的印迹。概而言之,民元之前的歌曲,“多以发扬蹈厉、尚武爱国为指归,蓋是时外侮日亟、国耻日深,民族向上精神,异常兴奋”;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肇兴,歌咏之歌词意旨又多趋向道德方面,“以培养良好共和国民为主旨”。[8]至民国十二三年间,社会上流传之歌曲又多转向萎靡颓废之类。“九·一八”之后,抗日救亡之声愈高,爱国志士振臂高呼,群众性质的歌咏活动日益频繁,所传唱之歌曲亦转变为雄壮激昂之调,蹈厉发扬之情蕴涵其中。考察不同时期的歌曲取材,不难看出歌咏与国家民族之关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歌曲文本又同时表述了不同的政权话语。国民政府战时歌咏宣传具有特定内容,下文主要以战时歌曲文本作为主要分析与考察对象,以进一步探讨国民政府歌咏宣传的深层意图。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之后,救亡歌曲及爱国歌曲被大规模创作出来,并且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国民政府为充分发挥音乐效能,曾多次组织制定及颁布宣传歌曲。如1938年12月,中央社会部“以值此抗战时期,音乐效能,至为伟大”[9],特制成《铁路工人歌》,颁发全国各铁路特刊党部转全体工友歌唱,以激发抗日精神,鼓励服务兴趣,并请作曲家贺绿汀作曲,声调词句,均极其雄壮。
为将歌咏宣传的主动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进一步掌握舆论导向,国民政府战时加大了对歌曲文本的审查力度,并由教育部专门审查公布了所谓优良歌曲与歌词。综合考察国民政府歌咏宣传活动中主要演唱之歌曲文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歌咏宣传歌曲多数为抗日救亡歌曲及爱国歌曲,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适应大形势,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抗日救亡的现实因素。此类歌曲与民间音乐团体及中共所开展之歌咏活动演唱歌曲类似。
在单纯的抗日救亡歌曲及爱国歌曲之外,国民政府尤其重视利用歌咏推广宣传自身的政策、主义以及拥护政党及领袖等,企图以此从思想意识上进一步控制民众,维护政党自身的统治基础。如1942年2月8日下午,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为响应国家总动员文化宣传周于夫子池广场举办露天音乐大会,大会开始后,跟在《国歌》后面的是《国家总动员》歌,“在这个合唱里,四五十个嗓子同声地告诉我们以‘总动员’的意义,代表了开会前的讲辞,在节目单上也特别地印出了这个歌的‘曲’和‘词’,为的是让‘加强总动员’的歌声,经过每个人的耳和口,产生出实际行动的力量。”[4]1943年3月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音乐大会,由教育部主办,分十区举行,大会所选歌曲,“除国歌及精神总动员歌等外,以平等新约歌曲为主体……”。[10]其中第三区较场口举行之歌咏节目较有代表性,分别为《国歌》、《精神总动员歌》、《国家总动员歌》、《青天白日满地红》、《自由中华》、《平等颂》、《绥万邦》、《总理纪念歌》。[11]
考察国民政府战时歌咏活动中予以宣传及推广之歌曲,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国民必唱歌曲。所谓国民必唱歌曲,共五首,即《国歌》、《国旗歌》、《领袖歌》、《精神总动员歌》、《精神改造歌》,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为加强国民心理,奠定民族复兴基础起见而下令颁布。[12]该令颁布之后,各级机关均需遵照执行。战时国民政府歌咏宣传网络范围之下,各级学校、机关、团体歌咏宣传活动以及各种民众教育中,大多要求演唱国民必唱歌曲,如1942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即发令给齐鲁大学,规定国民必唱歌曲五首,以此加强对学生思想之控制。为增进兴趣,普及民众教育,在教厅所颁布之民众教育施教教材中,除民族英雄故事及抗战将士壮烈牺牲史实、战时重要法令及有关抗战之知识技能、国内外时事新闻、增进生产及日常生活必备知能、必备公民常识等之外,国民必唱歌曲被列为其中主要内容之一。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国民政府音乐节歌咏活动等亦以国民必唱歌曲作为主要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国民必唱歌为国民政府歌咏宣传中最为基础之歌曲文本。
“不论是属于那一种性质的歌曲,当以国歌为最主要。什么是国歌?国歌是由于民族意识发达以后的产生物。凡是国家与民族间的生存竞争愈厉害,则其需要国歌的程度愈增高。国歌为团结民族向外发展的武器,所以世界上常有已亡之民族,利用这国歌,为唤醒民族恢复祖国独立的运动。”[13]8中华民国《国歌》为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必唱歌曲中之第一首,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展普及民众歌咏宣传活动时期,曾普遍开展国歌运动,要求民众人人会唱国歌,以此激发民众之民族国家意识。《国歌》是孙中山作词的原黄埔军校校歌,歌词如下: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澈始终。
显然,国民政府借助国民必唱歌曲尤其是《国歌》,想要传达的重要思想主要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家民族观念等。“三民主义为吾国革命建国之一贯方针,……自宜继续阐扬,普遍宣传,使一般国民有更坚定正确之信仰,以达成我中华民族之神圣使命。”[14]《国歌》中简单明了地指出三民主义是一切思想的标准,是主旨思想。针对“我国一般人的国家观念,向来薄弱,民族意识,亦不如欧西各国发达,自私自利行他的个人享乐生活,好像国家是国家,个人是个人,国家与个人,秦越相视,……”[15]的现状,国民政府歌咏宣传加大培养民众国家民族意识的力度,《精神改造歌》中即号召民众“争取民族的生存”。此外,《领袖歌》将蒋介石颂扬为国家民族复兴的“救星”,试图以此确立起蒋的政治领袖地位,将民众团结在政党的队伍之下;《精神总动员歌》提出“民族复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三大目标。国民政府通过反复的推广宣传活动,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歌曲文本积极推广其主义观念。
综合考察国民政府举办之歌咏宣传大会,可以看出其目的多数为抗战动员之宣传与号召。从具体的宣传内容,即宣传歌曲的文本入手分析,可以看出,其宣传活动大体上围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四点宣传方针,即“阐扬三民主义”、“倡导全国总动员”、“倡导战时建设,增进抗战力量”、“统一全国意志服从政府法令”。可见,国民政府除动员民众加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队伍、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之现实目的之外,在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歌咏宣传的另一个更深层目的是为了传播主义,激发民族气节,灌输国家民族意识,以完成抗战建国的目标,最终达到巩固国民政府统治的目的。
[1]刘良模.序[M]//高唱吧!中国!——民众歌咏ABC.上海青年会校友组,1936.
[2]儿童歌咏会素描:千万人的歌声都高呼着反抗[N].大公报, 1938-07-31.
[3]陈恩平.一次盛况空前的音乐大合唱[G]//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年代不详.
[4]露天音乐大会,齐唱总动员歌[N].中央日报,1942-02-09.
[5]献金音乐大会[N].大公报,1938-07-19.
[6]节约宣传圆满结束,火炬游行印象深刻,希望国人都努力奉行[N].大公报,1938-08-10.
[7]昨天的劳军歌咏会[N].中央日报,1938-12-11.
[8]潘公展.救亡与歌咏[N].申报,1937-08-08.
[9]中央社会部颁发铁路工人歌[N].申报,1938-12-11.
[10]音乐大会明日分十区举行[N].中央日报,1943-03-11.
[11]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音乐大会[N].中央日报,1943-03-12.
[12]校闻辑要·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颁下国民必唱歌五首[J].协大周刊.1942(8).
[13]仲子通.抗战与国家的歌曲[G]//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编.抗战与歌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14]制订各省市党部三十一年度宣传工作计划要点[N].中央党务公报:第9册,1942-03-16(4).
[15]吕震崐.战时民众歌咏问题[J].浙江教育,1940,3(1).
(责任编辑:徐星华)
Singing Propaganda and"Anti-Japanese War and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EN Hui-hui
(Seco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y,Nanjing Politics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03,China)
After the breakout of Anti-Japanese War,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and promote singing activities for mobilizing the mas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singing propaganda and"Anti-Japanese War and Founding of New China"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ism.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demonstrate the purpose of singing propagand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to fully reveal the relations of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singing propaganda;Anti-Japanese War and Founding of New China;Republican Government
K265.2
A
1008—7974(2011)07—0059—04
2011—03—20
陈惠惠(1983-),女,江苏东台人,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教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