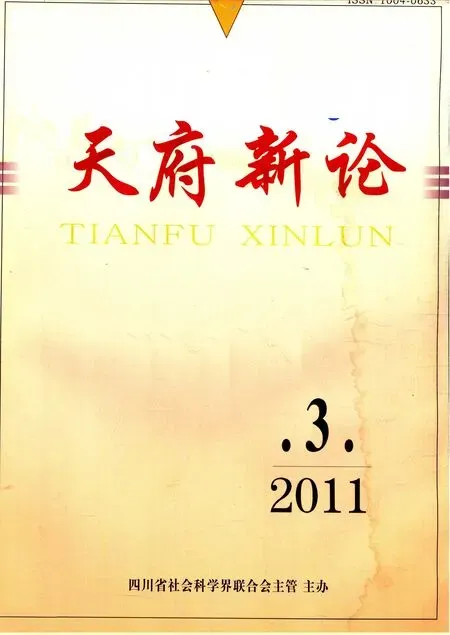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2011-03-18汪太伟
汪太伟
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汪太伟
在近代西方强权外交的背景下,晚清开始向外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具有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复合性,他们出使异邦,思考中外异质文化的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论文拟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以便从整体上对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做出一个合理的界定。“使外文学”的异质文化书写,表现了创作主体在他者语境中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应当在跨学科范畴中加强研究的力度。
晚清;外交官;使外文学;异质文化;交流
晚清使外文臣的派遣
晚清外交官是在近代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不断发生中外交涉事件的形势下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的。19世纪,西方国家早已步入了近代国际观念和体制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往往按照近代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规则来运行。西方国家向清政府提出互派使臣到对方国都常驻一事,早在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表弟乔治·马嘎尔尼勋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来华时就有所提及。〔1〕那时清朝虽已国事衰微,但却依然自尊为 “天朝上国”,只是把马嘎尔尼看作是英国派来的愿意臣附中国的朝贡者,在传统宗藩体制观念的束缚下,乾隆对马嘎尔尼提出的不合清朝道统的外交诉求不屑一顾。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中国与西方各国互派公使的呼声更加迫切。1844年, “法国公使刺萼尼 (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来华亦以通商传教之事”〔2〕,提出了两国互派公使一事。法国公使刺萼尼一方面要求 “遣使进京朝见,即留住京城”;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亦遣使至伊国都驻扎,庶两国消息常通”。〔3〕对刺萼尼的要求,当时责办洋务的两广总督耆英等视之为“越分妄求”,予以“正言覆绝”。西方国家想要外派常驻公使至华的愿望,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得以实现,当然,这种实现的基础是对中国的武力征服和强权交涉,并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款:“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4〕为此,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遣常驻国外的使臣是在 1875年,英国借云南马嘉理事件之机,要挟清政府派员赴英“谢罪”,1875年 8月,清政府正式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衿身 (后改为刘锡鸿)为出使英国的正副使。1876年 12月,清政府开始正式对外派遣驻外使节,郭嵩焘等一行人在举世唾骂之声中出发前往英国“谢罪”。与此同时,清朝又任命美国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副监督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1877年 9月,调任原为驻英副使的许衿身、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驻日本正副使,后许衿身丁忧未能赴任,最终由何如璋、张斯桂任驻日正副使。清政府首批常驻国外使节的派遣,标志着晚清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建立,这些被委任的“公使”,在清政府文书中被称为 “钦差大臣”或“使臣”。
“使外文学”概念的界定
晚清外交官是清政府直接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这些外交使臣在国外广泛接触到近代的科学成就、社会文化和政治思想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走出国门、接触西方、了解世界潮流和探索改革道路的群体之一。晚清使外文臣的著述介绍了世界的情况、不仅使国人眼界大开,而且也启蒙着有志之士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877年 (光绪三年)十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的《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中对出使大臣款定:“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都应“详细记载,随时咨报”。以便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总理衙门认为出使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应随时汇报 “各国如何情形”和 “虚实”,故严令“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 (即总署)备案查核。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报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咨考证”。〔5〕自郭嵩焘等人出使国外以来,出使国外的使外文臣用呈送日记的方法,向总署提供外国“风土人情”和“交涉事宜”遂成为惯例,清政府从这些日记作品中不断地获得了来自国外的各种报道。使外文臣不仅按期递呈日记,很多人还在国内刊发出使时写作的日记和其它作品。1898年前曾有 10位出使大臣刊行出使日记,即郭嵩焘《使西纪程》、刘锡鸿《英轺私记》、陈兰彬《使美纪略》、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李凤苞《使德日记》、张荫桓《三洲日记》、刘瑞芬《西轺纪略》、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和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日记》等,这些作品都是晚清使外文臣出使东西方各国实地考察的内容呈现。
当然,晚清使外文臣关于东西方世界的著作,并不仅仅只限于日记,还有短篇游记、笔记、诗文以及史地专著等。据统计,从 1866—1900年,66人所撰写的有关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其总数就已超过 158部。〔6〕而在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又是晚清外交官的作品。驻德随员王咏霓的《道西斋日记》被誉为“足扩华士迂执之见”。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赅综形势,洞中肯綮,足称洋务中之鸿宝”。黎汝谦翻译的《华盛顿传》因记录了“美国创立民主合众之全规”,被称为“美国开国史略”。黎庶昌“反映19世纪西洋生活的一卷风俗画”的《西洋杂志》,也备受时人追捧。黄遵宪撰写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更是享誉海内外,其《日本国志》被 “海内奉为瑰宝”。据杨易先生粗略统计,在 1898年前,至少有 53位晚清使外文臣的 118部有关外国情况的著述刊行于世。其中以涉及日本的最多,达 15部;英国居次,为 8部;俄国 7部。以日记形式刊行的有 28部;笔记、杂记 、琐记等 23部;政略、志略、纪略等 15部。〔7〕这些著述被大量引用和传播,许多再版以供需求,不仅具有了解异邦,开启民智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晚清使外文臣创作的作品,内容驳杂,形式多样,然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固定的专有名词对其包举而囊括之。学术界对于晚清使外文臣创作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日记、游记、诗文等文本,而对于使外文臣以中外异质文化为书写对象的其它文类则关注不足,这就必然造成对使外文臣整体文学创作现象理解的片面。
若从传统目录学来看,使外文臣的作品除了诗文以外,都应归于史部地理外纪之列 (依《四库全书》分类法)。但“外纪”的概念又似乎过于宽泛,不能体现这类作品的内容特性。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丛书》中采用“载记”一词概括此类作品,但传统的“载记”专指记载历朝历代僭乱遗迹的史籍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用于指称晚清使外文臣对于异邦的见闻记述,并不妥当。单从对日记的概述来说,固然可以用 “星轺日记”〔8〕,也可用朱维铮的“使西记”〔9〕。王飚在与关爱和、袁进《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的对话中,还将晚清的域外游记分为“随行者游记”、“外交官游记”、“流亡者游记”、“考察者游记”和“留学生游记”五大类,〔10〕开始朦胧地注意到了游记作者身份的差异,为此类文学创作的研究提供了分类的启示。
以上研究虽然对使外文臣的日记、游记等一定体裁范围内作品的概括名实相副,然而并没有对使外文臣这种特殊身份影响下的整体文学创作给予特别的留意和关注,亦未能为使外文臣其它驳杂的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找到一个恰当的称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对于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有必要进行整体的观照并作出界定,从而揭示出这种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创作现象的特性,以加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晚清派遣的使外文臣,从文化身份上说,是中国具有较深传统文化背景的杰出士人,在对于清政府的述职呈文等写作中,他们或以政治家的立场,或以传统士人的思考,或兼以文学家的笔触,直接反映了其在使外经历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以中外文化为背景,描述了创作主体参与文化认知的一种身份建构,这一现象,成为认识晚清居庙堂之高的士人担负国家使命与外交责任时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为读者打开了中国传统士人直接面对世界时,其身份建构艰辛选择的图景。这类由使外文臣所创作的作品,笔者拟将其界定为“使外文学”,“使外文学”是由出使异邦的外交官所创作的,以异域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创作现象,反映了异质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自我与他者文化关系的思考,是文学书写异质文化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
晚清“使外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晚清派遣国外的常驻外交官,因此这类作品的内容就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受制于创作主体的传统文学素养之外,也受创作主体使外文臣这种特殊政治身份的影响,并体现了中外文化相异背景所带来的冲击。就使外文臣创作的文学形式来说,由于“使外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和自足发展的文学主体,其所赖以表述和采用的文体,自然也就与中国传统的文类密切相关,因此中国传统的散文 (包括游记、笔记、日记、传记等)、诗歌等文类,成为使外文臣创作时所常采用和驾轻就熟的文体;使外文臣兼具的特殊政治任务和国家使命,又使得他们采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政论,比如奏折,上书等等涉及中外事务的论说文体;另有在日常交往中,使外文臣与异邦人士文章往来,进行学术讨论和文学创作心得交流的书信以及为异邦人士著述所撰写的序,跋等等创作;还有各种政略、志略、纪略等等。这些体式各异的文章形式,都无不与“使外文学”创作主体的使外经历发生着联系,体现出对中外异质文化的思考,因而对以上创作形式均可以“使外文学”的概念统摄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一个整体上来观照和解读使外文臣的创作及其与中外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
当然,对本文“使外文学”中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的涵盖,或许会有不同的意见。“使外文学”定义中的“文学”概念,借鉴自罗根泽先生等人的说法,也是对“文学”采取的折中义,以期达到解读“使外文学”的合理性。罗根泽先生认为:由于取义的广狭不同,关于 “文学界说”,也是各家纷坛,莫衷一是,他说:
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我之采取折中义有三种原因:第一,中国文学史上,十之八九的时期是采取折中义的,我们如采取广义,便不免把不相干的东西,装入文学的口袋;如采取狭义,则历史上所谓文学及文学批评,要去掉好多,便不是真的“中国文学”、真的“中国文学批评”了。第二,就文学批评而言,最有名的《文心雕龙》,就是折中义的文学批评书,无论如何,似乎不能捐弃。所以事实上不能采取狭义,必需采取折中义。第三,有许多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在分析诗与文的体用与关联,如采取狭义,则录之不合,去之亦不合,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而采取折中义,则一切没有困难了。〔11〕
被誉为“批评家们的批评家”的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12〕因此,有鉴于中外文论家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将使外文臣创作中具有中外异质文化因素的政略、志略、纪略、奏折、上书、序、跋等视为 “使外文学”,其中的“文学”一词并非所谓的“纯文学”。
“使外文学”与异质文化的交流
晚清使外文臣具有特殊的多重性身份,他们一方面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特征,在体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与家关系的儒家传统文化濡养之下,他们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断地进行着传统身份的合理定位。而另一方面,晚清使外文臣又是晚清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在中国传统的道统里面,他们无疑要考虑和不断调整自己文人与官员的身份界定。而更为特殊的则是,在出使异邦的域外环境中,晚清使外文臣所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相异背景,这种相异背景所造成的冲击,又使得晚清使外文臣常处于身份调试的尴尬境地。通过分析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创作,可以从中窥视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代表的使外文臣,在自我与他者存在巨大差异性的时代氛围中所具有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以强烈的自卑与自尊,羸弱与坚强构成了矛盾的综合体,展示出晚清文人,尤其是使外文臣一段特殊的心态历程和历史文化景观。中国近代士人在接受异质文化时的复杂心态,客观上也为中国打破原有的闭关锁国的统治格局传递了新声,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提供了参考。因此,晚清的 “使外文学”创作,为异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文学书写范式,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一)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审视中,对于深化自我认识的意义。在文化交往中,自我对他者的借镜,往往带有自我反观的性质。这种状况,以形象学的观点来看,在自我认知他者,并以他者为借镜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折射出某些重要的信息,出使到异邦的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他者形象的建构。
“他者” (the other)一词,虽然目前还没有一致认可的定义,但可以从对“他者”的各种表述中去理解它的本质以及它作为一种文学话语的全部意义。布林克·加勃勒(Gisela Brinker-Gabler)在关于 “他者”的专题论文集的前言中总结学者们关于“他者”的各方面研究时说:“学者们或者把他者作为自我内部的一种变体,或者在种族上、性别上、阶级上或民族上区别自我的他者来探讨,或者涉及另一社会,另一文化的男女他者等论题。”而霍桑 (Jerny Hawthorn)在 1994年出版的文学术语汇编中把 “他者”的所指范围大大拓宽了,“人们将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种制度定义为他者。是将他们置于人们所认定的自己所属的常态或惯例 (convention)的体系之外。于是,这样一种通过分类来进行排外的过程就成了某些意识形态 (ideological)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3〕“使外文学”作品既涉及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遭遇,也涉及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冲击。所以“使外文学”作品既涉及到外来他者问题,也涉及到他者语境下的自我问题,尤其反映出对他者的密切关注。
对他者的关注往往是出于自我的原因。日本学者熊野纯彦说:“在他人的情况极明了、生活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很少能用反省的目光看周围。‘他者’的问题多是在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破绽时才被注意到的。”〔14〕19世纪中后期,中国对西方的关注是因为当时中国文化出现的危机。而今天,全球化对所有的文化都提出了挑战,无论孰强孰弱,东西方文化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每种文化都需要不断审视自我,调整与他者的关系,以利于自我的生存发展。因此,对使外文臣笔下的他者形象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使外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阐释,将“使外文学”文本内部所隐含的文化信息具象化,以此揭示出东西方异邦形象在使外文臣意识中的建构和衍生过程,同时也将折射在异邦 (即他者)形象之上的晚清使外文臣 (即自我)形象的信息展示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更加理性地分析使外文臣认识西方、接受西方的曲折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拓宽使外文臣文学创作的研究视域。
(二)对于完善国家文化形象的意义。无论是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还是前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就从未停止过。在自我与他者的彼此认知过程中,隔膜总是短暂的,而理解却是永恒的,因此暂时的隔膜能否被永恒的理解所代替,往往取决于对于往昔文化沟通困境的认知和对未来所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的思考。斯皮瓦克认为:第三世界作为西方的他者,既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剥削对象,又有需要发现和阐释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这种二重性,现代西方小说一方面言说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公理,另一方面又必然存在着这一公理在干涉第三世界时候的不完全性。这里有着疑窦和空白。这疑窦和空白就是由受压迫文化和受压迫的人不能说话形成的。〔15〕当前,在国际竞争中,作为国家软实力代表的国家文化形象,其地位已日益彰显出来,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如何创建和完善国家文化形象,就不单单只是要认清当前局势,思考和谋划未来发展战略的问题,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脉络加以理清。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以历史过往为借鉴,将当下的梦想变成未来的现实。“使外文学”正是在书写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体现了斯皮瓦克所说的 “二重性”,因此,对“使外文学”的研究,其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也是文学研究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尝试。
(三)为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启示。晚清“使外文学”的创作无疑具有开眼界的作用,然而,若仅仅从猎取异邦奇异物象以取悦统治者和读者的角度来阅读晚清使外文臣的创作,显然并不能凸现晚清“使外文学”的价值所在。应该说,从使外文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对于其所表现的民族心态的考量,更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指出的是,晚清“使外文学”体现出了一个意识到自我与他者存在差异的民族融入世界的过程。这种过程,首先通过作为晚清“使外文学”创作主体的士人面对世界时的心态历程呈现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外文臣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晚清中华帝国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的群体观念,其现代化的诉求也在不经意间被导引出来,认识这一现象,实际上对当前的全球化融入过程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说:“由现代帝国主义发动的全球化过程,使得这些移民人口的声音早已成为事实,无视或低估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的共同经历,无视或低估不同文化源流之间的相互依存,就等于忽视 19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中,通过谋划或对抗性的地理学、叙事和历史叙述而形成同舟共济又彼此排斥的关系。”〔16〕他在《东方学》的后记中还提到:“我的目的,如我前面所言,并非消除差异本身——因为没有谁能否认民族和文化差异在人类交往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是对差异意味着敌对、意味着对立永远无法消解这类观念以及从中产生的以整套对立性认识提出挑战”〔17〕。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在方方面面互通有无,其中占很大分量的就是文化的沟通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我们对自我和他者应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特别是作家和批评家由于政治纷争、种族或文化歧视而衍生的定型化偏见;还有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贬抑他者,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灌输主仆尊卑、贵贱对立思想的种种失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如何破除成见,反省自我并丰富自我,同时与其他民族、文化、社会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这种对待自我和他者的态度对于研究西方、研究中国以及中国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演变都是不无裨益的,这也正是认真解读晚清“使外文学”对西方形象描绘的核心意义所在。
“使外文学”的研究范畴
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目的是想强调这种文学与中国晚清外交的特点及其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对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创作做多重层面的文化思考。与此同时,从晚清 “使外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出发,去探求和认知晚清士人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
“使外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实为中国寻求现代化的时代氛围所赐。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惊扰了中国封建帝国的上层统治者,打乱了中国封建农业社会缓慢发展的固有秩序和结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8〕。近代长期闭锁的国门一旦被迫向西方开放,西方文化就会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而国人也迫切地想要了解世界并开始陆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是那些身份特殊的晚清常驻国外的外交使臣,他们把自我走向世界的历程和体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促进了“使外文学”创作的蔚为风潮。从传统士人与使外文臣的身份出发,使外文臣所创作的“使外文学”,必然需要担负起历史反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成为国人走向世界接受近代文明思想洗礼的重要通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碰撞、比较、交流的前沿阶梯。
对于丰富驳杂的“使外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可以借助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不同主题的分析比较,比如说现代性体验、身份认同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入。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对“使外文学”进行跨文化研究,在解读其文学价值的同时,了解近代中国使外文臣认识西方的过程,借以关照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文化形象的衍生和构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国文学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这一形象是在“文学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19〕。这就要求在重视文学文本内部研究的同时,超出文学领域进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跨学科性将成为最鲜明的特点,具有非常开放的研究姿态。这可能是今后晚清“使外文学”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甚至可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使外文学”是较好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学载体,“使外文学”作者的“外交官”身份,必然涉及文化认证与文化转移,中国与异邦文化形象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痕迹,必然会在“使外文学”文本中体现出来。形象学理论观点只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并不是完备的可供操作的研究步骤和方法。对晚清“使外文学”研究而言,这一个崭新的领域并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资参照。因此,如何做到研究方法和文本内容、现代研究理论与传统治学路径相得益彰,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实践和探索。
〔1〕王曾才.清季外交史论集 〔C〕.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53.
〔2〕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欧西及其贡献 〔J〕.文史杂志,1944,第 4卷,第 3-4期.
〔3〕[清 ]文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第 72卷 〔Z〕.文海出版社,1970.45.
〔4〕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 1689-1949〔Z〕.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32.
〔5〕光绪十九年总署奏定.出使章程 〔Z〕.光绪年铅印本,20、21.
〔6〕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02.
〔7〕杨易.晚清外交官及其著述 〔M〕.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1999.217.
〔8〕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 〔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
〔9〕朱维铮.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王飚,关爱和,袁进.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展望 〔J〕.文学遗产,2000,(4).
〔11〕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4.
〔12〕[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 〔M〕.刘象愚,邢培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6.
〔13〕祝远德.他者的呼唤一康拉德小说他者建构研究 〔M〕.人民出版社,2007.11.
〔14〕[日 ]熊野纯彦.自我与他者 〔J〕.杨通进译.世界哲学,1998,(4):45.
〔15〕张法.20世纪西方美学史 (修订本)〔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273.
〔16〕[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 〔M〕.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73-174.
〔17〕[美]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 〔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53-454.
〔18〕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卷 〔M〕.人民出版社,1963.110.
〔19〕[法]巴柔.从文化到集体想象物 〔A〕.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 〔Z〕.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0.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K254.3;I04
A
1004—0633(2011)03—149—05
2011—03—08
汪太伟,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贵州贵阳 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