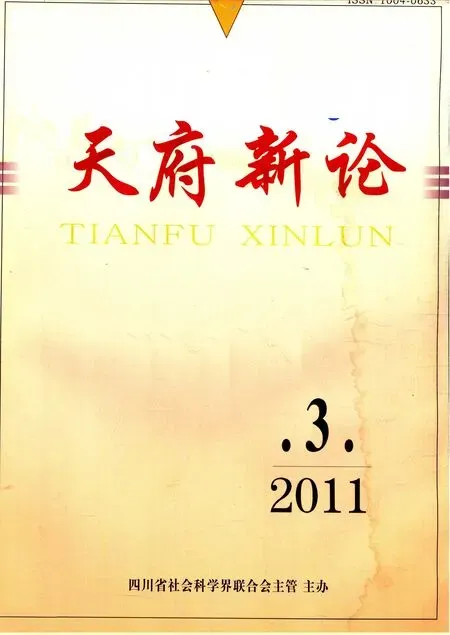从“浪漫”到“古典”的倾重
——现代文学建构视阈中梁实秋之批评选择
2011-03-18潘水萍
潘水萍
从“浪漫”到“古典”的倾重
——现代文学建构视阈中梁实秋之批评选择
潘水萍
梁实秋是一位饱受中西传统文化浸染的极富现代性人文精神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为 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创作作品,而且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提供了大量极具启发性与锋芒性的理论言说指引。极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历史语境的种种因由使然,梁实秋之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理论学说始终未能引起学界正面的大力弘扬、关注,而一度处于一种至偏的有意或无意的低视、误读、尘封与遮蔽的沉寂命运。这正是亟待当下学界对其整体的思想学说进行进一步敞开性阐释与探究的空间。
梁实秋;欧文·白璧德;古典主义;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当代文化价值反思与独立不倚的人生审视,梁实秋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学说理应引起人们以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和高瞻的气度而加以广泛的注目、回顾、正视及作出前沿性的批判与释读。事实上,梁实秋是一位执着于秉持、传承新人文古典主义的较具稳健、理性学术理路精神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其独特的文学批评思想蕴涵着清醒而鲜为人知的自我反思的锋芒力量和人文精神,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依然有着穿透当下力量的现实维度指引及启示意义。梁对欧文·白璧德的批评理论学说的肯定、选择、吸纳与阐释,诚然有着其深刻而独特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梁实秋不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史家,却是一个很有理论个性的批评家。他对 20世纪 20年代很多文学热点背后潜伏的问题和危机,有相当敏锐的体察。所以,几十年后重读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历史总结,反而可能觉得比当时某些文学史著作更有深刻的见地。”〔1〕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实秋对新思潮激进浪漫派注入的特殊而不失温和的批驳是对的,有助于促成人们对激进新思潮的冷静而客观的反思。有学者这样评述:“如果说在吴宓关于五四文学的批评中,我们尚可以发现一种纯粹而抽象的文化理想对于文学实践的某些漠视,那么在梁实秋的批评中我们却读出了他对于当前文学发展问题的关切与敏感。”〔2〕
不难看出,梁实秋从“浪漫”到“古典”的学术思路的倾重、转向与嬗变,毋庸置疑是其在现代中国文学建构视阈中作出的批评选择。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论题。梁实秋以其稳健、理性、适度、节制的别开生面的文学批评观和反思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诸多学者对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背后或显或隐的甚至被遮蔽的复杂问题的重新关注和再度发现。
(一)
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不仅蕴藉着浓郁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同时也富含着耐人反省、嚼味的思想魅力和丰厚的人文素养,而且更是凸显出其对中西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后更富知性之人生底蕴和博雅之知的超迈通达。
梁实秋曾经《文学的美》一文中曾怀疑根据“美学原理”去解释“文学”的论说。因为他承认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里有“美”,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里“所要表现的东西”才是最为关键的。他曾颇为有力地宣称作家提供给观众的“仅仅是一面 ‘映照自然的镜子’”。〔3〕事实上,梁实秋一生都在追寻一种乐生而不猖狂的内心的清雅与通脱,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其文学抒写深深地染指着一种爽朗干净、短洁利落的深致韵味和情满而不溢的独特格调。梁实秋向往淡泊、宁静、豁达、致远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讲求“节制”而趋于“稳健”、“理性”的文学批评学术理路。他认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是内心均衡的心境产物。梁实秋认为艺术家的真实质素表现为隐隐的“审慎”、“冷静”艺术创作态度,而情感稍为急躁、任意、颓废、伤感、放纵的艺术,其创作则是不甚健全而至少病态百出的。梁实秋曾极有见地的强调:“艺术的批评家实在是负着两重责任,一方面要指示艺术创作家以成功的途径,一方面更要领导艺术鉴赏家上正当的轨道。”〔4〕
梁实秋讲求文学创作作品“布局”之严谨、整体。他认为文学家一味地追求作品的“通俗”并不是好事。针对小说的创作,梁实秋有自身独到的理解:“一部小说必定要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必要是合乎人情的,必要有起有讫,有变化有结果,有艺术的安排,有单纯的效力。简言之,小说家所最要致力的就是布局 (plot)。”〔5〕显而易见,这段文字足以透视出梁实秋谨严的古典主义文学创作观。他强调小说至为关键则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讲求整体的 “布局”,也就是说必须 “有一个故事”,且故事要 “合乎人情”。毫无疑问,梁实秋这种文艺观显然受到西方古典主义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
梁实秋留学期间极为推崇西洋文学批评的鼻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文学批评的诗学理论,尤其是他那部被西洋文学批评奉为不可多得的经典《诗学》。他给予《诗学》这部最富独创性的批评理论的残稿极高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创作论正是根植于对亚里士多德文学批评之“中庸之道”的经验教益的汲取、融通与秉承。一言以蔽之,梁实秋既有学者之承古启今且明心见性的学养襟怀,又兼具通脱湛然且高远不俗的生命姿态,更不失缜密而理性的文学批评内涵的思想力度。梁实秋强调文学创作之“题材”必须是“人本”的,即是“人性的描写”。“一部作品必须是描写人性的,必须是描写人类的基本情感如喜怒哀乐之类,然后才称得起伟大。”〔6〕事实上,梁实秋是一位倾重于褒扬儒家学说而贬抑道家思想的文学批评家,在他的身上凝集了中国儒学传统文化 “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哲学。梁实秋曾自评为一个大概是儒道释三教合流杂糅影响下的地道中国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梁实秋不仅极为推崇古希腊时代之均衡、节制、理性、稳健、适宜之和谐人文精神价值观,显然,儒家之 “中庸”思想在其兼具深厚、朴实、平和、稳健的人生观中固然占却相对优越的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梁实秋常以“老年人”喻示稳重之“中庸之道”的思想。他颇有精义且令人服膺地阐述:“人的一生,最值得赞美的时代,便是老年时代。西塞罗‘论老年’是一切古典主义者对老年的态度。他说老年是人生思想最成熟的时代,亦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孔子说他自己年至七十才能 ‘从心所欲不逾矩’。古典主义者所需要的文学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学,这种文学是守纪律的;浪漫主义者所须要的文学是‘从心所欲’而‘逾矩’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不负责任的。……古典的文学是凭理性的力量,经过现实的生活以达于理想;浪漫的文学是由情感的横溢,撇开现实的生活,返于儿童的梦境。”〔7〕诚然,梁实秋一以贯之地推崇健全、稳妥、清晰、理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态度,而反对任何趋于极端、病态、矫揉造作的的浪漫主义倾向。
此外,梁实秋给予罗马批评家贺拉斯 (Horace)及其《诗的艺术》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除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之外,再没有比贺拉斯的《诗的艺术》重要的。〔8〕梁实秋在论述文学的“纪律”和“纯正的古典”的时候,更是肯定了贺拉斯提及到的 “把文学标准 ‘规律化’”与“‘适当律’(Law of Decorum)”的观点。梁实秋颇为认同贺拉斯关于文学创作最为“稳当”的方法就是对“古典作品”或“古典典籍”的取材或效法的主张。“贺拉斯的文学批评,其功绩在能继承古典主义的正统,其缺点则在未能尽得希腊的自由精神。贺拉斯的新古典的趋向,实为开后来文艺文艺复兴期及十七十八世纪文学批评思想之根源,亦为后世浪漫派文学批评之反动的伏因。不过就全部观察,贺拉斯的批评是健全的,偶有武断之处,而武断之批评固犹胜于无纪律之批评。……我们研究《诗的艺术》,要注意他的两方面:贺拉斯一方面是古典主义者,因为他主张文学的标准,理性的纪律,与希腊时代之最优的思想完全同调。”〔9〕由此段文字不难见出,梁实秋关于文学批评理论中提及到的“文学的标准”、“理性的纪律”、“文学的纪律”等概念正是源于他对古希腊时代思想精神及贺拉斯文学批评观点主张的颇为暗合性的承袭与新扬。梁实秋认为文学有“永久性”,同时文学也有其自身的“时代性”。任何描写人类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毕竟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带有其特定的时代性。
梁实秋尤为注重对文学之根本“纪律的形式”的强调。文学家应以冷静、理性而谨严的创作态度来操控“情感”与“想象”于之适度之中,这正是文学创作之“守纪律”的精神表现。毋庸置疑,梁实秋在对古典“传统”文化之整体坚守的同时,更为可贵的是他能以一种超越时代历史语境的眼光和宽容的学术态度,自觉地体认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迎合了新历史时代文化需求而给“现代”中国文学理想构筑带来了有益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很在必要对梁实秋的思想渊脉作一深层的梳理与整合。
(二)
众所周知,梁实秋文学批评上的古典倾向是其对中西传统文化进行鉴照、审视、接纳与选择的结果。他认为思想上不该“复古”,艺术上却无法维新。〔10〕显然,梁实秋是一位怀旧思古却不守旧惟古的现代学者。他认为中国文学思想一直以来深受到儒、道两大潮流的支配。他曾颇具学术敏锐眼光地指称:“儒家虽说是因了历代帝王的提倡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是按之实际,比较深入于我们民族心理的却是道家的思想,这在中国文学里表现得极其清楚。西洋文学有‘古典的’与‘浪漫的’两在潮流;中国文学也有儒道两大潮流。这是事实,不是故意拼搭的对偶。我们的儒家的文学思想还没有西洋文学中古典主义那样的完美,但是我们的道家的文学思想却很像是西洋文学中最超极端的浪漫主义。西洋文学以古典主义为正统,以浪漫主义为一有力之敌对势力。中国文学则以极端浪漫之道家思想工作最活跃之势力,以奄无生气之儒家思想为陪衬。就大致论,这是中西文学思想上最不同的一个现象。”〔11〕
梁实秋主张读书应读“长久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作品”。他由于受到闻一多早期研究杜诗的影响而萌生了偏爱读杜甫诗歌的雅趣。他曾在其散文创作中透露其随身五十年都带有一本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也曾收集各种版本的“杜诗”六十余种。梁实秋认为“读经”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经、史、子不可不读,更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十三经和老庄道家一派的思想更是理应“抱着批评的态度”进行涉猎。梁实秋指出道家的思想支配我们的民族性的养成,其影响力之大似不在儒家思想之下。〔12〕不可忽视的是,梁实秋参与下的现代中国新文学建构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文学的全局性阐释意识和“现代”人文精神的自觉反思立场。他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趋向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和清醒的把握。事实上,这种学人精神的时代历史使命感的担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尤为难得的。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条例》的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提高抓好党支部工作、推动党支部建设的本领。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
实事求是地说,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蕴涵着一种使人振奋与嚼味的思想锋芒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暗示性指引。有学者认为:“古典文学的标准,就是这样使得梁实秋失去了与现代大多数作家产生共鸣的内在机制,使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中的独行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以古典主义作为自己的批评理论的现代古典主义者。”〔13〕的确,梁实秋对中西古典传统文化教养的接受与崇尚无疑是异乎寻常的。一方面,梁实秋接受了儒学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曾颇为爽约地直率强调古往今来理应值得年青人阅读的文学经典为《柏拉图对话录》、《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等。显然,梁实秋对儒学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是持肯定的态度。
对于自身思想学说受到中西文化之深远影响,梁实秋曾坦言己身无疑是受时代历史风气之使然。他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梁实秋论文学〉序》一文中更彻底地揭示其成长过程中所受到古典传统文化和胡适文学观的影响。其中有一段文字颇为精辟地记述了其文学思想之成长经历:“新文学运动肇自民国六年,在那一年胡适先生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从此文学运动风靡一时。当时我只有十六岁,尚在学校读书。我没有私塾,没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可是我一面在古文圈子里摸索,一面也开辟了新的天地,那便是偷看小说。最先偷看的是《水浒传》、《红楼梦》等。深感古文之格调词藻陈陈相因,不若白话小说给我莫大的启示与喜悦,虽然我对于古文未敢公然加以訾议。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我而言,确是发聋振聩,把许多人心目中积存已久的疑惑一下子点破了,我顿时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14〕这段文字诚然可以迹出梁实秋思想生成之独异性:一面“在古文圈子里摸索”和一面“也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正是梁实秋古典主义思想所涵蕴着的“传统”与“现代”的源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响梁实秋一生文学观的除了儒学传统之外,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胡适、闻一多和白璧德三位挚友的思想点拨与激荡。事实上,正是由于胡适的大力提议、倡导与期许,梁实秋翻译了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全集。为此,人们也深受其益。梁实秋对儒家学说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思想学说大致上呈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内涵的一种明确的反思立场、批评标尺和审美理想的倾向。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诚然是实实在在地接受过“浪漫”与“古典”双重文化熏陶之第一人。他早年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刻影响,浸润和印染着一种古典的天性和一种真正的古代精神成长。梁实秋认为“浪漫的”与“古典的”并不是对峙的名词。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节制”与“集中”的古典精神,而不在于“放纵”与“开扩”的浪漫态度。“盖古典主义之作家,其头脑必须清晰,其方法必须审慎。其结果虽以简单为极则,但其简单必须为理性选择后之产物。世人误简单的美为不加制裁之流露,为不经纪律之自由,实乃大误。”〔15〕
事实上,梁实秋认为大凡真正伟大的古典作家都注重文学之“内在的制裁”的坚守与遵奉,要求文学创作情感表现之“理性”与“合度”,否则文学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混乱”的隐患。文学创作之 “节制”的力量,即是以“理性” (Reason)驾驭、节制情感和想象。梁实秋指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万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我屡次的说,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说把理性做为文学的唯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做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16〕实质上,梁实秋坚守古典传统文化之稳健、适度与理性,是因为他洞悉到“浪漫主义”在西方的极端泛滥给社会文化与文艺创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恶劣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梁实秋颇为令人激赏地谈及没有真正读过“古典文学”的人是没有资格去批评 “古典主义”。事实上,“古典主义”与“古典派批评”尽管有区别,但于“精神上”是一致的。真正的古典主义者并不偏重“智巧”、“形式”、“规律”或“现实”,亦不“过度”地崇奉“古典文学”,这是区别于 17、18世纪部分的“新古典主义者”或“假古典主义者”的关键。〔17〕更为明显的是,梁实秋强调“浪漫派”的一时勃兴是代替不了“古典派”的地位,“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不仅是同时萌发的,而且将要“永久地”共同存在。他认为对于文学史上 “派别”或“思潮”勃兴生发的现象并不能以“新陈代谢”一词来概述。浪漫派是以抗议、打倒“新古典派”或“假古典派”过于注重规律的不合理之批评的姿态出现的。然而,浪漫派之过于“放纵”而陷于“混乱”的批评是建立在无限度的“同情心”横溢的基础之上。
由此看来,真正的古典派文学家或批评家则尤为注重“节制”、“冷静”、“理性”、“适度”与“均衡”的理想之批评尺度,这是其能于“浪漫派”与“新古典派”两派之间“执两用中”之稳重的体现。梁实秋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者,他以“稳健”、“节制”理论为其文学批评的标尺,强调文学内在的理性秩序、常态理智和纯正规律。任何“健康”、“冷静”而“理性”的文学家,常常都能保持着其心理的平和、致远宁静、均衡,而不至于过于“偏激”或“消极”。〔18〕梁实秋对“适宜、“健全”、“文雅”的文学批评原则尤为推崇备至,他认为任何以“经济”或 “阶级”的划分来作为衡量文学的惟一标准,都是浅薄、偏激甚至鲁莽的。毕竟,文艺审美品味之高低显然与“阶级”没有多大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梁实秋是一位接受过中西古典传统文化熏陶过的颇具才气与眼量的作家与批评家。梁实秋稳重之文学批评学说源于其对深刻“人性”的洞悉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反思,而其理论思想之哲学基础源于对中西古典传统文化之融通和古典作家有益经验的秉持与发扬。这使得他的文论思想始终灌注着一股高瞻的气度和通达高远的审美意蕴。他潜心于古典“传统”文化如何对接“现代”之文化建构的反思,其文学理论思想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鉴照与启示意义。
(三)
值得一提的是,梁实秋研读并深受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学说日益凸显的脱颖而出的影响,使他再次印认了其一直偏好的 “古典文学”,并由对 “浪漫”的质疑真正地转向“古典主义”。实际上,梁实秋是继学衡对白璧德文学批评思想进行译介、阐释与倡导之后,对其著述之学术理路的美学追求进行精妙的研磨、打量和反顾的基础之上作出的颇为深入的把持与儒雅的融通。白璧德教授是美国近代的人文主义 (Humanism)运动的代表,其鲜明而肯定的思想系统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对“人文主义”的论说开端就痛斥“现代”人文精神缺失的诸多隐患和弊端。梁实秋曾坦言:“我并不把白璧德当作圣人,并不把他的话当做天经地义,我也并不想藉白璧德为招牌来增加自己的批评的权威。在思想上,我是不承认什么权威的,只有我自己的‘理性’是我肯服从的权威。白璧德的学说我以为是稳健严正,正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的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21〕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催生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的确,与其说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思想源自于其历史性地审视、看待生活和文学倾向的问题,倒不如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是由儒家传统思想、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欧文·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的核心精神融汇而成。
梁实秋曾指出:“对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而言,无论它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它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对于自身文化的质疑与批判。……影响过新儒学第一代思想家的生命哲学是在质疑和批判现代文明的物质主义与‘理性万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影响过学衡派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民主潮流的一种反拨。”〔22〕
实际上,梁实秋在美国留学时深受强调人文修养、自制克己的白璧德之新人文古典主义的影响。他深深地警觉到白璧德之强调节制、以理节情的通脱自律的人格之魅力。俞兆平曾认为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崇,不仅源自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而且还立足于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23〕无论如何,梁实秋倾重于以 “古典”之稳健调整与修正其当时对“浪漫”的追随,不能不说是受到白璧德学术理论思维的左右与熏染。他颇为称赏阿诺德关于“文学是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之看法。白璧德思想学说之理论精神对梁实秋文学批评言论及学术理路的潜在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自从对白璧德著述进行深入的整体性品读与审视后,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理路顿时变得具体而富有意味。
事实上,梁实秋备受关注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思想形成应溯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缘起于其早年浸染着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留美期间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接受与倡导,使他对其早期信奉的唯美浪漫思想的戏剧性的轰然厌倦与自觉反拨,日后渐已形成充满思想活力与锐利批评精神趋向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古典主义思潮,主要是基于以吴宓为首的学衡派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知识分子对白璧德思想学说的宣扬。然而,这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却因时代历史具体语境的一度误读而一直处于沉寂、遮蔽的命运。有学者指出:“承认而不是漠视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性与相通性,也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化。”〔24〕梁实秋对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的接受,主要是他们在文学思想批评上一致认同和尽力证明的古典传统文化所蕴涵着的思想力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白璧德思想学说的影响下,梁实秋深深地体认到在外来文学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文学用“人文主义”一词概述更为恰当、稳妥。的确,若仔细追溯梁实秋文学批评思想流脉则可发现,他不仅受到儒学传统文化的浸染,同时也基于他留学美国时所接受的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传统文学批评趣味和习惯辐射的深远影响。
梁实秋对英国文学有着较为深层的解读,这主要源于其对英国文学如《莎士比亚全集》等的翻译。多米尼克·塞克里坦曾于《古典主义》中独创性地强调:大凡认真研读法国和英国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都会使我们透过其严谨的形式表层,发现一种美的财富,一种灵活变通的诗学财富,而现代的偏见往往在我们面前遮蔽了这一切。〔25〕显然,梁实秋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好,这使得他在日后的文学阅读中与译介中渐已体察到英国文学及白璧德学说于“现代”文学建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然,他对白璧德文学批评理论的昭示与彰显也在日后渐趋形成其较为系统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理论批评观。梅光迪曾指出:“如今给予青年一代熏陶的,不是儒家的经典,也不是近代本国的文学和哲学,而是西方的现代报纸及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于是,他们变得易怒而任性,越来越不沉稳,失掉了其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稳重与宁静。”〔26〕
经受到五四新文学洗礼的梁实秋,在留美求学的岁月里则以一种高瞻的气度审视着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中“传统”与“现代”的重大命题。“在这无家、无根的边际状态和由此所带来的惶惑痛苦之中,一种新的世界性眼光和兼取兼容的胸怀开始赋形生成:他们开始努力寻找一种既包含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新的立场和基点;寻找主动介入和了解异域社会的途径和机会,逐渐培养对异域社会和文化的兴趣,包括拓展视野、兼取众长或兼容众异的胸怀。”〔27〕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语境下,他认为白璧德学说以其正统、纯洁而处处显得强而有力的文学观。梁实秋文学批评思想折射出其一生持守的古典、理智、适宜的人生处世价值观,而且带有严重的他个人所受到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的影响痕迹。梁实秋继学衡派知识分子后对激进派的自觉批驳的论调和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传播,颇为有力地凸显了其之“冷静”而“理性”的文学态度。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梁实秋顺应时代留学风潮之召唤而于 1923年怀着“复兴中国文化”的理想与时代历史使命感赴美求学。在对“传统”文化之眷恋与对“现代”时局反省的双重刺激下,梁实秋渐已转向寻求一种可以接通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未来发展之路,希冀寻找到一种对现代中国文学有启示意义的思想学说。正是在此历史时代语境下,他极为偶然地接触并渐渐走近白璧德颇具耐人寻味的人文主义学理脉络的文学批评。饶有兴味的是,梁实秋对白璧德看似艰涩难懂的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而是在慢慢接触的过程中细细思量才警觉到其学术蕴涵的批判价值与力量。他曾直言不讳地印证性提及:“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可是我并未大力宣扬他的主张,也不曾援引他的文字视为权威。”〔28〕细而推敲,梁实秋在接续白璧德深具针砭时弊的文学批评的维度上,延伸性地反思了文学“人性”论的标准和深度。不言而喻,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几乎同白璧德之人性观如出一辙。他极为看重文学所承负着的“生活的态度”和“所处时代弊病的纠偏”,这正是其受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观影响的结果。应该承认的是,梁实秋文学人性理论的阐发或多或少地投影与辐射着白璧德鲜有的一脉相承学术理路。
更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学界遗漏或逐步销蚀对白璧德核心学说价值的拓展性诠释与更深层的探究的褊狭,梁实秋作出了彻头彻尾的重新质疑、确认和启示性的矫正。实际上,中西方文化视域中的白璧德文学批评理论内涵,正是建立在对 16世纪以来培根之“科学”和 18世纪卢梭倡导之“浪漫”文化的深深质疑、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然而,也正是由于中国学者对其学说一开始就产生某种片面性的误读而一度处于遮蔽、沉寂。这正是尚待学界对其进行敞开探究与阐释之处。白璧德的文学批评思想深深地激发了梁实秋对中西传统文化之对接、融通、激荡、互渗等种种可能性的高度思考。梁实秋曾直观性地提及白璧德身上凝集着一种“有闲”的绅士贵族精神和理想。他对白璧德思想理论的根本上认同、接纳与融汇,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在精神气度与文学思想底蕴的潜在契合。于此无庸赘言。
(四)
综而观之,梁实秋最深层的文学思想精神渊源一方面可追溯至其成长的家庭背景影响下的传统文化深深接触、浸染,另一方面是其留学时期特殊环境中现代时局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思。换言之,与新思潮时期的文坛上那被禁锢或栖居在毫无灵性理解力之中的激进之过度、浪漫之极端的相比,梁实秋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思想的自觉接受就显得极为清醒。面对新文学运动,梁实秋一方面欢迎外来思想,另一方面则对新思潮持守着一种谨严而警醒的审视态度,以强大的抵抗力抗衡与捅破文坛新思潮那心急若渴的“全盘西化”的呼声构筑起来的对文坛的无形障碍与亵渎。实际上,梁实秋是一位行文敛采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颇为认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关于“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把应尽的责任尽完”的稳健人生观。这也是梁实秋之所以能接受具有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余光中在《尽牍虽短寸心长》一文中则认为梁先生的笔下一面力排西化,另一面也坚拒‘大白话’的俚腔,行文庶几中庸之道。〔29〕梁实秋清明豁朗地主张以“纪律”节制情感之“放纵”,显然受到白璧德主张以“道德”纠偏现代文明社会缺失的人文精神隐患的某种内在精神的深层感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梁实秋对新思潮反省的文学批评理论学说尽管对当时极端浪漫主义之泛滥、之激躁、之颓废有着清醒而健全的警醒和纠偏作用,但毕竟也透露出梁实秋文学批评观褊狭的一面。由此可见,学界应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给予梁实秋文学批评观独特的概观与评述。事实上,梁实秋是继学衡派知识分子之后,于 20年代后期推举白璧德学说的学者。有学者认为:“白璧德学说与梁实秋的人生哲学形成了某种内在精神契合,这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又一个来源。……这种以平衡、谐调、纪律等为内涵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性存在着本质的偏差,因此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实际上新人文主义思想并非仅仅是一套浅显的文艺理论,而是一种人生哲学。梁实秋以这种稳健与理智的人生哲学观念对待文学,这显然与当时文学主潮的革命与激进的精神相悖。然而,置身于主潮文学之外却未必意味着守旧。”〔30〕
梁实秋并不是一位局促、拘执或淹没于古典传统批评标准的象牙塔式的守旧学者,而是一位浸润过中西先进文化的极富个性而浩气朗然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属于那种以保守的面目出现的知识者,这种保守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复古与反动,它指的是一种人生观,处世态度与认识事物的方式。梁实秋其实就是以一种稳健、理智、纪律、节制的方式对待生活与文学的,这与现代文学主潮自由、创新、激进的精神相抵触,而使梁实秋成为一具不合时宜的人。”〔31〕殷国明则认为学衡派的文学主张并不系统,并没有形成有个性的古典主义理论模式和规范,而且原本就具有稳重、节制的文学倾向的被称‘新月派’中理论家的梁实秋,则促进了他新古典主义文学现象的形成。〔32〕实际上,梁实秋是一位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保持着一份高洁的敬畏之心进行理性摄纳、秉承的堪称为时代精英,更是白璧德学说忠实而非盲目的追随者。他透过白璧德颇具锐气的文学批评学说而试图接通儒家传统学说与现代中国文学建构的种种可能性。
〔1〕〔8〕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128.
〔2〕高旭东编.梁实秋与中西文化 〔C〕.中华书局,2007.108.
〔3〕〔6〕〔11〕〔17〕〔18〕〔19〕梁实秋.偏见集 〔M〕.南京正中书局,1934.34,279,146,221,242,247.
〔4〕〔10〕〔21〕〔28〕梁实秋.雅舍谈书 〔M〕.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5,143,267,227.
〔5〕〔14〕梁实秋.人生几度秋凉 [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7,224.
〔7〕〔9〕〔15〕〔16〕〔22〕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5-26,129,88,117 -118,89.
〔12〕梁实秋.梁实秋杂文集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87.
〔13〕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
〔20〕武新军.古典浪漫之争的东移——20世纪 2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古典主义诉求论纲 〔J〕.河南大学学报,2003,(6).
〔23〕俞兆平.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J〕.厦门大学学报,2006,(4).
〔24〕周冰心.京派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兼与西方古典主义比较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1).
〔25〕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古典主义 〔M〕艾晓明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102.
〔26〕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 〔Z〕.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07.
〔27〕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7.
〔29〕余光中.余光中集:第八卷 〔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92.
〔30〕严晓江.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 〔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0-31.
〔31〕白春超.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 〔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32.
〔32〕殷国明.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比较性描叙的尝试 〔J〕.暨南学报,1999,(6).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I206
A
1004—0633(2011)03—143—06
2011—03—04
潘水萍,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国文学批评。广东广州 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