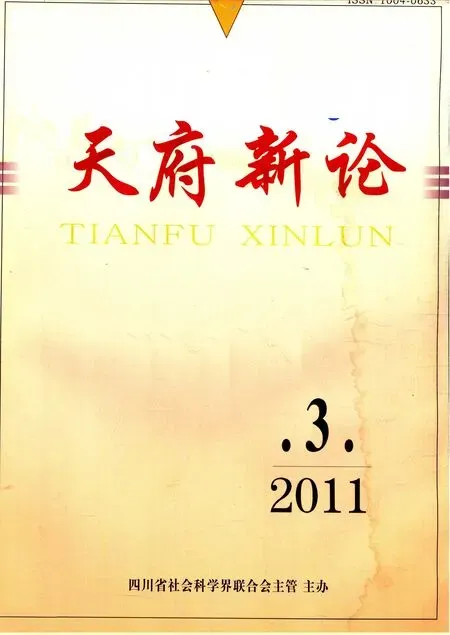走向传奇: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动向
——论长篇小说《锁沙》“传奇现实主义”叙事话语的意义与价值
2011-03-18支宇
支 宇
走向传奇: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动向
——论长篇小说《锁沙》“传奇现实主义”叙事话语的意义与价值
支 宇
郭严隶的长篇小说《锁沙》通过传奇化的小说人物、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多元化的叙述策略,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塞北草原三代“浪漫英雄”,描绘了诸多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天真意象”,从而成功地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克服草原沙漠化和人性荒野化的时代颂歌。从弗莱的“原型批评”角度看,《锁沙》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也超越了 1990年代以来的欲望现实主义写作和反讽美学,是一部当代小说“传奇现实主义”的代表性文本。
郭严隶;《锁沙》;弗莱;原型批评;传奇;现实主义
新世纪以来,四川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郭严隶的小说创作热情高涨,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在先后出版《浮途》 (2006,花城出版社)、《十步莲花》(2009,花城出版社)等 4部广受好评的长篇小说以及多部中短篇小说佳作之后,郭严隶于2010年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锁沙》。这部小说叙述了当代大学毕业生郑舜成放弃优裕的都市生活,回到塞外家乡曼陀北村,带领村民以坚忍不拔的意志与肆虐的风沙抗争,最终战胜重重困难建成草原绿色立体经济并开创幸福生活的故事。从题材上看,《锁沙》是一个现实关怀很强的叙述文本,广泛触及了当前许多社会热点问题。无论是 “生态环保”、“大学生村官”、“乡村改革”,还是“官场斗争”、“招商引资”、“民族团结”,郭严隶都能将这些社会热点话题巧妙地聚集、组接和镶嵌在一个治沙锁沙的情节当中。从选题角度看,这篇小说完全可能走上 20世纪中国重大题材文学作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老路子。说实话,刚开始翻阅这部书时,我对这种现实主义叙述话语的当代有效性充满了疑虑。
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福柯所谓“话语”,当然包括对文学。就此而言,这个命题提示我们,决定小说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的核心要素,不是小说题材本身,而是小说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叙述方式。从这个角度看,郭严隶及其《锁沙》所面对的问题必然是:在新世界的汉语言文学语境中,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来处理“乡村治理”与“防风治沙”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
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环节上,郭严隶显示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眼界和话语方式:我将其命名为“传奇现实主义”。借助于这种独特的叙事模式和美学法则,郭严隶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和新时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话语。
“传奇”这个词来自加拿大“原型理论”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 (Northrop Fry,1912-1991)的《批评的解剖》一书。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这部书被称为“划时代”的批评巨著。在这部著作里,弗莱提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世界文学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基本模式:“神话”、“传奇”、“高级摹仿”、“低级摹仿”和“反讽”。弗莱不仅严谨而详尽地阐释了这五种文学模式的内涵与特征,而且还提出其运行规律。他认为,在西方文学中,这五种文学模式会按上述顺序不断地循环流动。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不是重述或梳理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而是“传奇”这一文学原型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场域中的隐蔽踪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解读长篇小说《锁沙》重要的思想入口之一。我认为,郭严隶在《锁沙》中摆脱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神话”、“高级模仿”、“低级摹仿”和“反讽”等文学模式,找到了一种 “传奇化”的写作道路,从而成为中国当代“传奇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这一种美学形态与叙述方式有代表性的文本。
一 浪漫英雄:传奇化的小说人物
按弗莱的看法,“传奇”这一文学模式中的主人公,其行动力量绝对高于普通人并能超越自然规律。弗莱说:“在传奇的主人公出没的天地中,一般的自然规律要暂时让点路:凡对我们常人来说不可思议的超凡勇气和忍耐,对传奇中的英雄说来却十分自然。”〔1〕这就是说,在文学叙事的主人公设置上,“传奇”文学主人公的角色典范是“浪漫英雄”。在超越自然环境与常人能力这方面,“传奇”中的主人公与“神话”极为相似。其不同之处仅在于,“神话”的主角则是“神”,而“传奇”文学的主人公“虽然出类拔萃,但他仍被视为人类的一员”。人物的“浪漫英雄”化以及其超越日常经验的神奇能力与情节是“传奇现实主义”小说叙述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
作为“传奇化”的现实主义写作,《锁沙》全面体现了上述特征。一方面,它的叙事话语塑造了乌兰布通草原上整整三代 “传奇化”的人物 (三代男性英雄和三代美丽女性);另一方面,小说还设置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离奇情节。
构成《锁沙》叙述话语主体部分的一代“浪漫英雄”是返乡大学生郑舜成、镇委书记刘逊和青年突击队成员巴特尔等男性人物。郑舜成是曼陀北村历史上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是郭严隶塑造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浪漫英雄”。在小说叙事话语中,郑舜成刚刚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在远赴深圳巨星电子集团公司去报到上班之前,抽空匆匆踏上回乡探亲的旅途。没想到,他就此卷入了家乡生态移民的风波,并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建设家乡的使命意识和现代科学生态理想的指引下,郑舜成迅速将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村党支部。在领导的支持与村民的拥戴下,他参加了村里的“双推一选”会议,最终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此后,郑舜成带领曼陀北村村民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大搞生态建设,并最终带领大家走上了致福之路。
在《锁沙》的叙述文本中,郑舜成这一“浪漫英雄”形象是通过一系列生活历练和离奇的小说情节而被塑造出来的。与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所表征的 80后大学生形象不同,小说中的郑舜成有金子一般的赤子之心,他心系家乡,内心涌动着对父老乡亲炽热的大爱之情。他心怀崇高的理想,大学毕业后不惜放弃繁华都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毅然重返祖国北部贫穷的乌兰布通草原。即使回到家乡深陷陆显堂等人的阴谋与纠缠,他仍然没有逃避,拒绝参加高中同学梅兰朵力荐的公务员考试。从经验上讲,郑舜成年青气盛,没有基层政治斗争与乡村经济建设的实际经验,他的理想与抱负在真正的现实生活未必能够顺利实现。然而,《锁沙》的小说叙事话语显然将郑舜成的成长历程进行了“传奇化”处理。在超真实的叙述话语中,郑舜成对曼陀北村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全面、科学而且系统。他首先在村党支部书记的竞选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构想。当选后,他又能以极快的速度将其付诸实践。在他的领导下,曼陀北村的人民通过修建水库、关闭采石场、退耕还林还草、草场围封等手段来治理作为沙龙之首的曼陀山,并最终使沙化了的草场的植被得以全面恢复。此后,郑舜成又引导村民把传统粗放型畜牧方式转化为现代化的舍饲养畜方式,并通过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而实现了产业升级,成功地将曼陀北村建设成为祖国北部著名的生态优良和生活富裕的村庄。
在这一过程中,郑舜成屡经磨难,但每次都有惊无险,总能化险为夷。镇党委书记刘逊是郑舜成最坚定的支柱和靠山。他总会在小说情节发展到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出场,戏剧化地扭转局面。在郑舜成的感召下,村青年突击队队员巴特尔和斯琴娅娃为建成神珠水库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最终为此献出了年青而宝贵的生命。
郑舜成、刘逊、巴特尔构成了《锁沙》主叙事层中的男性“浪漫英雄”系列形象。除此之外,小说叙事还成功塑造了其他两代“浪漫英雄”。依据叙述时间的顺序,从郑舜成这一代往前推,《锁沙》重点塑造的男性人物是郑舜成的亲生父亲白照群。他同样是一个高度“英雄化”的传奇人物。白照群是 1970年代初到乌兰布通草原上接受再教育并支援草原建设的北京知青,因与下放到草原劳动改造的北京水利学院老水利专家宋一维教授一起劝阻人们砍伐树木大炼钢铁并进行水库修建勘探而献身。再往前推,《锁沙》还塑造了蒙古民间传说中的一代“浪漫英雄”,即占古巴拉,他曾经以自己的生命救护了老榆树。
与上述三代男性“浪漫英雄”相对应,小说叙述话语同时还塑造了三代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美女”。现实生活中的一代有陶可、梅兰朵、斯琴娅娃、白诗洛等,其形象都是充分浪漫化与传奇化的。再往前推,小说叙述中的“浪漫美女”是郑舜成的生身母亲上官婕 (她与白照群生下了私生子郑舜成);进一步往前推,还有与占古巴拉配对的“浪漫美女”阿兰美尼。这些女子,无不美丽聪慧、心地善良,富有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情怀。通过三代“浪漫英雄”和“浪漫美女”,我们不难看出《锁沙》在小说人物塑造上的“传奇现实主义”叙事语法。
《锁沙》现实主义写作的传奇化处理还体现为离奇的情节设置。在“浪漫英雄”生命攸关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块椭圆形白色大石成为郑舜成救命神物,当他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飞鸟从高处栽下来,它稳稳实实挡住了他。左腿足踝处软组织拉伤,也就是筋伤了,没有殃及骨头。”〔2〕同样,当郑舜成的乡村生态建设规划遭遇困境的时候,小说叙事总能跳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形,另行安排一些突然出现的人物来解开阻碍情节发展的症结。比如,沙化问题初步解决之后,郑舜成面临着提升曼陀北村经济发展的难题。这时,陶可及其男友就出面促成了一位来自北京的企业家投资建厂。这个名为“曼陀草原绒毛肉食收购公司”的企业即刻成为曼陀北村产业发展的龙头。紧接着,其他公司如绿野公司、养鹿厂、鹿产品加工厂等企业也相继创立。产业链的发展与壮大不仅留住了曼陀北村的外出务工者,而且还吸引了邻近旗县的劳动力。这样,郑舜成家乡生态重建和致富规划的神话得以圆满实现。显然,如此快速推进的小说情节并不一定经受得住生活现实与市场规律的检验。小说设置这些离奇情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高效率地完成小说“浪漫英雄”的传奇书写。
二 天真意象:理想化的生活世界
在故事场景和景物上,《锁沙》还特别擅长对生活世界与文学意象进行理想化书写与设置。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中,如果说 “神话”文学模式主要采用“神谕形象”而“反讽”文学模式主要采用“魔怪形象”的话,那么,“传奇”、“高级摹仿”和“低级模仿”这三种文学模式更多地采用“类比的形象”。其中,他称“传奇”文学模式所采用的“类比”为“天真的类比”。我们不妨更简洁地称之为“天真世界”和“天真意象”。弗莱通过西方文学总结出来的常见的“天真意象”有孩童、少女、羊、战马、猎犬、火、生命之树等,它们含有童贞、忠实、温驯、献身等品质与特性。“天真世界既不像神谕世界那样整个充满活气,也不像我们世界这样多半处于死亡:它是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到处都是自然的精灵。”〔3〕《锁沙》小说叙事话语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到处都是自然的精灵”的“天真世界”。
这个“天真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天真意象”是什么呢?答案是——“老榆树”。
“老榆树”在《锁沙》的叙事话语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繁多的叙述者之一,“老榆树”的叙事拉开了小说情节的序幕。小说第一章第一小节一开始的“占古巴拉和阿兰美尼凄美的爱情故事”,就是通过“老榆树”的回忆开始的:“是的,旷宇无双,再没有比阿兰美尼更美丽的姑娘了,再没有人。大树轻轻叹息,再没有那么美的爱情了。”“老榆树”有生命有灵魂有记忆能力,是小说重要的叙述者之一。不仅如此,它还是曼陀北村世代相传的 “神树”,具有超越现实的 “魔力”:按陆二楞的说法,“这老家伙站在这儿至少有一千年了”。赵铁柱更是回忆说,“老榆树动不得,谁动谁遭殃……有一年,有个人,想砍这老古榆的杈子当柴火,结果树杈子没砍下,他当场得了头疼,疼得满地打滚,回家去没几天就死了。”当陆二楞和赵铁柱准备爬到树上去扯树枝上的红布条时,老榆树还发出了“哗哗啦啦”的笑声,“弄得树下的指挥官及其手指下团团忙碌的人物全都一傻。”在曼陀北村,老榆树被许多人认为“干娘”。〔4〕
作为一种神话原型,“老榆树”在蒙古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我们注意到,郭严隶的民族身份虽为汉族,但她出生并成长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大学毕业后,又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赤峰日报》社任过多年记者。小说文本《锁沙》多处显示出作者对蒙古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的深切领会。据《蒙古族树木崇拜》一书介绍,“榆树崇拜”在蒙古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蒙古,榆树的名称很多,大多数地方称之为“萨格拉格尔毛都”(意为“繁茂的大树”),而内蒙古东部地区则称之为“尚食毛都”(意为“掌管人们食物的大树”)。〔5〕蒙古族学者席哈斯巴特尔认为,榆树在蒙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中起码具有三重象征意义,分别象征着“守护神”、“祖先”、“火神与生命”。〔6〕直到今天,蒙古地区仍保留着榆树崇拜的古老习俗。村民会到作为“尚食树”的“榆树”旁下马捧上哈达,互致祝福。在重大的仪式上,榆树也是蒙古人不能离开的神圣象征物。人们将榆树当成祖先、火神进行祭祀,祈求榆树给予保护与恩惠。结拜兄弟的仪式也要在榆树下面举行。
作为曼陀北村村庄和村民的“守护神”,老榆树已经历经千年而不朽,它是曼陀北村生生不息的历史象征。郑舜成、陶可、乌仁其其格等对古榆树的保护,也是对曼陀北村生命命脉的保护。小说不仅用老榆树串连起了许多重要的故事情节、完成了许多其他叙述者难以替代的叙述功能,而且还引入了蒙古地区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信仰,对营造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天真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锁沙》文本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天真意象”是“月光”。小说多次描述“月光”:“她朝着那里走去,披一身花朵似的月光。只有天边的村庄才有这样的月光,只有这样的月光才叫月光。”“村庄中充满人尘的香气,炊烟、老牛、幼童、男人和女人相视一笑的眼光,它们在月光的背景下化为意象,而月光因为它们成为物质和永恒。”“那时月亮已经在东边天上闪亮了,月光是神女更细长的银线满山坡编织着。月光使那最大的泉眼像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夜明珠。”在中华文化中,“月光”意象源远流长,意蕴极为丰富。其中,美好、圣洁、理想等象征性意义无疑在《锁沙》中得到了非常饱满而充分的继承与体现。
除了老榆树和月光,小说还描绘了其他许多“天真意象”:星星、彩虹、蘑菇圈、生态泉、雪花鱼和曼陀罗花等草原上盛开的各种各样的花朵等等,最后连北京来搞开发的人养的都是梅花鹿。“草原有两种别处难觅的美景,一是蘑菇圈,一是彩虹。都是要等到雨后才会出现。”〔7〕阅读过程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这些给人带来美好情感和诗意感受的“天真意象”。它们相互呼应,相互联接,共同描画出一个美丽纯洁的“天真世界”。显然,这些意象不仅仅是在内蒙古独特的地域环境中经常出现的现实之物,事实上,它们既有中华文化的深刻涵义,又有具有弗莱所谓“文学原型”的意义。
从弗莱的原型理论看,《锁沙》出现的这些天真意象确是小说“传奇化”倾向必不可少的美学要素。小说传奇化的目的是展现纯真的理想——用作家本人的说法,是“美化生活”,承担“文学的职责和意义”①2010年 7月 17日,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报社、四川省作协、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在北京共同主办了长篇小说《锁沙》研讨会。在题为《文学必须美化生活》的发言中,作家郭严隶提出:“相对于‘生态小说’这个界定,我更愿意称《锁沙》是‘幸福小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它提示我们,《锁沙》以传奇化书写而营造出的 “天真世界”,其内涵可能远在“生态批评”的阐释学意义之外。。一方面,《锁沙》的思想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在郑舜成的带领下,曼陀北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小说的又一重要主题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地蕴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人的欲望、贪婪、势利以及争权夺利必然会导致内在心灵与社会关系的“荒漠化”,其结果必然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沙漠化”。针对自然与心灵的双重“沙化”,《锁沙》以“天真意象”来提供价值认同的理想,有力地烘托了“浪漫英雄”崇高的精神境界。无论是郑舜成、刘逊、巴特尔,还是白照群、陶可、阿兰美尼,小说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几乎都从来没有打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算盘,他们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团结在郑舜成绿色经济和生态建设的旗帜之下一路前行。
在写给《作家通讯》的“创作谈”中,郭严隶将“乌兰布通草原”称之为是“我的心灵的故乡”、“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意义上的皈依之地”。在此,“乌兰布通草原”就是作家心目中的“天真世界”。郭严隶在创作谈中对《锁沙》的“天真世界”给出了最为形象、妥帖与深刻的表述:
“那里的一切都是温暖的、充分浸润于爱的,那种遍地皆泉,水波浩淼,鲜花织锦,林草繁茂,俨然天堂的美丽都是温暖和爱的结果和直呈。跟世外的清明、鲜丽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人性的淳善,那是一方被神的水彻底清洗过的土地,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有一颗金子样的心灵。那是一个天地人神大和谐的乐园。”〔8〕
与 19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写实、晚生代等写作倾向截然相反,郭严隶通过《锁沙》把世俗生活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们的价值观理想化了。批评家陈晓明曾将 1990年代和 2000年代的文学写作分别概括为“平面上的狂欢”和“暧昧的后现代性”。〔9〕与这些倾向相反,《锁沙》像一出传奇,其天真意象和纯美世界无疑进一步远离了1990年来以来中国文学界惯常的欲望现实主义或反讽现实主义文学话语。
三 通灵叙述:多元化的叙述策略
在叙述策略上,《锁沙》对叙述视点的考量与选择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与分析的。多元化的叙述层面与叙述者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叙述功能?又为《锁沙》的“传奇现实主义”写作增添了什么样的审美特征与文化调式?
从叙述层面上分析,《锁沙》起码隐藏着三个叙述层次。上文曾提及郭严隶小说叙事塑造了三代浪漫英雄,正是这三代人展开了文本中的三个叙述层次。其中,发生时间最早的故事是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凄美的爱情故事,然后是上世纪 70年代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宋一维教授考察水利、知青白照群与上官婕相爱并生下郑舜成的悲剧故事,最后是作为小说“主叙述层”的郑舜成返乡从事生态建设最终锁住沙龙的当代故事。除此之外,小说还不断零星地插入一些微型的叙述层面,诸如噶尔丹和康熙的草原战争导致了森林大火、巴尔特在曼陀山上为救玉凤而牺牲的故事等等。
随着叙述层面的多元化或分化,传统现实主义惯常采用的单一叙述者与叙述角度在《锁沙》中解体了。三个叙述层次分别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叙述者。在“主叙述层”,郑舜成建设草原绿色家园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女画家陶可,叙述接受者则是“《千柳日报》记者”胡文嫣——显然,她是作家本人的文学镜像。我们知道,郭严隶原来做过多年记者。从新闻叙述转入文学叙事,受职业习惯的影响,作家往往会将新闻采访的现场感和纪实性带进来。比如,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曾出现过一种以记者为写作主体的文学思潮,史称“新新闻主义”。这种文学思潮特别强调纪实性和亲历感,其叙事聚焦的法则要求叙述话语尽量逼近小说所叙述之事件。幸运的是,郭严隶超越了这种单一的叙述人和叙述角度。
随着胡文嫣的出场,陶可之外更多的叙述者不断地加入《锁沙》的叙述文本:巴特尔的女朋友银凤、郑舜成的养父郑义、那斯图老村长等等。阅读过程中,读者们只有通过这些不同叙述者的叙述才能完整地勾勒出郑舜成返乡就任村支书前后所经历的全部事件。
除了“主叙述层”,《锁沙》还有另外两个叙述层面,这使小说叙述者的身份与角色更加复杂与多元。小说故事的第二层面叙述的是郑舜成的身世。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 1970年代初,主体人物是宋一维、白照群、上官婕以及郑舜成的养父郑义和陆文秀等。与“主叙述层”不同,这个层面的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隐身叙述者”:“在曼陀北村,只有郑舜成自己不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乌兰布通草原的儿子,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血缘。二十八年前,他的亲生父母,白照群和上官婕,是随一群满怀接受再教育愿望来到乌兰布通草原的北京知青中的两名。”〔10〕这里,隐身叙述者以超时间与空间的全知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乌兰布通草原上的那段往事。
文论家赵毅衡曾对小说的叙述层次作过“超叙述”、“主叙述”和 “次叙述”等详细的区分,并提出:“叙述分层的标准是上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11〕我们可以据此析出《锁沙》的第三个叙述层面,即传说中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叙述层面的叙述者也是多重的: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个。开始的时候,叙述者是陆显堂等人想要焚毁的“老榆树”,后来,又演变成曼陀山昭慈寺的住持慧鉴法师:“这段内容,胡文嫣便是从慧鉴法师处得来的。”〔12〕在这里,“慧鉴法师”是显在的叙述者,是他讲述了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生下两个儿子的故事。更进一步分析,从叙述学角度看,讲述“这段内容,胡文嫣便是从慧鉴法师处得来的”这一事实的叙述者又是谁呢?显然,这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位“隐身的叙述者”。
这样,《锁沙》这部小说不仅叙述层次多重,而且叙述者也极为繁复与多元。事实上,它正是由许多不同的叙述话语、视点与角度交织而成的。如果一定要为这种“传奇现实主义”叙述方式找一个术语,我们不妨称之为“通灵叙述”。在这一叙述方式中,叙述层面的交错展开和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使读者的感知领域、阅读经验与生命体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探究这种多元化的“通灵叙述”策略的效果及其原因,无疑会最终指向作家郭严隶独特的宗教性叙述视野——佛性视野。
我们发现,郭严隶在所有宗教文化形态中对佛教情有独钟,佛教文化及其宗教体验对《锁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表层的叙述话语中,而且还体现在叙述策略 (层次、视点等)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显然,小说叙事层次的不断跨越和叙述视点的自由切换这些特征与“六道轮回”、“众生平等”等佛学观念和“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等佛教神秘体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我认为,“通灵叙述”这一隐含着佛家慧根与灵性的叙事策略是《锁沙》叙述话语得以传奇化的重要原因。
长篇小说《锁沙》的叙述文本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所关注的重大题材,完全有可能找到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新的世纪,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迫切需要找到全新的话语方式和表征手段。从这个角度看,《锁沙》这部小说,不仅仅在四川文学界,就是从全国范围看,都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也超越了 1990年代以来的欲望现实主义写作和反讽美学,是一部当代小说“传奇现实主义”的代表性文本。
作为一个严谨、勤奋而且高产的作家,郭严隶当然还会继续拓展自己的文学空间。《锁沙》已经出版,一个更大的期待留在我们面前:郭严隶的“传奇现实主义”小说之路还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与奇迹?
〔1〕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M〕.刘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46.
〔2〕郭严隶.锁沙 〔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192.
〔3〕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M〕.刘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218.
〔4〕郭严隶.锁沙 〔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12-13.
〔5〕贺·宝音巴图.蒙古族树木崇拜 〔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0.88.
〔6〕席·哈斯巴特尔.榆树在蒙古族民间信仰中的象征意义 〔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06,(6):122-126.
〔7〕郭严隶.锁沙 〔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342.
〔8〕郭严隶.我的乌兰布通草原 〔N〕.中国艺术报,2010-08-09(3).
〔9〕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 〔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8.
〔10〕郭严隶.锁沙 〔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64.
〔1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62.
〔12〕郭严隶.锁沙 〔M〕.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205.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I206
A
1004—0633(2011)03—137—06
2011—03—10
支宇,文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