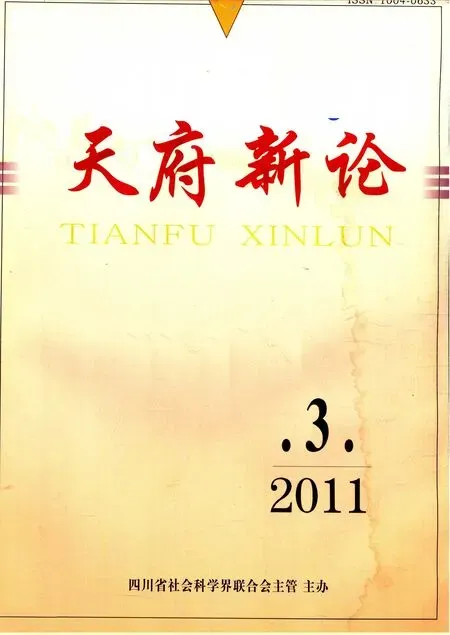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
——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2011-03-18张娟
张 娟
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
——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张 娟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政制创新;路径依赖;路径替代
政制创新就是通过改革或打碎旧政制,构建一套更具功效的、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新政制的方式与过程。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政制创新的目标就是构建起一套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宪政制度。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政制变迁始终处于皇权专制的路径“锁定”状态而无法突破,晚清政府试图藉体制内改革来消弥合法性危机的努力也遭到破产,正是辛亥革命以突变型政制创新的方式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王朝帝制循环的路径依赖状态,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实现了中国政制变迁进程中的路径替代。但是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未能有效地完成路径塑造和政治创制,辛亥革命中建立起的议会共和政体仅是昙花一现,旋即凋谢。本文尝试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把辛亥革命纳入制度范式和制度话语中进行新诠释和新剖析。
一、路径依赖与晚清政制改革的困局
“路径依赖”范畴由保罗·A·戴维首先提出,由经济学家W·B·阿瑟进一步深化发展,最初应用于技术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后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并很快成为当代社会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诺斯认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制度变迁史上遭遇的制度僵化、制度惰性和制度滞后之困局,无不与制度依赖有关。而导致制度依赖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制度的自我捍卫机制。某种制度一旦被选定和确立就具有极大的惯性和惰性,并会产生一种自我捍卫和自我强化机制,沿着初始选择的轨迹一直演化下去,非凭借强大的外力难以扭转其发展路向,这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借助路径依赖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精辟地解释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以及长期不良绩效的社会和经济为何会持续存在。路径依赖的根源在于制度的收益递增和具有交易费用的不完全市场。诺斯认为,制度初始创建时的高成本、由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而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和协作效应、制度创设过程中衍生的非正式规则、制度产生的适应性预期等等都会产生制度的收益递增。而由于现实世界中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备、交易费用高昂,行动者的主观模型将会被非常不完全的信息反馈及既定的意识形态所修正,“历史上由行动者派生的观念就会规定他们所作出的选择”〔1〕,从而使他们在收益递增规律的约束下,很难摆脱即使是已经意识到的,但却是低绩效的变迁路径,于是制度变迁就出现了种种模式和持续的无效率。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制度一经确立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繁衍出各种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 “具有抵制任何变革的动力和权力,因为变革会剥夺它们所攫取的扩大了的社会产出份额”〔2〕。制度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现存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打破与再分配,影响既得利益集团的租金收益,因而必然会遭到旧制度庇护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与阻碍。
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派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观深为认同,但同时强调,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政治学家皮尔森 (Paul Pierson)指出,相对于经济生活而言,政治世界具有几个明显的相互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强化了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活动中,任何一项政治产品 (政策)的产生过程都是集体活动的结果,每一项政治活动也都依赖于他人的合作,极易产生人们对制度的适应性行为;二是政治制度的高度密集。供给公共产品的政治生活必然要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因此大多数政治活动也就必须基于法律和制度约束的基础上而展开,而无法自由退出;三是能够运用政治权威来提高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活动主要是一种权力活动,权力具有非对称性。权力的支配方在巩固自己权力的同时,也在巩固既存制度;四是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政治生活中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五是政治活动所提供的是一种非竞争性公共产品,政治供给的非竞争性决定了政治活动的主体缺乏改善制度的动力。〔3〕
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帝制统治给后人积淀下一份以皇权为运作轴心,以官僚、专制、集权、人治、封闭、重农轻商为特征的传统政制文明遗产。这种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超强的行政权力宰制一切,压制了经济社会的自主发展空间。中国传统政制文明在中华帝国早期崛起的过程中,在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整合、增强民族内聚力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明清之后,这种政制却愈来愈显得僵化与停滞。众所周知,在明朝中后期,我国曾经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循着西方的理路而发展兴盛。传统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集权专制政制对社会经济的超强控制,乃是压抑和窒息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壮大的重要因素。传统集权帝制与以小农意识为基础的臣民政治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政制变迁的路径依赖,这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导致传统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被 “锁定”在皇权专制主义的路径上,进行王朝的闭合循环。传统中国只有王朝之更迭,而没有政体之创新。政体的僵滞严重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导致中华帝国迟迟无法突破农业文明圈而从传统走向近代,也导致了在近代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东西方文明冲突性际遇中天朝帝国的衰落。
鸦片战争一役,华夏大国败给蛮夷小国,朝野震惊。一系列的签约、割地、赔款不断地瓦解着中国主权。一部分眼光敏锐的天朝士大夫开始认识到中国历史格局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西方国家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语)。如何“应变”以“图存”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而师法西方就成为求解这一难题的主方向。早期的先觉者主要从器技层面来反思天朝落败的原因,主张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而震惊朝野的甲午之败不仅宣告了以“器物”师西为主旨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政制的省觉与反思,于是甲午之后,求变思潮开始滥觞,政制改革成为显性话语。虽在甲午之前,甚至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封建统治营垒少数比较开明和清醒的士大夫阶层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洪仁轩、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郭嵩焘等,不仅已经看到了对手的船坚炮利和军事技能的优长,而且已开始模糊的认识到了西政优越之处和中西政制的落差,然其呼吁曲高和寡,未得国人响应和上层青睐。
因此,近代中国真正开启政制变革尝试帷幕的乃是由康梁所发起、却中途流产的戊戌变法运动。在忧于民族危亡的焦灼急迫心理中,在惊于日本经由政制创新一跃崛起的奇迹之时,以康梁为代表的一部分敏感先觉的知识精英试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酝酿在中国发起一场君主立宪取向的政制改革运动。然而,由于以光绪和康梁为首的帝党派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制创新集团的政治资源的薄弱、政治经验的阙乏、改革策略的操切激进与改革心态的浪漫主义、以后党派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压制和绞杀,使得这场政制创新尝试甚至尚未实质性启动就已胎死腹中。
在戊戌变法流产后,清王朝的政治衰败过程加快,政治权威不断弱化、政治认同危机日益扩散。随着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与八国联军的挥师入京,民族危机与政权危机进一步恶化,政治动荡加剧,全国各地反清起义此起彼伏。在内忧外患形势的逼拶下,继续盲目固守传统制度和政策已是死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20世纪初晚清政府终于正式启动了政制层面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已似风中残烛的晚清政府希图通过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将外援西政嫁接到本土皇权专制政体上来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化解日益深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然而由于改革者宪政信仰的薄弱和立宪动机的功利工具性,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和匮乏,政治控制能力的虚弱,上下既得利益集团对新政的消极漠然、敷衍搪塞,僵化滞后的传统政制无法适应迅速膨胀的政治参与,等等,使得晚清王朝的这场自救性改革注定无力回天。尤其当清政府拒绝立宪派的数次国会请愿和所谓“皇族内阁”的成立,更是折射出腐朽的晚清政府名行立宪,实欲借立宪之形式维续专制之实的本质,令国人彻底失望。近代中国试图通过政治改良实现政制创新、打破皇权专制的路径依赖状态、迈向现代政制文明的努力陷入困局和僵局之中。
二、辛亥革命与政制变迁的路径替代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突然的,但又有其历史必然性。美国政治学家温德尔·菲利浦斯曾有句经典的话:“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4〕一场革命的爆发不是某个人所能煽动或蛊惑的结果,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是不会听别人的指使去进行革命的”〔5〕,革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积聚到临界点必然的爆发,“任何革命本身都意味着危机,而且是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6〕。
晚清末年,权威流坠,民生凋敝,哀鸿遍野。虽然清政府自 1901年起开始推行新政,却非但未能刷新吏治政风,且各级官僚均借新政之名中饱私囊,政治更加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史料记载当时由于庚子赔款“遍摊于十八行省,民间已啧有烦言。近则新政所需,无不用其摊派,计臣但知提拔,不问款项之何来,疆吏无计搜罗,且复刻剥以塞责。”本已灾荒连年,上层仍然肆意屯粮居奇,而广大“细民无以糊口,思乱者十室而九”。〔7〕各地民间骚乱和暴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也前赴后继地在各地策划和发动起义,晚清政府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1911年的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火苗,随后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革命之火迅速蔓延全国,不到两月,全国已有14省纷纷起义宣告独立,满清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中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代替了满清王朝,以议会内阁制代替了封建皇权专制。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分析,辛亥革命的政制创新意义有二:
(一)以突变型政制变迁的方式打破了传统政制的路径依赖
制度创新可分为渐进型和突变型两种方式。渐进型制度创新是一种在保持根本制度框架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对局部制度或外层制度的调整、变革和更新。突变型制度创新是指以激进的、急剧的、全局的方式在短时间实现制度的替代更换。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压倒性的方式是渐进式变迁,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一个制度框架的总体稳定性使得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换成为可能。〔8〕但是诺斯也同时指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战争、革命、武力征服以及自然灾害等情况下,会发生非连续性、断裂性制度变迁,即突变型制度变迁。当政治交易或政治冲突双方无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达成谈判和妥协时,其中一方就会利用意识形态凝聚支持力量,凭借暴力手段打破制度僵局,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新制度。对于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的优劣评价,应结合具体民族的具体历史情境来判定。在和平时期通常采取渐进型,以逐次铺展、探索试错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社会长期陷入了制度无效率的路径锁定状态下,就必须通过突变型制度变迁来跳出僵局,粉碎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创新的抵制和阻碍,以更具效益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则正是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史上的一场突变型制度创新。
(二)实现了从帝制轨道转向宪政共和探索之路的路径替代
关于革命在政治发展和政体更迭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经典的论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9〕因为旧制度的创设者,旧的统治集团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必须经由革命去推翻它,以完成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递嬗。当代新制度主义学家对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革命的意义也作了精辟的分析:革命是突破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路径锁定而实现路径替代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武器。革命能够打破既有体制内的权力结构,剥夺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摧毁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垄断,拆除旧制度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桎梏,解放人们的思想,促成制度变迁的路径突变和路径替代,从而为政制创新提供契机和动力。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就指出,革命可以引起与过去的彻底决裂,甚至改变以前的趋势,“革命是变化的必要高潮——正如为了让小鸡生出来就要打破蛋壳,为了让蝴蝶出来就要打破蝶蛹一样。”〔10〕刘易斯认为辛亥革命正是推动中国制度变迁发生路径替代的突发性事件。
辛亥革命废除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打碎了自秦以来二千多年超稳定的传统政治秩序,使近代中国走出了王朝封闭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在中国进行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首次尝试。因而可说正是辛亥革命正式启动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开辟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为此后的政制创新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千年官僚帝制统治下,虽然各种农民战争和起义不绝于书,但历次起义最终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只有王朝的循环,而无政体的更迭,更谈不上近现代意义上的以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政制创新和政治现代化。辛亥革命虽然未能巩固民主共和,但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路径锁定,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从此引入了宪政民主的探索之路。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曾讲:“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11〕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帝制皇权再无生存空间。身历其境的张謇在当时曾说道:“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有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12〕自此后,任何独夫民贼妄想复辟帝制都会遭到人们的唾弃。正如梁启超于 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言:“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13〕
三、共和制的昙现与政制创新的夭折
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宣告诞生。随后所确定的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集中地映射出新生政权的奋斗目标:效法欧美政制,建设民主共和。1912年 3月 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 7章 56条,对国家机构体制设置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在政体选择和国家机构设置上,《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临时约法》仿照欧美式“三权分立”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参议院;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有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人身、财产、言论、结社、集会、通信、居住和宗教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有依法纳税和服兵役之义务。
辛亥革命中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本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续 3个月,政权就落入了封建军阀袁世凯手中,《临时约法》随后被袁废除。南京临时政府所建立的共和政体宛如昙花一现,遂即凋谢,从袁世凯篡位起,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开始滑堕入封建军阀专制的泥潭。政治倒退使得近代中国的政制变迁再次陷入僵滞之境。
如何评价辛亥革命这场政制创新运动的绩效呢?评价一场政制创新运动的成功与否是看其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牢固地确立起了一套先进有效的政治制度。对于革命型政制创新来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仅要看政制创新主体能否成功地创建新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制创新主体能否牢固地确立与巩固新制度。亨廷顿曾经精辟地说道,革命不仅要成功地实现政治动员,而且“一个彻底的革命还包括第二个阶段: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成功的革命往往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制度化结合在一起。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能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程度的标准,是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和范围。但衡量一场革命成功与否的尺度,是革命所创立的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14〕不能牢固地确立新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革命无疑是不彻底的革命,也是不成功的政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不是一场成功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所诞生的中华民国却仅仅是割掉了一条 “辫子”,民初议会共和政体犹如漫漫黑夜中的流星,破空一划、瞬间陨落,近代中国遂进入军阀专制、四分五裂时代。辛亥革命虽然打破了传统中国几千年来皇权帝制的路径依赖,但却未能成功地实现宪政民主的路径塑造。
四、辛亥革命中政治创制失败之反思
为什么辛亥革命中作为政制创新主体的中国同盟会未能在近代中国有效地确立起民主共和政制呢?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政制创新集团未能克服集体行动 “搭便车”问题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研究发现,“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5〕。由于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而理性的、算计的经济人并不会致力于追求集体利益,这样就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人对集体行动的不负责任和搭便车 (个人总是希望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这就导致政治团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盛行、组织纪律涣散、效率低下等现象。
辛亥革命虽以“创立民国”为旗帜,但同盟会内部从事革命的有的怀具功利性目的,有的单纯是反满,许多成员并不具有对宪政共和的坚定信仰。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同盟会中流行一时。武昌起义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一度使许多同盟会员陶醉而忘乎所以,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对形势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大多数同盟会员沉浸在“清史推倒,共和建立”之中,认为这就是“新生活的开始”,革命成功了,因而“奋斗精神逐渐丧失,革命事业再也不肯继续去做”〔16〕。而且,由于变成了执政党,许多同盟会员追逐名利,蜕变堕落。连袁世凯也说:“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的识时务者,今日多已踞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17〕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更加庞杂,许多旧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道革命旗帜下来投机和“搭便车”,造成了革命队伍的鱼龙混杂和先进性的退化。正如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而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18〕在辛亥革命所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充斥了大量并没有真正的共和追求、亦不抱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的“搭便车”式的官僚政客。制度创新行动集团的内聚力薄弱和组织的涣散,决定了这场革命尽管打破了近代中国政制变迁的路径锁定困局,也无法成功有效地在中国建立起宪政共和。
(二)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有效创制所需的行动资源匮乏
政制创新是不同政治行动集团重复博弈的结果。成功的政制创新需要政治行动者拥有强大的行动能力,而行动能力基于行动资源之上,没有足够的行动资源,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预期行动目标和抱负。正如政治学家沙波夫指出的:“在缺少行动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最清楚的理解和偏好,也不能使实践发生改变。”〔19〕行动资源包括权威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等。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于政制创新进程中遭遇挫折之原因,就在于行动资源的薄弱。
首先是权威根基太浅。武昌起义的突然爆发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仓促成立,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尚未来得及在通过全国规模的政治动员而实现执政党权威对社会的广泛渗透。辛亥革命中所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占据 2/3部长席位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对革命派也并不支持。同盟会势孤力单,权威资源比较薄弱。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亦未能建立起有效的个人权威。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虽然名义上还是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但已是一筹莫展,他的话很少有人听了。章太炎曾轻蔑地嘲笑他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20〕
其次是经济资源匮乏。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呼吁“中央财政匮乏已极”,从各省也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援,海关由外国控制,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公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向外国银行借债也屡屡遭拒。〔21〕据史料记载,一次安徽都督因继续军饷,派专使前来求救,孙中山批给他 20万,派胡汉民去财政部提取,可是财政部“金库仅存十洋”〔22〕。
再次是组织资源涣散。如前所述的,同盟会始终未能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未能锻造成一个具有内聚力和团结力的现代政党组织。
最后是军事资源薄弱。一场成功的、由政治革命所引发的突变型政制变迁中,需要政制创新主体拥有和借助一定的军事资源来巩固和保障政制创新的成果。辛亥革命之后议会共和制的夭折,就在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并无兵权,军事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手中。没有足够的军事资源来为刚诞生的民国保驾护航,民主共和制在封建专制军阀的包围中就无法确立和成长,政制创新的夭折就不可避免。
(三)政治创新行动集团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
意识形态是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套认知体系,反映了该集团的利益取向、价值诉求和政治理想。当代新制度学派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对于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动员力、整合力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来说至关重要。而制度创新行动集团常常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诺斯通过研究发现,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确有很多政治团体存在着成员白搭车、机会主义行为、组织纪律涣散、效率低下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些组织具有高度的内聚力和强大的动员力,其组织成员能够自觉自愿地不计个人得失而为组织的共同利益而努力。
诺斯指出,对于这种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相背离的情况,“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23〕。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那么,我们解释现行资源配置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的缺口”〔24〕。一套成功的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克服白搭车问题,使成员能够不按个人成本收益算计来为团体利益而行动或作出牺牲,帮助政治集团跳出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在政治集团成员中发挥一种凝聚、引导、动员、激励功能,从而有助于型塑和打造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有助于拆除分利集团壁垒,推进制度发展。
当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流派——话语性制度主义也认为,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除了论证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凝集和团结集团成员之外,还应该把其指导功能贯穿于制度创新的整个阶段:在制度变革的“前夜”,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和传统体制的功能已经出现危机,已经无法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指导,意识形态通过提供一套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理想设计蓝图,并附有合理的实现路径和行动指导原则,能够减少政治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引导和激励团体成员为之奋斗,从而开启制度变革之门。在制度变革阶段,意识形态通过在本集团成员之间形成价值共识和认同,从而能够形成“统一战线”,凝聚改革力量,保证制度供给。〔25〕
而反思辛亥革命中政治创新夭折的原因,未能构建起一套系统、严谨、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并将其内化于集体成员的思想信仰中,成为集体行动的航标和动力,则是一重要因素。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但却缺乏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步骤、依靠力量、阶级基础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深入准备。而且其“建立民国”的目标也未能成为其成员的集体认知和真诚追求,许多成员并不怀有对宪政民主的自觉尊崇和信仰,组织松散的各革命派别仅是在“反满”的旗帜下暂时联合,虽不乏民族革命之热情,却欠缺民主革命之自觉,更缺乏对革命后如何巩固共和、创设新制、推行宪政等重大问题的周密细致的规划蓝图。
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中诞生的中华民国虽然移植了西式的三权分立制、议会内阁制、多党制,希图“揖美追欧”,建设宪政共和,然而民主、自由、人权等宪政诸要义并未真正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依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有的仍然只是披上各种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26〕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易劳逸所说:“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新的共和国为民主政府的建立准备了一整套设施:如宪法、众议院、公民选举以及孟德斯鸠式的分权政府。然而,这一切却被证明是对其所模仿的西方民主模式的嘲弄。”〔27〕
(四)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分为两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被称为“外在制度”、正式规则,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所供给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包括政治制度、法律规章、经济制度、政策条例和合约等。非正式制度也被称为“内在制度”、非正式规则,是人类在长期社会交往中演进而来的,包括价值规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相比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为艰巨和复杂。诺斯在肯定突变型制度变迁之于打破路径锁定时的作用时,同时也指出,突变型制度变迁也有弱点,除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暴力流血之外,还有一大弱点就是,突变型制度创新的结果是正式规则发生了迅速改变,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异常缓慢,由此就会形成“非正式规则与新的正式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28〕。由于作为非正式规则是基于社会深层次的文化遗传,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便是当正式规则的向前延伸与发展的时候,非正式规则的巨大引力仍会导致正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和变异。因此,对于许多经激进革命而完成新制度创建的国家来说,革命后的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任务比革命本身还要艰巨复杂得多。
辛亥革命中之所以未能使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牢固扎根,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乃是一重要原因。中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轴心,以等级、从属、专制、集权等为价值取向的臣民文化深刻久远,已与民族习惯、民间生活浑然一体,无所不在,成为国民普遍的思维定势。这种臣民文化在近代已经成为抵制一切现代化取向的政制变迁、改革与创新的强大阻力。梁启超在1903年就曾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之品格缺点有: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而且中产阶级力量薄弱,这些缺点决定了在中国很难一蹴而就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因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启发民智,逐渐过渡到民主共和。〔29〕虽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有待商榷,但是他在 20世纪初就对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深层阻碍确是洞悉得极其透彻。
反观辛亥革命中效法欧美政制的南京临时政府,创制宪法、组建国会、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多党竞争等西方式民主政制形式都有体现,但是宪法完全不具权威,政制完全不具稳定性,国会选举徒具形式,多党竞争的游戏规则被肆意破坏。为何西方的选举民主、竞争民主被移植到中国就被运行得面目全非呢?其深层根源还必须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去探寻。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帝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使得专制主义、权力崇拜观念沦肌浃髓。这种政治文化土壤不仅使得近代中国自身未能生长繁衍出民主法治观念,还使得近代以来“每一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陷之具”〔30〕。缺乏适宜于宪政民主扎根成长的政治文化土壤和温床,是革命派未能巩固共和制的深层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一部分知识精英基于对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而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试图对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遗产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淘汰,以西方的民主科学来改造国民性。然而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本身顽固的生命力,以及新文化运动仅限于在部分知识群体范围开展的缺陷性,使得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民主”、“科学”等启蒙口号一时响彻云霄,但却终因没有广泛渗透社会,融入民心而归于沉寂。
五、结论
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来看,对于外源后发型国家来说,现代宪政共和制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从早发内源的现代化西方移植和效仿成为后发国家推进政制创新的首选之路,从节约探索试错的成本角度来说,不失为一条优选之路。但是在进行制度学习的同时,更必须致力于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制度的融合创新,把师法与鼎新相结合,既顺应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又独具本国特色、契合本土文化,只有如此才能使制度成功运转、绩效斐然。毛泽东有句名言:“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1〕具体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旧制度突然崩塌之后的图景是:权威真空、政权分裂、社会混乱。制度断裂和制度真空的现实,亟需一个现代化导向、秉持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拥有强大的集团行动能力、具有强大凝聚力整合力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承担政制创制和政制发展的历史使命。然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意识形态的虚弱、组织结构的溃散、行动资源的阙乏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主义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有效地建构起一套现代宪政制度,成功地创立民主共和国。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127-128.
〔2〕[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 〔M〕.商务印书馆,1993.157.
〔3〕转引自: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38-242.
〔4〕[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
〔5〕列宁全集:第 24卷 〔M〕.人民出版社,1957.462.
〔6〕列宁全集:第 30卷 〔M〕.人民出版社,1957.309.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313-314.
〔8〕[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11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 〔M〕.人民出版社,1956.315.
〔10〕[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186.
〔11〕林伯渠.荏苒三十年 〔N〕.解放日报,1941-10-10.
〔12〕张謇.致袁世凯函 〔A〕.张謇存稿 〔Z〕.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
〔1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5集 〔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3251.
〔14〕[美 ]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华夏出版社,1988.260.
〔15〕[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
〔16〕谢俊美.中国同盟会的三个月执政与辛亥革命失败 〔J〕.历史教学,2005,(6).
〔17〕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 〔A〕.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 1辑 〔C〕.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4.
〔1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下)〔M〕.人民出版社,1997.873.
〔19〕Sharpe,Fritz,Games Real Actors Play:Actor-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 in Policy Research.Boulder an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1997,pp.51.
〔20〕金冲及,胡绳武.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 〔A〕.郭双林,王续添主编.中国近代史读本 (上)〔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60.
〔2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下)〔M〕.人民出版社,1997.875.
〔22〕闾小波.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8.
〔23〕[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 〔M〕.商务印书馆,1992.16.
〔24〕[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 〔M〕.商务印书馆,1992.55.
〔25〕朱德米.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J〕.国外社会科学,2007,(4):29-33.
〔2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人民出版社,1979.309-310.
〔27〕[美]易劳逸.1927-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 〔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178.
〔28〕[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121.
〔2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集 〔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702-703.
〔30〕鲁迅.花边文学·偶感 〔A〕.鲁迅全集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6.
〔31〕毛泽东选集:第 2卷 〔M〕.人民出版社,1991.633.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K257
A
1004—0633(2011)03—120—08
2010—12—30
张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国防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科系讲师。 湖南长沙 4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