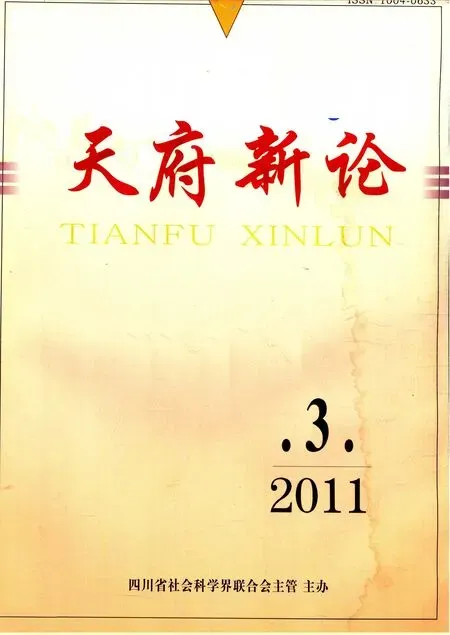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2011-03-18张华民
张华民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张华民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法治化;问责文化;问责理念;问责体制;问责制度
一、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内涵辨析
要理解行政问责法治化,就必须充分认识法治化的根本性和全面性。所谓法治化的根本性,是就法治化的本质而言的,现代民主政治提倡的法治应该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众人之治,而且多数人意志的表达是自由的、真实的,多数人意志的实现是理性的、规范的,法治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根本宗旨在于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保障多数人的权益,追求的是人类治理的根本价值,法治化的根本性意味着肯定法治的公益性、权威性。所谓法治化的全面性,是就法治化的范围和对象而言的,即对社会某一领域、某一现象的法治化是指对涉及这一领域、产生这一现象的所有主体、行为、过程实行最大程度的法治,而不是对部分主体、行为、过程实行法治,同时对其他主体、行为、过程实行他治,法治化的全面性意味着推崇法治的主导性、排他性。
基于对法治化的根本性和全面性的认识,本文对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理解是: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主体、根据多数人的意志、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损害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行政工作人员追究责任、并使受损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得以最大程度恢复的过程以及该过程的规范化。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组织是问责主体,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组织是通过公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如代议制机关;间接组织是指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的组织再通过一定程序产生并赋予特定功能的组织,如政府有关机构、司法机关等。根据多数人的意志,是指问责主体实行问责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问责的程序都必须体现公众的意志,排斥个别人或少数人意志的专断。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损害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行政工作人员追究责任,这意味着对行政工作人员的问责应当由过去局限于过错问责,发展到包括过失问责,由过去仅对损害公众权利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行为进行问责,发展到包括对损害公民权利的一般行为进行问责。使受损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得以最大程度恢复是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我国对行政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必须摈弃以片面追求惩罚报复为目的的“为了问责而问责”的惯性思维,要坚持权利救济的法治要求,对受损权利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使问责制度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正确认识行政问责法治化还必须厘清问责法治化与问责制度化的关系。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问责法治化是一个体现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追究公权力不当或非法行使的责任、维护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过程,是正当或合法权利与不当或非法权力的一种较量。问责法治化的核心内容是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贯穿于问责过程并体现于问责结果,问责规范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内容,而且,多数人利益和意志实现的程度是衡量问责规范和问责效果优劣的首要标准。问责制度化不能涵盖问责法治化的实质内容,只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和意志的制度化设计,才有利于问责法治化的实现,否则,将成为问责法治化的障碍,在行政问责界域内,甚至会使问责由形式上的法治化走向实质上的专制化,成为某些权力专断者推卸责任、压制异己的手段。
二、行政问责法治化的价值追求与根本动力
(一)行政问责法治化的价值追求
价值追求是事物发展内在品质的需要和体现,也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它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而标志于事物发展的终点。行政问责法治化的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
首先,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内在品质看。一则,行政问责法治化承认人民主权是现代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根本理由。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基于维护多数人的正当权益而履行的必要义务,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必要义务,都是对维护多数人正当权益的背离、是对人民主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漠视,因而,承担必要的责任以恢复正当权益的尊严和彰显人民主权的存在,就成为现代政府保持合法存续的必然要求,而正当权益的合理内涵和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正是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再则,行政问责法治化承认多数人参与的问责优于少数人或个别人参与的问责、异体问责优于同体问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现代政府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公权力,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容易滥用权力也是“万古不变的经验”,要使政府的公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对政府的行为加以监督,行政问责法治化正是民主政治视野下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形式。行政问责法治化承认多数人参与的问责优于少数人或个别人参与的问责,就是承认多数人的权利优于少数人或个别人的特权,就是承认多数人比少数人或个别人更能代表和准确反映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从而更有利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行政问责法治化承认异体问责优于同体问责,就是承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就是承认行政问责必须以异体问责为主,而相对政府主体来说,异体问责主体的合理建构和程序的正当设置不仅是多数人能够真正参与问责并取得实质成效的根本路径,而且是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其次,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功能来看。一则,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政府是与专制政府相对应的,与专制政府依赖权威且权责失衡不同的是,法治政府要求依法行政且权责一致,任何违法的行政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代法治本质上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众人之治,政府法律责任的承担实质是因政府违背众人意志的行为而遭受侵害的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得以恢复和维护的体现,如何使政府及时充分地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正是行政问责法治化存在的理由和追求的目标,可见,行政问责法治化通过追究政府法律责任而契合于实现和保障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再则,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公众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公民私权利受到侵害有两个来源,一是其他私权利,一是公权力。在权利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私权利相互间产生纠纷的救济机制已相对成熟而且有效,而私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因为主体间实质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使私权利寻求救济的路途异常坎坷,这其中又因为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更具有广泛性和主动性,而使政府成为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主要形式。为了控制政府行政权、促进其依法行政从而使行政权不能甚至不敢侵害私权利,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有效监督就成为一种必然,而体现多数人意志的行政问责法治化,就是监督行政权行使的有力形式,其保护的私权利的主要体现即是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
(二)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根本动力
根本动力是驱使事物向前发展的根本作用力,它产生于事物发展的起点、作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趋向于事物发展的目标和终点。根本动力不同于一般动力,它对事物的发展力度、发展方向、发展效果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一般动力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与根本动力契合的程度。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首先,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演进过程看。封建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法治化,因为专制的体制和官僚的理念使政府不需要也不习惯于在体现民意的制度的监督下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况且,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和环境相对封闭且沟通形式单调的社会构成,在一定意义上对专制的治理模式有一种合理的依赖,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封建性会导致行政治理模式的单一,很少有中介的、社团的和杠杆性的治理手段可供选择,民意的表达也缺乏有效的渠道。行政问责法治化肇始于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获得解放并取得政权后,为了进一步促进资本的发展,不仅倡导平等、自由的理念,以塑造最优的资本发展环境,而且构建起符合资本发展要求的政府治理模式,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人治走向法治,从根本上防止了封建专制政府死灰复燃;民主、法治决定了政府治理的性质,民主、法治的程度决定了政府治理适应资本发展需要的程度,所以,民主、法治范围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要求;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得到主导性和全面性的发展,市场经济主体的易变性和广泛性进一步凸显,与资本发展休戚相关的利益主体已由少数人普及至所有公民,因此,广大公民已成为政府走向民主、法治的最大推动者。行政问责法治化,不仅是防止封建专制政府死灰复燃的有力手段,更是政府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内容,其发展动力及功能发挥的大小,从根本上取决于公众广泛而有效参与的程度。
其次,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需要看。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3〕我国更有学者指出:政府决策的失误比腐败更可怕。〔4〕行政权是现代社会与公民联系最广泛、最直接的公权力,如何防止行政权被滥用、使其不产生腐败甚至杜绝腐败呢?行政体制内部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尽管重要但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现代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反映现代社会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由国家本位或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广大公民真实有效地参与对行政权的监督,使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在公民的监督下得到落实,使行政权在围绕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条件下得以健康运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的基础是和谐,发展的重点是经济,社会和谐和发展经济是现代政府行政的两大重心;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其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只有体现广大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分配,才能保证最大的公平,只有满足广大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任何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需要,都不可能从根本上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所以,政府行政必须反映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的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正是通过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以达到实现和保障公众权利的目的,因此,其存在的意义和期待的愿景决定了其天然地依赖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
三、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一)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
影响我国法治化问责文化形成的因素很多,如传统思维习惯、政治演进过程、物质生产条件等,但从根本上说,贯穿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中且对我国法治化问责文化尚未确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权利本位思想的缺失。权利本位思想的缺失,是我国传统习惯思维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长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大一统政治集权模式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商品经济等现代生产方式长期难以充分发展的内在原因。权利本位思想缺位的必然结果,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漠视和轻视,以及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畏惧和无奈,因而从根本上导致我国行政问责中“重统治权威、轻权利需求”和“重明哲保身、轻匹夫有责”现象的存在。要使我国建立起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现代法治化问责文化,灌输问责理念和加强道德教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极为悠久的灌输和教化历史的国度来说,仍然有需要但绝非最重要。目前最重要的,一是完善真正体现权利本位的国家权力结构。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意,这就决定了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既是现代国家权力产生和建构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在,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蹂躏权利本位的权力狂想,都必然遭到谴责和否定。这种国家权力结构的构建必须遵循“由权利产生权力、由权力制约权力、由权利否定权力”的逻辑主线,使国家权力行使者在权利否定权力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权力因权利而存在、使私权利拥有者在权力服务权利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监督国家权力就是维护自身权利,从而树立权利意识、促进法治问责。二是大力开展真正维护权利本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每一部充分体现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布,都会积极推进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因为法律法规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认可,使公民对权利的认识由抽象到具体、由模糊到明确、由不可触及到可以预测和可以操作,为公民捍卫权利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如《行政诉讼法》、《劳动法》、《物权法》等法律的颁行,无不是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助推器。同时,每一次充分体现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的司法实践,尤其是经典判决,都是公民乃至整个社会法治意识进步的生动教材,其宣扬法治的作用往往是一般的灌输和说教所难以企及的,中外法治进程中均不乏此例,如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孙志刚案”和推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5〕,因为它们都以最直接的方式、最有效的结果向公众展示:无论面对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权利的维护不仅是正当的、现实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二)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
理念,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一种主观思想认识,是人的思维对事物的规律及本质经过长期认识和判断而形成的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总和。法治化行政问责要求以权力受到制约、程序保持公正、权利得到保障为其基本理念,而我国行政问责出现了“重权力问责、轻权利问责”和“重应急效果、轻实质效益”的理念错位。更新我国行政问责理念,从根本上依赖于公众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到行政问责过程之中。其一,只有公众参与问责,才能真正实现由“权力问责”走向“权利问责”。权力问责与权利问责的关键区别在于:权力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的存在和延续,而权利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尽管现代民主政治从逻辑上诠释了权力产生于权利并服务于权利的内在联系,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独立和膨胀的天性,所以,权力一旦由权利产生之后,其背离权利甚至侵害权利的冲动和举动就从未停止,而且这种背离和侵害在民主意识欠缺和民主制度欠成熟的国家则愈加明显。在我国,要使问责能真正羁束权力且使权力始终服务于权利,拥有权利的广大公众采取各种方式广泛而有效地参与问责过程是根本路径而且是根本保证,也只有这样,法治化问责理念才能真正形成和深入人心。其二,只有公众参与问责,才能真正实现行政问责维护权利、促进发展的实质效益,而不是仅仅追求应急效果。问责实质效益的发挥依赖于问责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其中,实体正义表现为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程序正义表现为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程序正义不仅是实体正义的保证,也是问责发挥实质效益的关键,而从本质上说,公众参与才真正是程序正义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基础。一方面,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经常性决定了公众参与问责必须依赖有效的程序,否则就会出现无序问责;另一方面,公众参与问责的权利要真正摆脱利害权力人的干预,法治化的程序设置是最有力的保障手段,否则,权利问责最终将走向虚化和人治化。在我国,公众参与问责除了公民个人通过法治化程序直接参与问责外,更多的是通过能够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特定组织依照法治化程序行使问责权。这种特定组织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组织是通过公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如代议制机关;间接组织是指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的组织再通过一定程序产生并赋予特定功能的组织,如政府有关机构、司法机关等。法治化问责程序 (如公开、透明等)能够有效规范特定组织的行为、排斥个别人或少数人意志的专断,从而使多数人的意志能够贯穿问责的始终,以保证问责实体正义的实现。
(三)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
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都是监控权力运行的具体形式,权力制约强调的是以权力合理分配为前提条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权力监督更多表现为权力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约束,尤其是上级对下级的事后监督。相对于权力制约来说,权力监督一直是我国控制权力运行和防范权力滥用的首要的机制安排,因为它契合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当代曾经实行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需要,即“监督制度在中国非常发达并有顽强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它与中国社会以权力为核心的精妙绝伦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与官僚体制相关。”〔6〕但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权力监督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权力控制需要,且弊端日益显现,我国行政问责中“重同体问责,轻异体问责”及由此衍生的问责对象选择上“重形式对象、轻实质对象”的现状就是例证。若要真正根除“谁来监督监督者”和“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现有问责痼疾,我国必须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在着力构建有利于公众直接参与问责的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两方面建设。一是改进现有行政问责机制,关键是合理界定行政体制内的问责主体,而且增强并保障其独立性和权威性;二是从实质上建立起独立于行政权的体现权力制约要求的行政问责机制。这种问责机制在问责主体的设置上,突出其异体性、制衡性和权威性。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使议会 (我国是人大)和法院成为其主要形式,如,美国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等,对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计,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并提出法律决定和建议;法国在 1993年通过了反贪法,并成立了跨部门的“预防贪污腐败中心”,该中心由高级法官及内政部、地方行政法庭、司法警察和税务部门的专家组成。〔7〕在问责形式的选择上,突出其外部性、他律性和威慑性,如建立弹劾制度,使自律性的引咎辞职制度作为必要的补充,因为弹劾具有他律性,具有足够的威摄力。
(四)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我国长期以来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主要以地方政权机关为主,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方式等多方面,不同地区的问责规范存在非常大的差别,造成同事不同罚、同责不同罚现象的大量存在,与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基本理念相去甚远,也与我国除港澳台外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不相适应。所以,从全国看,问责的社会效果十分有限,甚至导致随意问责的负面影响。随着行政问责制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必须纠正这种“重制度颁行、轻制度统一”、“重实体规范、轻程序规范”的现象,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已成为提升问责公信力、体现政府责任心的必然要求。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的重点在于:其一,必须提高立法层级。目前,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是我国行政问责立法的主要形式,至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行政问责法律和法规,如全国人大立法或国务院立法。依我国立法惯例,对于某些有待进一步考察的立法事项,一般先地方或部门实践,待时机成熟时才上升到国家层面。行政问责已经过多年、多地方、多部门的立法实践和实际操作,其立法意义、规范构成和实践要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到了时机成熟上升到国家层面立法的时候了,否则,长期不统一、低层次的问责现象将严重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其二,必须统一问责规范。问责规范的统一要求问责制度在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设计上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包括问责主体的产生和类型、问责对象的性质和范围、问责事由的内涵和外延等都必须有统一的明确规定,特殊情势下的特殊规定只能是统一原则前提下的例外,从而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尊严,从国家层面、从制度上克服我国现实问责中普遍存在的问责规范不统一现象。其三,必须突出程序建设。我国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从古至今的法律制度建设中一贯忽视或轻视程序规范的制定,使执法或司法的程序依据缺乏,尽管近年来程序法制建设有了快速发展,但与现代程序正义的法治要求依然相距甚远。纵观我国数十部有关行政问责的有地方规章和部门规章性质的规范性文件,除浙江、深圳、公安部等制定的少数法规、规章中辟专章规定问责程序外,绝大多数法规、规章中的问责程序散见于实体规范中且条文稀少、难以操作。所以,在统一立法中,必须突出程序规范、开辟专章规定,而且避免过于原则和脱离实际,使行政问责在公正的、可操作的程序保障下实现其维护公众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法治目标。
〔1〕〔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M〕.商务印书馆,1961.156,156,156.
〔4〕尹卫国.决策失误比腐败更可怕 〔J〕.领导科学,2006,(9).
〔5〕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 〔M〕.法律出版社,2004.172.
〔6〕孙笑侠,冯健鹏.监督,能否与法治兼容?——从法治立场来反思监督制度 〔J〕.中国法学,2005,(4).
〔7〕秦佩华,胡玥.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N〕.人民日报,2010-09-29.
(本文责任编辑 谢莲碧)
DF3
A
1004—0633(2011)03—084—05
2011—01—22
张华民,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法治政府建设。江苏南京 2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