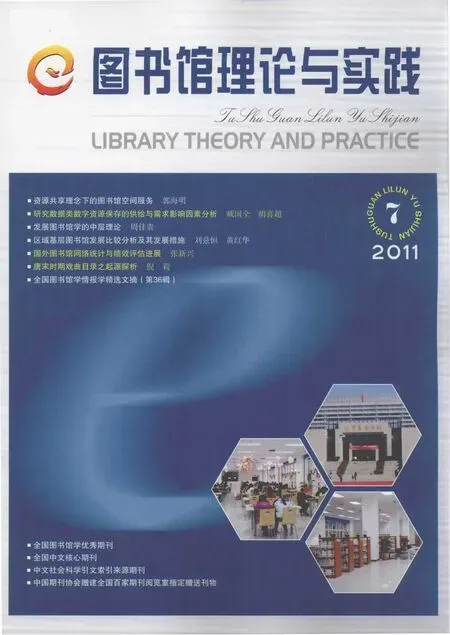敦煌写本《茶酒论》文体考论
2011-03-18钟书林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西安710065
●钟书林(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敦煌写本《茶酒论》自发现后,引起学人的极大关注,成果夥多,但意见的分歧也较大,尤其以它究竟归于哪一类文体的分歧为最大。现按照其说法出现的先后顺序,逐一梳理,然后阐述浅见,以期能将方家对《茶酒论》文体的认识及其渊源的理解有所补充。
一
敦煌写本《茶酒论》见于伯2718、伯2875、伯2972、伯3910、斯406、斯5774六个卷子。《茶酒论》最早为刘复先生编入《敦煌掇琐》,在目录中,它与《韩朋赋》《燕子赋》等,同被归入小说类。[1]至于原因是什么,可惜刘先生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这却是对《茶酒论》文体最早的说法。
稍后,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首次对《茶酒论》作了粗略研究,他认为《茶酒论》是从战国时期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发展来的“争奇”一类的游戏文章。[2]大、小言赋的结构主要采用问答对话的方式,《茶酒论》的结构模式与之大体相同。由于郑先生是在俗文学史中说这番话,后世将《茶酒论》称为俗赋或由此而来。不过要强调的是,郑先生本人并未使用“俗赋”一词。
到了20世纪50年代,王重民等6位先生编撰的《敦煌变文集》中收录了《茶酒论》,[3]王先生将它归类为敦煌变文中的对话体。[4]80年代初,张锡厚先生率先突破成见,指出《茶酒论》应是受诽谐文影响的论议文体,短小精悍,论战性强。[5]随后,周绍良先生进一步肯定了《茶酒论》受前代诽谐文体的影响,并将它归入论说体。[6]受周先生的影响,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等书中将《茶酒论》归入敦煌文的论说体进行了深入论述。[7]到了90年代初,赵逵夫先生又从戏剧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茶酒论》应是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8]稍后,或受赵先生说法的启发,王小盾先生提出了一种“论议”的新文体:“指一种由表演双方围绕特定命题往复话难、以问答形式进行的伎艺及其文学记录”,[9]并将《茶酒论》《孔子项论相问书》《晏子赋》和五言体的《燕子赋》等归入了此类文体。尽管众说纷纭,新见迭出,但在90年代末,张鸿勋先生编撰《敦煌学大辞典》“茶酒论”条时,遵从一般性的说法,将《茶酒论》归入俗赋一类。[10]不过这一分类,仍然遭到了谭家健先生的异议。谭先生提出:“据我所见,似乎可以算作白话散文。”[11]
以上从刘复到谭家健先生,纵观《茶酒论》文体研究近百年的历史,围绕《茶酒论》的文体分类先后形成了8种不同的说法,虽然有些说法较为近似,但总体分歧仍然是较大的。可见《茶酒论》文体的复杂性。
其复杂的程度,还表现为对《茶酒论》文体的认识,有时甚至在同一位研究者那里也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看法。如对敦煌文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颜廷亮先生等在《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 中将《茶酒论》归入“论”体,但到了他们编写《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2000年)一书时,却转而同意王小盾归入“讲唱”体的说法。[12]这些前后不一致看法的出现,正证明了颜廷亮等先生仍然还在孜孜不倦地思考、探索,以求找到关于《茶酒论》文体的最佳答案。
二
《茶酒论》以拟人的手法,采用对话体的结构方式,茶与酒论辩短长,相互争功,最后由水出面调停,点明题旨。这些特点都能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先秦诸子散文作为中国散文的源头之一,大多都采用的是语录体对话形式。春秋时期,《论语》《墨子》多以语录对话的方式结构谋篇;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阐明各自的主张,论议辩对之风盛行。以《庄子》《韩非子》为例,多有与《茶酒论》结构、文体相似者,兹举数例以证,并明瞭其间的源流关系。
《庄子·逍遥游》开篇写鹏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招来了蜩与学鸠的讥笑:“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而庄子最后出面批评二者说:“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在这里,庄子充当了第三方“水”的角色,蜩与学鸠炫耀己能,攻击对方,实有茶、酒争妒的身影。而众所熟知的《庄子·秋水》中河伯与海神若的对话,通过7轮的反复问答、辩对,最后庄子给出结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首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不过其最为相像者,应首推《秋水》中夔、蚿、蛇、风之间的对话:
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不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
蚿曰:“不然。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谓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何也?”
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夔、蚿、蛇、风互相争胜,论辩短长,而都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对方的短处。这一番对话,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茶酒论》很接近了。前文所引郑振铎先生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茶酒论》是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发展来的。大、小言赋是有名的对话体辞赋,将《茶酒论》归为俗赋也即由此而来。其实,宋玉的对话体辞赋并不是最早文学样式。已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指出:“宋玉的辩对作品在辩对结构、辩对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等方面,对《庄子》借鉴颇多”,“宋玉的赋,都采用问答的方式,以问开头,从而引出后文的长篇大论。这正是《庄子》辩对文体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同时“汉大赋的文体结构远承《庄子》,近承宋玉之赋,与之有明显的渊源关系”。[13]因此,《茶酒论》的文体渊源并不止于宋玉的大、小言赋,它还得从《庄子》说起。
不过,它的文体渊源也并不局囿于《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对它也应有较大的影响。《韩非子·外储说》记载的“郑人争年”较为典型:“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两人为了争年,竞相夸耀,虚妄无比。而《战国策》的“鹬蚌相争”:“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舍,渔者得而并禽之。”蚌、鹬互相斗狠,两败俱伤。这一极为深刻的反面教训,为《茶酒论》所吸收。
上述例证足以让我们明瞭《茶酒论》的文体特征是散文,而不是其他。实际上,在上文回顾的有关《茶酒论》文体归类研究的8种代表性意见中,如果浓缩一下,主要是5类:(1)小说类:刘复先生持此说;(2) 变文说:王重民等先生持此说;(3) 俗赋类:郑振铎、张鸿勋先生等持此说;(4)散文之论说类:张锡厚、周绍良、谭家健先生等持此说;(5)戏剧讲唱类:赵逵夫、王小盾先生等持此说。小说类、变文类的分法,是早期敦煌学家的观点,由于当时时代条件的束缚,他们看到的资料很有限,所以他们的归类也有点欠于稳妥,后来信从的人也极少。戏剧讲唱类的分法,“以表演的伎艺特征来区分敦煌文学作品的类属,固然无可厚非,但是若以此替代敦煌文学作品的文本特征,就有可能导致把某些不具备表演伎艺特征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散体叙说为特征的敦煌文,将继续被摈逐在敦煌文学之外”。[5]所以以此对《茶酒论》的归类,似乎就有些不恰当了。
“俗赋”类的分法,带有较深的“敦煌俗文学”的色彩。由于郑振铎先生在敦煌俗文学上的贡献,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就用它来指代了整个的敦煌文学。直到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及周绍良先生牵头而由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的相继问世后,“敦煌文学”的提法才逐渐取代了“敦煌俗文学”之说。因此,笔者以为将《茶酒论》归于俗赋,仍然是“敦煌俗文学”提法的遗留的体现。最可称道的是张锡厚先生,他在《敦煌文学》专门设有“俗赋”一章,但他并没有将《茶酒论》简单地归入俗赋,而是高度评价了《茶酒论》在敦煌文学论议文体中的独特价值。他说:“敦煌藏书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论议文体,常常是为了论述某种道理而写成的短小精悍的杂文,语言通俗,驳诘有力,论战性强。如《茶酒论》就是一篇代表作。”[5]这是很有见地的。谭家健先生也说得很好,如果将《茶酒论》“归之于俗赋,然而与同时的俗赋《燕子赋》、《晏子赋》、《韩朋赋》似有区别,否则何以不叫《茶酒赋》?”这一质问是很有道理的。《茶酒论》之所以称之为“论”而不称之为“赋”肯定有它的道理,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仅从“论”字上就判定它是论说文。
三
敦煌地处中西方交通要道,是中原文化与与西域文明的交汇之地。《茶酒论》出自敦煌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具有鲜明的敦煌地域特色。所以,它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又吸取了西域文明的养分。敦煌是佛教的圣地,也是佛教由此传入中原的重镇。佛教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心,出土的敦煌文献中佛教文献占了绝大的比重。因此,《茶酒论》的出现,不仅来源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饱受佛教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茶酒论》一文,从内容到形式,也受到佛教典籍的一定影响。《茶酒论》拟人的手法,对话的方式,论辩短长,相互争功等诸多文学要素,似也与佛教文学存在一定的渊源。《杂譬喻经》中记载有“头尾争大”的故事。
昔有一蛇头尾自相与诤。
头语尾曰:“我应为大。”
尾语头曰:“我亦应大。”
头曰:“我有耳能听有目能视,有口能食,行时最在前,是故可为大。汝无此术,不应为大。”
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以身绕木三匝三日而不已,头遂不得去求食饥饿垂死。”
头语尾曰:“汝可放之,听汝为大。”尾闻其言,即时放之。
复语尾曰:“汝既为大,听汝在前行。”尾在前行,未经数步堕火坑而死。[14]四528
这是佛教教诲僧众时援引的例子,《茶酒论》中的茶、酒争胜,与此处的头、尾争大,较为相似。只是头、尾争大中,没有中间人出面调停,虽然头到最后做出让步,但仍不免头、尾一同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其警戒意义令人深省。《杂宝藏经》《佛本行集经》等典籍中还记载有二头鸟[14]三923、共命鸟[14]四464的故事,情节与此略微类似:昔雪山中有鸟,名为共命。一身二头。一头常食美果,欲使身得安隐。一头便生嫉妒之心,即取毒果食之,使二头俱死。可见佛教故事,虽然大体情节与《茶酒论》相类,但结局都带有悲剧性,或是佛教为加强劝世教化使然。
《茶酒论》中多处涉及佛教,即为受到佛教之影响的明证。如在茶、酒的第三番辩对中,茶对酒说:“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千劫万劫,诸佛相钦。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以后,令人只是罪深。[15]茶多为高僧所钟爱,但酒却为佛教五戒之一,所以《茶酒论》中借茶之口指出:“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以后,令人只是罪深。”在第五番的辩对中,茶又对酒说:“阿你不见道:男儿十四五,莫与酒家亲。君不见生生乌,为酒丧其身。……阿阇世王为酒煞父害母,刘零(伶)为酒一死三年。吃了张眉竖眼,怒斗宣拳。状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求首杖子,本典索钱。大枷植项,背上抛椽。便即烧香断酒,念佛求天,终身不吃,望免迍邅。”[15]在这次的辩驳中,茶不仅提到人们“烧香断酒,念佛求天”,还引用了广为流传的阿阇世王为酒杀父害母的佛教典故。阿阇世王因为酒而杀父害母的故事,出自《观无量寿经》等佛经,足见作者对佛教典籍的熟悉。就在与《茶酒论》的同一张经卷上,还写有王梵志诗。其中有“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造酒罪甚重,酒肉俱不轻。若人不信语,检取《涅槃经》”等诗句,都为劝化世人戒酒。可见《茶酒论》的创作由于受到一定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茶、酒的辩论中,一些佛教的教义、典故等也随之自然流露出来,渗透在《茶酒论》的行文之中。
经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茶酒论》传世以后,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及藏族文学、布依族文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藏族文学《茶酒仙女》将《茶酒论》中所受的佛教影响扩展到整部作品,“从故事背景、内容情节、人物取名等,都显示出一种浓厚的佛教气息”。[16]在《茶酒仙女》中,茶炫耀自己身世的高贵,自称是天界如意宝树的后代,生在天竺为菩提,生在支那为茶树。在行文上,《茶酒仙女》与《茶酒论》有一些较为明显的传承和再创作的关系。如《茶酒论》中茶的自我夸耀语:“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到《茶酒仙女》中则改为:“只有我才能使名僧大德欣然,使他们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又如《茶酒论》中茶攻击酒说:“酒能破家散宅,广作邪淫,打却三盏以后,令人只是罪深。……阿阇世王为酒煞父害母,刘零(伶)为酒一死三年。吃了张眉竖眼,怒斗宣拳。状上只言粗豪酒醉,不曾有茶醉相言。不免求首杖子,本典索钱。大枷植项,背上抛椽。便即烧香断酒,念佛求天,终身不吃,望免迍邅。”到《茶酒仙女》中有了较大的改动,变为“(酒)饮一碗,烦恼心起,手摸刀柄,口乱言语;饮二碗,丢掉了理智谨慎心,产生种种诡计邪念;饮三碗,全然忘记罪孽;饮四碗,竟勾引女仆、女商和娟妓;饮得再多,犯下了十不赦罪。”[17]相比较而言,内容更细化、具体,更富有生活气息,语言也更加通俗化。因而,藏族文学《茶酒仙女》浓厚的佛教气息,恰也从“流”与“源”关系谱上逆向折射出了《茶酒论》中所受的佛教影响。这样,《茶酒论》的创作既受到了诸子散文的影响,又有佛学的沾溉。不过,由上文的分析看到,在这二者之中,它所受到的诸子散文影响无疑是主要的,并最终决定了它的文体特征。因此,它仍是一篇受诸子散文影响较深的论说文。
[1] 刘复.敦煌掇琐[Z]//黄永武.敦煌初集丛刊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175.
[3]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67-272.
[4] 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C]//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
[5] 张锡厚.敦煌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J].甘肃社会科学,1988(1):104-115.
[7] 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492-494.
[8] 赵逵夫.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J].中国文化,1991(3):157-163.
[9] 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20.
[10] 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586.
[11] 谭家健.中国古代通俗文述略[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33-40.
[12] 颜廷亮,张彦珍.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9.
[13] 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50.
[16] 张鸿勋.敦煌故事赋《茶酒论》与争奇型小说[J].敦煌研究,1989(1):66-73.
[17] 李德龙.敦煌遗书《茶酒论》中的茶酒争胜[J].农业考古,1994(2):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