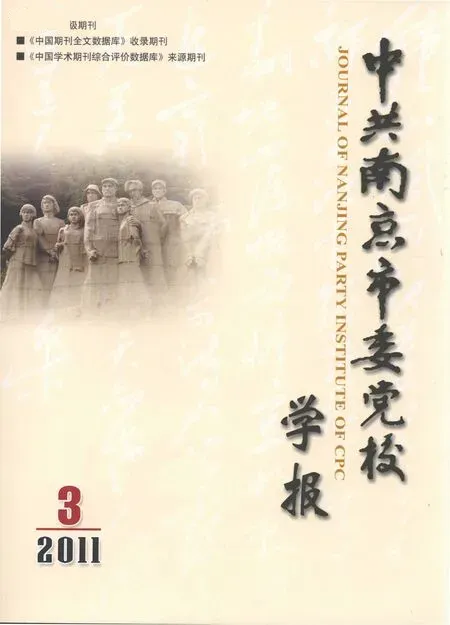专业差异与集体抗争倾向*——以大学生“北漂”群体为例
2011-03-04魏钦恭毛洁雯
魏钦恭 毛洁雯 王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北京 100732)
一般认为,文科比理工科专业学生在政治上更活跃,因此,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用集体抗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一通常看法在有关中国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中亦得到证实。然而,在我们最近关于大学生“北漂”的一次调查中,却发现事实刚好相反:以理工科为代表的非文科毕业“北漂”比文科毕业生参加集体抗争的倾向更为强烈。那么,集体抗争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专业差异?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准备回答的问题。
一、问题与理论回顾
在北京,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从外地来到北京,既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有合适的、稳定的工作,于是只能“漂泊”,靠一些临时性工作维持生计。他们通常被称为“北漂”。①[1]在形形色色的“北漂”人群中,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2]这样一群大学生“北漂”的存在,让人很容易将其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青年学生是各个年龄群体中最有叛逆性的一群,因而经常成为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的主力,[3][4][5]而且是因为以漂泊青年为主要构成的法国巴黎骚乱殷鉴不远。[6][7]有鉴于此,2009年初,我们对大学生“北漂”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涉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倾向。结果发现,在接受访问的336人中,赞成或比较赞成在表达不满时采取公开集会、游行示威或罢工等集体抗争方式的有185人,高达62.29%。虽然意愿并不等同于行为,却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行为,因此,这个数字背后隐含的是较高的集体抗争发生风险,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更进一步,从专业分布来看,文科与理工科学生的集体抗争倾向有显著差异:文科表示赞成的为55.42%,不赞成的为44.58%;理工科则分别为70.99%和29.01%。文科明显低于理工科(见表1、表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差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以往关于教育因素与集体抗争之间关系的研究做一回顾。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教育因素与集体抗争关系的定量研究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特点:
首先,尽管许多文章都将教育纳入到集体行为的研究中,但对之进行的操作化却多限于“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8][9][10][11][12][13]

表1 专业与集体抗争意愿的交互分析

表2 专业与集体抗争意愿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其次,在这些引入“受教育程度”或“受教育年限”的研究中,针对的群体或抗争事件不同,教育会呈现不同的作用。如国内研究发现,当城镇居民面对环境抗争时,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环境抗争的发生比也相应增加。[14]但在关注下岗失业群体抗争意愿的研究中,教育却发挥着抑制作用,即文化程度低的下岗失业工人,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更强。[15]国外的学者如奥尔森(E.Olsen)在对属于“中上阶层”的都市白人所作的抗争行为认同研究中,发现教育对各种不同抗争行为的认可都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即个人所受教育年限越长,越有可能认可这些抗争行为;但这种单调的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却变成了曲线关系,即高教育程度群体与低教育程度群体在抗争行为量表上的得分较高。[16]但作为探索者,奥尔森只是指出了这种行为的存在,却没有给出他的解释。
第三,虽然各研究都发现了教育对集体抗争意愿起作用,但是对这种作用的发生机制却鲜有说明。虽然霍尔(Hall)等人试图探讨教育对不同种族群体抗争意愿的作用机制,[17][18]但他们的研究仅仅是对抗争事件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分类(如争取公民权的事件,反对政府运用暴力的事件,劳工福利事件等等),发现教育程度在不同事件中的作用方向、大小不同,便总结出教育通过提升公民对自由的认可,减少人们对暴力的支持,增加对抗争正当性的了解,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兴趣及认同四个途径影响抗争态度。该项研究忽视了教育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结论显得不够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在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对专业变量的操作化不明晰、教育的影响作用矛盾不一以及对作用机制研究不够的三个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并结合本次调查发现的现象,我们将在下文中试图探究作为教育操作化变量的“专业”对个体集体抗争意愿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假设
正如上文所言,教育对集体抗争意愿的作用在本文中体现为专业的差异,即文科专业具有抑制作用。根据教育的一般作用机制及集体抗争的政治性行为特点,本文拟从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预警机制、社会经济地位机制出发,来解释文科专业更不赞成集体抗争行为这一现象,同时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政治社会化机制(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受访者所学专业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机会越多,其参与集体抗的意愿越低。
假设2.政治预警机制(political warning mechanism):受访者政治危机感越强,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低。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机制(socioeconomic mechanism):受访者社会经济地位愈高,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下面我们分别阐释这三个假设机制的作用过程。
首先是政治社会化,从不同角度考察政治社会化会有不同的内涵。社会学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指个人逐渐学会被现存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和行为等的过程,它强调使个体与社会主导方向一致,内化社会的政治规范并能将其传递给后代。[19]众所周知,在现今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不论何种专业,都需要通过“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学习。有研究者发现大学本科中的文科生两课总学时数达到470学时以上,理科生则达420学时以上。[20]即使是在80年代,与非人文社科专业相比,拥有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大学举办的各种以西方政治思想和当前中国政治为议题的讲座和座谈会,比没有这类专业的院校要多得多;同样,与非人文社科专业相比,大部分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对80年代末的各种讲座与座谈会的参与率也是非常高的。这给浸染于文科学习的人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经过潜移默化,个人肯定并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将其内化到日常生活中,因此面对不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体制外集体抗争时更不可能赞成,这是一种成功的社会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另一种可能是,经常地接触主流意识形态也许并不会使个体接受或内化这种意识形态,而是由于通过意识形态宣传,使得人们认为自己缺少反抗的手段,缺乏反抗的能力,从而达到在人们心中产生恐惧感的作用,使之不赞成有违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行为。这第二种结果则是所谓政治预警机制,即更多接触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会促使其对违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恐惧感。个人对参与不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行为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认识,因此更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东西。[21]所以文科教育的专业设置及其所接触和习得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会起到提醒个人远离政治危险的警示作用。
教育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日益为人所认识的。开创性的研究始于布劳和邓肯(Blau&Ducan)的“地位获得”模型,他们发现在工业化社会中,出身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对被调查者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与间接作用不如自致因素(被调查者初职和教育程度)。[22]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形式,所受教育的强度、能力及经验与个人的生产效能间具有较强相关性,进而导致不同的个人收入。[23]而不同专业之间的学习内容、强度等的差异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市场需求率都不同,理工科相比于文科就业率与市场需求率都较高。[24][25]作为毕业不久的青年“北漂”,自然会因为专业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本文的调查数据也显示,非文科专业的毕业生在收入与工作满意度上都高于文科学生(收入平均值上,非文科专业比文科专业高出近110元;满意度上,非文科背景毕业生表示满意工作的人数比文科高出4.8%)。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个体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过往研究也证明这种差异会影响集体抗争意愿。[26][27][28]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分析价值变迁与新社会运动关联性时,提出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认为人类需求存在着一个层级,较高阶的需求只有在较低阶的需求被满足时才会出现。与物质主义者看重的是经济和物质安全维度的东西不同,后物质主义者的目标是自由、自我表现和平等。[29]而英格尔哈特等人对7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所做的调查进行分析后,证实了后物质导向价值观的兴起。从英氏的理论中可以发现,后物质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持有者是根据其所认同的基本原则而发出行为的。[30]这也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满足了经济物质需求之后,他们更可能追求自己在其它方面的权利,诸如公民权、言论自由、享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等。
正是由于专业对个人在这三方面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个体的体制外集体抗争意愿。所以本文认为专业差异影响着大学生北漂群体对集体抗争行为采取不同的态度,而这种影响可能通过三种机制产生作用,即政治社会化、政治预警和社会经济地位(见图1)。
当然这三个机制假设并没有穷尽所有专业教育对个人集体抗争意愿的影响方式,因此即便以上三个假设机制没有一个起作用,专业的影响仍旧不能被抹杀,因为它可能通过其他本文没有涉及的机制产生作用。

图1 专业差异与集体抗争意愿之间的路径关系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由于调查对象的流动性非常大,很难得到完整的抽样框,因此本次调查选用了滚雪球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18-30岁没有北京户口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成年人,调查方式为入户面访,回收问卷340份。经过数据清理,最后样本量为336。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集体抗争意愿。在调查中我们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您是否赞成某些个人或组织利用下列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身利益的意见?”这些方式包括公开集会、游行示威、罢工、上访。被调查者可以选择的意愿有:非常赞成、比较赞成、比较不赞成、非常不赞成以及难以选择。
在被询问的四种方式中,只有“上访”被宪法明文规定为公民合法的政治权利,其他几项或者是公民只具有有限权利(公开集会、游行示威要经有关部门批准才是合法的),或者是宪法上根本没有涉及。因此我们把公开集会、游行示威及罢工定义为性质相同的体制外集体抗争,同时将“非常赞成”、“比较赞成”赋值为1,其他为0,然后将三个变量相加,出现三种结果:0、1、2、3。我们将1、2、3赋值为1,表示赞成体制外集体抗争行为,否则为0。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分为以下三组:
第一组,政治社会化假设中的有关变量,主要是教育变量,此次研究将“教育”操作化为两分专业和三分专业。两分专业分为文科(包括财政金融、经济类、管理科学、服务专业、法律、人口、社会、政治学、马列社科、文史哲、外语、教育、心理、图书情报等)和非文科(包括理科、生物工程、计算机应用、软件、其他工科、医学、药学、农林牧渔及其他)。从表1中,可以看到专业差异的影响。
政治社会化机制假设的是不同专业学生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机会不同而导致了集体抗争意愿的不同。为了检验该假设,本文根据不同专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接触机会由少到多分为:理工医农类(包括理科、生物工程、计算机应用、软件、其他工科、医学、药学、农林牧渔及其他)、经济管理类(包括财政金融、经济类、管理科学、服务专业)和社科人文类(包括法律、人口、社会、政治学、马列社科、文史哲、外语、教育、心理、图书情报等),形成三分专业变量,本文将该变量视为定序变量。
第二组,政治预警机制假设中的有关变量,涉及两个方面,即政治面貌和“担心”。党员被要求有较高的政治敏感度,需要对党的政策、法律法规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们显然比非党员更了解体制外集体抗争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本文选用该变量作为测量政治危机感的指标之一。另外,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您是否担心失去这份工作(简称“担心”)的表达是否与自己的情况符合”,“符合”为1,“不符合”为0。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调查者对危机的敏感度。
第三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机制假设的变量,主要涉及的变量包括收入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问卷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分为五个层次: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本文将上层与中上层合并,中下层与下层合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三个等级。收入包括被调查者上月的工资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补贴等。所有变量的描述和说明见表3。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及婚姻状况。
在本文的统计分析中,所有定序变量都被视为连续变量来处理。所有变量的缺失值都不纳入计算。
四、结果与讨论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采用的是Logistic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表4中模型1是只进入人口学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准上引入政治社会化机制的操作变量——三分专业(理工农医类、经济管理类和人文社科类),由于二分专业与三分专业两个变量只是划分的维度不同,其实质是同一变量,两者的相关性很高,为了避免“同义反复”,本文在以下的分析中将用三分专业代替二分,既作为验证政治预警机制和社会经济地位机制的前置控制变量亦作为政治社会化机制的操作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测量政治预警机制的变量,模型4则是在模型2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5是全模型。

表3 本文所采用变量的描述和说明

表4 集体抗争意愿的logistic分析
我们首先将人口学变量与两分的专业变量一起引入模型中,发现文科赞成体制外集体抗争的可能性明显低于作为参照组的非文科。即相对于非文科,文科使得发生比降低50.83%(=e-0.71-1),且在统计上显著(表略去)。这也与本文在开篇发现的问题作用结果一致。下面将通过对模型的分析来检验各假设。
(一)政治社会化假设
如前所述,本文采用将专业依据接触主流意识形态机会的差异,按由少到多分为:理工类、经济管理类和社科人文类,来进行操作化。表4的模型2显示,专业的影响依然显著,并且方向也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与主流意识形态接触机会越多的专业,可以将支持体制外集体抗争的发生比降低34.14%(=e-0.42-1)。这表明更多的接触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能起到抑制集体抗争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作用可能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也可能是政治预警带来的。所以此处还无法证实假设1成立,只有在假设2未被证实的情况下才能说明接触主流意识形态多会促使人们接受并内化它。
(二)政治预警假设
Logistic回归模型提供的是偏回归系数,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考察回归方程中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而本文的理论假设认为,专业通过政治社会化、政治预警和社会经济地位机制对集体抗争意愿起作用,其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变量产生。那么,要证实假设2、3,统计结果应该是:在模型中控制了测量机制的操作化变量(中介变量)后,专业的作用减小或消失(统计上不显著),而中介变量的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只有这样才能验证理论假设2和3是否被实证数据所支持。
基于以上的思路,我们来分析模型中的系数。可以发现,引入代表政治预警机制的党员和“担心”这两个变量后,在表4的模型3中专业的作用相比模型2的确减小了(从-0.42降到-0.39),且显著性也减弱了,但是这两个变量本身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专业与引入的变量有关,但这两个变量对集体抗争不产生影响。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两者间的确不存在关系,也可能这只是一种假象,即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被其他某些变量所抑制或掩盖了,但这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所关注的是,这样的结果无法证实假设2。也正因为假设2无法证实,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假设1被证实。
(三)社会经济地位假设
同样地,可以看到在表4的模型4中专业的作用没有减小,而且引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变量的作用也不显著,那么假设3亦未得到证实。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专业变量以何种方式进入模型,除了其在作用系数上的大小不同外,趋势及作用方向都没有变化。在表4的全模型中(模型5),在控制所有引入变量的情况下,专业的作用依然显著。毫无疑问,这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的成立,表明在本文所讨论的三个作用机制中政治社会化机制对体制外集体抗争意愿具有独立的影响作用。而模型5中,党员变量系数与模型3中的相比增大并显著了,这是在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之后产生的,所以可能是由于党员变量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之间有交互影响,本文在此也不展开讨论。
五、结论
本文讨论和检验了专业差异对大学生“北漂”群体集体抗争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
第一,专业不同确实使得这个群体集体抗争意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相对于非文科,文科使得体制外集体抗争意愿发生比降低50.83%。这就是说,在面对引发集体抗争的事件或者境遇的时候,具有文科教育背景会抑制其参与或加入抗争之中。当然意愿并不等同于实际行为,本文只是在其抗争意愿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
第二,政治社会化机制的作用在文中的统计分析中作用显著。与主流意识形态接触机会越多的专业,可以使得体制外集体抗争发生比降低34.14%。
第三,政治预警机制的作用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文中测量政治预警作用的两个变量分别是政治面貌和是否担心失去工作。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在假设1中,政治社会化机制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政治面貌尤其是具有党员身份是政治社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理应与假设1相一致。造成这种不显著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经历市场化后,党员身份的政治资本贬值,[31]所以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的认同有所下降,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已不足以说明其政治社会化的差异性。当然也可能由于本文的抽样方法及样本数量限制,造成统计上的不显著。
第四,社会经济地位机制的作用也是不显著的。虽然以往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是导致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但研究结果却也有矛盾之处:如在城镇居民的环境抗争中它起到促进作用,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可能参与集体抗争;[32]但在探讨单位中发生不公平事件时城镇居民的抗争态度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却减少参与集体抗争的发生比。[33]足可见,对于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抗争事件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因而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可能源于研究对象即大学生“北漂”群体的特殊性而导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仅仅是对教育与集体抗争关系之间的多种影响机制的部分性假设和检验,即专业教育的作用机制,这些机制当然并不仅限于本文所讨论的三种。而由于研究访问的样本量及概念操作化的限制,存在一些缺憾。因此希望通过本文引起学者们对此问题的关注,藉以抛砖引玉。
注释:
①本文使用大学生“北漂”这一概念,是为了分析和表述起见,时下,有一流行概念——“蚁族”,(参见: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与本文所谓的大学生“北漂”,有很多的重合与相似之处。“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简称,该群体高智商、经济地位弱小、像蚂蚁般聚居;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806199.htm?fr=ala0-1-1)当然本文对大学生“北漂”群体的界定首先是从其户籍状态出发,而“蚁族”的概念更多的关注于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两个概念亦有共同之处,如都受过高等教育、年龄比较集中等。对于这些概念的区同,本文并不准备进行划分和比较。
本文在分析中所指“二分专业”,是将受访者所学专业分为文科和非文科;而“三分专业”是为了考察受访者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而进行的操作变量,根据受访者所学专业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远近程度而区分为理工医农、经济管理、人文社科。
[1]陈静.想象中的北京:都市人类学电影中的“北漂”群体[J].电影文学,2008,(6).
[2]王远征.女北漂归属感在哪.新京报网,2009
-03-02;蒋理.危机下,新“北漂”先过心理关[EB/OL].新京报网,2009-02-04.
[3]王胜国,张焕琴.试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特征[J].中国青年研究,1999,(3).
[4]R·G·布朗加特,M·布朗加特.从易比士到雅皮士——20年来美国大学新生的心态变化[J].中国青年研究,1992,(2).
[5]王文.试析70年代初台湾的青年运动[J].青年研究,1992,(9).
[6]马振超.我国转型期可能面临的社会危机问题分析——由巴黎骚乱引发的思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7]张俊.浅析巴黎骚乱的成因[J].法国研究,2007,(4).
[8][14][26][32]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9][27][33]冯仕政.“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J].学海,2007,(5).
[10][15]刘爱玉,王培杰.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报,2005,(4).
[11][16]Olsen,Marvin E.Perceived Legitimacy of Social Protest Actions[J].Social Problems.1968,Vol.15,No.3.
[12][17]Hall,Robert L.et al.Effectsof Education on Attitude to Protest[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6.Vol.51,No.4.
[13][18]Mark,Rodeghier et al.How Education Affects Attitude of Protest:A Further Test[J].The Sociology Quarterly.1991,Vol.32,No.2.
[19]孙爱军.政治社会化: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点[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6).
[20]杨晓娟.关于“两课”课程设置的再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3).
[21]吴正荆等.信息社会学理论流派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7,(3).
[22]Blau,P.&Ducan,O.D.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New Y ork:Wiley,1967.
[23]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社会学研究,2006,(6).
[24]陶小江.浅析当代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J].现代教育科学,2006,(4).
[25]李婵娟.不可忽视的结构性矛盾:专业与就业[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6,(2).
[28]Inglehart,Ronald.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1,Vol.65,No(4).
[29]Inglehart,Ronald&Abramson,Paul R.Measuring Postmaterialism[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9,Vol.93,No(3).
[30]Porta&Dinai.社会运动概论[M].苗延威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2.71.
[31]Nee,Victor.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Vol.54,No(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