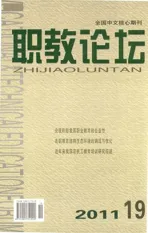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实业教育思想
2011-02-21彭干梓夏金星
□彭干梓 夏金星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实业教育思想
□彭干梓 夏金星
《盛世危言》是甲午战争后最受人欢迎的读物,为维新变法作了很重要的思想准备,还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近现代政治重要人物。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是19世纪70、80年代改良派思想代表,他全面表达了当时民间工商业实际的利益和要求,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无商”就会导致“格致之学不宏”,即科技、教育不能发达的观点,也是第一个系统介绍欧美和日本实业教育的人。郑观应在招商局成立驾驶学堂,在总办汉阳铁厂时,创立机器书院,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是继福州船政学堂后,实行半工半读的实业教育家。
郑观应;盛世危言;半工半读;实业教育
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山人、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中山人。士子——买办——企业家,是毕生关注祖国命运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是晚清与西方文明接触最早的中国人之一,对近代工商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英商宝顺、太古洋行办事30多年,以捐资得道员衔。后参与洋务派兴办的企业,协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办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厂、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在上述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干,晚年回上海致力于教育工作。
早期郑观应曾受王韬(1828—1897)的影响,著有政论短文,“未敢出以示人”,1879年春托友人请王韬批评,为王所推崇,为之付梓,名《易言》(1871)。1894-1895年经增补为《盛世危言》,于甲午战争前夕开始初刻,1895年、1900年两次修订,共收正文111篇,另有附录和序跋72篇,煌煌30万言,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式出版,版本多达20种。
《盛世危言》的刊行问世,正值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潮日益高涨之时,它所宣传的“富强救国”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加之郑观应本人在官私商界的杰出才干和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视和推广。礼部尚书孙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向光绪推荐此书,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了5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十多万册之多。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
郑观应以买办商人而成为著名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要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由于他的经历与主张,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作者从一介草民到工商实业巨子的经历与切身体会,由表及里,深刻剖析了处于19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大清帝国在“太平盛世”表象掩盖下的封闭落后以及种种内在社会矛盾与危机,提出“商战为主,兵战为末”、“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的治国经略,把改良政治与兴办教育当作国家富强的两件大事,强调“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治国之本。
郑观应在招商局任职期间,买来不合商用的船改为教练船,先招学生学习驾驶,继则正式成立驾驶学堂。在总办汉阳铁厂时,又创立机器书院,招收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是继福州船政学堂后,我国较早提出设立结合机器操作实践的半工半读的教育家。1917年以后,他还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以及上海商务公学的名誉董事等职,主持或参与学校的实际工作,以广兴学校、培养人才、开通民智、研究学术。
《盛世危言》为维新变法作了很重要的思想准备,是甲午战争后最受人欢迎的读物,引起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震动,还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近现代政治重要人物。本文简要介绍《盛世危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有关实业教育的论述,分析郑观应在近代实业教育思想史中的地位。
一、改革教育是改良派变革思想的核心部分
19世纪70、80年代是革命大风暴过后的萧杀又相对稳定的时代,农民革命的失败使晚清社会走上了艰苦曲折的行程,出现的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要求政府发展民族资本的经济思想,然后反映在文化教育出现的变革上,这种思想是直接从洋务思想中分化出来的。在最初阶段,无论是思想的本身,或者其代表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洋务主义,但它已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物在发展中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性格。[1]
一种新的思潮在这个古老国度的思想界中出现,往往引起震荡,并因而对正统封建顽固派产生刺激,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使近代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他们不满足于洋务运动,因为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富强,逐渐脱离洋务思想原来的方向和轨道,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提出了更为切实合理的主张和建议,客观上开始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新兴经济力量的要求。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王韬、马建忠(1844—1900)、薛福成(1838—1894)、陈炽(1855—1900)、郑观应等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们都曾是“船坚炮利”的主张者,强调讲求新式武器以至工艺技术,完全是洋务运动的主张。到了70年代,他们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开始指责洋务运动“徒袭皮毛”,提出“开矿务以采煤矿五金”、“制机器以兴制造”、“许民间用轮船以达内河”、“立公司贸易于外洋”等主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开始萌芽。
改良主义思想家当中,郑观应比较早而且系统地论述了经济近代化的内容、途径、方法、目的和意义,明确指出其核心就是工商立国、富强救国,并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思想。他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系统地阐述了“商战”之道,认为商“握四民之纲领”,第一次提出“无商”就会导致“格致之学不宏”,即科技、教育不能发达的观点。在他看来,实行商战,才能“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他把所有这些都与发展现代教育以培养人才联系起来了。
改革教育一直是改良派变法思想的重要部分,知识更新是社会进步和更新的前提。改良派要求改革科举八股取士制度,设立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郑观应反复指出,富强的关键是废科举,办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他说:“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发愤自强,必自留意人才始。”“一言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他重提洋务派的过渡性步骤:“另立一科,专考西学”,并建议在各省建设西学书院,“至于肄业的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还把兴学校、育人才视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他说:“学校者,人才之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其又学其所学也。”[2]这是既看到本原又有切实步骤的建议,可惜的是几经艰难,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得以实现。
郑观应超越洋务思想之处,还在于提出了培养新式农工商服务人才,以实现其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思想。他关注人才培养的内容和制度设计,这不仅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关系,也与他个人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他认识到,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并提出了整套的思想与方法,对晚清实业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引进西方工业和农业教育制度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改良派较为系统地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教育制度,郑观应在《易言·论洋学》和《盛世危言·学校上》及附录《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划》、《英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等著作中,对德、日等国的工业教育制度作了详细描述。从那些不完整甚至不够准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郑观应已认识到工业教育是包括了商业的一种专门教育,有高等、中等和初等的层次之分,还分日间、夜间等不同形式。实业教育的确立使人人从小学实学到实功,以实功呈实效,从没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情况。当时,日本也因为学习西方,重视实业教育,培养实业人才,逐渐超过中国而达到国势振兴,国强家富的程度。为借鉴日本和西方的教育制度,郑观应提出了实业教育制度和体系的初步构思,形成了一套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基本框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设立专管教育的行政部门
郑观应主张仿“日本设文部大臣”,其重要的职能就是统管全国实业学校,建立以州县、府省会及京师三级制为主干,分文武两系的教育体系。在文学的六科中,格致(含声学、光学、电学、化学)、艺学(含天文、地理、测算、制造)和杂学(含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三目传授自然科学、技术及实业知识。
(二)以工艺学堂为“急务”
“学战”很大程度上指工业教育,把兴办工业教育作为中国致富的急务,一是为育才。他说:“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西洋各国“士之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才能“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即商战。他还说: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我国极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3]二是为富民。中国国贫民穷,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甚多,“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作为解决贫民生计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其不致流为盗贼。他进一步分析:“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本不至流为盗贼。闻泰西工艺院急于文学院,以工艺一事,非但有益于商务,且日益人心。院中课习制造、机器、织布、造线、缝纫、攻玉以及考察药性与化学等类,教分五等。中国生齿日繁,生计日绌,所以工艺学堂亦今世之急务也”。[4]
(三)多层次办学
《盛世危言·学校上》主张设童艺院、机器学堂或工艺学堂、工艺院等多层次办学,郑观应是晚清实地考察欧洲各国工业教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把亲眼目睹的情况实录如下:
童艺院:类似短期培训学校,始创于瑞典,被丹麦、德国等仿行,学制限六星期,教授雕刻、订书等易学之技艺,每年由政府两次集中无业无告之贫民子弟,教以一工一艺,经考核后推荐到工厂以谋衣食。
机器学堂或工艺学堂:培养制造和使用机器的工匠,对象是幼童,分专业实行因材施教,学制分两级,初级三年,谓之“粗识”;高级六年,谓之“学成”,毕业后按声、气、电、光、铁路、熔铸、雕凿等专业,由工部衙门使用。
工艺院:他建议广开艺学,“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选本国聪颖子弟入学学习,延西洋名师原原本本悉心教授,待以有年,则必出现器物日备,制造日精的局面。那时,“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
1894年,郑应观回国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提出14条整顿意见,其中一条是设驾驶学堂,培养驾驶人才,以改变依赖洋人驾驶的被动局面。他用英国商部考核学生驾驶技术的30条标准作为学堂课程,是近代中国驾驶学堂最早制定的课程设置计划。[5]
1896年,郑观应在总办汉阳铁厂时,连续几次致函盛宣怀(1844—1916,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请求设立钢铁冶炼学堂,并拟定了学堂章程,规定招收学生40名,一半学熔炼,一半学机器绘图;上午读书,下午入工厂学习操作实践。师资以厂中“工目”充当,培养中国自己的工师匠才。[6]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空洞不实弊端的同时,强调专门人才的实用性,是后来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实业教育制度的先导,对近代实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三、“恃商为国本”,“商战不如学战”
改良派把兴办新式学校和培养科技工艺型实用人才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为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作了准备。商人出身的郑观应是70、80年代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思想代表,他在“恃商为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商战不如学战”,使之成为早期改良派中实业教育思想的代表。
(一)“恃商为国本”取代“农本”思想
郑观应质疑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他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7]他全面表达了当时民间工商业各种具体实际的利益和要求,强调必须振兴商业和民族工业:
商务之纲目,首在振兴丝、茶两业,裁减厘税,多设缫丝局,以争印、日之权。……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购机器织绒毡呢纱、羽毛洋衫裤、洋袜、洋伞等物,炼湖沙造玻璃器皿,炼精铜仿制钟表……上海造纸,关东卷烟,南洋广蔗糖之植,中州开葡萄之园……制山东野蚕之丝茧,收江北土棉之纺纱……遍开五金煤矿铜铁之来源,可一战而祛。[8]
他还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系统地阐述了“商战”之道,认为商“握四民之纲领”,“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这可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无商”就会导致“格致之学不宏”,即科技、教育不能发达的观点。
“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9]
商人,近代概念即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都包容在内。所谓“商务”并非仅仅指商业流通,而是包括了农、工、商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国家采取奖励扶助农工商业的经济政策,这种新鲜思想有日益向前发展的民族资本作为客观的物质基础,尽管微弱,却已不是一闪即灭的偶然现象,而是日益发展、丰富而逐渐汇成一股清流,代表了一种先进思潮,集中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等人的著作中。
(二)“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
学战很大程度上指工业教育,郑观应说:“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西洋各国“士之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10]因此,同时也要学习“泰西士、农、工、商之学”,才能“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他所说的“裕无形之战”,既指商战也指学战,最根本的是人才之战。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实业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他们顺应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趋势,适时地提出培养资本主义农工商矿铁路商船等各业需要的专门人才的任务,在批判封建教育空洞不实弊端的同时,特别强调专门人才的实用性,把实用作为对专门人才及其教育评定的标准。他们对近代实业教育制度构思的方案,成为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实业教育制度的思想先导。
而且,他较早地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和人才培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主张考试分立两科,考试格致、化学、电学和天文、地理、医学、种植新法等门,录取对富强之道实际有用的人才。在当时人们仍然崇尚虚文、皓首穷经、拒绝西学的环境里,郑观应把兴办新式学校和培养科技工艺型的实用人才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视学校和实用型人才为富强的根本,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其思想主张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人的近代化和文化近代化这两个敏感而又极其关键的问题。
19世纪以农工商矿为概念的“实业”一词,至少在甲午战前已经产生。在实业学堂、实业学校的名称出现前,改良派把培养农工商矿应用人才的学校叫“实学”,或艺学,这实际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思想的萌发。如果说王韬、马建忠、陈炽的实业教育思想还只是零散的、狭窄的,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仍然处于近代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一阶段,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教育实践,则不愧为集此前之大成者。尽管真正开始使用“实业学校”“实业教育”两词,还是跨入20世纪的大门之后,[11]但至少为洋务派晚期的领军人物张之洞在世纪末发展实业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一种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制度的建立已经露出了曙光。
史家评论郑观应“卅余年来,不惮心力交瘁,不顾忌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12]他与晚清一批又一批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知识分子,尽管不断地发出“盛世危言”,有时还参与勇敢的抗争,但都无力防止中国滑向苦难的深渊。腐朽的大清帝国听不进“盛世危言”,几年后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十多年后,这个专制政府便寿终正寝了。郑观应所期许的盛世并未实现,警世之言也未能获得当权者的重视。壮志未酬,留下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极其缓慢的一个侧影。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8.
[2][7][12]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61.592、237.
[3][4]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学校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95-296.
[5]招商局盛办督办书.附录//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卷1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9
[6]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43.
[8][9][10]盛世危言·商战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46、267、247.
[11]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38.
G719.29
A
1001-7518(2011)19-0093-04
彭干梓(1933-)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思想史;夏金星(1966-),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研究”(DJA080186)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夏金星。
责任编辑 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