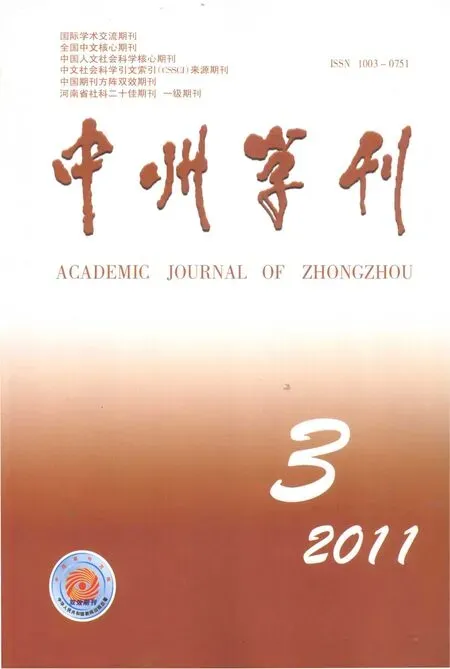试论风险传播悖论与传媒角色担当*
2011-02-21杜建华
杜建华
试论风险传播悖论与传媒角色担当*
杜建华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风险传播;悖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媒角色
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风险斗争的历史。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险发生频次与强度大大加速。仅以我国观之,2008年以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陇南事件、甲型H1N1流感、校园安全等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存在成为社会常态和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表象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①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的风险特点,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吉登斯、拉什等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当传统的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时,随着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生活开始面临两种根本性转变:“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②,人类随之迈入风险社会。与此相应,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农业社会的自然危险→工业社会的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风险社会中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公共风险。因此,现代风险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以科学技术为直接源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而产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未意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影响多半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很可能是全球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关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解释。该组织报告《面向21世纪的新风险— —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报道着眼点由信息公布转向娱乐,使得相关问题以大众化而非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信息闭塞,加剧了危机的社会后果。”拉什也从技术手段特别是传播技术极度扩展来揭示风险形成。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技术资本主义希望能够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化解一切风险,消除一切不利事件”,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③。罗森塔尔、贝克等人也都谈到大众传媒在风险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罗森塔尔甚至将媒体化作为公共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影响与作用。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宏观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有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也有贝克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问题呈现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从微观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据粗略统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造成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二十万人,伤残超过二百万人,经济损失超过六千亿人民币”⑤,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难以估量。童星和张海波把我国高风险社会表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二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三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四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概言之,我国的风险社会特征既具有与其他国家风险社会的相同特点,又表现出自身特殊性。
二、风险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悖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它强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紧急性和非常规性。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发生时的突然性、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公共性、后果的严重危害性、突发事件的多样性等特征。无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社会事件,在公共边界日益模糊的状况下,都会滑向突发公共事件,危及公共安全。为行文方便,笔者对这些事件不作详细区分,概以突发公共事件称之。
在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传播就深深打上风险的烙印,并表现出传播中的内在矛盾和悖论。这种矛盾和悖论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微观层面内在的现实/表现这种实在论和认识论的二元分立,即媒介呈现(认识)与独立于呈现(认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传播主体建构的传媒镜像与现实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宏观层面的、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环境与风险社会特性并存的社会的高度信息化、网络化。前者内置于媒体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后者作为媒体外部环境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介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从本质讲也就是人的媒介化、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突发事件传播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大众媒介。但不幸的是,风险的媒介化却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传播悖论的形成,其一,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定义机制;其二,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内化机制。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构筑的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联系真实世界的桥梁,即麦克卢汉所谓的“传媒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对于受众来说基本上就是他能够认识的世界的全部”,而李普曼则以“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或“拟态环境”、“传媒镜像”称之。由此,传播媒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则“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进行加工并深刻形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⑥。这种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经传播媒介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传媒镜像”具有风险预警和揭示功能,从而使得风险公开可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大众往往把这个间接、虚化的“拟态环境”当做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从这个虚构中介出发安排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媒体的预测瞭望功能就被极度放大,当媒体的聚光灯将某一风险拉入公众视线时,媒体往往成为卡斯帕森所比喻的“风险的放大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恐慌的形成。由此,媒体往往难以避免地陷入传播的矛盾之中——预警的天职和促进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观意图与可能成为风险的渊薮的客观传播效果之间的矛盾。
从宏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按照贝克的观念,“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⑦,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简而言之,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⑧。而在网络社会中,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表现为一种认知的信息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结构”⑨。这就注定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具有自反性、牵连性和扩散性,导致“飞去来器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特别是当媒体将支离破碎的风险知识密集塞给公众时,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风险状况,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而且使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反而会毁灭其所置身的当下社会。
媒介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下社会又叠加上风险社会的特征,就构成风险传播的一个混乱而矛盾的悖论场景:信息借助网络和手机的巨大传播张力,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广,不负责任感大增,也使得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传媒能制造出强大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⑩在这个过程中,与危险有关的事件总是和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产生互动,从而强化或者弱化个人和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着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这些被形塑的人们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这些后果大大超出了对人和社会的直接损害范围,导致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三、风险传播悖论下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媒体角色
新闻传播事业永远是一项“带着镣铐跳舞的事业”,新闻传播中的矛盾、悖论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在风险社会下,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内外矛盾更为尖锐与激烈,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悖论,即传媒有关风险报道的碎片式呈现与受众强烈的完整的风险知识需求之间的悖论;二是报道观念的悖论,即传媒寻求确定性的努力与不确定的现代风险的悖论;三是风险媒介化的悖论,即媒体不但再现风险而且定义并内化风险的悖论;四是效果的悖论,即风险预警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悖论⑪;五是新闻报道的快与准之间的悖论;六是传播生态的扩散性、网络化、信息化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安全性、约束性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样的传播矛盾和悖论下,新闻媒体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才能在不断变动的风险和不断形成的紧张张力中出色完成自身使命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
人类的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的深入而呈现与日俱减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他认为:“风险社会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在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⑫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依次提升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需求又可以分为“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而安全需求属于个人刚性的“生存性需求”,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其目的是维持人类最基础的生物性存在,因此,它具有自然性、生存性、底线性几个明显特征。所以,安全是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生存发展之基,是追求和实现其他价值的首要价值基础。因此,在现时背景下,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巨增,而且安全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首要价值。当下,安全自然成为生活其间的人们普遍关心和追求的首要利益与价值。
因此,大众媒体必须考虑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如何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心理情绪上的恐慌焦虑;消除行动上的骚动、混乱、动乱乃至暴乱,进而建立起大众基于媒体报道知识的心理感知安全,促进社会安全,这是风险社会下突发事件报道最急迫、最现实的要求。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安全作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及时、公开等原则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则加以确立,既在新闻原则上加以确认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
2.坚持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原则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传播或新闻报道既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中信息安全的重要维护方式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知情需要或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通道之一;新闻工作者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在国家→媒体→大众三者之间充当桥梁并维持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这需要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要实现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并以此为出发点安排报道。
3.坚持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原则
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这是媒体的使命所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的公开性是有规范的公开性,有限度的公开性,更是相对的公开。公开有度,才能公开有效。“经验告诉我们,讲透明要有个‘度’,不能超度,讲公开也不能凡事都完全公开,要注意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⑬例如,从2010年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到5月12日发生在陕西南郑的校园血案,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连续发生了6起校园血案。惊人相似的血案频发,是否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带来“示范效应”呢?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连续发生的杀童惨案与媒体传播后导致犯罪嫌疑人效仿有关。因此,即使能自由报道,也必须要足够的有节制,才能符合社会的最高利益。”⑭
因此,需要对媒体报道的公开性做出适度限制,并且必须是合理的制度性限制规范。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规范,必须是良性的规范,即必须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发展和人民有利的规范。一切恶性的规范都将对新闻传播公开性形成恶性的限制,也必将损害社会和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虽然对新闻传播的公开性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对限制本身应当有所限制”⑮,即把限制本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在制度上追究不合理限制的各种责任,以保障新闻传播公开性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之间的良性平衡与并重。
4.坚持及时性与准确性并重原则
“及时性”与“准确性”的矛盾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尖锐的矛盾。罗森塔尔从突发事件角度揭示了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才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之间充满张力与矛盾,迫切需要作出决策。在此状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常常是在极大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因而就产生天然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媒体努力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现场,获取全面、真实、客观的事件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报道给社会公众,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矛盾又统一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又快而准”,既要有及时性,又要有准确性,二者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既构成“传媒镜像”,又在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这就使得大众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时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②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③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④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⑤吴庆才:《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死亡20万人,经济损失逾6 千亿》,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 tics/2006-07/15/content_4837443.htm.⑥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⑦⑫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4、56—57页。⑧王小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⑨张锋:《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12期。⑩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⑪马峰:《现代风险报道中的传播悖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⑬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54 页。⑭曾革楠:《专家称警惕媒体报道带来校园血案示范效应》,《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9日。⑮杨宇冠:《人权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附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G206.2
A
1003—0751(2011)03—0255—04
2011—03—25
2010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风险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传播因应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杜建华,男,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讲师(兰州 730080)。
责任编辑:采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