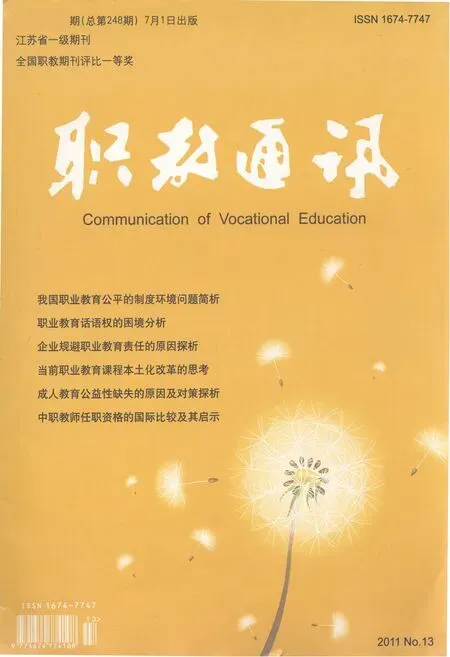论学历无用论
2011-02-19臧志军
臧志军
论学历无用论
臧志军
据说,参加高考的人数正逐年减少,一些专家认为此现象有可能缘自部分学生和家长中产生的新“读书无用论”。如果只有到学校注册上学才能叫读书的话,专家们的评论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读书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那些选择不读书的青年并不真的相信知识无用或读书无用,这是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将会无数次地拜师学艺或参加各种培训以获得完成某项工作的能力,他们只是认为学历(或用以证明学习经历的那张让许多人既爱且恨的纸片)无用,因为他们看到专科或本科学历并不能帮助那些手握这些学历的毕业生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到社会中接受那些非正规的教育,增长自己的社会才干而不是到学校学习那些迂腐的所谓知识。
不要以为相信学历无用的都是些没有见过世面的粗鄙之人。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曾写过一本名为《学历无用论》的超级畅销书,书中对日本社会的唯学历主义深恶痛绝,提出要“烧掉简历”,因为如果公司在招聘或晋升的时候把学历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实力评价”了。无独有偶,被季羡林称作“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的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以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表明没有在名校学习的经历也许是人生的一大资本。至于说从大学退学的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史蒂夫·乔布斯等人更是学历无用论的强有力注脚。
世人都把这些人当作成功的楷模,他们的成功显然反证学历这种证明方式的不成功。盛田昭夫鼓吹“在一切公开记录上抹掉学历”,是因为他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混沌中产生出新的评价习惯”。很明显,在他看来,学历与它所表征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所以要用一种全新的评价方式取代之。那么这种落差是如何产生的?
哈斯金斯这样描述十二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学生“大学”排斥在外的教师组成一个行会,并且规定了入会的某些资格条件——以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学生为了获得教职而参加这种考试以获得教师许可证,这个证书因此成为最早形式的学位。文学硕士是有资格教授“自由七艺”的学者,法学博士则是一位被证明合格的法学教师。原来,所谓的学历(在许多国家学历系统与学位系统是同一的)只是当年的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哈斯金斯特别强调,在当年的博洛尼亚,并非所有学生都会从事教师职业,但由于有无能力教授一门学科是对自己是否精通这门学科的一种有效测试,所以学生还是纷纷前来寻求教师许可证,把它作为自己已达到这种能力的一个证明,而不管自己将来从事什么职业。
我们可能会认为用一份教师资格证书到其他行业去求职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但在当时,知识阶层所能从事的职业并不多,一份教师资格证书所证明的能力也基本适用于其他行业。将近一千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学历这种证明方式的封闭性并未改观多少。从根本上讲,学历只是教育用以证明自身自洽性的一种把戏:按我的标准把学生挑选进我的系统,学习我所规定的知识,完成我所规定的考试,发给我所承认的证书,从而证明这些学生按我的标准是合格的。在这个循环中,知识与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机构所定义的那些知识与能力。同一千年前一样,教育机构所定义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是教师从他们的老师那里承袭而来的知识与能力,但不同的是,教育以外的工作世界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把一纸学历作为毕业生进入任何行业的敲门砖真正变得荒唐了,学历在当今社会变得无用了。
在这个问题上,职业教育倒远比高等教育清醒。许多职业教育工作者发现一些企业家也是学历无用论的拥趸,他们不相信高一层次的学历证书有更强的证明力,所以许多企业安排高职毕业生与中职毕业生或本科毕业生与高职毕业生在同一岗位上竞争。于是,职业教育开始采用学历以外的另一套证明系统——职业资格证书,从而产生了“双证书”毕业制。但问题是,中国的职业资格证书产生机制并不能保证这种证书真正反映工作世界的要求,资格证书并不比学历证书的证明力强多少。同时,中国的教育机制使得获得学历证书的难度小于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来自于企业界,许多企业家毫不隐讳地要求职业教育工作者不要教给学生职业技能,只要让他们学会基本知识和养成良好习惯即可,显然,他们在批评教育未能做好份内之事;一种来自职业教育内部,许多学校在法定的职业资格证书之外为学生寻找更为市场认可的能力证书,希望学生能掌握为工作世界认可的知识与能力。这真是一幅和谐的画面——企业家在考虑教育家该考虑的事,而教育家在考虑企业家该考虑的事。
也许企业家才是真正把握了问题实质的人,他们知道教育的本质正如涂尔干所说是关乎“观念、理智、情感”的,而如今的学历证书所能证明的除了那些知识与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在理智或情感方面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学历不仅不是无用的,而且比资格证书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