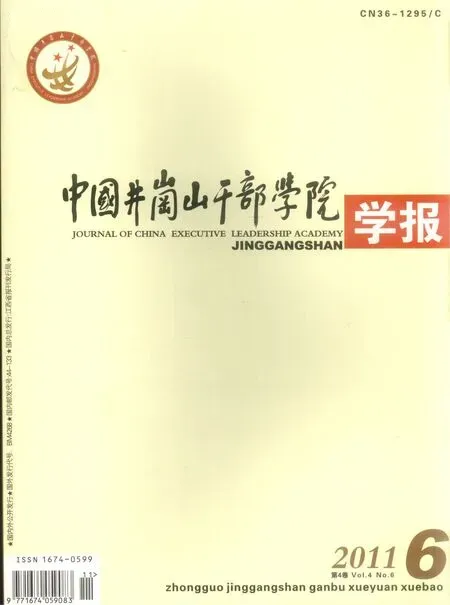“十二五”中国通胀治理的战略运筹
2011-02-18杨枝煌
□杨枝煌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十二五”中国通胀治理的战略运筹
□杨枝煌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导致“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通胀主要有四大因素:货币超发、预期催化、美元输入、成本推动。为科学治理此轮通胀,必须具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利用经济、政治、法律等综合手段,尤其要在金融、财税、行政方面做出战略规划,控制好通胀的同时控制好通胀预期,把通胀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以通胀对冲稀释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货膨胀;预期;综合治理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曾经一枝独秀。但2011“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通胀周期却由于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提前出现。为了科学治理此轮通胀,必须以整个“十二五”规划为视域,以整个经济周期为区间,梳理通胀表现,深挖通胀根源,进而为实现通胀的综合治理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建议和策略。
一、“十二五”开局之年通胀的具体表现
我们曾一度否认通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但是经过多次冲击,我们对通货膨胀才有了比较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就当前形势看,我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时期,而且颇有滞涨苗头,未来几年我国将较长时期处于抗通胀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物价上涨通道。虽然市场严格分裂,出现价格结构性起伏,但总体上通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房市由于宏观调控价格略有下降,但这是政府“有形的手”,沪深股市跌声一片,菜市价格高歌猛进。去年以来,物价上演了一场场诸如“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米高扬、猪超强、煤超疯、棉花掌、药你哭、油你涨”等疯狂飙升大戏。“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涨,CPI一路上蹿,已经不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也不是单纯的通胀预期,而是现实的、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还出现了结构性滞涨的迹象。据央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为9.7%(2010 年同期增速为 11.9%),CPI增长5.0%(去年同期为2.2%),涨幅比上个季度继续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各月涨幅分别为4.9%、4.9%和5.4%。4 月份 CPI同比上涨5.3%,略低于3月份的5.4%,但仍高于预期水平。5月的CPI为5.5%,6 月CPI破六并高达6.4%,7 月CPI再创新高6.5%。[1]2010年2月以来一直处于负利息时代(CPI指数为2.5%,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几次加息,都赶不上CPI上涨速度,而且我国货币政策时滞都在几个月甚至1年以上。物价上涨由食品向非食品、由消费品向服务类领域不断扩散。生产资料、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
二、“十二五”开局之年通胀的深刻根源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为了科学研判上述通胀的原因,我们经过充分调研发现,此次通胀是一种综合性通胀,而且有滑向滞涨的风险。通盘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语境,我们认为此轮通胀的根源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通胀的货币基础
佛里德曼认为,通胀从来都是货币现象。此次通胀也不例外,其最大原因亦在于货币大跃进。自从2001年我国GDP总量超过一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周期,而且一直潜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就是我国自从1997年经济成功软着陆以来,就进入了抑制型通胀时期。后来又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过大,2007年出现了流动性膨胀(有些专家已经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再加上2008年货币政策前后迥变(上半年为了防止通胀,年底为了抑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2009年和2010年的天量信贷,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引发了房地产业的超级泡沫,时刻威胁着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
其实,为了对冲金融市场化改革风险,我国自1999年以来就实行了几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此次通胀是十几年货币超发累积的后果。具体而言,第一种量化宽松是1999年用1.4万亿元人民币将四大银行坏账剥离到4大资产管理公司;第二种量化宽松是2003年起央行动用外汇储备790亿美元注资商业银行(2010年6月,央行报告说,中国银行系统的货币乘数是4.37,基础货币发行大约是15.4万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央行动用票据对各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支持;第三种量化宽松是印人民币承接超过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这三种货币宽松使得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由2000年的13.24万亿元飙升至 2010 年的 72.59 万亿元,增长3.48 倍。[3]
除了货币超发,另一大的原因是天量信贷。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以“4万亿”为主导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推出以来,关于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速的关注和疑惑就从未间断过。“天量”信贷、信贷“井喷”、“雷人”信贷、信贷“大跃进”等媒体的创新语汇见证了信贷投放量的飞速增长。2008年全年新增信贷4.9万亿元,2009年9.59万亿元,2010年为7.9235亿,加上4万亿元刺激计划,3年投放接近30万亿元。据央行数据,2008年12月底 M2为475166.60亿元,2009年12月底 M2高达 610224.52亿元,2010年 12月底为725851.79亿元(货币总量近两倍于2010年GDP,2010年M2余额占GDP的比例达到182%。),截至2011年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7.29万亿元,同比增长 14.7% 。[4]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我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通货膨胀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超速增加。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GDP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但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美国。可见,我国通胀主要是纸币泡沫,而不是资产泡沫和资源泡沫。
(二)中国通胀的预期催化
央行政策犹犹豫豫,走走停停,造成了通胀预期无法控制。央行之所以没有迅速控制通胀,是因为没有控制通胀预期。而且,通胀预期已经内化为通胀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大的诱因。
从近期加息和提高储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可以从反面看出我国货币超发的严重程度,但更激发了广大消费者的通胀预期。自2007年出现物价异常波动以来,短短不足4年央行连续30次调整存款储备金率。仅2011年上半年就调整6次,而且存款储备金率远远超过国际标准。央行甚至在《2011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强调,准备金工具运用力度和调整空间取决于多个可变的条件,并不存在绝对上限。
面对今年CPI异常升高的状况,政府管理通胀的愿望更加强烈,引发了新一轮加息预期。截至10月,央行已经在2011年度加息3次。2011年8月底,央行下发文件,9月5日始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以健全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调控功能。央行迟迟未能在CPI到达一定时点之前一步加息到位,且3.5%的基准利率远远低于6.4%的CPI;另外,各种紧缩手段都基本上用上了。动作迟缓和良策缺失,大大加剧了囤积、炒作等市场恐慌行为。
(三)中国通胀的美元因素
数据研究表明,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外汇资产之和(外汇占款+黄金占款+其他国外资产占款)为222399.56亿元,而基础货币和央票之和为226133.51亿元,两者非常接近,意味着外汇资产完全支配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多余的货币被央行发行央票所对冲[5]。
由于外汇储备成为人民币发行基础,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人民币不得不对冲发行。2001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43%左右,2006年初这一比例超过100%,此后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最高时达到129%,目前维持在1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购买外汇投放的,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回收因购买外汇投放的部分基础货币。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前后两次推出了高达1.5万亿美元左右的金融救援计划和经济调整计划,并且辅之以2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开动印钞机这个非常规武器。首轮定量宽松政策的执行期间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计划为6000亿美元,加上其他工具甚至可能有1.5万亿美元。今年6月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到期,至今虽然没有如预期地推出QE3,但是9月21日美联储宣布实施卖短债买长债的“扭转操作”来置换国债期限的决定,即计划到2012年6月,出售剩余期限为3年及以下的4000亿美元中短期国债,同时购买相同数量的剩余期限为6年至30年的中长期国债。同时,维持2008年12月以来的0.25%的史上最低联邦基金利率至2013年中期。这些新举措实际上相当于延长了其持有的4000亿美元国债的期限,即以在不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前提下降低长期利率,其实就是一项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2011年虽然没有推出QE3,但是其势难免。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特别是美国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时,QE3必将出台或者以其他形式露面。有关测算显示,[6]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所新增的美元大概有40%流入了中国,两次量化宽松流入我国的热钱大约有1.25万亿美元,给我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另外,2011年8月5日美国通过债务上限法案,将政府法定债务上限分三个阶段调高总共2.1万亿美元的额度。美国以“四次债务违约三次未对美元汇率及国债价格造成冲击”的“致命的自负”再次提高债务上限,充其量就是变相开动美元印钞机,让全世界为其分摊风险与成本。截至5月美国公共债务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持有9.8万亿,占比68.6%,美国社保及养老基金为最大的持有者。海外持有占比为31.5%,其中,我国大陆占8.1%。因此我国内地必将再次受到新一轮美元冲击。
美元超发,导致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国际市场上所有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都水涨船高。而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政策,因此以人民币标价的所有原料物资也都在猛涨。而且美国一超独大,充分利用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有利条件,战略性地拉高大宗商品价格,然后又突然打压大宗商品交易价格。近期黄金、石油等价格暴跌可能就是美国故意的战略操作。美元贬值率就相当于送给中国同量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3.2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约占70%。美元贬值让中国外汇储备损失严重。但是,中国外汇增速却远远高于其蒸发的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速。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5.8%。7月全国进出口3187.7亿美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出口 1751.3 亿美元,增长 20.4%;进口 1436.4 亿美元,增长 22.9%;顺差 3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0.3%。[7]外贸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其增速仍然远远高于GDP增速,且贸易增长量和趋势仍然呈现正增长状态,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外汇储备。央行9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外汇占款总额达252645.6亿元,其中8月份新增外汇占款达3769.4亿元,较7月份的2195.64亿元环比大幅增长71.7%。[8]业内一般以外汇占款与贸易顺差和实际使用外资间的差额作为衡量热钱入境规模的主要参数。根据海关总署和商务部日前公布的数据,8月份我国贸易顺差177.59亿美元,比7月份的314.84亿美元大幅下降;同期全国实际使用外资84.46亿美元,只有10%左右的小幅增长,将这两数额与外汇占款相减后可以发现,外汇占款大幅增加,热钱大量流入我国市场。因此,一直以来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正在或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转化为通胀压力。
(四)中国通胀的成本推动
成本上升是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当然,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是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
1.生产成本上升。一是工资成本提高。“民工荒”、富士康员工跳楼、各种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现象都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和稳定,不得不提高待遇并提供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同时,中国各地政府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也导致工资成本上升。二是原料价格暴涨。我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三是环保费用增加。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满足日益提高的节能减排标准,企业不得不增加人力物力财力。四是居民消费要求提高。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的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推高企业在满足这些要求方面的各种投入。
2.物流成本太高。物价高企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物流不畅是一个重要推手。由于国内流通体制不顺,流通环节一直过多,流通费用一直过大,导致物流综合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2倍。汪同三[9]指出,全世界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流通成本占50% ~70%,让人震惊。韦森[10]认为,我国产品在国内消费,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统计显示,1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1.5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6~8元。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等费用,这些费用最终由消费者埋单。据2011年5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我们的不少商品价格畸高。
3.税费负担过重。此轮通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是主战场。但真实税负是中国最大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我国近30年来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四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 18%、21.9%、8.7%和当前的6%左右,人民币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也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国内售价高于国外售价,外国制造的产品在本国售价低于在中国的售价(例如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出售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2/5)。据高培勇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2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另外,我国税收和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不够透明,使得这种统计也难以靠近现实的客观情况。例如,美国的商品都标明价外税,我国商品只显示最终价,看不出价格中的间接税。
三、“十二五”期间我国通胀的综合治理
客观分析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通胀的具体表现以及深刻根源,是我们预测“十二五”期间价格波动趋势的着眼点,也是我们进行战略统筹通胀治理的着力点。
(一)“十二五”通胀趋势的基本判断
从国内看,国家为保持经济增长,面对就业等民生问题,必须加大投入,从而使得通胀和经济增长较长时间共生共存。第一,要素成本上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使得“十二五”通胀压力必然长期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况将出现逆转,民工荒等现象将时有出现,劳动力成本将迎来较快上升期。能矿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及税收提升,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高,必将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低利率和负利率现象将在“十二五”期间退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政府可能主动推进人民币升值来对抗通货膨胀,[11]都将大大提高企业融资和经营成本。第二,由于心理惯性和媒体效应,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定势,使得通胀预期仍然较强。目前通胀预期管理的局面十分复杂,而且政府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仍然缺乏经验。2011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日用品抢购现象反映了居民通胀预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这种情况在“十二五”期间将可能再度出现甚至有增无减。第三,政府旺盛的投资需求以及民间过剩的流动性仍然是“十二五”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将以投资为主,“十二五”设定的14个目标、56个重大任务,都亟需资金投入。贯彻落实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为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项目还有3~5年的建设周期,货币发行已经占用未来几年的指标。同时,地方平台债务总额已达14万亿元,一旦完全收紧货币投放,政府投资资金链断裂,整个经济一朝缺血,将面临空前风险。而且,“十二五”时期全国GDP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但大多数省、区、市提出的预期目标都在10%以上。另外,党政换届将引发新一轮经济周期,这也使通胀一时难以控制。2011年基层党委换届,2012年中央换届,2013年政府换届,新一届中央和地方政府上任后,面对保障房建设、全面社会保障、全民医保等重大民生任务,将不得不考虑调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第四,各种情况显示,国内流动性已经偏紧。2011年抗击通胀的高压政策已经使中小企业频现信贷饥渴症,温州这一我国资本高地,竟然也出现债主出逃、高利贷崩盘等现象,严重影响经济实体,搅乱金融市场秩序。为了保证就业以及贯彻实施《“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政府未来必将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还有,近几个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低于荣枯线下,汇丰银行9月30日发布的中国PMI为49.9%,[12]连续3 个月跌破 50%,而且这种趋势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我国官方PMI自4月起连续4个月下跌,至8月份止跌回升,但都处于历史低位的51%上下。可见,制造业经济扩张乏力,流动性以及经济景气已经压力重重。
从国际看,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协调机制,各国为拯救经济必然继续实行积极货币政策,输入性通胀压力将贯穿于整个五年规划。第一,国际热钱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我国,这将对国内通胀压力雪上加霜。同时,持续发酵的欧美债务危机,也使一部分避险资金流入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人民币避险潜力彰显,人民币几乎成为避风港。第二,欧美债务危机恐慌加剧。欧债面临崩盘危险,难以找到治标治本的良药,而且各国都乐于旁观而束手无策;美联储悲观论调以及货币宽松政策,导致整个市场信心不足,全球股市熊劲十足,给2012年以及未来发展蒙上阴影。第三,国际舆论普遍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IMF将中国2011年GDP增长率由9.6%下降为9.5%,2012年由9.5%下调至9%。国际预期低迷,必然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外在压力。第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高位运行。201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上涨,今年9月份前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已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近期美联储扭转操作政策出台以后,造成黄金和石油价格异常波动,但是短暂跌降以后再次蹿升。受全球需求恢复、流动性充裕以及地缘政治和重大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还可能继续上涨。第五,全球通胀压力仍然高居不降。一方面,新兴经济体通胀率继续高企。3月份,巴西、俄罗斯、韩国和越南消费物价同比涨幅分别达到 6.3%、9.5%、4.7% 和13.9%,印度2月份涨幅达8.8%。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通胀呈抬头之势。3月份美国消费价格同比上升2.7%,是2009年12月以来的最高涨幅;欧元区消费价格上涨2.6%,创2008年10月以来新高,连续第四个月呈上升态势,超过欧央行2%的警戒线。第六,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0-0.25%的目标区间,继续按原计划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4月初,欧央行自2008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主导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1.25%,但现行利率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英格兰银行则保持0.5%的基准利率水平不变。日本银行除了保持0.1%的基准利率不变以外,还因地震进一步放宽了政策。[11]
(二)“十二五”通胀治理的战略运筹
既然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这次治理通胀也引发了各种后果(例如,浙江等地已经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并将存续于整个“十二五”期间,我们就必须以整个通胀周期为时间窗口对症下药地进行综合治理,制定并实施整体配套的金融财税政策。特别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上“四率齐发”,加强流动性管理。将通胀率控制在5%~10%的可控范围内,同时以通胀对抗美元贬值,抵消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过来以有管理的人民币升值幅度对抗通胀,实现通胀与汇率的有效对冲。另外,将存款储备金率、利率、汇率、贴现率调整到合理区间,熬一副融合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的“政策中药”,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尽快改变负利率现象,建立货币供应量目标制,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努力减少新增货币供应,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科学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目标制。即在保障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前提下,把本国货币与某种商品或低通胀大国的货币挂钩,或者采取爬行盯住汇率制,从而锚定国际贸易商品的通货膨胀率,提升中央银行信誉,自动缓解时间错位问题;推进人民币自由汇兑,早日做到藏汇于民,并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吸收和消化不断增加甚至被动超发的货币;密切关注境外热钱流入和境内投机资金流向,防止借机炒作造成价格异常波动。
其次,财税上有保有压,提高收入分配效益。要征好税收用好税收,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要为市场主体减税,降低企业成本。物价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一种路径是选择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另一种路径则是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发布报告[13]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出现高税负低福利的畸形反转状态。因此,“十二五”期间应该实施一揽子减税计划。因为只有减税才能维持或加大产品供给,从而平销价格提升压力。推进在生产环节纳税向消费环节纳税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生产、流通环节税负水平;进一步清理各种涉企收费,最大程度地降低各种成本上升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税率。二要提高有关待遇,促进居民消费。一是发补贴,大幅度增加财政对农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健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低保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二是提工资,实行收入倍增计划,不断增加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人员的收入水平。三要努力开源节流,增加财税收入。一方面节约开支,特别是政府要压缩行政成本,减少公车、出国、公款吃喝消费;另一方面加大偷税漏税查处力度,特别是加强海关缉私,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四要保障市场供应,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择机扩大国内紧缺物资进口调节;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同时,利用外汇储备等剩余资金扩大投资等经贸活动。
第三,行政上科学组合,提高价格监管水平。国家依法建立和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地方财政相应建立通胀治理的储备基金,科学投放资金并确实平抑属地物价;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监测;继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严禁擅自收费、超标准收费和变相收费;规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中远期交易,遏制过度投机;强化价格执法,颁布价格指导线,对工资、物价实行强制性的控制或管理。尤其必须做到稳定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需,防止短期物价上涨引起长期通货膨胀预期上升,保护低收入群体;切实将经济方式尽快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投资、贸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特别是促进内需、优化供给,保护经济增长引擎可持续运转;通过加大科技、培训投入,加强热钱管理,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科学协调,提高通胀承受力和容忍度;切实做好预期管理,一是降低政府的增长预期,二是控制通胀预期,三是锚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实现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实现通胀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效结合。
总之,中国的通胀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困境”。另外,中国曾经经历过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四轮通胀,通胀并不是难以治愈的癌症。只要我们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综合运用治理通胀的蓄水池,综合运用市场、行政和制度手段,我们就一定能既防止通胀、通缩、滞涨又防止急刹车硬着陆。
[1]国家统计局.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EB/OL].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809_402745781.htm.
[2]海宁.中国历次量化宽松[EB/OL].http://www.tianyayidu.com/article-190048 -1.html.
[3]中国人民银行.历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si/359/index.html.
[4]中国人民银行.2011 年 7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EB/OL].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3172/2011/20110812150048444102009/20110812150048444102009.html.
[5]陆前进.改革货币发行机制需两种模式结合[N].证券时报,2011-05-03.
[6]陈静思.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新增美元约四成流入中国[N].东方早报,2010-12-28.
[7]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EB/OL].http://www.customs.gov.cn/Default.aspx?tabid=2453&moremoduleid=3760&moretabid=4370.
[8]田俊荣.外汇占款为何猛增[N].人民日报,2011-09-22.
[9]钟晶晶.国内流通成本高达70% 流通体制亟待改革[N].新京报,2011-04-26.
[10]周小苑.部分商品价格中贵美贱 消费者埋单额外成本多[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7-14.
[11]胡晓炼.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稳健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EB/OL].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52/2011/20110419144540500655242/20110419144540500655242_.html.
[12]马文婷.汇丰中国发布9月PMI指数 制造业PMI终值仍不景气[N].京华时报,2011-10-01.
[13]马海涛.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R].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03).
China’s Strategic Operations for Controlling Inflation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YANG Zhi-huang
(Center for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Studies,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China’s infla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rises from four main reasons:liquidity overrun,expectation of inflation,input of US dollars,and rise of costs.To control this round of inflation scientifically,we must have an over-all vision and a long-term plan and make good use of economic,political,legal and other measures.In particular,we must work out strategic plans in finance,taxation and administration,relieve the expectation of inflation,use inflation as a too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lute the stress of Renminbi appreciation by inflation.
inflation;expectation;control inflation by integrated measures
F712
A
1674-0599(2011)06-0130-07
2011-09-05
杨枝煌(1975—),男,福建漳州人,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金融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
(责任编辑:廖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