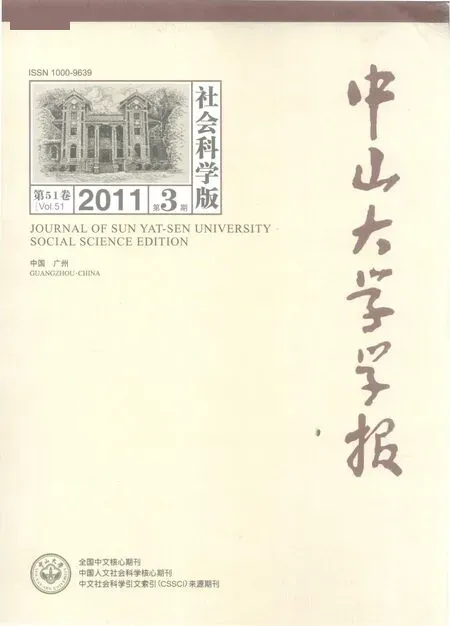辞官与颂圣*
——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
2011-02-10史洪权
史洪权
学界论及高启之于朱元璋及其明政权的态度,一言以蔽之曰“不合作”,尤以钱伯城先生的观点最具典型性:“明太祖之所以蓄意要把高启置于死地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乃是高启作为当时东南地区士大夫阶层中一个代表人物同张士诚政权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明朝政权的依违态度。后者似乎尤为重要,依违态度说到底就是不合作态度。这对一个刚建立的新政权来说,是不能容忍的。”①钱伯城:《诗人高启之死及其诗歌评价》,《中华文史论丛》第30辑,1984年,第153页。按:宋佩韦《明代文学》、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等均与钱氏持相同的观点。此说之最重要证据,即高启于洪武三年的辞官。然而,高启在金陵一年零八个月,先后参修《元史》、入宫授经、擢拔翰林,假如纯属政治立场的问题,缘何这些阶段均不辞官,偏偏于超擢户部侍郎的当天请辞?缘何他在金陵时期的作品中,时有流露渴求进用的心态?足见“不合作”说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拟从高启与朱元璋两人的行为互动、心态变迁等角度,重新审视该说,以期有所发现。
朱元璋予高启之恩遇
目前的高启研究,几乎无人留意到朱元璋对高启的态度。朱元璋之于高启,可谓恩深意厚,究其尤者有三:一曰征修《元史》,二曰超迁官秩,三曰赐金允归。
明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诏修《元史》,任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壎、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等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天界寺。时人徐一夔曾高度评价修史诸儒:“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此书(注:指《经世大典》)可以参稽,而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陶中立、赵伯友、赵子常、徐大年辈皆有史才史学,廑而成书……”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85《徐一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23页。除徐一夔赞赏的胡翰、陶凯、赵壎、赵汸、徐尊生外,宋濂、王祎俱为文章大家,汪克宽为理学名儒。高启能跻身其中,为胜朝修史,留名万世,颇有几分惶恐。如其诗云:
圣主念前鉴,述作征名儒。群来高馆间,厕迹愧我愚。(《高青丘集》卷7《天界玩月》)①高启著,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按:此后所引诗句,非特殊说明者,皆出于本集。
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议论名。(卷15《被召将赴京师留别亲友》)
然骄傲之情,自豪之感,亦在文字中流露无余。如:
诏预编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龙墀。(卷14《奉天殿进元史》)
东华叨列仙班入,五色云中觐九天。(卷15《赴京留别乡旧》)
而此份荣耀,无疑是拜朱元璋之赐。
高启官职的升擢,更可看出朱元璋对他的赏识。高启金陵之行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洪武元年冬至八月,为修史阶段,此时高启尚是布衣;第二阶段从洪武二年八月至三年二月,为授经阶段,高启先是为功臣子弟授经,三年正月后主要辅导太子朱标及常遇春二子,身份依然是布衣②《高青丘集·凫藻集》卷5《志梦》(第944—945页):“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梦与启同被召至上所,上授以一纸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越六日,上御奉天门,宰执并侍,小黄门招启等升,上顾中书右丞汪公曰:‘诸儒在学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游吾门,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职处之。’因趣谢……”;第三阶段从洪武三年二月至七月,为翰林阶段。朱元璋在二月二十六日召见诸儒,赞其皆有文行,命中书右丞汪广洋“亟以翰林之职处之”③《高青丘集·凫藻集》卷5《志梦》,第945,944—945页。,高启得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七月二十八日,高启再被朱元璋任命为户部侍郎,同日辞官并得到允许,结束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京师生活。即使朱元璋喜欢以大升大降来慑服群下,但像高启从一介布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擢升为正三品的户部侍郎,在当时亦可谓“火箭式的干部”了。
我们还可以把高启与其他修史授官的诸儒做一横向比较。修史十八人中,汪克宽、徐尊生、陈基、赵汸、胡翰、赵壎六人辞归或赐归,黄篪事迹已不可考,仕者有宋濂、王祎、高启、谢徽、傅著、宋禧、傅恕、张文海、陶凯、王锜、曾鲁十一人。高启至辞归时,官品仅低于礼部尚书陶凯,甚至高于追随朱元璋多年的宋濂、王祎。另外,高启与谢徽为挚交,同至京师修史,同入内府教功臣子弟,同迁翰林国史院编修。洪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朱元璋面授启户部侍郎、徽吏部郎中。户部与吏部属同级机构,户部侍郎为正三品,吏部郎中仅为正五品。高低之间,自可显出朱元璋对于高启的宠任。
相较于前两者,朱元璋的赐归无疑让高启更为感激涕零。关于辞官时的情境,见于《志梦》一文:
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母夫人林氏,梦中使舁二橱授两家,发各有白金在焉……至二十八日暮,出院还舍,有控马驰召余二人,上御阙楼俟焉。既见,奖谕良久,面拜启户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启以年少未习理财,且不敢骤膺重任,辞去。玄懿亦辞。上即俞允,各赐内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国公给牒放还于乡。④《高青丘集·凫藻集》卷5《志梦》,第945,944—945页。
作为一个帝国的创建者,朱元璋非常希望与群贤共治天下,以臻太平。早在吴元年,他就派遣起居注吴琳、魏观等以币帛求遗贤于四方。洪武元年,下求贤之诏,征贤才至京,授以守令之职。同年冬,再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分行天下,访求人才。正因如此,对于具有真才实学的高启,不惜以显官相与。高启婉谢辞归,刚烈雄猜的朱元璋也没有恼羞成怒,而是遣之以礼,给牒放还。毋论朱元璋内心所思如何,高启所能感知到的,只会是一个宽宏慷慨的圣君形象。
因此,高启对朱元璋的感激应是真诚的。他在出都时尝赋诗感怀:“诏贰民曹出禁林,陈辞因得解朝簪。臣材自信元难称,圣泽谁言尚未深。远水江花秋艇去,长河宫树晓钟沉。还乡何事行犹缓,为有区区恋阙心。”(卷14《辞户曹后东还始出都门有作》)蔡茂雄先生解此诗云:“至于他在《辞户曹后东还始出都门有作》说:‘还乡何事行犹缓,为有区区恋阙心。’是故作姿态,因为高启是个心细的人,他了解自己坚辞户部侍郎,是不跟明太祖合作的举动,可能因此招来祸害,所以处处小心。”①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22页。如果联系到朱氏对高启的宠遇,高启纵不能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儒家传统为明王朝鞠躬尽瘁,也不至于一意掩饰做作如此。对此,钱穆先生的评论远为精当:“此殆亦一时由衷之言。盖明祖之于诸儒,恩意礼遇,不可谓不优渥;良使季迪临去,亦不能不稍有恋阙之心也。”②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三《读高青丘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高启辞官的心理考察
洪武元年冬,高启应召赴修《元史》,从而开始了将近两年的仕宦生涯。就高启本人而言,他所秉承的,还是儒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信念③关于这一点,笔者《试论高启与张吴政权的关系》(肖永英等编:《资讯管理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8—397页)有详细的分析。。这在其元末的作品中就已有所表现:
颇闻君子心,道穷贵益贞。己志未获施,安用轩裳荣?所以不苟出,出则时当平。(卷4《感旧酬宋军咨见寄》)
奉觞置君前,长歌发哀声。时乎苟未得,饮此全其生。(卷4《答张山人宪》)
安居且复俟时宁,出岂无能非退卷。(卷10《次韵杨孟载早春见寄》)
张吴政权灭亡后,高启意识到天下即将步入治世。他在《野潜稿序》中,勉励朋友审时度势,不负所学:
当张氏擅命东南,士之抠裳而趋、濯冠而见者相属也,君独屏居田间,不应其辟,可谓知潜之时矣。及张氏既败,向之冒进者,诛夷窜斥,颠踣道路,君乃偃然于庐,不失其旧,兹非贤欤?然今乱极将治,君怀负所学,可终潜于野哉?闻君素善《易》,于随时潜、显之义,必自有以审之矣。④《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野潜稿序》,第881页。
此文虽为朋友所作,但联想到高启相似的经历,未尝不可看作曾胸怀壮志的本人的思想。因此,当他受聘参修《元史》时,一方面是“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议论名”(卷15《被召将赴京师留别亲友》)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风流已遂明时志,岁月空惊壮士年”(卷15《赴京留别乡旧》)的慨叹,矛盾的心态、对立的情绪流露无遗。
如果没有朝廷的征聘,依高启的性格而言,他或许不会主动求仕。但是当出仕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几乎被现实磨灭掉的雄心开始复活。修史在他的眼中,未尝不是自己实现夙愿、经世裨国的良好机遇。更何况本年的高启已经三十三岁,颇有些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了。如《召修元史将赴京师别内》云:
承诏趣严驾,晨当赴京师。佳征岂不荣,独念与子辞。子自归我家,贫乏久共之。闺门蔼情欢,宠德不以姿。天寒室悬罄,何忍远去兹。王明待文,不暇顾我私。匆匆愧子勤,为我烹伏雌。携幼送我泣,问我旋轸时。行路亦已遥,浮云蔽川坻。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加餐待后晤,勿作悄悄思。(卷7)
然而,亲朋好友们的或死或谪、对于明政权的一无所知等因素,使高启对未来又有些举棋不定。在他初至金陵,与好友杨基重逢时,他虽极力鼓励对方出仕,自己则准备修史完毕即还乡里:
嗟余忝载笔,鼠璞难自炫。幸兹际昌辰,魏阙宁不恋?但忧误蒙恩,不称终冒谴。秋风楚潮满,归舸帆欲转。君若念故交,殷勤一相饯。(卷7《赠杨荥阳》)
洪武二年八月,《元史》修毕,朱元璋“诏赐纂修之士一十六人银币,且引对奖谕,擢授庶职,老病者,则赐归于乡”⑤《高青丘集》卷7《天界玩月》,第286页。。高启并未像陈基、汪克宽等人那样辞官,而是接受了朝廷的任用,入内府辅教功臣子弟。在由天界寺迁至钟山里时,他在诗中依然表达了“谁言新舍好,毕竟未如归”(卷12《自天界寺移寓钟山里》)的愿望,可他终究没有离去。
授经属教职,不入官品。我们试揣度朱元璋的心理,高启诗名虽著于世,却并没有从仕经验。将其放在身边,一方面可以考察其真实才能,另一方面让他熟悉朝廷状况,为将来的出仕做好准备,这也未尝不合情理。但对于高启而言,无疑有些失望,这种消极情绪偶会流露于诗中。如《西清对雨》:
楚台云起远,汉苑雨来微。晓湿宫城旆,寒沾陛楯衣。沟中随叶堕,炉畔带烟飞。坐咏西清暇,君王召对稀。(卷12)
短短数月间,“布衣亦得拜龙墀”的骄傲已经荡然无存,原本就非坚定的出仕信念开始动摇。这种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终于在洪武二年的冬天爆发。《京师苦寒》云:
北风怒发浮云昏,积阴惨惨愁乾坤。龙蛇蛰泥兽入穴,怪石冻裂生皴痕。临沧观下飞雪满,横江渡口惊涛奔。空山万木尽立死,未觉阳气回深根。茅檐老父坐无褐,举首但望开朝暾。苦寒如此岂宜客,嗟我岁晚飘羁魂。寻常在舍信可乐,床头每有松醪存。山中炭贱地炉暖,儿女环坐忘卑尊。鸟飞亦断况来友,十日不敢开衡门。朅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黯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陌头酒价虽苦贵,一斗三百谁能论?急呼取醉径高卧,布被絮薄终难温。却思健儿戍西北,千里积雪连昆仑。河冰踏碎马蹄热,夜斫坚垒收羌浑。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卷10)
钱伯城先生分析此诗云:“寒风雪景,本是骚人墨客饮酒赋诗的绝好雅事,他却写得如此阴森凄惨;学士太史,何等华贵清高,他却写得如此卑微。一向总是人的思想感情决定他对外界事物价值的判断;因此反过来,从他对外界事物价值的判断,也可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何在。高启这时对待他所处环境和官职的思想感情,实在是很清楚了。”①钱伯城:《诗人高启之死及其诗歌评价》,第169页。其实,此诗诗题下自注“洪武己酉”,可知作于洪武二年的冬季。此时,高启尚是一个授经的布衣,虽然当初出仕是“王事靡敢辞,非关徇微禄”(卷7《早发土桥》),但在“此地居,大不易”的京师,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早在洪武二年春,高启与杨基相会于京师寓馆时,他已经处于“客中虽无钱,自写赊酒券”(卷7《赠杨荥阳》)的境地了。此后,经济状况的恶化使高启对前途的看法更为黯淡。《客中述怀》一诗即可读出高启的真实心态:
故园生计日蹉跎,不觉青春客里过。旅食自惭空旧橐,朝衫谁为换新罗?多愁未必关花事,长醉原非困酒魔。几度欲归归未得,空弹长铗和高歌。(卷15)
高启借用冯谖与孟尝君的典故,更真实地表现出他并非不愿与朱元璋合作,而是急于求用的心态。对他而言,既然不得后者的重视,那么“一蓑归钓江南村”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希望总是诞生于绝望之时。洪武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朱元璋召高启等陛见,授启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高启任职翰林,既可算是才得其所,又有了明确的官秩名分,其内心多少有些宽慰。这段时间的诗歌中,求归的心思淡了许多。明初的翰林沿袭了元代的传统,属清要之官,且高启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编修,这与他的自期还是有些落差。如《池上雁》云:
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沼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耿耿宵光迟,戚戚寒响聚。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岂无凫与鹜,相顾非旧侣。朔漠饶燕云,梦泽多楚雨。遐乡万里外,哀鸣每延伫。犹怀主恩深,未忍轻远举。傥令寄边音,申报聊自许。(卷4)
观其所描述的内容,知高启为文学侍从之臣时作。他以被主人豢养的野雁自比,真实刻画出自己去留两徘徊的矛盾心情,并于末句再次表达了急切用世的信念。
落差归落差,高启对于翰林院的平淡生活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习以为常。此时,高启已将家人从苏州接至金陵,生活也趋于稳定。这个时段的他,依然还会有江湖之兴,但开始有些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味道了。《京师寓廨》三首云:
谁言旧隐非?静里且相依。绿树城通苑,青山寺对扉。官闲休直早,客久梦还稀。是物春来典,唯存旧赐衣。
几夜频听雨,经春不见花。蘼芜青渚燕,杨柳白门鸦。拙宦危机远,工吟癖性加。闲坊车马少,不似住京华。
寂寞过芳时,幽怀只自知。袖无投相刺,箧有寄僧诗。鼠迹尘凝帐,蛙声雨到池。疏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卷12)
如果高启一意拒绝与朱元璋合作,那么选入西清授经、擢任翰林编修皆是很好的辞官机会,可是高启并没有如此选择。究其原因,除了用世之心不死外,朱元璋的恩宠也使他很难就此拂袖而去。这种心理可证之于洪武三年入翰林后所作的《送顾式归吴》(卷7):“顾君野王孙,与我生共县……余方谬通籍,讲帷近清殿。故园岂不怀,君恩正深恋。远欲谢乡人,殷勤附君便。”《送证上人住持道场》(卷9):“诉公昔年住宝坊……我方无用靡太仓,叨逐剑佩趋明光。醉歌欲觅玄真狂,怀恩未得寻归航。明朝举首空相望,云飞笠泽天茫茫。”
高启辞归后,感慨“柴门药圃小江边,蚤得闲居是偶然”(卷15《漫成二首》其一),很清楚地说明得归也出乎他的意料。高启在布衣授经时心情灰暗,多次提及要归钓吴江,但当朱元璋将其擢拔为翰林编修时,他尚且都没有顺势请归,那么短短五个月后的辞官,只可能和其超迁户部侍郎一事密切相关。
高启是以“年少未习理财,且不敢骤膺重任”①《高青丘集·凫藻集》卷5《志梦》,第945页。求去的。高启“身长七尺,有文武才,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4页。,但他确实没有理财方面的经验,那么贸然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无疑蕴含着极大风险。朱元璋是奉行重典驭下的专制君主,他将高启从正八品的翰林编修连擢十阶,其期望值既高,其求全责备之心也必强,对此,身为文学侍从之臣的高启自是心知肚明。明初一直奉行财政紧缩的国策,作为管理天下财赋的户部自是十分艰难。洪武一朝共计三十一年,户部尚书则多达四十余人,且多不久于职,绩用罕著③[美]黄仁宇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和税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4页)对此有详细的论述。。高启简授户部侍郎之前的三任户部尚书朱昭、杭琪、滕德懋,无一幸免贬谪的命运④雷礼:《国朝列卿纪》卷31:“朱昭,洪武二年拜户部尚书……本年十一月以怠职降苏州府知府,后卒于官;杭琪,(洪武)三年十一月升户部尚书……本年以事贬陕州知州,后卒于官;滕德懋,洪武三年改户部尚书……本年以事免官,卒。”明代传记丛刊本。。此时的高启对此应知晓一二,以“逾冒”为由拒绝任命也是情理中事。高启辞官后,喜为《始归田园》二首,可以看作他真实心声的流露和表现:
辞秩还故里,永言遂遐心。岂欲事高骞,居崇自难任……父老喜我归,携榼来共斟。闻知天子圣,欢然散颜襟。相期毕租税,岁暮同讴吟。
白露芜草木,荒园掩穷秋……乍归意自欣,策杖频览游。名宦诚足贵,猥承惧愆尤。早退非引年,皇恩未能酬!相逢勿称隐,不是东陵侯。(卷7)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启并非一意求隐,只是“居崇难自任”,“猥承惧愆尤”而已。言外之意,户部侍郎一职既高且险,除了坚辞不受之外,他别无选择。明文震孟曾感慨太祖用高启之失:“国家官人,当视其才。如高先生之材,宜为翰林,不宜为户部。其以不习握算辞,可谓允矣。”⑤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明代传记丛刊本。
后辞官时期的诗文颂圣
高启辞官后的第一反应是重获自由的愉悦。这份适意来之不易,他形容为“休轻一枕江边睡,抛却腰金换得来”(卷17《雨中晓卧二首》之二)。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仕宦生涯之后,高启真正体悟到“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两事不可齐,人生苦难足”(卷6《晓起春望》)。但对于朱元璋,他依然怀有感激之情:
今朝无事役,睡足亦君恩。(卷16《睡足》)
且放疏狂醉杯酒,圣恩元许作闲人。(遗诗《示内》)
高启还将自己与韩愈、苏轼相比,认为名声虽不及二人,命运则更胜一筹,这正是遭逢圣主所致。《送钱文则序》云:
韩文公诗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苏文忠公谓公身坐磨蝎宫也,而己命亦居是宫,故平生毁誉颇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纪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说身命舍是者多以文显,以二公观之,其信然乎!余后生晚学,景仰二公于数百载之上,盖无能为役,而命亦舍磨蝎,又与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与之同也。二公之名虽重当世,而遭逢排摈谤毁,几不自容,仕虽尝显于朝,而贬阳山,谪潮州,窜逐于罗浮、儋耳之间,逾岭渡海,冒氛雾而伍蛮蜑,其穷也甚矣。顾余庸庸,虽不能致盛誉,亦不为诽谤者所及,况遭逢圣明,忝职禁署,蒙恩赐还,无投荒之忧,是幸而不与之同也……①《高青丘集·凫藻集》卷3《赠钱文则序》,第889—890页。
对于自己拂逆朱元璋的善意,高启不免有“皇恩未能酬”的歉疚感。他谈及辞官,总是归咎于自身的“无能”、“无用”②《高青丘集》卷5《天平山》(第202页):“身今解组绶,明时愧无用。”卷9《赠治冠梁生乞作高子羔旧样》(第386页):“清时无能耻恩泽,朝簪乍脱归田扉。”,即使是面对挚友时亦是如此。张羽尝赋《奉答吹台先生送蜀山人见简之作》:“子畏伐檀刺,余怀白驹美。”③张羽:《静居集》卷1,四部丛刊本。吹台是高启的别号。《伐檀》见于《诗经·魏风》,毛传:“《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④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白驹》见于《小雅·祈父之什》,毛传:“大夫刺宣王也。”郑笺:“刺其不能留贤也。”⑤《毛诗正义》卷11,第673页。张羽讥刺朱元璋不能用贤,而高启则认为自己不应无功受禄。
如果说居于庙堂之上,为皇帝效命算作第一种忠诚,高启无疑是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但歉疚之心使他选择了第二种忠诚——诗文颂圣。早在金陵时期,当徐尊生在议礼完毕后,准备布衣终老时,高启尝对那些困惑其圣朝不仕的士大夫们解释徐氏的动机,认为徐尊生虽是引退,但是“必能著书立言以淑诸人,咏歌赋诗以扬圣泽,则又非洁身独往而无所补者也”⑥《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送徐先生归严陵序》,第883页。。退而不隐,诗文颂圣的理念似乎肇始于此。洪武三年,王彝辞官归养,高启赋《妫蜼子歌》(卷11):“妫蜼子,幸际明良时,无为寂默坐老东海湄。青丘有客钝且痴,与汝欲结同襟期。左鼓清瑟,右吹鸣篪,作歌共祝天子寿。五风十雨,万国赤子同熙熙。”同年七月,高启与谢徽结伴还乡,赋诗言志,要与谢徽“来往片帆通,相期作钓翁。高歌虽鄙野,犹可赞王风”(卷7《酬谢翰林留别》)。诗文颂圣的想法溢于言表。
高启屏居青丘后,采郡志所载山川、台榭、园池、祠墓等景致,赋诗咏歌。他觉得自己身为圣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时取一篇,与渔父鼓枻长歌,以乐上赐之深,岂不快哉!”⑦《高青丘集·凫藻集》卷3《姑苏杂咏序》,第907页。可以说,高启并没有忘记朱元璋的恩典,也没有忘记颂圣:观画,他会回忆起“曾谒真龙游太清”(卷10《题董元卧沙龙图》)的昔日荣耀;游山,他会由山名“龙门”联想到“我尝谒真龙,天门谬通籍”(卷5《龙门》);听琴,他会对琴师“起请且莫弹胡笳,文姬思家意咨嗟。请莫弹履霜,孝子在野心彷徨。愿君拂拭登高堂,先弹南风后文王。美哉大雅声洋洋,使我坐听忧俱忘”(卷11《听钱文则琴呈良夫》)。甚至为工匠题诗,他都会联想起朱元璋的丰功伟业:“我看十年太白西方明,铜山寻凿兵纵横。幸逢圣人生,干戈戢,四海清,愿生但制此器勿制兵!民无疫疠乐太平。”(卷11《赠刘生歌》)洪武四年二月,好友丁俨赴河南省亲,登门求序,高启借题发挥,洋洋洒洒成就一篇盛世颂歌:
夫殊乡远别,忽父子相见,上堂起居之余,举觞奉欢,此人子之深愿,而天下之至乐也,然其得与不得,则有幸不幸焉。盖自海内分崩,所在梗阻,子之思其亲而不得见,陟岵而歌,望云而叹者,有不可胜数。今皇上削平四方,车书既同,虽遐邦异壤,往来若东西州然,故至恭之思其亲,欲见即往,无有关阂者,实遭逢升平之时也。然则人子之深愿,而天下之至乐者,在当时人有所不能得,而至恭今得之,岂非由上德惠之所及哉!幸逢斯时而蒙上德惠之及,则为臣子者,可不思所勉乎!①《高青丘集·凫藻集》卷2《送丁志恭河南省亲序》,第887页。
对于国事,高启亦保有一份关怀。洪武四年,明军消灭明氏政权,高启喜而有作:
蜀国兵销太白低,将军新拜汉征西。浮桥已毁通江鹢,进鼓初鸣突水犀。不假五丁开道远,俄看万甲积山齐。从今险阻无人恃,夷贡南来尽五溪。(卷15《喜闻王师下蜀》)
洪武五年,魏观出任苏州知府。高启与魏观素有旧好,遂应聘与王彝、张羽修订经史②《明史》卷140《魏观传》(第4002页):“五年,廷臣荐观才,出知苏州府……观尽改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之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耆民周寿谊、杨茂、林文友行乡饮酒礼。政化大行,课绩为天下最。明年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并协助魏观实施教化,遂成一方之治。这固然与高、魏两者的友谊相关,但高启不肯为“洁身独往而无所补者”之心由此可知。至于他受魏观牵连而惨遭腰斩,借用钱穆先生一语以作概括:“上下暌隔,情乖志离,藉端诛锄之祸,遂此酿致,此非明初开国一至可遗憾之悲剧乎?”③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三《读高青丘集》,第129页。
君臣遇合,本为天下至难之事,故齐桓公与管仲、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之情,方会成为知识分子咏歌的永恒主题。朱元璋对高启不惜高位,却不能用其所长,展其所能,致使后者全身而退,这只是君臣难以遇合的又一典型。学人们将辞官误读为不合作,究其原因: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腰斩高启;二是张适《哀辞》中言高启“力辞忤旨”;三是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颁行《御制大诰三编》,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④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之《苏州人材第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332页。加之宋濂、刘基等众多明初文人的悲惨命运,后世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将朱元璋目作撒旦,而冤死的高启,则被人为塑造成因对朱元璋说“不”而殒命的勇者。高启被腰斩缘于他卷入魏观的谋反案,与宋濂被流性质相似,而谋反在历朝都是不赦之罪。张适所言,则与高启本人自述“上即俞允”有出入,自当以后者为准。至于《大诰》的规定是果非因,我们不能用十八年的律令反推洪武三年发生的事件。谢徽、张适、贝琼等吴中文人于洪武三年先后辞官,不仅未受迫害,数年后又被诏复出。可见此时的朱元璋对辞官的知识分子尚无暴力解决之想法,还是以求贤为第一要务。至于双方最后陷入完全对立之境地,钱穆先生《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对此有精辟的解析,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