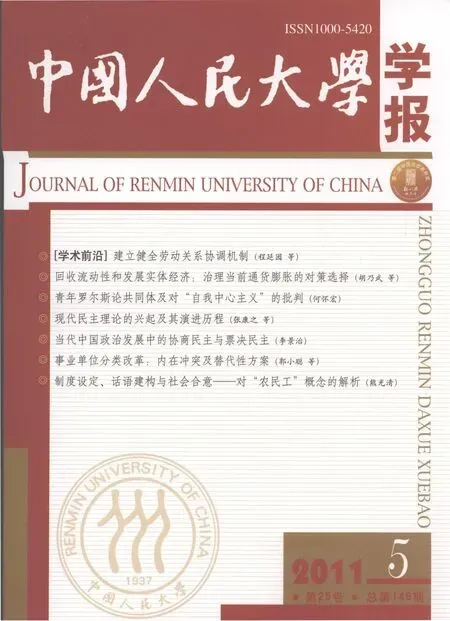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对“农民工”概念的解析
2011-02-09熊光清
熊光清
一、“农民工”概念的“漩涡效应”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一些农民自主进入工矿企业务工或者进入城镇经商务工,“农民工”概念开始出现,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但是,“农民工”概念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吴忠民认为,应当逐渐淡化“农民工”或“民工”的称谓,逐渐将之分别改称为不同行业、部门、单位中的“员工”、“工人”或“职工”等等。[1]贺汉魂、皮修平认为,“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时代局限性和歧视性的概念,不宜再提。[2]厉有为认为,农民工的称谓把这一群体界定为农民,而没有界定为工人,应当以他们从事的职业来称谓他们。[3]李永海认为,“农民工”称谓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离,其消极影响正在增大。[4]汪勇认为,“农民工”概念蕴含着“农民”、“市民”与“农民工”的区别,“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区别,“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区别等。[5]叶育登、胡记芳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称谓对他们的社会认同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应改变农民工称谓,转变农民工身份,从而改善群际关系,实现社会公正。[6]尽管存在对“农民工”概念的质疑,而且“农民工”概念确实具有许多不合理性,但是,这一概念近年来使用的频率却非常高。
为什么一个不合理的概念被广泛使用,甚至于一些人认识到了它的不合理性而仍然在使用呢?这一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笔者认为,由于在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之间形成了对“农民工”概念的“漩涡效应”①在自然界中,漩涡是具有旋转中心的独立旋转体系,如龙卷风、水漩涡等。漩涡的旋转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如果漩涡体内的各个部分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旋转就会停止或者出现断裂。在社会领域中,对于“农民工”概念的使用,仿佛存在“漩涡效应”。,对这一概念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强化并自我复制,导致这一概念的活力不断增强,使质疑和消解这一概念的难度极大。可以说,一定的社会制度为某一特定问题或现象的产生、形成和固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为人的信仰、意识和行动取向设定了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不断重复的话语为某一特定问题或现象提供了符号系统,强化了社会中相同或相近的信仰、意识和行动取向,并使之表现得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相同或相近的信仰、意识和行动取向的他人认同与自我认同,这种相同或相近的信仰、意识和行动取向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合意,特定社会问题或现象的社会认同感也不断得到强化。由此,这种针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和社会合意之间又不断相互强化,并使这三者具备更加强烈的自我复制能力而难以控制,从而形成一种漩涡效应。这样,关于某一特定事物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和社会合意之间就会形成相互不断强化而无法停顿的状态,仿佛一个漩涡。
“农民工”概念的使用正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漩涡。制度设定提供了“农民工”概念形成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规范,在制度层面预先设定了“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政府、学术界、新闻界和其他社会领域通过“农民工”话语建构了一种符号系统,强化了“农民工”的话语体系;社会合意赋予“农民工”概念与“农民工”身份的社会合法性,并使之具备了内在的强制性;同时,这种对“农民工”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和社会合意又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漩涡效应,使这一过程不断深化而难以停顿。在这种漩涡效应中,相同的认识得到强化,不同的观念和质疑被忽略,即使出现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也会被这种漩涡效应所湮灭。这样,就使得“农民工”概念的不合理因素难以被充分认知,其使用频率不断增大,从而不断强化“农民工”群体的特定社会身份和边缘化地位。
二、制度设定:“农民工”概念形成的制度背景
制度不仅提供了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而且设定和塑造着人或者组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No 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7](P225-226)他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8](P225)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政治学家也非常重视对制度及其作用的研究。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 uel P.Huntinton)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9](P10)历史制度主义总体上感兴趣的是影响行为者如何界定他们的利益、如何塑造他们与其他群体权力关系的所有国家与社会制度。[10](P2)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治机构或者政治经济的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制度的范围可以包括从宪政秩序的规则、官僚体制的标准运作程序到主导工会行为及银行—企业关系的惯例”[11]。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提供了对于策略有用的信息,而且还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12]简单地说,制度是关于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制度规定和塑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或者组织在社会行为中的地位、角色和权利。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概念形成和被广泛使用的至关重要的制度背景。户籍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紧缺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局面,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吃自产粮,城镇居民实行粮食按人定量供应,粮食供应与户口直接联系在一起。1955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的标准,中国人口从此开始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类型。中国政府从1953年4月到1957年12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劝止、防止和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3]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14]这一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人口迁移制度固定下来,它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这一条例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结合起来,共同构筑了中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
与一般意义上的户籍制度主要是登记人口基本信息、确认公民身份、掌握人口数据,从而为社会管理提供依据不同的是,中国户籍制度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第一,对人口迁移流动进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在《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国家又发布了一些进一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流动的补充性规定,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堵住了农村人口自主向城市迁移流动的途径。自此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民要跨越城乡隔离这一门槛非常困难,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严格。[15]第二,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制度挂钩。按照户口性质和户口地域分配社会资源,使不同户口性质、不同地域人口在权利上出现了极大的不平等,非农业人口获得了许多特权,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对立和城乡分割。第三,户口性质带有浓厚的“世袭”色彩。户籍制度下的户口身份是一种终身的和世袭的身份,一个人的户口性质并不取决于他的努力程度或者其他因素,而是取决于他出生时父母的户口性质。农民这一本来只表示职业的全球通用的称呼,在中国却成为代表绝大多数国民的一种身份标签。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制度背景下,“农民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才得以产生,并被广泛使用。也许其他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户籍制度,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才没有出现“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或打工,但他们“农民”的身份难以改变,以至于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虽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但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同时,对他们的称呼,一种身份与职业混合的称呼——“农民工”产生了。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的“农民”身份不会变,他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职业状况是“工”了,正好称之为“农民工”。如果不考虑“农民工”这一概念所带有的社会偏见与社会歧视的特性,它是一个非常简明清晰的事实陈述性概念:“农民”指身份,“工”指职业。从这一层面而言,正是由于具备了这种简明清晰的特性,“农民工”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后一直沿用至今。
“农民工”概念直接产生于这种制度背景,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预先设定了“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第一,由于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即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甚至完全离开了农村,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不过又表现出“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尴尬特点。第二,由于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规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都与户籍挂钩,也就是说,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般只提供给当地户籍人口,这种制度预先设定了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人员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第三,由于户籍制度设计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城乡对立和对农民的剥夺,只要这种制度不变革,对农民的剥夺就难以彻底改变,对“农民工”的剥夺只是对农民剥夺传统的延续,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户籍制度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基础事实上已经动摇,但是,户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仍然被严格管制,以户口定身份的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16](P119)当前,中国户籍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但是,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根本无法解决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而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由于受到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的步伐十分有限。在户籍制度影响下,即便社会中的某一群体突破了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但也无法突破户籍制度在其他方面(例如,社会身份、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务等)的限制。因此,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农民工”概念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一群体的特定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已经基本被设定,并且很难发生变更。
三、话语建构:“农民工”概念的不断强化
由于受制度条件、文化环境、认知能力和主体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与约束,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对客体的认识会带有主体自身一定的特性,或者反映主体自身一定的需求,并且,这种认识特性会对主体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会对客体进行主观建构,并会对主客体双方及其关系产生影响。这一建构过程只有通过一定的工具或者中介才能表现出来,这种工具或者中介就是话语。一般来说,话语是指已经说出来的话,没有说出来的不叫话语,也不是话语分析所要研究的对象。[17]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 ichel Foucault)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内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8](P159)他非常强调“话语”的重要性,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19](P159)同时,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实践在传统和创新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重塑社会(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同时,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20](P65)
在社会学史上,与建构论的社会问题理论相似的是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21]。标签理论是以社会学家埃德温·M·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工作理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一个人是否会被贴上越轨者标签,不仅取决于他的所作所为,而且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居住社区、民族和肤色,等等。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理论也有助于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理解。他认为:“自我实现预言是指一个虚假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况去行动,结果最初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结果。简言之,它是产生一种社会实在的过程,而这种社会实在在其他情况下是不会存在的。”[22](P8)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自我实现预言”的结果呢?他认为:“在这一行为方式中,一种最初是虚假的但被广泛接受的预言、期望或信念,最终却实现了,这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太多的人把它当做是真实的并以此去行动。”[23](P117)这一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以及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农民工”中的“农民”与“工”这两个词是一种极为尴尬的组合,它没有直接表明这一群体是“工”还是“农民”,而是表现出一种“非工非农”、“亦工亦农”的矛盾。而这一特征又正是“农民工”这一概念的巧妙之处。按照语言习惯,职业称谓一般都非常直接,在农村工作的人称“农民”,在工厂工作的人称“工人”,经商的人称“商人”或“老板”。这些称谓都是按他(或她,以下省略)现在从事的职业来称呼的,而与其原来的户籍身份无关。如果按照这个称谓逻辑,农民离开农村,从事非农产业,也应该按照他从事的职业来称呼。事实上,有些农民离开农村,从事其他工作后,也确实是按照他后来从事的职业来称呼的。例如,有的农民参军入伍了,被称为“军人”,没有被称为“农民军”;有的从事教育工作,被称为“教师”,没有被称为“农民教师”;有的被正式招工,当了工人,被称为“工人”,也没有被称为“农民工”。那些自主离开农村、进入工矿企事业单位务工的农民,按照这一逻辑推理下去,也应被称为“工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把他们称为“农民工”。这成为“农民工”话语建构的开始,并由此展开了对“农民工”话语建构的过程。可以说,话语建构在“农民工”这一概念的形成和使用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过程符合制度设定的需要,特别是与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已经实行了50多年,在此期间,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差别(尤其是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变得非常清晰,并且在社会成员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农民工”概念广泛使用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在于人们“骨子里”强烈的工农差别意识。在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这无疑是话语构建的语言的“温和的暴力”(the gentle violence)。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问题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24](P287)“农民工”一词的高频率和长时间使用,实质上就是这种语言的“温和的暴力”的不断演练。被贴上标签的“农民工”成为愚昧无知、落后肮脏的符号象征,成为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鄙视和欺凌的“另类”社会群体。这使一种语言的“温和的暴力”转变成了一种温和的社会暴力,通过一种并不激烈和看似并没有强制性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迫使这一群体不得不接受话语标识赋予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不断重复和反复操练的“农民工”话语使这一群体成为语言“温和的暴力”的牺牲品,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定格他们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这一话语不但强化了其他社会群体把农民工视为边缘群体的观念,从而影响到针对该群体的资源分配和社会政策,进一步稳固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话语过程也强化了“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社会边缘化意识,使得该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自身同样认同这种话语,成为语言的“温和的暴力”下的“顺民”,并往往把自己的命运归咎于自己的出身,或者命运的安排,从而自觉接受这种现实,在其他社会群体面前存在强烈的自卑心理,甚至是自惭形秽。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接受了“农民工”话语强加给他们的身份标签,他们就会更加自觉接受并服从社会对他们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安排。这样,又造成了罗伯特·K·默顿所说的那种“自我实现预言”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民工”陷入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陷阱,导致他们真正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或者边缘群体。
四、社会合意:“农民工”概念的社会合法化
一般意义上的合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就一定事项作出一致的意思表示。一般来说,合意是一个私法上的概念,其所隐含的前提是合意双方当事人必须地位平等,合意的对象应当是私法中的事项。意大利学者鲁伊吉·拉布鲁纳(Liugi Labruna)追溯了合意的历史,认为:“合意(consenso)不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契约法的基础。人们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罗马人的法律中,寻觅到合意主义的诸渊源。该诸渊源孕育了作为债的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完全协商一致。”[25](P360)他认为,合意是债的基础,他说:“如果没有合意,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意愿的碰撞,就不会产生契约之债,因而也就不会抽象地产生法律关系构成的资格方式。”[26](P362)随着公、私法融合趋势的加强,原本泾渭分明的公、私法中特有的一些原则和制度,也逐渐延伸至对方领域,成为公、私法上共有的原则和制度,同时,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合意中蕴涵着丰富的平等、自由、协商、合作、信用的精神,有助于社会经济关系、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关系的正常孕育和发展,合意对促进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国家各项政策和方针的顺利执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社会中所有人意志的合意就是社会合意。①社会合意与卢梭提出的公意并不完全相同。卢梭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以及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见卢梭:《社会契约论》,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同时对政治权威加以限制。卢梭认为,公意不是由某一个人指定的,而是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讨论和投票形成的,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为了使公意能成为真正的公意,卢梭认为必须使每个公民都带着自己的愿望作为个人加入投票。人们在服从通过“公意”制定的法律时,等于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卢梭还对公意与众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公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更明确地说,社会合意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因维护共同利益经相互协商而达成的对社会事务及其相互关系相近或者相同的看法。社会合意与自然人意志不同。自然人意志是指自然人所持有的一种心理现象,是自然人基于理性和思考,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而社会合意不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不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总和,也不是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社会成员遵循特定程序经过协商而对公共利益所达成的合力意志,是一种公共利益的需求均衡。[27](P108)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合意不是个体理性的最大化,而是集体理性的最大化。
社会合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一致性。社会合意意味着社会成员对某一事务或问题有大致相近或相同的看法。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一致性必须经过一定的比较和鉴别才能体现出来,社会合意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利益磨合和权衡而达成的一致。第二,均衡性。均衡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是指博弈达到的一种相对稳定或平衡的状态,没有哪一方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社会合意一旦达成,就意味着社会成员所选择的策略达成了均衡,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或平衡的状态,任一社会成员在这一问题上都难以做出其他的策略选择。第三,权威性。权威可以使众多独立社会成员的行动保持有秩序的状态,或者被协调起来在合作中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对权威的接受,不是通过武力等暴力威胁进行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教育、传承、劝导等方式使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成员自愿接受。社会合意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依靠社会成员公认的威望和影响而形成较强的支配力量,从而具有权威性,并形成一定的强制力。
当前,对“农民工”概念的社会合意通过制度设定和话语建构已经形成。皮埃尔·布迪厄认为:“任何一种权力都要行使符号暴力,即都力图强加各种意义,通过掩盖那些作为自身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促进人们将这些意义都视为合法之物。”[28](P291)由于户籍制度形成的工农差别意识在社会成员中根深蒂固,加上对“农民工”概念的话语建构,于是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并不觉得有不妥之处。这种不假思索的随意使用,一方面表明“农民工”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人们难以摆脱的话语定势,人们在潜意识中已经将“农民工”群体看做是既不同于农村人也不同于城里人的一个特殊群体;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已经成了话语温和暴力的俘虏,接受了“农民工”话语的合法性,从而不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经常性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来不断强化和捍卫这种合法性,使“农民工”这一概念进一步合法化。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概念,事实上也加入了这一概念的合法化过程。
值得重视的是,对“农民工”概念的社会合意实质上形成了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夺。“农民工”概念反映出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是农民,因为他们是农业户口而不是非农业户口,但他们的职业又不同于农民,他们相当长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城镇,从而构成中国社会一个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样,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夹缝中,似乎产生出由流动人口②流动人口包括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和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中国有流动人口约为2.2亿人。其中,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他们是流动人口的主体。不过,“农民工”还包括一些“离土不离乡”的人,也就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非流动人口。所组成的第三元社会,由此,中国社会结构又似乎变成了一种三元社会结构。这样一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强大惯性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在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中,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处于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之间的边缘社会。①徐明华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二元结构不但没有弱化,反而有强化的趋势,而且产生了以城市农民工为第三元的三元社会结构,从而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参见徐明华、盛世豪、白小虎:《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载《经济学家》,2003(6)。张忠法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发达地区的城乡内部,由于外来农民工和当地居民在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上的较大差别,已经产生较明显的新的二元结构现象。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课题组:《我国走出城乡二元结构战略研究(上)——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工及城镇化有关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6(69)。三元社会结构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受到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目前很难通过单纯的市场力量予以解决。[29]
在这种三元社会结构之下,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实际上受到双重排斥:一是乡村社会的排斥,二是城市社会的排斥,他们在事实上成为一个被严重剥夺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在某一城镇之中,但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又没有获得当地城镇的认可,尽管他们已经进入城镇居住、工作和生活,但是没有被纳入流入地城镇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体系中,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等方面都很难享受到与流入地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并且他们与流入地户籍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存在很大问题,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他们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生活之外。徐勇认为,中国农民创造了“中国奇迹”,农民勤劳、节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等理性的扩张创造了“中国奇迹”。[30]毋宁说,这一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牺牲“农民工”利益来实现的。而正是因为牺牲“农民工”利益换得了整个社会巨大的收益,并使其他社会群体成为一定的受益者,也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概念的社会合意。
五、结语
“农民工”这一概念当前处于制度设定、话语建构、社会合意的漩涡效应过程之中。由于户籍制度设定的先赋身份是对农民不公平的预先规定,农民在社会生活的起点上就是不公平的,他们难以摆脱农业户籍的束缚,即使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身份仍然是农民,被隔离在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之外,无法有效地在流入地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对“农民工”的话语建构形成了一种温和的话语暴力,使“农民工”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任一社会群体都会无意识地使用这一话语,从而固化了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农民工”概念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具备了普遍的社会合法性,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合意。由此,对“农民工”概念的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三者之间相互强化,并形成具有内聚力的漩涡效应,导致这一概念的活力不断增强,并难以被质疑和消解。
因此,要消除“农民工”概念,可以通过变革相关的制度设置,消解对“农民工”概念的话语建构和消除其社会合意来实现。应当明确,表面上力量很强、高速运转的这种漩涡效应,只要打碎其中的任一环节,它就会停止,因为,作为一种不合理的东西,它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并非完全是坚不可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带有偏见和歧视性的概念必然成为历史。
[1]吴忠民:《应当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称谓》,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05-20。
[2]贺汉魂、皮修平:《“农民工”:一个不宜再提的概念》,载《农村经济》,2005(5)。
[3]厉有为:《关于农民工的话题》,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03-04。
[4]李永海:《应尽快淡出“农民工”称谓》,载《中国工运》,2005(8)。
[5]汪勇:《“农民工”称谓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11)。
[6]叶育登、胡记芳:《“农民工”称谓对民工认同状况的影响》,载《浙江学刊》,2009(1)。
[7][8]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10]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in Sven Steinmo et al.(eds.).Structuring Politics:H 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 parative Analysis.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1][12]Peter A.Hall,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 s”.http://www.mpifg.de/pu/mpifg-dp/dp96-6.pdf.
[13][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载《人民日报》,1958-01-10。
[15]赵耀辉、刘启明:《中国城乡迁移的历史研究:1949—1985》,载《中国人口科学》,1997(2)。
[16]熊光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7]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载《社会》,2010(2)。
[18][19]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0]No 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21]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1)。
[22][23]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4][28]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5][26]鲁伊吉·拉布鲁纳:《单纯合意即形成债:论罗马债法中的合意主义——从历史的足迹到中国债法之引人注目的演进》,载杨振山、桑德罗·斯奇巴尼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7]王蓉:《环境法总论——社会法与公法共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9]徐明华、盛世豪、白小虎:《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载《经济学家》,2003(6)。
[30]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