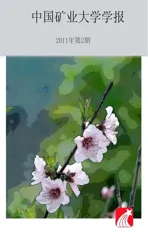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
2011-02-09郑国友
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
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回到官场生活世界和人的本身,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展开了对官场人物的灵魂探寻和生命叩问。在其对官场充满生活气息的叙述中,凸显着的是一个有着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立场,以及在现代性焦虑中发出的对官场现实的质问和对官场文化的质询。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艺术创造,开辟的是当代官场小说精神重建的努力方向。
现代性焦虑;日常生活;王跃文;官场小说;美学价值
对于官场小说的评价,似乎早有定论:“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1]这句话,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如果仅从“官场伎俩”的题材角度敷衍成篇,则无论创作手法还是艺术效果,都将了无新意。而对研究者而言,跳出传统研究模式的窠臼,用新的理论话语来阐释图书市场日益火爆的官场小说创作现象,以厘清其审美类型和辨析其艺术质地,进而导引官场小说创作步入活跃多元的艺术轨道,则显得尤为必要。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热潮中,王跃文无疑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创作者。其作品具有着独特的艺术韵味和美学价值。王跃文的创作选择的似乎是一个远在官场之外的民间话语姿态,将笔触深入到纷繁的官场日常生活之中,以充满生活气息的叙述逼真地呈现了官场中人的精神状态和灵魂处境,表达出其对官场文化精神生态的现代性焦虑。其创作拓宽了官场小说的思维和表现空间,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官场文学构造体。
一、官场日常生活的建构和日常生活审美化
将王跃文及其作品放置到中国文学的历史流程中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小说带有鲜明的“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写实小说”将文学的镜头对准“日常生活”,书写小人物的“一地鸡毛”,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学创作趋势。这种新的文学创作趋势很快就被生成、转化成了“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一种文学优势。在这种趋势和优势中,“底层叙事”和“日常生活审美”似乎成为了一种美学潮流而引人关注。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契合了这种美学潮流,在官场这个“老掉牙”的题材域地里,打破官场小说创作的狭窄局面,将视点下移,在绵实的写实情节和细节中,以精确的笔力,展现出作者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深度把握和寓言式的思考,其作品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对官场进行日常生活化的叙事构成了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文学景观。“对官场生活的演绎成了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基本线索。通过扩充生活化的场景如官员的接待宴饮、日常社交、家庭婚姻甚至婚外情等官员日常生活含量,生成了王跃文官场小说对日常生活表达的结构性框架,这可以说是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2]
在王跃文的官场书写中,严肃的政治庙堂被生活化的场景所取代,生活化的语言毕显出政治话语的空洞和虚假。可以这样说,王跃文用其文字为我们营造的是一个具有浓郁现代都市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世界。王跃文巧妙地改写了“主旋律”官场题材小说将官场置于政治上层的书写方式,而是以人性化视角、人文关怀的眼光,在将官场进行生活化的言说中,完成了在官场之外透视官场、批判官场文化的崭新创作路径,掘开了一个敞亮官场现实和文化根基的别一通道。正如有评论者在评价王跃文的《国画》时有言:“作者是有意把人物命运的整体变化,心灵的的深层搏斗和时代的普遍风尚,通过对日常生活、庸常琐事的从容叙述来加以表现,这就使作品具备了艺术表象世俗化和充分生活化的品格。”[3]
王跃文独特的艺术创造能力体现在其文字回到了鲜活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对官场生活化的表述中揭示出官场生存文化逻辑的荒诞和可怕之处。在王跃文作品中,家庭生活、人际日常交往、婚恋及婚外情生活、宴饮游乐等官场中人的日常生活都成了王跃文官场小说叙述的重心。如在《国画》中,官员朱怀镜与艺术家李明溪的交往便很精到地传达了作为一名文人型官员朱怀镜,其精神结构中人文理性与官场规则的游离又冲撞的状态。在王跃文的许多作品中,如《国画》、《天气不好》、《蜗牛》、《无头无尾的故事》、《苍黄》等,夫妻间讨论的问题甚至性生活问题都与权利话语纠结在一起。温情的夫妻性生活成为了作者大篇幅言说的内容,但这种言说基本摒除了当今文学倍受人诟病的欲望化叙述动机,显现的是王跃文在对官场日常生活的蕴含与结构的把握中真切地触摸到了官场生态并生成了官场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在这方面,王跃文的新作《苍黄》很能说明问题。李济运与妻子舒瑾关于“哑床”的夫妻性暗语,竟然与宣传部长朱芝的职业责任——将乌柚县摆弄成一架大哑床这样的官场生态取得了联系。于是,诙谐化解了庄重、世俗驱散了神圣,严肃的政治命题与荒诞的官场文化便在个人日常言说的角落里找到了其存在的文化的根基和归宿。这显然又涉及到了王跃文官场小说对官场日常生活叙述的另一创作路径,即回到人本身的问题。
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必然要回到人的本身,以此探明“生活”的意义,并从生活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解释文学。回到人的本身,是王跃文关注人、关怀人,特别是关注和关怀官场人性异化这一重要问题而确立的审美站位和选择的审美创作路径。其小说给我们描绘的人物群像大多没有具体的轮廓、清晰的容貌、身材、打扮,他们都是官场中一些平常的人物,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王跃文似乎抛弃了传统道德评判体系,在他的小说中我们无法辨别出什么是好人坏人,但作家都赋予了他们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不分职位高低,不论人生长短,一律不顾一切地朝着仕途狂奔。在王跃文官场小说中,领导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色、一个动作,都会在这些人物的心里掀起轩然大波。他们似乎都或轻或重得了精神病。多疑、紧张、敏感似乎是这种“官场综合症”的典型症状。王跃文官场小说提供的官场独特的人物画廊,已经在符号化、典型化的层面,以小说人物规模化、群体化的呈现姿势,“集束”式“爆炸”性地直指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症结之所在。可以这样说,人物行为的重复模式在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成为了一种官场日常生活观照的方式。在对权利“拜物教”似的崇拜意念之下和权利意志覆盖一切的强势功能面前,官场日常生活受传统、习俗、经验、教训、规则等方面的积累和规训,甚至在官场的耳濡目染示范、模仿最终被样式化,显现出官场日常生活自在的文化因素。而官场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与传统文化的惰性、保守性达到了契合。于是,官场日常生活成了官场劣质文化、官场潜规则、官场不正之风、官场腐败和官场黑幕的寄生之所、栖息之地。透过王跃文用文字描摹出的官场模态,我们可以发现,模式化和重复性的官场日常生活为官场亚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寓所,而官场亚文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了官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自在性。这使我们触摸到了中国官场令人气闷窒息的精神气候:一方面,政治文明建设是如此的迫切而重要;一方面是官场亚文化大行其道而且越来越完备。从“政治庙堂”下移到官场日常生活,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视点的位移为我们把脉中国官场文化的精神气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站位。
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回到人的本身,使王跃文官场小说获得了生活的质感和话语的张力。正如评论家聂茂所指出的:“作品注重官场生态环境,写的大都是八小时之外的日常生活流,司空见惯,却又鞭辟入理,把政治文化的本质和生活中的繁华苍凉、精神之累和世事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颇具惊世、警世和醒世意义。”[4]
二、现代性焦虑与官场日常生活透视
文学即人学,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5]。官场作为一种国家公共权力结构,其权力运作对官场中人的生活、生存和生命无疑会构成巨大的精神渗透。因此,对官场各色人物的生命过程进行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的形象化解释,是官场小说创作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领域,具有极大的创作空间和拓展余地。将日常生活引人官场小说创作,是王跃文惯用的一种创作路径。在这里,他与“新写实”作家一样,从揭示日常生活真相的角度,对官场中人的真实心态和处境进行了描摹和指认。“王跃文显然无意于在宏大的叙事空间里展示官员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或政治权谋。他将笔触沉入到纷繁的官场各色人物特别是官场小人物的生活细节之中。”[6]通过建构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王跃文进而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展开了对官场人物的灵魂探寻和生命叩问。正如王跃文在其博客创作谈中夫子自道:“我的着眼点还是人性,我只是睁着我的眼睛在看,看这些生活在官场的人,古往今来,他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看见的是人性在权力磁场中的变异和缺失;往更深处说,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当然,我也力图写出这种异化的根源。”[4]值得注意的是,王跃文官场小说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勘探是在当代官场生存世相的场域中展开的,以低调冷峻而又微带反讽的笔调,在看似平常的官场生态描摹中,呈现了公共权力对官场中人精神渗透所造成的心灵景观,充溢着对官场人物的理解和关切,透露出对官场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感伤,叙述中表征着的仍然是一个有着责任和担当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现代性焦虑中发出的对官场现实的质问和对官场文化的质询。
西方几百年来的工业社会使人们陷入了技术理性、商品经济、消费社会和工业生产为基本内涵的现代化构想和理想冲动之中。然而,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政治文化积累的国家,同时又是个家园情怀深重的乡土国家。在当下,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以竞争和创新为内核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正被权力组织机构照搬、移植到了我们这个有着强烈政治情结和权力意志,以及崇尚田园牧歌情调的乡土中国,映照着多重文化纠结的文化母体上。正是在这个历史改写和文化转换的时期,中国官场构造机制与现代生产机制急需一个适应性调整。在现代性的召唤之下,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与才近百年的现代工业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摩擦、磨合和整合。然而,工业化大生产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激发人们创造性的同时,文化精神和道德理想的疲弱和滞后使现代性想象危机不断、阻隔重重。官场小说作为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构造体上切分出来的一个粒子或断面,它很容易让我们审察到并进而诊断到中国官场文化的病态、病理。王跃文官场小说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之下,对这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透视。正如王跃文自己所说:“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是我的小说里最悲凉的东西,也是官场人生里最可悲悯的东西。”[4]在《秋风庭院》中,小说的开头写的是地委书记陶凡在自家小院里很惬意地打着太极拳,并对“村野农舍”式的小院进行过细致的描绘。而小说的结尾是退休后的陶凡“终日为这里的环境烦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年老了,本来就有一种飘泊感。这里既不是陶凡的家乡,也不是夫人的家乡。两人偶尔有些乡愁,但几十年工作在外,家乡已没有一寸土可以接纳他们,同家乡的人也已隔膜。思乡起来,那情绪都很抽象,很缥缈。唉,英雄一世,到头来连一块满意的安身之地都找不到了!”《秋风庭院》呈现的这种官员生活和人生,折射的是较为普遍的官场中人的特殊生活方式与生存处境。漫长的官场生涯,不知不觉间将陶凡作为正常人的“人性”慢慢地侵蚀,慢慢地掏空,剩下的只有“官性”。一旦退休,他作为“官”的身份不复存在,人性已被掏空。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昔日田园牧歌般的日常生活世界连同它的安全感和“在家”感的失落,使一大批官员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被切割和被埋葬。人生的诗意消散了,权力成为了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但人都有告别权力的时候,人生的诗意却再也无法找寻到。在《很想潇洒》中,曾经那个崇拜普希金的汪凡步入官场经历了官场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不得不告别诗人气质,“换一种活法”,选择了在官场安身立命,从而也确认了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以丧失主体人格和尊严的方式获得提升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和价值认同。官场中人将官场潜规则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官场习俗,并深深地渗透和贯穿到官场中人的生活流程之中,生成其精神结构和价值选择。现代性理念加速了权力对官场日常生活绑架、渗入,这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聚集到权力场域的中心,越来越密集的介入官场潜规则对日常生活的绑架和规训的具体行动之中。“对官场生活体察的细微和感受的细腻,王跃文打开了官场日常生活的隐秘之门,以其独具特色的官场小说成为了官场内在生活的探寻者和构筑者。”[2]
现代性作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诉求,表征着的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7]。然而,当王跃文用触目惊心的文字呈现出官场样态,裸露出官场人物内心的隐秘,抖露出官场文化的荒诞之处,那种“持续进步、合目的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竟然与现代性的诉求产生了强大的紧张与悖反,这便是王跃文官场小说中裹挟着的一种文本情绪,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焦虑。王跃文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透视,揭示出的是对现代社会中官场中人的精神关切问题。官场权力对人的异化导致了主体的丧失,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是“现代性的社会境况强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8]。王跃文官场小说负载着的这种现代性焦虑,是其文本价值诉求的表意实践。正是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透视,使其小说生成了“重整生活信念的现代使命”[9]。
三、现代性与官场日常生活的精神重建
正如上文所引,文学的职责在于“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解释”。但与此同时,文学更应该给人们提供精神支撑,提供给人们“对付困境的努力”[5],这也是几千年来文学生生不息的理由所在。也就是说,文学应该存在一种价值预设。在这个意义上,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通过对官场生活世界的发现和建构,凝聚成了官场人格的自我生成之域,在现代性的焦虑之下,对官场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变异和官场灵魂的自我拯救作出了文学的文化的甚至是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析。这显然有别于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等为代表的主旋律小说。主旋律官场小说“依然还是停留在以整体主义的方式来宣说本质主义与表象主义,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依然是要把人视为某种‘本体’或‘本质’的模仿者或相似物,因而这些‘宏大叙述’不仅不能真正为人类的存在世界确立终极意义与客观基础,而且事实上已经沦为束缚个人自由的枷锁。”[10]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乌托邦叙事框架,以及青天意识,按照理想主义甚至不无浪漫主义的主题先行法则,按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叙事套路,重述了与革命英雄具有相似精神质素的反腐英雄的革命传奇。在世纪之交这个文化大转型的历史语境中,主旋律官场小说文学想象也就只能是一种精神抚慰和精神麻醉。
但是很显然,在现代性的焦虑之下,王跃文通过官场日常生活的构建和透视,所呈现和表征出来的是一种复杂、纠缠,甚至是悖反的生活多样性和可变性。首先,从时间范畴来看,“现代性”的本质建基于进化论的逻辑之上,但在王跃文铺陈的官场精神症候中,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竟然越来越微妙,越演越有着难以说清的味道,这显然是种悖论。其次,从人物个体发展轨迹来看,在王跃文的小说中,官场小人物趋之若鹜在权力魔棒之下丧失了自我,“以‘个人主体’的神话建构一套有关‘人’的伟大叙事,这曾经是‘现代性’对于人类未来的明丽想象与庄严承诺”,“在社会现代性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却日益显露出一幅颓败而萎缩的‘人’之图景”[11]27。再次,诚如有学者所言,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某些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与西方社会一同进入了人类新的文化困境命题的讨论之中”[12]。因此,“在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中出现了前现代、现代乃至后现代‘同步渗透’的格局”[11]27。官场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文学的使命、价值和意义,在王跃文官场小说文本中遇合、叠加,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和大众人格的现代化,便成为了其价值性表达的重要渠道和着力点。通过上文分析,王跃文官场小说似乎开辟的正是这样一条创作新路。在现代性的焦虑之下,通过构造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回到了日常生活这个丰富的、斑斓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里,在官场日常生活的现场,指认了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等官场‘不成文规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绑架;体认了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处境;进而确认了官场中人生存的悖论和困境,构筑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官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2]王跃文通过这种独特的官场小说创作风格,似乎在探索着官场日常生活精神重建的方向,呼唤着一种现代官场生活的公共伦理。在陶凡、关隐达、朱怀镜等文人型官场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封闭的个体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价值构成已经难以支撑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构架。在《蜗牛》、《天气不好》、《棕红色皮鞋》、《旧约之失》等作品中,王跃文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接受过现代教育观念熏陶的官场“新人类”。他们在初进官场的时候,仍然抱守着“五四”以来自由、民主的价值内容,但官场现实却一再拒绝这种精神立场,他们也由此处处碰壁、仕途不畅,王跃文在小说中为他们吟唱着的是一曲人生的悲歌。在《苍黄》中上演的选举大戏中,我们看到的是民主意义的玷污和荒诞。自此,我们可以发现,王跃文官场小说的价值系统显然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对以伦理道德为中心、以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追求为主导的个体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价值构成在现代社会失落怀着深深惋惜的同时,却又质疑着自“五四”以来带有自由、民主、科学现代质素的价值内容能否为当下官场文化所包容和吸纳。在王跃文用语言符码编织的那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中,王跃文怀着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着的一种现代性焦虑精神质素,似乎在建构着一个形成以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类幸福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建设价值系统,在对“官本位”为核心的官场文化的质询中,呼唤着的是建构以人为本的官场公共伦理秩序;在对“人治”下的官场人性摧残的拷问中,试图以“法治”思想观念推进政治文明的现代化。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郑国友.日常生活现场的指认、体认和确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风格[J].广西社会科学,2010 (9).
[3] 刘起林.官本位生态的世俗化长卷——论《国画》的价值包容度[J].理论与创作,1999(5).
[4] 王跃文.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EB/OL].[2007-01-13]. 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 _ 55f402f60100076h.htm l.
[5] 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J].甘肃社会科学, 2002(5).
[6] 郑国友.“心事浩茫连广宇”——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0(5).
[7] 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J].文学评论, 2002(6).
[8]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3.
[9]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53.
[10] 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44.
[11] 唐欣.权力镜像——近二十年官场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 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J].文学评论,2001(3).
Modern Anxiety and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Aesthetic Stance and A rtistic Value of Officialdom Novels by Wang Yuew en
ZHENG Guo-you
(Chinese and History Department,Hunan First No rmal College,Changsha 410205,China)
Wang Yuewen’s officialdom novels have constructed a huge bureaucratic world of life.By returning to official life and the peop le them selves,the officialdom novels by Wang Yuewen exp lore the soul of the officialdom characters and questions the life from the aspectof meaning and value.His full-oflife accounts of officialdom highlight a responsible realistic novelist’s reflection and aesthetic stance,the question of the officialdom reality w hich is uttered in modern anxiety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officialdom culture.The unique artistic creation in Wang Yuewen’s officialdom novels directs the spiritual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empo rary officialdom novels.
modern anxiety;everyday life;Wang Yuewen;officialdom novel;aesthetic value
I247.59
A
1009-105X(2011)02-0114-05
2010-12-24
2011-04-0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YS10S01)
郑国友(1974-),男,文学硕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