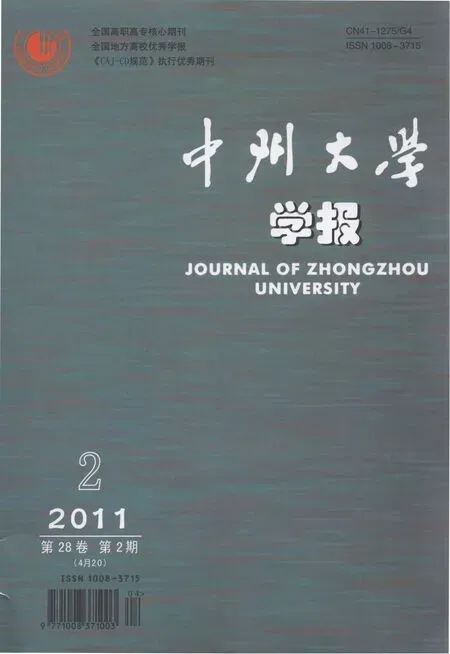界在有无缥缈间——评鲁枢元的《文学的跨界研究》
2011-02-09李红英
李红英
(河南师范大学人事处,河南新乡453000)
鲁枢元先生三卷本的《文学的跨界研究》新近出版,这应是他三十年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结晶。《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三本书,可以看作他学术生命之树上生发的三根枝桠,至今仍显露着勃勃生机。
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一个突出的关键词就是“跨学科”。早就有学者论述,“跨学科研究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实现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当今国内外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而鲁枢元则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文学跨学科研究意义并长期进行理论实践的学者,并且明确将其上升到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高度上。从文艺心理学研究到文学言语学探讨,从精神生态追问到生态文艺学建构,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贯穿了鲁枢元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而且在文艺学学科建构的开创性努力中,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追求。回顾三十年的跨学科研究,鲁枢元先生却认为不是“跨越”,而是“攀爬”,“不同的学科就像两座山头,别人或许可以轻轻一跃就可以‘跨’过去;而我却往往先要一步步从这边的山头爬下谷底,再慢慢一步步‘爬’上对面的另一座山头。”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鲁枢元先生的自谦,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理论探索的轨迹。从山头“爬”下谷底,是他探索的起点,因为“谷底”恰恰是不同学科的交汇之处,因而也具备了更多的创新与生成的可能性。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这些跨学科、富有原创精神的研究便是他由谷底攀爬所取得的硕果。或许正是由于立于“谷底”,而非占据“山头”,由边缘学科开始探索,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总是显得与当时“主流思想”不很协调,于是,学界对他的学术观点不断有商榷、争鸣乃至批判的声音。然而,先后出版的《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等专著作为他三十年中由谷底向不同山头攀爬所取得的硕果,却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乃至引领了中国文艺学的走向。
至于鲁枢元先生的跨学科研究是如何发生的?他本人至今都语焉不详,只是说“我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最初确是在‘无界’的心态下展开的。”然而,这“无界”不正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吗?学术本无界,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灵,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的知识也具有统一性,所谓的学科界限只是人为划分的,是近代工业社会才出现的,并且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王元化先生就曾论到:“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后来分化为独立的学科,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可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的学科彼此隔绝开来,形成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外强调各种边缘科学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我认为,这种在科研方法上的保守状态是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各个方面都陷于停滞难以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鲁枢元先生由于是在“文革”中度过大学生活的,恰恰缺乏了这种科研方法的训练和严格的学科意识,因此也少了许多学科戒律的束缚。在他看来,学科与学科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面,但它并非冰冷坚硬的壁垒,并非不可跨越的鸿沟,而应是可以自由漫步的“谷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界”的心态,他才能够做到“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的自由跨越;也正是由于这种“无界”,他才会在“不自觉”、“下意识”的状态下进入“跨学科”的研究。“无界”状态下的“跨越”不仅是自由的、下意识的,更是自然的、合情合理的。
“如果说‘学科’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就不会永远是一道森严壁垒的围墙,随着对于现代性的质疑,随着后现代思潮的逼近,那些根深蒂固的学科成见也该变通一下了吧。”
“世界知识的统一性、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使文艺学的跨学科成为一种必然——尽管跨越的方式可以有种种不同。”
在鲁枢元先生看来,跨学科的前提不在充足的知识储备而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性情,在于观念的转变。原来,“有界”抑或“无界”与个体的生命状态、个人的性情密切相关。可以看出,鲁枢元先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文字风格还是思想内容都比别人多了一份对自由的追求。他正是以“一条裸露的生命”、“一颗神往的心”漫步在这片文学与其他学科交织的“迷谷”,实现着生命对于自由的诉求。我觉得,这种“无界”实际上就是生命原初的自由状态,是人的自然天性,也是自然本应拥有的状态。谈到跨学科研究的体会时,他说自己像一个玩积木的孩子,在拼接的过程中有时会豁然开朗地进入另一个境界,并自诩为“读杂书,开天眼”,天眼一开,界限全无;天眼一开,异径突现。玩积木的喜悦我们体会过,“无界”的心态我们也有过,但一直葆有这份“无界”的心态却是难得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天性被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遮蔽了,我们自己也被人类自设的一些界限束缚住了。
虽然是“无界”,但是很显然,鲁枢元先生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漫无目的,而是有一个中心和立足点,所有的跨越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那就是对于文学的个体心灵以及文学的诗意空间的坚守,时代背景的转换、知识空间的拓展,他对文学那份赤诚的热爱与热烈的憧憬始终不渝。南帆先生将其形象地喻为“跨越的圆心与半径”,跨越的半径在不断地延伸,而立足的圆心却坚定不移。
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鲁枢元先生十分清楚人文学科在当下社会的地位与处境,“遗憾的是这三条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粗细不一,工业生产与资本运营的逻辑使得自然科学越来越坚挺,使得社会科学越来越庞大,而不能完全纳入这一逻辑的人文学科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萎缩。人文学科要想改变自身的危困,只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向‘科学’靠拢,向‘市场’屈膝。”而且他在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始终警惕了这种失去自我的“靠拢”。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逐渐活跃,跨学科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引起理论上的自觉,中国文学跨学科研究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鲜明的特点就是向新兴的自然科学借取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概念挪用到人文学科的文学中来。对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的信仰代替了人类精神的一切其他保护物。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来研究文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鲁枢元先生却不以此为然,1985年在厦门会议上,他说:“很难用定量的方法研究文学,不要把一切都交给科学,应该给人留一点东西。”
时代更迭,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精神、个体心灵以及诗意空间的坚守,始终不渝地怀揣着对文学那份纯真的热爱与虔诚的憧憬。三个阶段的跨越,始终渗透着他真诚的人文关怀,彰显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与守护。三个阶段的跨越,立足于文学,涉足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始终都在探索与回答人类精神与心灵方面的诸多问题,因而,一次次跨越,一次次转向,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更是对文学精神的一种坚守。文学是什么?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是一个‘自足的文本’,一种‘叙述的方式’,文学还是良心,是同情,是关爱,是真诚,是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的眼泪,你的笑容,就是你的不着边际的想象、不切实际的憧憬。”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界汹涌的是一种庸俗化、机械化了的文学观,文学作品被降格为平面镜中的映像,是现实生活的机械复制,文学艺术由精神的天空沦落为实用政治的泥淖。鲁枢元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在他看来,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个体性以及文学作品的心灵性、内向性是理解文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他的研究从心理学意义上纠正了“机械反映论”的偏颇,突破了过去那种禁锢文艺生命的“工具论”、“服务论”、“从属论”。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的心灵学,因而文学也回归到它本真的状态。
就鲁枢元先生本人所说,进入文学言语学的研究是出于“防守自卫”的心理,当时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向“主体论”展开猛烈攻势。结构主义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即使隐藏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经验,也都是结构的作用所致。”经过这样一番釜底抽薪的论证,主体终于被非人的语言结构吞噬了。“批评家对于语言的精确处理显然隐含了对于科学技术的臣服。”鲁枢元先生显然意识到了结构主义所隐含的这种危险,他提醒人们,结构主义的后果将是“结构长存,人已经死掉”,这是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取消人文精神。他的文学言语学研究就是对结构主义的应战,更是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坚守。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非文学性的质疑入手,到对汉语言的诗性资质的揭示落脚,鲁枢元把他的文学言语观表达得十分明确,这就是文学言语的研究应该紧贴艺术创造的审美特性,倾向“人文化”,而不是应该远离艺术的本质所在,走向“科学化”。正是为了切近文学艺术的特性,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鲜明对比,鲁枢元在阐述自己的文学言语观时,刻意突出了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化性”和“流变性”。他其实是在反对结构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文学,反对科学的理性思维对文学过多的介入,反对科学的理智之网对文学的“简化”。向语言学领域的跨越,完成了他对“文学言语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建构,却也使他的理论更加切近了文学艺术的特性,从而实现了他对文学主旨的坚守,或许跨越的目的本身就在于坚守,对人文性、心灵性、精神性的坚守,对文学阵地的坚守。
文学研究如今面临着比以往要复杂得多的环境,文学艺术还没来得及从伸张主体的亢奋中走出就迅速落入资本逻辑和市场原则的无情挤压之中。物质的日渐丰富与精神的日益贫乏、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此时,文学又应当何为?“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类精神是一致的,拯救的一线希望在于让诗意重归大地。”在鲁枢元先生看来,拯救的根本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在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和解中寻求解脱之路。如何解决自然与精神的双重危机,鲁枢元先生寻得的路径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艺术精神、诗意境界和审美体验去拯救人类精神的疾患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也就是让文学艺术在拯救之途中同时获得自救。站在生态、精神、文艺的交叉点上,鲁枢元先生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和鲜明的跨学科路向,在对文学艺术与审美拯救职能的思考中展开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构。很显然,这带有浓郁的审美乌托邦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思考也受到多方质疑。生态文艺学的审美理想能够承担得起拯救现实的重任吗?这样的理论体系是否缺少了干预当下现实的力度?如果不涉及国家、民族、经济、资本、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竞争这些炙手可热的社会历史概念,生态批评能够意识到对手的强大?也有人对他那充满危机意识、饱含理想和激情的话语中流露出的悲观消极的情绪提出了批判。然而,文学毕竟只是文学,相对于强大的科技与管理,文学显得那么柔弱、虚飘、幽微、苍老,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也只能是一种“柔弱的制衡作用”。面对现实的危机,忧虑、理想、激情、诗意、审美甚至还包括那些带有某种悲观色彩的希望,除了这些,文学还能够提供什么?文学也只能提供如此柔弱的拯救方式了,然而鲁枢元先生却从没有放弃对这种柔弱方式的信心,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柔弱也有可能胜于刚强。人文知识分子在怎样的层面上介入现实,鲁枢元先生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否则,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很有可能再次落入向科学技术臣服的圈套,也有可能重新落入政治话语的窠臼中去。如何保持文学在回归自身与面向现实之间、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独立与介入现实之间的适当张力?可以说,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文艺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尝试。
在几乎无意识的状态下进入神秘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后来又矢志于“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言语学”的学科建设,从一开始的“无意识”跨越,到后来“有意识”的学科建设,鲁枢元先生距离原先的思想起点已经走出了很远,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不断的思索跋涉、追求自由的天性都促使他要实现对自我的进一步超越。
从事“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鲁枢元先生也曾争取过这些学科的独立性。在这些学科逐渐建构完善时,他对自己的文学跨学科研究却由懵懂跨入、努力实践、全面认同的阶段转向反躬自问、再度反思、犹疑彷徨,对于“学科”开始由执着转向质疑。一门学科就是一个‘笼子’,如何才能重新获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鲁枢元先生对跨学科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学科的跨界研究,不只是某些知识领域、理论范式的交叉融合,也不单是为了催促更多学科的生成,那同时也是对某些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跨越,对某些权力话语方式的跨越。当然,那首先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观念模式、治学心态、写作模式的跨越。学科跨界不是改建一个更大一些的‘笼子’,而是要打开一片广阔的未知的天地。”
学科的跨越起源于原本的“无界”状态,经历学科壁垒森严的阶段,必然还要打破一个个“牢笼”,重新回归“无界”的自然状态。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这是一个经过否定之否定向着更高阶段的螺旋式发展,而非简单的回复,这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无”,它既经历学科的分立又超越了壁垒森严的学科分工。人类知识的发展,由无界限的状态到界限分明的专业分工,再到超越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的意义和出路何在?仅仅是促生更多的新的学科吗?仅仅是建制更大一些的“笼子”吗?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他做出了比别人更深入、更彻底的思考和回答。
跨学科的发展尚不能最终解决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学科的发展注定了要进一步超越学科。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阶段?反者道之动,或许它近似于学科前、原生态的阶段,复归于婴儿,怀着对世界真理的好奇,面对各种问题,返回到一种浑然的、本真的“思”的状态。
学科的跨越起源于原本的“无界”状态,经历学科壁垒森严的阶段,必然还要打破一个个“牢笼”,重新回归“无界”的自然状态。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这是一个向着人类认识无限境界的永无休止的探寻。“上穷碧落下黄泉”,文学艺术学科的跨界研究也许正在精神天空的有无缥缈间。
[1]代讯.跨学科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创新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07(1).
[2]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三卷本[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3]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J].社会科学战线,1983(4).
[4]鲁枢元.略论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J].人文杂志,2004(2).
[5]贺立华.厦门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综述[J].文史哲,1985(4).
[6]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南帆.超越的本义[J].上海文论,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