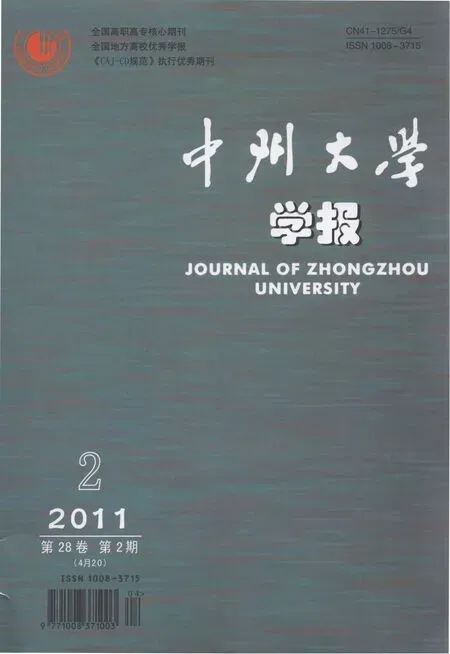欲望叙事·伪欲望叙事·叙事伦理——从电视剧《蜗居》说起
2011-02-09伍茂国
伍茂国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0)
作为一部社会剧,《蜗居》在2009年的热播和热议应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电视剧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囊括了当下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话题:房子、小三、腐败等等。受众轻轻松松就能找到情感或情绪共鸣的因素。但稍微细心一点,看似散点透视的题材之下涌动着的仍旧是焦点透视的格局,即聚焦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那就是“房事”:高房价之下买不起房子的房事以及初涉世事的女大学生与人情练达的贪官之间的那一点“房事”。一般大众的兴奋点集中在前一个房事:一日三变的房价让小老百姓们委实憋着一口怨气、怒气、窝心气,一旦从公共媒介中看见自己的典型生活,那种反观自身的命运所得到的强烈刺激,是其他虽然轰轰烈烈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或好莱坞大片般的连续剧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曾经万人空巷的《渴望》异曲同工。而第二个“房事”以暧昧的叙事调子挑逗着所谓80后哥哥妹妹们那潮起潮落的代际幽怨,引发无数控诉或同情。正因如此,《蜗居》被许多普通受众,也被不少职业评论家称为近年来难得的针砭现实的电视剧代表作,是“刺进现实的一根刺”,[1]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复兴”。[2]但也有些评论家不以为然,甚至视之为故意暴露社会阴暗面,有碍和谐社会建设大局。更有意味的是,北京电视台还迫于房地产商的压力而停播了该剧。其实,无论那种观点都是《蜗居》操作成功的体现。电视剧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消遣艺术,而在消遣之外能激起一点点有意义的讨论来,那当然是电视本身所孕育的社会意义的佐证。确实,从《蜗居》之中,我们看到了高房价和腐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其中的伦理危机。房子不仅让海萍夫妇失去了本来的纯洁,也使渴望人生美好远景的海藻陷入传统语境无法接受的人伦大忌。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正确的审题”无法透视《蜗居》真正可怕的危机:那就是欲望叙事的能指狂欢与对伪欲望的伦理首肯,这才是当代电视叙事伦理的“红色警戒”。
一、现实讲述及其背后的欲望
《蜗居》极尽能事叙述现实并且呈现其背后的欲望。《蜗居》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姐姐海萍。海萍与苏淳夫妇毕业于江城的名牌大学,却蜗居在10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攒够首付,变身房奴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另一条是妹妹海藻。海藻和男友小贝与人合租一套三居室。他们也是只等攒够首付就谈婚论嫁。这两条线索紧扣“房事”现实,并且经由叙事把这一现实所生发的空前焦虑展示得淋漓尽致。正是基于这种焦虑,才勾连起另一个令人侧目的现实主题:官场腐败。具体到电视叙事中则是宋思明与海藻的情欲纠葛,这构成“房事”的另一层含义。
尽管叙事框架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让成熟的(或职业的)受众自觉到电视剧的虚构性质,因而可以避免直接的现实对比。但同样无法回避的是,由于《蜗居》题材选择有意对时代敏感话题强烈触电,尤其是抓住了相当多的“真实细节”,因而仿佛构成了对当下现实的复叙事,这就造成绝大多数的受众无法区分虚构世界的复叙事与现实理性世界的原生叙事,所以面对虚构世界中底层人们的“艰难世事”和贪官与奸商狼狈为奸的种种镜像时,《蜗居》的虚构元素自行瓦解,并且暴晒在现实的广场上,原本深藏不露的“人类的欲望逻辑与乔装打扮的社会逻辑”[3]直接撞击观众的眼球,这种撞击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不费吹灰之力就激起了观众对于电视叙事逻辑所生成欲望的敏感反应:物欲、情欲和支配欲。
《蜗居》为房子而活着的海萍们(白领),其人生理想无非就是打拼、赚钱、住别墅、成为人上人,而伴随着房价的一步步高涨,欲望也如暴雨般倾泻而下。从整个电视叙事看,与其说,海萍们是为了满足“居者有其所”的基本欲望,毋宁说,房子无形中已经成为对金钱、对物质疯狂追逐的表征。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里,受众清晰地看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巴尔扎克所描述的19世纪巴黎物欲横流的景观复制:金钱成为人们的上帝,“……运转社会的枢纽是金钱,或勿宁说是缺乏金钱,渴望金钱。”[4]看看被“房事”左右着的海萍们,那曾经神圣而纯洁的爱情变成了什么:“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别尽玩儿虚的,你爱这个女人,第一个要给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肉体,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让女人不必担心未来;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拥有不了男人的时候,心失落了,身体还有着落。”而宋思明一句似乎玩深沉的话:“通往精神的路很多,物质是其中的一种”,则一览无余地告诉人们,就连精神也从价值蜕变为沉甸甸的使用价值,可以说物欲已经无孔不入。
情欲是《蜗居》着力渲染的另一欲望。原本以“房奴”和“反腐”等现实话题为切入点的电视剧,在开篇不久就严重跑偏,重心变为海藻为达目的甘心做二奶的故事。其中,巫山云雨的镜头和诸如“我是来×你的”之类的“色情”台词层见叠出,让整个叙事浸润在情欲中不可超拔。所以在许多受众眼里,所谓“蜗居”,实为“蜗在居室里”干的“那点事儿”。
与物欲及情欲纠缠不清的则是第三种欲望:支配欲。支配既表现为对物的支配,也表现对情的支配。《蜗居》中所有为房子而活着的人们说到底无非想在大都市江城拥有、支配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常理说,这一要求并不过分,但当拥有房子的欲望变身为“据为己有”的偏执心理时,作为物的房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居住功能,而抽象为空洞的“支配”对象。电视剧放肆渲染的宋思明与海藻的所谓“情欲”,也不过是居于强势地位的宋实现、满足自己对于作为“他者”的海藻的占有、支配欲望。因此,无论物欲、情欲抑或支配欲根本上是一体的,都是变革时代释放的欲望总体的变形金刚。所以,《蜗居》已从表面的现实主义转换为充满吊诡的欲望叙事。
二、从欲望叙事到伪欲望叙事
欲望是什么?迄今人言人殊。但五花八门的看法中,认为欲望是匮乏的满足则是最大众化同时也是最古老的观点(有据可查的历史在西方最远可以上溯到柏拉图)。以这种观点看来,欲望是一种主体匮乏和被动存在的实体,一旦匮乏填满,欲望便得以满足。从哲学探究看,这一普泛性的欲望观在黑格尔手里得以认真思考。黑格尔认为对立着的自我意识和生命都是欲望,只不过前者是差别性统一,而后者则是统一本身。“当下欲望的对象即是生命”而“生命乃是自身发展着的、消解其发展过程的、并且在这种运动中简单地保持着自身的整体。”同样“自我意识就是欲望”,[5]“但是在自我意识的这种满足里,它经验到它的对象的独立性。欲望和由欲望的满足而达到的自己本身的确信是以对象的存在为条件的,因为对自己确信是通过扬弃对方才达到的;为了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在。”“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5]显然,黑格尔已经悄悄地切除了欲望的实体性尾巴,指认了欲望的他者化。
拉康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欲望空无说。他把欲望(desire)与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加以区分。需要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匮乏,属于具体的、可满足的生物性欲求。而要求表征着“从具象的需要到非具象的欲望的一个中间环节。”[6]即离开了原初的需要的想象化,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欲求。如果说,需要自然性地表征人与物的关系,指向对象,那么要求“就是用语言这个骗人的东西表达出来的需要。”[6]它不再直接指向对象,从而成为一种主体间关系,主体间即意味着他者,而象征性语言构成文化的大写他者。欲望在整体的要求和个体需要的缝隙中成长,换言之,欲望总是寻求需要和要求无法达成的整体性。但欲望的这种努力在拉康看来也是劳而无功,无法臻至最后满足,因为在他的哲学语境中,从弗洛伊德主义出发的、作为人的本真性存在依据的欲望(愿望)不再具有合法性,人的欲望总是虚假的,真实的需要和要求经过层层异化,欲望变为一种无意识的“伪我要”。按照拉康的观点,“个人主体的欲望从镜像异化以后不再是主体本己的东西,特别是在进入象征域之后,在能指链的座架之下,我的欲望永远是他者的欲望之欲望。”[6]归根结底,欲望总是虚假和变动不居的。
从拉康对欲望的别具一格的哲学分析可以看出,电视剧《蜗居》欲望叙事正试图把现实的需要经由要求转化为非具象的欲望,欲望成为欲望的能指链,从而追索人类欲望空无化的本体境界。
《蜗居》通过叙事表征欲望空无最明显但又不太好理解的当然是海萍们的“房事”,也就是对房子的需要。按照一般社会看法,在中国这样安土重迁的文化语境中,拥有自己的房子几乎是所有老百姓最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经过媒体的不断放大,骤然凸显,并衍化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的焦点。所以,否认海萍们的“房事”欲望的真实性,视之为空无,显然是故意的“找抽”行为。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反省叙事背后的欲望逻辑,这种看似铁板钉钉的真实性还是会露出可疑的尾巴。
海萍对房子需要的迫切性来自孩子。有一天女儿冉冉(六六的同名小说中是一个男孩,叫欢欢)从海萍的钱包中偷取硬币到门外骑电动马,当问及孩子如何处罚时,冉冉歪头想了想,回答说:“妈妈抱抱吧!”此时海萍愣住了,呆住了,怔住了,心如刀绞。海萍要处罚她,她选择抱抱。孩子已经懂事了。他知道谁是她的亲人,她只跟那些与她日夜在一起生活的人交流情感。而妈妈,什么是妈妈?妈妈就是电话那头的“喂”,妈妈就是每年来两个星期的女人,妈妈就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我为什么要一个孩子?我要她,难道就为了有一天,她想起我的时候,甚至想不起来模样吗?难道就为了有一天给她一套房子吗?难道就为了别离吗?”这样拷问过后,海萍蓦地决定:“回去就买房子!马上买!我要和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所以,这种欲望有着真真切切的现实基础。难怪一提起《蜗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房子的事,而且一致认为电视剧一针见血地触痛了扭曲变形的房市的神经。但海萍对房子的欲望没有那么真实和简单。房子远不是隔离海萍与孩子的罪魁祸首。她和苏淳完全可以租住一间大房子以解决暂时困难,为什么一定要买了房子才能担负一个妈妈的责任呢?所以我在想,电视叙事虽然为海萍找到了一个似乎很符合观众心理的理由——母爱,但母爱对于房子只是微不足道的由头,因为房子的压力是自己找的。正如海萍和苏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意识到的,他们可以回到家乡,回到有房子的地方。但海萍觉得自己家乡太小,什么都没有,没有高高的电视塔,没有麦当劳,没有伊势丹,什么都没有。所以关键的不在房子,关键在房子所表征的现代性欲望,即城市这个“近似于语言的一项最可宝贵的集体发明”,[7]在现代性视域中,像语言一样成为以“磁体-容器”为隐喻的大写他者。城市“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这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个证据,这同乡村那种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7]城市不仅像容器一样装载海萍们这样的人群和她们所需要的器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像磁体一样充盈着海萍们欲望着的欲望。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当看新房的时候,海萍的手机里出现“江苏移动欢迎您”的短信,姐妹俩所发出的无奈的笑,因此具有了尽管虚假然而逼真的形而上意义:一种对于欲望空无的无奈。
《蜗居》欲望空无的另一吊诡的叙事可以用一个问题提出,即宋思明何以要以海藻为欲望对象。对此电视剧中有几处交代。原因一,作为官场潜规则,没有小三会被看作另类,无法融入官场。对于深谙官场三昧的宋思明来说,这无疑是其与海藻生发“房事”的重要动机。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一动机并非充分理由,它最多只能说明宋思明的欲望对象的不确定性,他可以选择海藻,也可以选择其他女孩,何况海藻还是那么普通的一个女孩呢?因此第二个原因应运而生。宋思明第一次占有海藻之后,发现海藻还是处女,按照世俗理解(也可以称为人类学依据吧),宋思明的处女情结使得海藻成为他的欲望对象。但电视叙事在接下去不远的地方却含蓄地点破那一点点让宋思明心旌神摇的处女之血不过是海藻月经提前的结果。所以,这第二个原因实际上叙事用十分世故的噱头把欲望对象的本质悬搁了。但电视剧又不经意地交代了第三个似乎更有力的理由:海藻酷似宋思明大学时代的梦中情人白逸纯(六六的同名小说中叫程惠)。这个理由很容易迷惑人,电视剧的一处旁白也似乎刻意强调这一看似美好实则媚俗的理由:
宋思明心里充溢着一种熟悉的,曾经有过的冲动,像毛头小伙儿一样热血沸腾。这些日子,从见到海藻的第一天起,他的眼前总是那个普通的小姑娘。她是那么的普通,谈不上姿色,清汤挂面的头发,不施粉黛。可不知道为什么,是哪里,是哪一种神态,竟如此打动宋思明的心。也许就是那种无时无刻,都可以钻进自己的童话世界梦游的神情,还有那简单像句号一样的眼睛,宋思明可以看见那双善良的明眸后,有一天会有晶莹剔透、温润湿热的泪水流出,只为他流。
然而这真是宋思明欲望着海藻的原因吗?或者说,由此可以确认海藻真的成为宋思明的实质的欲望对象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继续分析。
宋思明出身农家,靠着弟弟让出来的读书机会考上了大学,与父亲为大学教授且聪明漂亮的白逸纯相比,显然名不当户不对,所以应当可以假设即便宋喜欢白逸纯也不敢表白,最多只能使其成为梦中情人。叙事过程中,白逸纯虽然作为实体的欲望不在场,但却永远成了宋思明的欲望着的欲望。电视剧有一个情节安排,我以为很诡秘,那就是让白逸纯红颜薄命,这一安排隐喻着宋思明对白逸纯的欲望的空无性,同时也无意识地断绝了宋思明在具备了支配欲望能力之后对白的欲望实现。这进一步提示我们,根本上宋思明对海藻的占有、支配并非爱情使然,而是对不能实现的欲望替换。有人可能会说,宋思明对海藻怀着的孩子不是充满着关心、爱护吗?难道这还不是爱情的体现吗?然而事实表明,这不过是编剧和导演明着误导或忽悠观众,在潜意识里海藻的孩子也是欲望的替换,这种替换就像海藻对白逸纯的替换一样永远不可能成功,孩子最终流产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本来,如果沿着这样的欲望叙事逻辑,《蜗居》在叙事艺术上可以突破一般社会剧的局限,臻至更加深刻的艺术境界。但令人遗憾的是,拉康意义上欲望空无的本体化并未真正成为叙事者的价值偏爱,正如分析所揭示的,它最多只是显现了欲望叙事的某些症候,叙事者真正专注的仍然是客体小a的欲望剩余——笔者称之为“伪欲望”。
客体小a是拉康欲望理论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即小写的他者,指主体的对象。如果说大写他者A是象征性语言,那么小写他者a则是非言语的,是一种不能称为欲望的零碎的东西。欲望没有这种东西不行,因为客体小a是主体欲望走向本体的过渡。没有小a欲望无从谈起,但反过来,欲望的最终结果要以抛弃小a为代价。“这个时刻是主体意识完全觉醒的时刻,也是主体以死亡为代价建构自身的时刻。”[8]然而《蜗居》伪欲望叙事展示的却没有到达主体意识觉醒时刻,也没有主体悲剧性的死亡意识,反而沉醉于客体小a位置的欲望剩余之中不可自拔。
这种伪欲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像花边新闻或社会新闻一样固然能够迅速吸引受众的眼球,获得较高的收视率,但危机也随之而来。著名艺术评论家贾磊磊教授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断言这样的伪欲望叙事“吸毒式的快感麻痹了人的进取精神”,“动摇了公民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信念”,“摧毁了人们奋斗进取的精神支柱”,是“电视剧误导观众的致命毒药”。[9]但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蜗居》将叙事伦理追求的现代性语境的欲望叙事阉割为基于妻子玉帛满足的伪欲望叙事,也就是将本体降格为实体,将欲望降低为客体小a,降低为零碎欲望。这实际上暴露了当下审美文化的叙事伦理六神无主,而其表征的现实人心秩序或精神生态也是乱象丛生,亟待疗救。
三、结语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欲望并非洪水猛兽,“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已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0](这里的“激情、热情”有的直接译为“情欲”)也就是说,欲望本身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过,“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0]当代许多打着欲望叙事旗帜的叙事文本,其中的欲望正是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的欲望,因而从欲望叙事变成了伪欲望叙事。而这种伪欲望叙事迄今为止不仅未能得到有效反思,反而遍地开花,蔚为壮观。我们的叙事艺术正遭遇着空前的叙事伦理危机。
虽然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与现实理性伦理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经由叙述者的价值偏爱而构建的虚构伦理会在与受众的互动中对现实伦理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卢卡契论及歌德奠定了把艺术陶冶功能推广为一般艺术的哲学基础时,曾很恰当地解释说:“如果人与自然对象及其组合的视觉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社会与自然界物质交换的反映的有关论述——那么在它的艺术映象所唤起的效果中,会产生具有道德特征的震撼作用。”[11]确实,“故事之蛇可以吞掉自己的尾巴,但对故事的模仿并未就此终止。”[12]由于叙事引导,受众对以《蜗居》为代表的虚构世界欲望人物的伦理同情正以无法逆料的方式和速度泛滥开来,为当下本已“贱贱”(《蜗居》有一句经典台词:“我贱贱地贱贱地爱上你”)的现实欲望更加鸡零狗碎化提供了不应有的美学支持。
[1]肖复兴.《蜗居》是指向现实问题的一根刺[J].学习时报,2009-12-07(9).
[2]张宏.从《蜗居》看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意义[J].经济管理文摘,2009(24).
[3]李勇.电视叙事的特征[J].当代电视,2003(12).
[4][丹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M].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03.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0-121.
[6]张一兵.伪“我要”:他者欲望的欲望:拉康哲学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5(3).
[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41-46.
[8]刘玲.拉康欲望理论阐释[J].学术论坛,2008(5).
[9]贾磊磊.问题作品的消极快感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心理裂变[J].艺术百家,2010(2).
[10][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6-51.
[11][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二卷[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87.
[12][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M].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