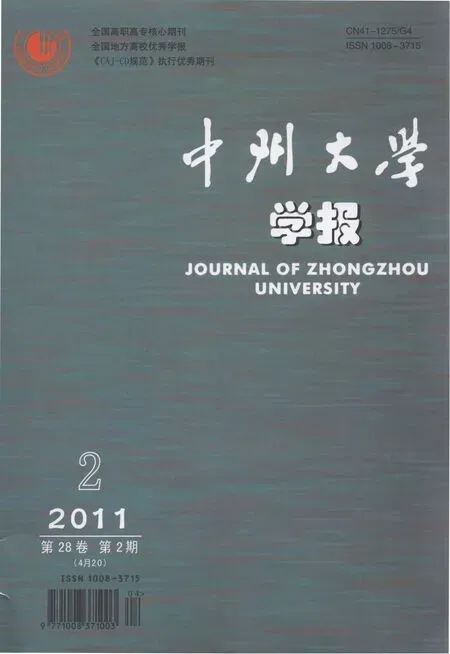口号背后的话语逻辑——对文革文学中“走资派”话语的一种考察
2011-02-09刘宏志
刘宏志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一
文革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政治斗争最为严重的时期,与之相适应,在文革文学中,政治斗争也比比皆是。文革中形色各异的政治斗争背后的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化理念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当时中国实际展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也多是以反对“走资派”为号召的,这样的城市政治现实表现不可能在文学中缺席。事实上,在文革文学中,政治斗争最为集中的关键点就是对“走资派”的斗争。出版于1975年的短篇小说集《盛大的节日》共收录了15篇短篇小说,这15篇小说都是反映文革时期的城市政治生活的,在这15篇小时候中,除了《苗子》、《闪亮的路轨》更加强调的是对“革命下一代”培养的这样一个政治任务外(其中《苗子》也涉及了反对“走资派”的斗争),其他13篇的斗争中心都是反对“走资派”。[1]1973年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是一个包含了小说、散文、文艺理论的文集,里面收集的9篇小说中,5篇是以文革时期的城市斗争为中心来书写的,这其中有4篇都是以反对“走资派”作为了小说矛盾的中心,只有小说《胸怀》表达的是对“革命下一代”培养的这样一个政治主题。[2]这两个文学集子只是当时众多文学作品的一个代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对“走资派”这样一个主题在文革文学中显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不夸张地说,反对“走资派”这样的一个斗争是文革文学中城市政治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反对“走资派”成为文学中的城市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的时候,事实上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怎么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或者说,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的政治行为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他们的行为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事实上,仔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文学中城市政治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指向。刘沪生的短篇小说《冲不垮的防波堤》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海边的装卸队的故事。小说是围绕王海林和李明东的矛盾展开的。装卸五队队长王海林是造反派出身,但是,他做了队长之后,特别强调多装卸吨位,为此还展开劳动竞赛,结果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工人只注重吨位,而忽略安全以及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的现象,差点酿成事故。李明东也是造反派出身,他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没有像王海林那样走向了修正主义路线,而是严守路线,和王海林进行斗争,最后使王海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这个小说中,王海林走向了危险的修正主义,小说中通过叙述既往的“走资派”的行为,实际指出,王海林当下的行为已经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为了对“走资派”做出更为犀利、明晰的批判,小说用一张工人写的批判王海林的大字报点出了所谓“走资派”的行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过去了,但这不等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装卸五队为了抢吨位而不顾国际影响,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突出事件。这件事,正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臭了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又在某些领导的头脑里作祟。现在,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余毒的潮水已经涨上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码头,危及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过来的胜利成果,严重影响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执行……[3]80
通过这个小说,以及上面所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已经被做了一个明确的限定,就是强调利益至上。社会主义不是不讲利益,而是首先讲政治,然后才是利益。当然,在小说叙事中,利益至上是受到批判的。事实上,在这样的分析定位的背后,有一个价值预设:只要强调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就是资本主义,就是错误的;只有强调政治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才是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这样,在对“走资派”的经济利益至上的发展路线进行批判的时候,其批判的指向实际已经点明:“走资派”的经济利益至上的发展路线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是西方路线,从而最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
如果说上述小说中的走资派还有错误的经济路线需要批判,并且利用这个错误的经济路线把“走资派”和西方联系起来的话,有些小说则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更明确地指向西方。《白浪湾》这个小说就不涉及什么经济路线,而围绕是否依靠西方的先进技术展开了斗争。局计划办公室副主任陶守文不相信中国的技术,主张等从西方进口的一艘打桩船来了之后再开工,而以船长柳钧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则强调毛主席强调的自力更生才是正确的工作方向,主张利用自己的技术打桩,不能等待、依靠西方。小说最后指出,陶守文所依靠的西方进口的打桩船由于资本家的有意刁难,无法正常工作,反而是柳钧他们自力更生搞的打桩船完成了打桩任务。小说通过陶守文的自我检讨,明晰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我又走了错道,是工人同志们和事实教育了我,把我从错误中又一次拉了回来!回顾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广大工人群众也批判过我头脑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对我的触动并不大。可以说,在我脑海深处这种流毒并没有肃清,因此一有时机,它就沉渣泛起,危害革命事业……”[4]353在这样的小说叙事中,西方只有一个西方,西方是不可以分为科技的西方和政治的西方等不同的范畴的,所以,虽然西方科技的确比较先进,但是它是隶属于西方的政治的,所以,迷信西方的科技事实上就是向西方政治投降。在这个小说中,陶守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相信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成为检讨、被教育的对象。陶守文这个没有任何经济路线,而只是由于迷信西方科技而成为走资派的过程其实非常鲜明地显示了对当时所谓的“走资派”的认定和价值指向:只要和西方接近或者没有敌视西方的人都是“走资派”。所以,“走资派”一词,与其说是一个对要实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批判,毋宁说实际表明了中国的反西方立场。对此,刘小枫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修辞表明,‘党内资产阶级’并无‘阶级’一词所具有的经济资产的意蕴,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理性的政治符号或隐喻。它无疑具有党内斗争的工具性意蕴,但这一意涵属于毛的论述的第一层表意结构。我们要探究的第二层表意结构,实际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在我看来,作为毛‘主义’论述之术词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意指结构定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民族性比较。……毛‘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论述具有现代性含义,即反资本主义是反‘西方’的隐喻性修辞。”[5]换言之,充斥于文革文学中的对“走资派”的斗争,其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而是借助对“走资派”的批判,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反西方的立场。
二
文革文学中的激烈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对“走资派”的斗争展开的,但是,小说叙事也都显示,“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支持者。革命的造反派为了能够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还要不时地和“走资派”以及其支持者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造反派们要革命,要抓生产,“走资派”及其支持者则是高举经济利益至上或明或暗地破坏造反派们的革命行为。这样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文革文学中政治斗争的激烈性。在这个斗争中,值得考察的是“走资派”及其支持者们的身份——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人物——他们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就曾经担任过伪职,相反,造反派都是普通工人出身。显然,这也是文革时期血统论的一种表达,只有无产阶级工人才是最革命的人。而在这些小说叙事中,非常有意味的是“走资派”及其支持者们往往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别于普通工人的特殊性要求,从这个意义讲,文革小说表现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批判就有了公平诉求的意味。
文革小说中的“走资派”及其支持者形象塑造有着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以几个小说中的人物为例来认识这种形象:《浪尖上的闪电》中的走资派站长的支持者是引水员戴林,小说先描述了戴林的形象。这人年纪约莫五十出头,一身白的穿戴,上身是件白纺绸衫,下身是条白哔叽短裤,脚上是一双白网眼皮鞋,白色的高筒袜子一直套到脚弯里,唯独鼻梁上驾着一副宽边的太阳眼镜是黑颜色的。他脚跷二郎腿独自坐在靠窗口的一张单人皮沙发上,悠闲地吸着烟,两眼望着窗外的景色,一直没有作声。后面又介绍了此人以往的作为,组织过“神仙会”,下面的注释对“神仙会”做了解释:就是几个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定期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碰头会。[6]7-15《骏马奔腾》中的陈国君是这样出场的,这个人穿着一身粗呢中山装,胸前围着一条白围裙,头上用条白毛巾从头顶一直包到脖子,上面又加了一顶呢帽子,这些穿戴似乎还不够,脸上又戴了一个大口罩,露在外面的就只有那两只骨碌碌转的黑眼珠。此人一出场,就给人不舒服的感觉,接着,小说介绍了此人的问题:这个人原来是车站的一个技术“权威”,过去曾在苏修学过几年铁路管理方法,回来后把苏修的那一套全部照搬到沪江站来,什么“局长休息室”、“特殊旅客休息室”,搞得富丽堂皇,锦上添花,而普通旅客候车室却一再缩小,甚至连受旅客欢迎的母子候车室也给砍掉了。他的这一套却得到铁路局一个走资派的赏识,把他从四级工程师一下子提升为一级工程师。[7]238
戴林和陈国君都是“走资派”的忠实的支持者,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是受到了“走资派”的赏识的,那么,从小说对他们的形象的刻画以及他们行为的描述上,我们其实可以窥见文革中的怨恨情绪的表达。从形象上来说,无论是戴林还是陈国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便是从形象塑造上,小说已经暗示了这些人是不会和工人阶级同心同德的。当然,他们的行为更值得玩味,戴林是组织“神仙会”,当然,注释已经表明,所谓“神仙会”,其实就是几个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吃喝玩乐的碰头会,在全国物质比较困乏的年代,还有人能够集体吃喝玩乐,这显然已经隐含了一种不公,一种小圈子的特权的存在。而陈国君的做法则更加醒目,他直接改革车站,把在车站等车这个行动由原来的全民平等改为按照身份差异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小说叙事对陈国君的改革车站是不满的,而且小说也交待,正是陈国君的这些行为导致他被打倒,那么,我们考察陈国君在车站的改革会发现,其改革的实质是凸显了身份的差异,换言之,在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陈国君强调了社会特权阶层的特权。戴林和陈国君都是“走资派”的支持者,他们的行为都是受到了“走资派”们的支持的,而戴林和陈国君之类支持“走资派”的人的一个共性就是强调特殊性,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待遇要求上和普通工人阶级的不同。而在小说叙事中,戴林、陈国君们之所以对抗无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行为,其价值诉求也就是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这种特殊性地位,他们还借助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工人阶级进行压制,如《浪尖上的闪电》,戴林等人为了占有引水员的特权,就取消了工人出身的引水员李明春的引水员资格,甚至在小说最后,当引水员程耿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对一个两万吨以上的船只的危险的引水后,站长居然还要开除程耿的引水员资格。这种对特殊权力身份的垄断最后是直接服务于其各方面的利益的,在小说《踏着晨光》中就表现了这一点,清洁工出身的造反派于春兴现在是区委常委,拥有了特殊的地位,而因为他有了这特殊的地位,于是,他的儿子就拒绝到清洁站上班,而是要求到无线电厂上班,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爸爸有这个权力。小说通过于春兴的回忆点出,前任的“走资派”总支书记李根生就曾经滥用职权,挖社会主义墙角,并且因此受到了批判。[8]通过小说对“走资派”及其支持者们形象、行为的刻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为实际是在吁求获得一种特权地位,这是一种社会不公,他们的行为自然就受到了造反派的批判。从这个意义而言,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批判显然就有了怨恨情绪表达的意味。
事实上,从文革小说中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冲突掩盖下的另外一层矛盾。在此类小说中,受到批判的“走资派”和其支持者其实就是原来的领导阶层和附属领导阶层的知识分子,而批判者、造反者往往就是原来的普通工人,而造反者对于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也多指向其特权的滥用。这其实暗示了造反派对于“走资派”的批判更多的是对其特权的不满而非意识形态的剧烈对抗。这种状况的形成显然和新中国的政党伦理有关。所谓政党伦理,就是由政党价值理念体系引伸出的党内成员的行为规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导性的政党伦理就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念,按照当时的话语方式,就是谁越“红”,谁就越符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5]400而且,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政党伦理开始和权力、财富的分配密切相关,从而有了社会法权。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已经成为国家伦理,符合政党伦理行为的人都成了国家权力阶层,开始掌控国家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带来社会的不公,事实上,在当时“红”已经带来了社会层面的福利、救济、晋升、加薪等各个方面的分配的不平等。而且,虽然中国强调平等,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平均化的社会,但是,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干部和工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而造成这样差别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治上是否够“红”。换言之,当时中国政党伦理和国家机体中的财富及权力分配的同构,使得“红”色阶层出现,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有攫取“红”的资本(重在政治表现)——他们曾经是因为不够“红”而沦为社会劣势地位的,现在他们可以通过极端的“红”的行为来获取社会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而言,“反‘走资派’的意识形态修辞为不满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表达侵犯性情感和诉诸暴力的报复行为的契机。”[5]386换言之,反对“走资派”,打倒“走资派”在充当反西方的话语符号的同时,还成为了文革时期国内处于社会劣势位置的成员表达政治怨恨,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话语逻辑。上述所引小说中的走资派如戴林、陈国君、站长等人之所以成为“走资派”,成革命群众打倒的对象,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其行为多么的暗合资本主义路线,而是其特权地位的获得和对特权地位的垄断引发了公众的愤怒。这种话语逻辑在文革时期的派性斗争中仍然适用。在描写红卫兵派性斗争的小说《领路人》中,实力较强的红旗兵团为了兼并燎原兵团,就声称对方是“走资派”的保皇派,以此借口对燎原兵团发动攻击。[9]25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打倒走资派”之类的词汇,其实在当时已经成了进行利益争夺时所必须依据的意识形态符号。
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两面实体,这个两面就是能指和所指,他强调语言符号中都存在不可分割的能指和所指。但是,他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必然的理由让我们把那种叫做马的四足动物用“马”这个词来表达,所以,索绪尔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约定俗成关系在起作用。但是,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语的使用,考察“走资派”这个词的所指外延的延伸,我们会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场所,所指其实是可以被超越约定俗成而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有意识地制定的。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要告诉你,生活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按照昆德拉的标准,文革文学显然不能称之为小说,因为这里面有太明晰的政治目的,有太单一的、界限分明的生活。但是,倘若我们能够深入到这些表面简单的小说深处,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表面简单的叙述的背后,深蕴着文革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以及操作规则,这些小说倒是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了生活和政治的复杂性
[1]盛大的节日三结合创作组.盛大的节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刘沪生.冲不垮的防波堤[C]//盛大的节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赵乃炘,刘沪生.白浪湾[C]//盛大的节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6]朱钟华.浪尖上的闪电[C]//盛大的节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7]孙克刚.骏马奔腾[C]//盛大的节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姚克明.踏着晨光[C]//金钟长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9]郑和中.领路人[C]//金钟长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