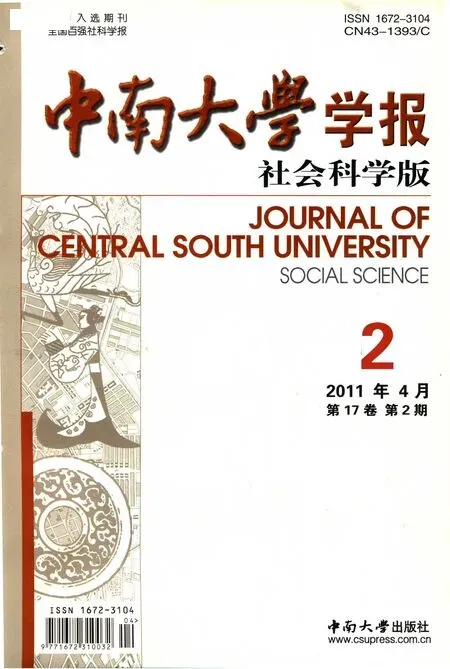堪舆与宋前志怪小说
2011-02-09张辟辟
张辟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堪舆与宋前志怪小说
张辟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堪舆作为一种传统方术文化,以“生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生克为理论基础,杂以八卦、天干、地支等来选择藏风聚气的理想宅地,并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受到了宋前志怪小说作家的重视。作家把它介入志怪小说,使堪舆所积淀的伦理道德观念、趋吉避凶社会心理、“官本位”政治意识以及对山川名胜的堪舆解读融入到生动有趣的故事之中;在叙事上,则使之起到了连缀故事、推进情节、表现人物、渲染气氛、展开细节等多种作用,增添了志怪小说神秘诡异的审美效果。
堪舆;志怪小说;文化意蕴;叙事作用;神秘诡异
古人执著地相信宅地、墓地的形势方位与人事吉凶、命运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感应,他们不是把感应作为偶然的巧合而是天、地、人互相感应的必然体现。命运的不可捉摸性使这种必然性看似为真,受到了志怪小说家的重视,因而志怪小说中常有相宅、相墓之类的“堪舆”叙事。志怪小说中的堪舆叙事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蕴? 堪舆的介入有何叙事作用? 这些问题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试图对此略加探讨。
一、堪舆的大致流变
“堪舆”一词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这里的“堪舆”指雌雄北斗之神,堪代表天干之神,舆代表地支之神,它们的运行合在岁前死,岁后无殃。①它指的应是一种择日术。这一含义亦见于《史记·日者列传》中:“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 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后汉书·王景传》载:“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其中“堪舆”奥旨与《史记》所述者同,仍然属于择日式占的一种。
“堪舆”与相风水直接联系最早出自三国时魏人孟康的解释:“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②而图宅术根据王充《论衡·诘术篇》所引原文推知,③它是以甲子堪舆为神,用五行配五音、五姓推断居宅所宜方位吉凶的一种方术。因它以宅子为研究对象,故被后世纳入风水术。又因以堪舆为雌雄二神,又称堪舆术。如《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初吕才钦遵唐太宗命,对世传风水术书加以刊正时,对当时以五音姓利来定行事吉凶之法,“验于经籍,本无斯说;阴阳诸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按《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说”,说明唐代的堪舆术是承袭图宅术而来,已有了风水的含义,因而后人多以堪舆为风水之最重要的别名。[1]
所以《辞海》说:“堪舆,即‘风水’,迷信术数的一种。指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也指相宅、相墓之法。”[2](1241)《辞源》说:“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3](3404)
具体地说,堪舆起源于先秦的相地行为,《诗经·大雅·公刘》记载周人的祖先公刘率周民来到豳地,从水源的流向和山势来断定豳地是建都的好地方。《尚书·雒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诰》。”可知相宅之事,其源甚古。其后《周礼·大司徒》有“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之说,《汉书·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可见相宅之事在秦汉已日渐盛行。相宅需要占卜,同蓍龟、八卦有关,其哲学基础不外“气”论和阴阳五行。
宅有阴阳,先秦两汉所相可能多是阳宅,至魏晋时代便出现了相阴宅。西晋时期郭璞所撰《葬经》,讲的就是相阴宅。其哲学基础也是传统的“气论”和阴阳五行:“葬者,乘生气也,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4](17−18)郭璞《葬经》对后世影响很大,堪舆界尊之为风水鼻祖。托名黄帝,实出现于唐宋间的《黄帝宅经》又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融入八卦,④将之与人伦道德结合在一起,作为相宅原则。它指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4](3)“凡阳宅,即有阳气抱阴;阴宅,即有阴气抱阳。阴阳之宅,即龙也。”[4](4)
唐宋风水术大抵形成两个派别:一是“形势宗”,一是“理气宗”。前者以注重寻龙、察砂、观水来定穴位,强调山形水态,山情水意;后者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人的命运与宅地方位的相生相克关系,来断定吉凶祸福以确定穴位。两派只是侧重点不同,不能截然分开。到现在,所流行的风水很难辨析归属哪派。总之,“堪舆”即“风水”,它是以“生气”为核心,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和地气流转以及人在其中,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来选择藏风聚气的理想宅地,从而推断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的一种传统方术文化。
气是无形的,它能“随物附形”,但必须依赖有形之物才能显示出形状,也要依赖一定的有形之物才能收聚。山形起伏不定,而龙善变化,又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因而堪舆家就以龙来形容山势,“山之行动,贵有起伏有变换,正象乎龙。故以龙名。”[4](111)把山川河流比附成龙身上的器官:“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4](41)寻龙即寻找生气是堪舆的第一步。寻到“生气”后,围绕着如何聚气、止气、找到气的凝聚之点,又有了堪舆的察砂、观水、定穴。整个堪舆的过程就是寻气、聚气、止气而确定穴的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阴阳五行学说,又有八卦的哲理,把天地人三才统一起来考虑,找寻环山抱水、藏风聚气的理想穴地。经过这样觅到的墓地,定能使父母骸骨乘着生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5](5),与子孙之气相触而应,“使子孙能接收并感应到‘吉气’直接的影响”[6](27),“以死荫生”;宅地则能找到通气采光效果良好的居住环境。
理气宗以三元、九星、五行为基本要素,用“玄空汤卦罗盘”进行操作,使宅的修建年份与坐向的吉凶相趋避,寻找机遇,改善命运。因为它对志怪小说的影响不大,这里不再详述。
宋前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录异传》、《异苑》、《幽明录》、《独异志》、《酉阳杂俎》、《宣室志》、《集异记》、《广异记》、《稽神录》等都有堪舆方面的叙事。堪舆的介入拓展了志怪小说题材,刻画了神秘的风水师艺术形象,由它引起的偶然性事件常用来制造悬念,增添了志怪小说神秘诡异的审美效果,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二、宋前志怪小说中堪舆叙事所隐含的文化意蕴
志怪小说中的堪舆叙事,隐含着风水文化所积淀的伦理道德观念、趋吉避凶社会心理、“官本位”政治意识以及对山川名胜的堪舆解读。
堪舆极其重视伦理道德同宅相吉凶的关系。《发微论·感应篇》云:“谚云‘阴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应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积德为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应之,是所以福其子孙者,心也,而地之吉亦将以符之也。其恶果盈,天必以凶地应之,是所以祸其子孙者,亦本于心也,而地之凶亦将以符之也。”[4](180)宋前志怪小说常极力渲染吉地之获得与遵守传统伦理规范道德的关系,且往往带有因果报应的色彩。例如《幽明录·袁安》讲的是诚信致福的故事:袁安之父亡故时,母亲命他以鸡酒诣卜工,途中,路遇三书生,问袁安何往,袁以实告,三书生自称知道有好葬地,袁即以鸡酒礼之,三书生感其真诚,便指点吉地。云:“当葬此地,世世为贵公。”后袁安果然本人官至司徒,子孙昌盛。[7](36)《幽明录·孙钟》讲的是孝道能获致福地。孙钟以种瓜为业,“少时家贫,与母居,至孝笃性”,后有三人到孙钟家乞瓜,孙钟热情款待,三人感其礼数周备,自暴其司命身份,并为之定墓,说此地将来可出天子,叮嘱他不到百步不能回头。可惜孙钟按耐不住,守信不笃,才走了六十步便回了头,见三人化为白鹤飞去,以致后人虽有孙权称帝,然福禄不永,至第六代孙皓遂归顺晋朝,由国君降为归命侯。[7](37)这些故事显然隐含着借堪舆诱导世人积德,甚至隐含着德行影响王朝政治兴衰的意图。
好风水虽是人之所愿,但当风水与伦理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会有人情愿选择伦理道德而破坏好风水。如《幽明录》所记“折臂三公”的故事: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后相者又云:“此墓尚当出折臂三公。”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7](39)
羊叔子即羊祜,世吏二千石,并以清德闻,都督荆州诸军事时能以德柔服吴人,晋武帝伐吴时因病重举杜预自代,祜死二年后吴灭,晋武帝称其功,《晋书》有传。《幽明录》说其父碰巧葬中了帝王之地,被相士说破。葬中吉地是一般人求之不得之事,羊叔子却自掘墓脉,斩断帝王之气,最后导致儿子夭折,自己也坠马摔成了折臂将军。这一故事的实质就是借堪舆故事表彰羊氏之忠,并借以树之为断绝非分之求的典型。
志怪小说中常有因葬地风水遭到破坏而引起灾祸的故事。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郭谊事[8](204)。郭谊葬兄时凿石为穴,挖到一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壁虎类动物)。肢体首尾毕具,为役者误断,郭氏恶之,请示刘从谏,要求另卜葬别处,从谏不许,郭氏只得勉强安葬此地。后来郭氏竟屡遭灾厄。先是“陷于厕,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口”,后来“刘稹阻兵,谊为其魁,军破枭首,其家无少长悉投死井中”。其后果之凶险令人瞠目结舌。因葬地如此重要,人们总希望通过卜得吉地来趋吉避凶,而志怪小说中也就多有这类趋吉避凶的故事。这类故事通常写堪舆家看到人们遭遇贫困,或遭逢疾病,于是建议人们采取措施,化凶为吉。《搜神记·淳于智》记载堪舆家淳于智看到一个叫鲍瑗的人家多疾病,贫苦,就告诉鲍氏:“君居宅不利,故令君困尔。”并告诉他到市场上去,会遇到一个出售鞭子的人,买下此人的一条新鞭,回来挂在宅东北的桑树上,三年以后就会暴富。[9](36)《搜神记·管辂》说信都令家总是“妇女惊恐,更互疾病”,于是请管辂筮之,管辂指出他的宅地“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浮游,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信都令依照管辂的意见掘墓把骸骨移葬他处,举家遂安。[9](34)这些故事表面上是在宣扬风水的重要、堪舆家的宅心仁厚和堪舆术的神奇诡谲,实际上反映了处于疾病、灾祸中的人们希望趋吉避凶的普遍心态。
志怪小说中的堪舆故事也隐含着非常浓厚的“官本位”政治意识。堪舆家利用这种意识,常常极力渲染葬到了福地便会本人发达、子孙受禄,福乐无疆。志怪小说也喜欢在这一点上推波助澜、添油加醋,来刺激读者的艳羡之心。上面提到的《幽明录·袁安》中袁安得到葬地而五世为公,《幽明录·孙钟》中孙钟得葬地而数代为天子等等,均折射出某种“官本位”政治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初看上去似乎有些迎合庸俗世态,但细细品味却可发现某人或其子孙的发达并非全靠风水,发达者对道德伦理的坚守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讲天命不忘人事,讲宿命不失理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志怪小说的特点。
有些堪舆故事看上去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实际上隐含着借堪舆故事解读某些风景名胜由来的意图,这种解读可增加该景点、名胜的奇诡与异趣,引发游客的联想或回味。如《酉阳杂俎·浑子》讲的就是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于长安西南郊所凿)中有一个叫做“浑子塚”的来由。[8](237)小说中的人物浑子在父亲生前总是违拗父命,其父本想葬在陵屯处,临死之时却矫说要葬于水中,以为浑子会反其言而行。出乎意料的是浑子此时竟幡然悔悟,泣曰:“我今日不可违父命。”遂不改父亲临终之志,葬在昆明池中,于是昆明池中便有了这么一个“浑子塜”。它还征引盛弘之《荆州记》,讲洱水北岸有个“五女墩”的由来:“固城临洱水(在古弘农郡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水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其墓。”又记一与“浑子塜”大同小异的故事以说明阴县水中之石洲的来历:“一女嫁阴县(古属南阳郡,治所在今老河口市傅家寨附近)佷子,子家赀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于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听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塚,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成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至今尚有人乐于在风景点虚构历史或神话故事以增添其旅游文化意蕴,可见这种传统由来已久。
三、志怪小说中堪舆的叙事作用
宋前志怪小说篇幅短小,小说家把堪舆元素引入志怪小说中,依风水的“破”与“立”,形成两种叙事模式。
第一种模式“破”,即以吉地被破坏,产生或本人遭灾或家人受祸的严重后果,令读者叹惋。这类模式注重因果联系,但重心全落在堪舆本身的吉凶上,叙事角色只有堪舆家和受害人,故事未能展开,因而情节往往比较单调,缺乏曲折生动之致。前述《幽明录·折臂三公》说羊祜之父之墓地本有帝王之气,因羊祜自掘断墓,幼子夭折,自己也盘马落地而折臂,叙述简略,殊无跌宕。《稽神录·庐陵彭氏》写堪舆家为彭氏所卜的葬地是“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并叮嘱“深无过九尺”,由于役者掘了丈余而破坏了风水,结果有白鹤自地中飞出,彭氏子孙最高职务便只有县令。[10](3120)《异苑·卷七·戴熙》写占者预测戴熙之墓有王气,被北魏宣武帝元恪派人凿破,有一物纵入江中,导致戴氏后嗣沦胥殆尽,也是叙写前因后果。[11](534)由于这一模式结构比较单一,施展不开,篇幅也往往比较短小。
第二种模式依风水的“立”来确定,多叙述某人选择宅地或葬地时,堪舆预兆所言最终都得以验证。
如堪舆家所言,预兆为凶。这类小说,尽管篇幅短小,作者却竭力昭示堪舆对人命运的决定性作用。有的极力通过预兆的解读,展开细节描写,让读者从中领悟堪舆的真实性。如《朝野佥载·补辑》所记李德林卜葬一事。[12](165)葬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李德林所找寻葬地所处的村名为“五公”,堪舆预兆他们家只能出三公。他认为这是命,于是迁葬其父母至此。葬后其子百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而到了曾孙一代,因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小说中堪舆家没有露面,采用父子对话的形式,详写李德林对堪舆预兆的解读,从“出八公”到实际上“出三公”自悟这个细节以及对命运的感叹,让人感觉到堪舆预兆吉凶的真实性。有的细节看似画蛇添足,仔细琢磨却寄寓深意。如《朝野佥载·补辑》所记一书生过唐郝处俊之墓时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书生所叹在他孙子手上得以应验,紧跟其后。但小说并没有结束,对俊的尸体焚烧后施以藻绘:“发根入脑骨,皮託毛着髑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也。”本是贵相人却在死后不得安宁,就是因为定穴不当。龙是墓穴后面的主山,其间的距离“愈远而愈秀,至近亦须有百步之隔,远则高峰无害,近则不可强于主”,其安葬严重违反了堪舆的原则导致了被其孙斫棺、焚尸的祸患。[13](58075)让人在叹惜声中领略堪舆这一文化的奥秘。有的通过堪舆的受用者对预兆与众不同的心理刻画,来凸显堪舆的灵验。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下》记载王哲掘地得朱书“修此不吉”,[8](204)这里的堪舆用谶纬的形式呈现出来,营造其神秘氛围,与王哲不信其有,反诬为家人偷懒而伪造以致深感厌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其凶兆并不因他的厌恶避而远之,“其年,哲卒”,就在他的身上就得到了显现。
这类小说因为集中某一点来表现堪舆对人命运的影响,读来并不单调乏味,颇具生动性和趣味性。
获得堪舆家的指点,预兆为吉,结果如愿以偿。在这类小说中,主要的叙事角色往往不止一个,作者总要将寻地者之人品、德业、家境等作出较详交待,对堪舆家的相地成功加以具体叙述,对堪舆的吉祥效应要加以点明,力求于志怪之外写出世情人情,于偶然因素中体现必然性,因而往往情节曲折,前后照应,首尾完整,且多夹以细节描写、气氛渲染、对话互动,务求生动、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由于这类故事尽量避免单调,注意变化,故更多小说意味。如《集异记》卷二所载张式故事: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野外,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惟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魇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魇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非择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 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14](60)
这则故事主要的叙事角色有三个:张式、周士龙和村夫。张式是寻地者,士龙自称郭璞之流,是堪舆家,村夫是印证梦境、指明福地所在者。张式幼孤,为人诚挚尚友,冬夜寄居村中仅有一榻,自己籍地拥炉而寝,让朋友据榻而眠,暗示了他得福地的道德原因;士龙虽是堪舆家,能识风水,却须借助张式本人在梦魇中获得神示,也说明堪舆成功须有神灵据德相助;村夫点出“亲家”二字提醒士龙,引导二人到欲求之地,实乃神之代言人。叙事角色的增加使人物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作者对勘地过程的描写融入了人物的言行举止描写、梦魇描写和细节描写,情节曲折而诡异,氛围神秘而谲怪,对话隐微而离奇,生动地写出了本来就带有神秘特性的堪舆过程。最后用“而式累世清贵”寥寥数字点出堪舆效果,使首尾照应,结构完整,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显然,堪舆在故事中充当了展开情节、表现人物、展开细节描写的媒介。
总的说来,堪舆作为志怪小说中的一种元素,有连缀故事、推进情节、表现人物、渲染气氛、展开细节等多种作用。志怪故事的奇异诡秘虽有赖于堪舆本身的神奇莫测特性,但更多的是作者善于运用这一元素来构筑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某一主题或理念,展示志怪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因此之故,像其它方术叙事一样,堪舆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注释
① 许慎云:“堪,天道也。舆,地道也。”(见于《汉书·艺文志》载《堪舆金匮》十四卷)他对“堪舆”的理解就是在此基础上延伸而来的。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2:1769.
② 见于《汉书》卷87颜师古注《汉书·扬雄传》中《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句所引述者。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2:3523.
③ 原文为“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易北向。’”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81、383.
④ 该书相传为黄帝所作,收入《道藏》洞真部众术类薑字号。任继愈、锺肇鹏主编之《道藏提要》(修订本)经考证认为“是书之出,盖在唐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 宋会群. 中国术数文化史[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 辞海[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3] 辞源[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4] 谢路军主编, 郑同点校. 四库全书·术数·葬经[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6.
[5] 周振甫. 周易译注·乾卦文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6] 黄文荣. 郭璞《葬书》中生与死互动理论之研究[D]. 南华大学, 2003.12: 27.
[7] 刘义庆著, 郑晚晴辑注. 幽明录[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8] 段成式著, 方南生点校. 酉阳杂俎[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9] 干宝撰, 汪绍楹校注. 搜神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0] 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1]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第1042册·异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2] 张鷟著, 赵守俨点校. 朝野佥载[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3]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第666卷·堪舆部汇考十六·杨筠松十二杖法[Z]. 成都: 中华书局: 巴蜀书社, 1986.
[14] 薛用撰. 集异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Abstract:Geomancy is a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ng Shu’s culture. At the core of“lively gas”, it is based on changes of Yin and Yang, the cycle of Five Elements, mixed with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eight diagrams, Chinese era etc, so that readers can find ideal houses and tombs avoiding wind and gathering gas as well as propitious omens, threats, disasters and blessing between man and matter. Therefore, the writ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it.Involved in mysterious novels, the writers make it interesting story that the geomancy accumulates ethical concepts,good fortun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official standard”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untains attrac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s together the stories, advances the plot, performs figures, renders the atmosphere, and expands the role of other details, which adds to the mystery of strange novels and mysterious aesthetic effect.
Key Words:geomancy; mysterious novel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role of narrative; mystery
Geomancy and Mysterious Novels Before Song Dynasty
ZHANG Bib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I206.2
A
1672-3104(2011)02−0151−05
2010−10−09;
2011−01−25
张辟辟(1977−),女,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