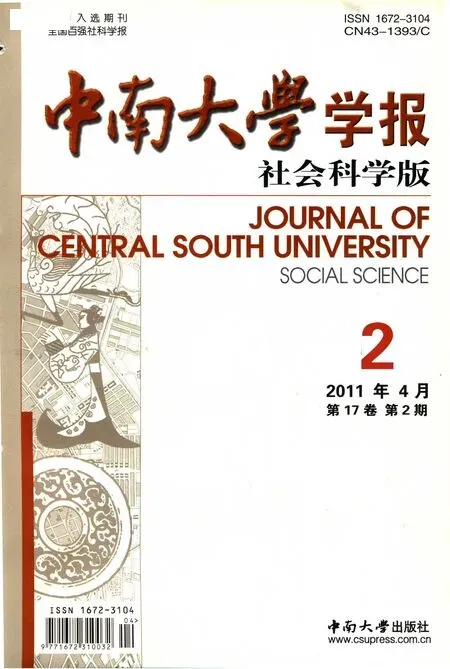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救赎意蕴
2011-02-09朱维
朱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9)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救赎意蕴
朱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9)
通过分析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指出王国维的文艺批评中不但包含“审美超越”品质,更包含“审美救赎”维度。“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的关系具体体现为:“审美超越”是进入“审美救赎”的必要条件,“审美救赎”是审美超越的必由之路。解读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超越”和“救赎”品质,旨在为反思当前文艺学界“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提供一个思考的切入点。
王国维;文学批评 ;审美超越; 审美救赎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有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莉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1](3)
在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电信时代,J.希利斯·米勒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独去研究文学。”[2](138)
伊格尔顿认为,随着原创性思想家离我们渐行渐远,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消失。而亨利希·米勒则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纯粹文学的研究空间又究竟还有多少。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不再,而纯粹的审美文学研究不合时宜,那么所谓的后时代的文学理论究竟何去何从,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面对这一问题,很多文艺学研究者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学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希望从中发现推进文艺学继续繁荣发展的道路。但目前的反思文章往往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分析文艺学六十年乃至百年间的发展,缺少个案研究的有力支撑。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森·阿拉克(Joanthan Arac)参加1996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中国文化研究会议时指出,中国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笼统的概念层面,对个案关注不够。[3](85)因为缺少有力的个案研究,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反思,很多时候都落入宏大叙事的圈套中而缺乏牢固的基础。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中西文艺理论的结晶,代表了中西融合的一种相对成功的尝试,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新纪元。王国维等学人重要的批评思想和批评范式逐渐发展成为文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当代研究者的潜意识中,成为了我们理解现代文艺学的前提。文艺学的反思如果忽视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前提,而只是陷入对马恩经典文本中是否有“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的争论,其反思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相反,我们应该追问: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型是如何完成的? 在文艺理论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什么、发展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抛弃了什么,这才是反思的重点所在。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视关键人物在文艺理论转型过程中所起到“革命性”的作用。所谓关键人物,是指他的文艺思想引领了文艺理论以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限制了文艺理论向其它方向发展的可能。而王国维恰好扮演了转折时刻的拓荒者角色——他不但赋予文学以审美独立性,而且引入了“审美救赎”思想,对当前的文艺学反思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王国维“审美救赎”思想产生的根源
“审美救赎”的前提是“审美超越”。王国维从美的性质、美的功用和美的表现形式三方面论述了美之为美的原因:美悬置功利性,直指人的内心,具有超越性的独特品质。王国维认为只有割断物我之间所包含的利害关系,才能进入“审美超越”的状态:“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也。”[4](18)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原因在于审美主体忘记了物我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怎样一种物我关系呢? 这个问题追问到最后,就是美的性质问题。所以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指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5](1903)“可爱玩”是什么呢?游戏。孩子在游戏中,忘记物我关系中所包含的利害关系,进入虚拟的自由世界,而“不可利用”强化了忘记物我之间利害关系这个观点。
进入审美状态后,审美者将直观到两种不同的美:优美与壮美。“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优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情。”[6](1694)王国维在这里论述了优美和壮美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提到优美和壮美的联系。在《红楼梦评论》中则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4](32)优美与壮美的审美愉悦使人忘记了现实的利害关系,这是王国维一以贯之的观点。到了《人间词话》中,优美和壮美又被镶嵌到了意境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中。“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7](192)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美学,把美分为优美和壮美,并一再坚持优美和壮美的划分,原因在于这种划分体现了美无关功利性,并且具有超越性。
可以看出,“审美超越”是王国维审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的思考只是到此为止,并不追问“审美超越”背后是否别有洞天,那么王国维文艺思想的“审美救赎”的维度就不会浮出历史地表。王国维文艺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面对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他既为文艺的独立性合法性问题提出了学理证明,又为新文艺思想的伦理价值取向进行了论证。先知式的人物注定“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有句话很有启发性:“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8](56)由此,我们必须把王国维的审美思想放到王国维文艺批评的总体性中,才能在王国维“审美超越”思想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寻出“审美救赎”的思想。目前,众多王国维研究者对其“审美超越”思想做出了可贵的研究。但由于不能把这一思想放到一个更大的总体性中,所以王国维的“审美救赎”思想一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审美救赎”思想的产生有如下几大根源。
首先,审美主体忘记物我之间的现实利害关系,进入审美超越状态之后将会产生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为审美救赎准备了必要条件。张法先生认为:“王是超越美学,即美和艺术让人从现实的功利中超越出来,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9](40)王国维高度重视文艺作品对人的心灵的净化作用。从表面上看,王国维的审美思想受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影响,主张审美独立,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从本质上看,由于康德和叔本华是在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明理所当然是孕育康德、叔本华美学的温床。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在笔者看来,就是对善的不断追求。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道出了基督教的精义所在。中国文化的精要之处在于人文关怀,只是王国维反对把政治因素参杂其中,他所理解的道德是更高层次的道德,是对自己灵魂的拷问。
其次,王国维忧郁的性格决定了“审美救赎”思想的产生。王国维生性忧郁,又喜读书,这种性格怎么能让他不喜沉思呢? 而沉思的两极,不是产生怀疑主义,就是相信某种理想。王国维治哲学和文学阶段,虽不排除怀疑主义,但大体而言,他仍是一个理想的追求者,这种理想,笔者名之曰“审美救赎”。
最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具有强烈的改造国民的使命感,这也是“审美救赎”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王国维这一代学人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精神,改造旧社会、树立“新人”是他们不懈的追求。王元化在自我反思时曾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往往成了一代人的悲剧。”[10](348)虽然王国维和王元化并不是同一代学者,但王元化的总结同样适用于王国维,理想主义精神在这两代不同的学人之间具有前后承接性。
二、王国维“审美救赎”思想的具体体现
王国维的“审美救赎”理想是王国维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如下。
首先,王国维的“审美救赎”思想在《红楼梦评论》中萌芽。众所周知,王国维文艺思想与叔本华哲学、美学思想关系密切。“寻找光明一直是美学的理想,可是从叔本华开始的西方美学却异乎寻常地‘爱’上了黑暗。这因为它让人发现的是两个东西:生命的不完整以及生命不完整所带来的为人类所无法承受的苦难。”[11](79)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欲望而已,一个欲望满足,另一个欲望又来。能够满足的欲望少,不能满足的欲望多。即使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还会产生厌倦之情。快乐可除掉欲望和厌倦,但是快乐也是痛苦的一种。“固欲望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4](4)人类脆弱的心灵如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王国维对于中国美学的意义在于,他不但给中国盗来审美自律的火种,即“审美超越”,而且为美学引入了“审美救赎”的维度。王国维认为世界、人生的存在,其实是人类祖先一时犯罪,所以子孙一直要承担这份罪责。从普通道德的角度思考,贾宝玉确实不忠不孝。“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知祖父之谬误,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顾得谓之不孝哉? ”[4](15)贾宝玉认识到了自己的“原罪”,并“忏悔”自己的行为,王国维对贾宝玉如是批评。这给中国文学的超越带来了根基。从此,“审美超越”不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叔本华说:“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活本身之罪。”[12](352)王国维领会了叔本华的意图,并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中国美学界盗来了审美救赎的火种。虽然王国维认为的救赎之路在于出世,而没有意识到必须依靠信仰——一种更大的爱,才能真正的达到解脱,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美学先知,意识到了“原罪”和“忏悔”对于“审美救赎”的重要意义。
其次,王国维“审美救赎”思想在对李后主词的批评中进一步深化。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高度评价了李后主词,并把李后主比作释迦摩尼和基督,可见王国维对李后主词的厚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李后主词本身具有的语言、结构等审美形式要素外,王国维更看重其中的“审美救赎”意蕴,即由对个体在人生面前倍感无奈与渺小的悲悯,上升到对人类在人生面前倍感无奈与渺小的悲悯。“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7](197−198)根据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秀”是王国维对李煜词的总体评价,“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赤子之心” “性情越真”和“后主之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对“神秀”的具体展开,并有层次感。“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赤子之心”和“性情越真”是讲“审美超越”,“后主之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是讲“审美救赎”;“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则是诠释李后主使词由俗变雅。李后主词的雅是有赤子之心的雅,而不是文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雅。那么怎么理解赤子之心呢? 这必须联系下面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李后主是也”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指的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为词人所长处’,就是指类似儿童寻找游戏的、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13](193)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其实是指李后主能以孩童的游戏之心,跳出政治和伦理的束缚,走向审美超越,为其“审美救赎”意识开启了大门。后主词之伟大不但在于审美的超越,更在于它对个人的超越,上升到整个人类的高度,担荷人类的苦难。如果说耶稣是走上十字架,用自己的血去洗净人类的罪恶,那么李后主则是用自己的诗篇感悟人生无常,负荷人类全体之苦难。所以王国维高度评价李后主词背后的原因正是其中蕴含的“审美救赎”意识。
在王国维的文艺批评体系中,“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审美超越”是进入“审美救赎”的必要条件,“审美救赎”是“审美超越”的终极指向,这也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专设一章探讨“《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的原因。许多人认为王国维评论《红楼梦》时,既谈美的超功利性又谈伦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借用亚里士多德和叔本华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所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伦理学上之目的也。叔本华置诗歌于美术之顶点,又置悲剧于诗歌之顶点;而于悲剧中,又特重第三种,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故。故美学上之最终之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4](105−106)王国维的高明之处正在这里!所谓无目的性也是一种目的性。他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体系的创始阶段,能深刻意识到“审美超越”与“审美救赎”之间的内在关系,认识到美与伦理是不可分割的,非常难能可贵。
三、王国维“审美救赎”思想的意义
张法在《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中指出,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代表了中国现代美学初创阶段的三种模式,王国维是超越美学的代表。某种意义上,张法抓住了王国维文艺思想的核心。超越必须有一种价值指向,否则超越便变成为了没有所指的能指。所以张法指出了王国维的超越美学是要净化心灵。可惜由于张先生文章的目的在于比较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所开创的三种美学模式,因此并没有对“净化”一词是否具有“救赎”含义展开讨论。
俞晓红则认为:“从原文的行文也可以看出,王国维从老庄释儒诸家角度切入,作哲学伦理的综合思考,于人生观的诉说中,流动着一种几近宗教情感的元素。”[4](4)同样令人惋惜的是,作者对这种宗教情感元素在王国维文艺思想中如何具体体现同样也没有做出论证,也没有指明“宗教情感元素”究竟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因为张法与俞晓红不能对王国维“审美救赎”思想做出令人信服的证明,而是因为前者关注的并不是王国维文学批评本身,而是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能够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后者关注的是如何理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而没有站在王国维诗学体系的高度去理解《<红楼梦>评论》的深层涵义。因此,本该在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处于本体地位的“审美救赎”思想,只能处于遮蔽的状态。
虽然没有学者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考虑“审美救赎”思想在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与价值,但是敏锐的学者还是捕捉到了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救赎”的气息。
潘知常根据其建构的“生命美学”体系,对王国维的“审美救赎”思想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他认为王国维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中国美学盗来了“灵魂”的火种,使我们认识到:“以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去创造生活的意义。”[14](229)但潘先生没有具体展开论述王国维的“审美救赎”思想。单小曦对王国维审美思想的宗教维度作了具体展开,提出了“审美救赎”的论点,认为王国维的审美思想包括审美超越、审美慰藉和审美救赎三个阶段,[15](10−11)但只是作了相关描述,仍然缺乏深入论证。
综上所述,本文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一方面,尝试从总体上推进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笔者在细读王国维的批评文本的基础上指出,王国维的审美思想是由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两个方面构成,不可分割,审美慰藉其实是审美救赎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指出“审美救赎”在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试图为我们反思“审美意识形态”的论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起点。很长时间以来,“审美意识形态”一直被许多学者看作是文学的本质,然而这一看法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董学文在考证了马恩著作以后,认为后者的著作中没有“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表述,这直接引发了“审美意识形态”说两位代表人物——钱钟文和童庆炳的反驳,其他学者也纷纷参与进来,使得“审美意识形态”说成为学术园地中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审美意识形态”论一直是很多学者和文学理论教材坚持的根本立场,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于审美意识形态之争,笔者认为,我们既要重视马恩经典著作中的论述,又要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从更宏阔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王国维的“审美救赎”思想无疑为目前学界的“审美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1] 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M]. 商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 J.希利斯·米勒著.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 文学评论, 2001, (1): 138.
[3] Jonathan Arac. Post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ty in China: An Agenda for Inquiry,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7, (1): 85.
[4] 俞晓红.《红楼梦评论》笺说.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5] 王国维. 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A]. 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五册)[M]. 台北: 大通书局有限公司, 1976.
[6] 王国维. 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A]. 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五册)[M]. 台北: 大通书局有限公司, 1976.
[7] 况周颐, 王国维.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8]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9] 张法. 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J]. 文艺争鸣, 2008, (1):40.
[10] 王元化.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A]. 陈引池. 学问之道[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1] 潘知常. 王国维——独上高楼[M].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12]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3] 佛雏.《人间词话》三题[A]. 姚柯夫.《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14] 潘知常. 生命美学论稿——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M].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
[15] 单小曦. 王国维早期审美主义思想——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理论的肇始[J]. 社会科学家, 2005, (11): 10−11.
Abstract:By analyzing Wang Guowei’s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is criticism does not only include the idea of transcendence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but also the idea of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whose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the former is the basis of the latter,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former. This article aims a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reconsidering the debates like the “aesthetic ideology”exis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ircle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Wang Guowei;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cendence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The idea of salvation through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in Wang Guowei’s literary criticism
ZHU We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I206.09
A
1672-3104(2011)02−0147−05
2010−07−31;
2011−03−05
朱维(1979−),女,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编辑: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