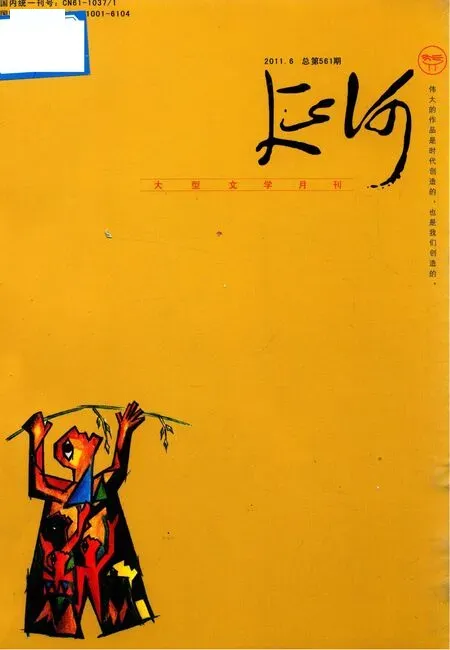胜算在握
2011-01-31李丹萍
李丹萍
事情有些荒唐。人人都说,老公偷情,当老婆的最后知晓。这种事,只要没捉奸在床,当老公的,说不认赃就不认赃。偷情么,既然偷,哪个声张?但何海就声张。而且在外边声张不过瘾了,回家声张到杜晶晶跟前。要不怎么说事情荒唐呢。
杜晶晶不信。
虽然,杜晶晶早就发现何海某些不正常的举止,比如说他动不动就站在洗手间里剪鼻毛,比如他出门前爱往嘴里扔个口香糖。这些讲究,他以前都不曾有过。再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微笑着恍惚起来……这些,傻瓜女人都知道是危险信号,特别是“动不动就微笑着恍惚起来”,可是男人真心爱上女人的标志性表情。这些信号在杜晶晶眼皮子底下发射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作为女人,作为人之妻,她不可能感觉不到。不是感觉不到,是不信,是鄙夷:就他,凭什么!
就是,他何海凭什么?
凭长相?拉倒吧。黑黄肤色,倒八字眉,一口烟熏火燎的碎米牙。身高,满打满算一米七,又胖。这些都不说了,关于男女的定论是:女人爱上男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外在,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男人的能力拿什么衡量?钱呀,事业呀。再歪瓜裂枣的男人,只要有钱,只要事业有成,就性感,就招人。可何海事业有成个屁呀,说起来都丢人。他先在乡下的兽医站上班,才上班不久,因一把手整他,他把一把手打得住了院,他人逃了。避过风头后,他回来了,经人介绍,他们两个陌生男女就闪电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时候杜晶晶的伯父还在市上任着一官半职。由伯父从中斡旋,何海得以重回兽医站,继续当他的兽医。他干了几年,不想干了,腻着杜晶晶的伯父要调走,但因为打领导一事弄得声名狼藉,没单位肯要他。
这么三搞两不弄的,直到杜晶晶伯父退休,他才彻底没了搞头。颓废了好几年,然后开始写小说。偶有作品见报。小豆腐块儿,还是倚着杜晶晶伯父的老脸。何海的伟大理想是当李白。不需太多酝酿,啪嗒,下一个蛋,啪嗒,又下一个蛋。个个是金蛋。杜晶晶心里明镜似的,他做梦呢,这哪是正常人思维呢。作为有着正常思维的杜晶晶,当然不准他脱离实际。她的意思是他就在兽医站干着,忍,只要有耐心,一步一步往前挪,总能等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坑位。急什么?他哪里肯听,把她当拦路虎,恨得武松的劲头都使出来了。到底没牛过他,单位每个月扣去他工资二分之一的钱请来代理替他,他成了有业却自由的撰稿人——幸亏有伯父,不然,他将被直接削为贫民。
乡兽医站的工资,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出它的多少,不要说又被生生削去二分之一。
他自由了。自由就得付出自由的代价,总不能老赖在兽医站写他的小说吧。天底下,没这么一说,就算再有她的伯父,她杜晶晶的脸皮也不能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第一要务:往后住哪走?第二要务:以后怎么个活?
何海气定神闲,他早就思谋好了:办补课学校。只办初三、高三的复习班。
你想,现在的家长多重视孩子的学习啊,复习再读一年的学生家长更是急得眼冒金星。县城一共有三所初中,两所高中,每所学校,每门课,都有一两个硬顶硬的老师,声名远播。好,就盯住他们,雇用他们。要来他们的课程表,仔细研究过,那个老师那堂课有空闲,直接拉来补课学校,上完课,立马送走,绝不耽搁人家正式教学。这么着穿插编网,密而不乱,按节计费,绝对是高效益高报酬。
事实证明,除了极少数几个不肯折腰的外,绝大部分被何海他们看中的老师,都愿意挣这份并不辛苦的意外钱。
杜晶晶依着何海的计,从伯父处借钱买来三辆二手车,雇来三个司机,这三个人专门在几个学校门口守株待兔,下课铃一响,迅速发动车,只见那些平时鹅行的老师便像兔子一样蹿进面包车,车像劫持人质一般,绝尘而去。
由于每个老师在县城里都响当当的,杜晶晶办的高费补课学校,学生爆棚,两口子赚了个盆钵溢出。
这钱挣得容易啊,两口子弹冠相庆。其实,这件事里最关键的人物,不是何海,也不是杜晶晶,而是杜晶晶的伯父。不说借钱给他们,就说没有老人家倚老卖老地在上边活动,各个学校固若金汤的大门怎么会像被施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随意为他们开合?学校校长凭什么允许他们挖这样的墙角?
伯父伯父,像阳光一样照耀大地的伯父。
何海谱大,趴在家里写小说的时候,左手随手捞着卤牛肉,右手随时啤酒侍候,嘴里抽着软中华。进得多,出得少。他整个就是一负数。男人正五正六的都在家乖乖地守着自己的老婆,他一个负数男人,居然偷腥?!——老天要是允许这么干,就太不像话了。
没天理的事,杜晶晶不信。
然而由不得她不信,是何海自己跟她说的。
先是试探着说。
早晨,杜晶晶照例拾掇房子。她讨厌何海乱扔水果皮烟头的恶习,况且烟灰缸垃圾桶就放在他手边身边。跟猪似的,走那拉那,她一边拖地,一边嘟囔。通常情况下,他不吭气,也不改,甚至会当她的面,再扔一个苹果核,以示抗议。但那天,他转过脸,认真地对她说,劝你好好些。你不待见我,自有人待见。杜晶晶听了,呵呵一笑。何海大声说,好!一把拉过她,指给她看他正在看的一封邮件,像是一首诗:
我喜欢牛奶,更喜欢奶牛,
请问,我何时能把奶牛牵回家?
我会把它照顾得溜光水滑,
从而让它产出更优质的牛奶。
看不懂。懒得弄懂。在杜晶晶直起腰欲走之际,何海给她解释,牛奶是指我写的小说,奶牛是说我这个人,她的意思是说,她很喜欢我写的小说,更喜欢我这个人。她想跟我过,好让我这个怀才不遇的作家写出更好的小说。
于是,一个叫上官绛珠的女人,浮出水面。
据何海讲,上官绛珠的父母,双双是大学生,有文化,喜欢读《红楼梦》。为什么给女儿取名叫上官绛珠呢?绛珠,绛珠草之意也,林黛玉的化身是也——你瞅瞅人家的境界。
杜晶晶听来,哑然失笑:绛珠,嗬嗬,犟猪。
杜晶晶对何海的话是这么理解的:比如是一盘子菜,馊了,马上要被倒掉了,菜有危机感,自己吆喝,我好香呀,谁谁谁都想吃我了,人家可是大人物——怎么,你还不宝贝我?杜晶晶懒怠搭理他,她才不着他的套儿,他肚子里装些什么牛黄狗宝,这么多年夫妻当下来,她最清楚。
在这之后,何海每逢杜晶晶对他态度不好,就拉出上官绛珠说话。有一次两人在床上,何海指责杜晶晶大腿太粗,指责她乳房上有皱纹,说她太老。你看看人家绛珠,何海舔嘴咂巴舌地说,人家奶大,屁股圆,腰细,三围好得不得了,人家一点皱纹都没有,人家到底是年轻。
就这,杜晶晶都没太当回事儿,她只想一脚把他踹床底下。什么玩意儿,还越说越来了。真是写小说人的天性,爱编。
事情突然像一记重拳打过来把她打得晕头转向,是在夏日的一个燠热的下午。
那天,一回家,她就发现不对劲。她看见他挂在院子晒衣绳上的衣服,刚洗过。他居然主动干家务,稀罕。走进房子,只见何海穿着睡衣倚坐在床头,紧皱着眉头在抽烟。
家里是不是藏着你的上官绛珠?无聊吧,这么表现?杜晶晶环顾四周,跟何海开玩笑。
我让上官绛珠给陷害了,何海狠狠吐出一口烟雾,嘶哑着声音说。
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说笑,好像很严重。
杜晶晶脸上的笑意还未退尽,人不由得紧张起来了。
何海说,我今天上街,正走着,上官绛珠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见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她那么说,我就觉得有种危机四伏的感觉,我就一直小心着。她说她在莲湖公园等我,我就去了。我跟她在湖边说着话,正说着,见上官绛珠的老公从湖边站起来,手里提着棍子,胳膊粗,一腿长,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上。
杜晶晶狐疑地看着他,犹自笑着,问,那么,那会儿,你的上官绛珠呢?
我挨打了,她解恨了,早跑没影了。我再说一遍,这是陷阱!是陷害!
真的不像是开玩笑。是真的。看来真有一个叫上官绛珠的女人?真有女人看上何海,跟他搞婚外恋?不对呀,就算因为外边的女人挨打,也应该被堵在房子里打吧?大白天的,公园里,只是说说话,就挨打?
杜晶晶把她的疑问一个一个说出来,何海暴躁起来,啊呀道,不信你查去,我的摩托车还在公园搁着呢。
不管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摩托弄回来。别的,秋后算帐。
老公让情人的老公打了,当老婆的去推车,这种事儿,杜晶晶干不来。臊得慌。遂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于小凤,让她帮忙去推车。
于小凤招之即来,杜晶晶不做解释,只说让她去哪哪推车。杜晶晶严防死守的样子,于小凤马上意会,眼睛先把何海看了个透彻,抓过钥匙,满脸意味深长的笑,小跑着去执行任务。
到晚上,于小凤才把车推回来,脸上的笑意更浓。从杜晶晶跟何海结婚到现在,于小凤的脸上时常露出这种意味深长的笑。一看到她这种笑,杜晶晶就有种四处漏风的感觉。
本来想好,要对何海来个严刑逼供,但是,何海说他头疼得去医院拍片儿。杜晶晶忍着气,陪他去医院拍CT。看完片子,医生说没事,何海很不乐意,说什么叫没事?是不是人死了才叫有事?跟医生吵,吵一肚子气回来。杜晶晶看他身上连片青都没有,凭直觉,她认为他是小题大做,又怕万一有内伤,少不得按下气恼,时不时地给他按两把,不一会儿,他呼噜连天,睡着了。
她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没等她问,何海挣扎着起身,让杜晶晶把拍CT的票根,抓的药的凭证归拢一处,他说,得找他们去,让他们赔偿,这事不能这么便宜。
杜晶晶不去,她必须得知道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就是,何海厉声说,你老公,我,被陷害了!上官绛珠想讹咱们的钱,设套儿让我钻,我钻进去了,现在出不来了,你要是不帮我,咱们就蚀大了。
也就是说,你们真的有一腿?杜晶晶慌了,喘不过气儿。
何海低下头,不吭气,算是默认。
杜晶晶顿时气促,呼呼大喘几口,极声尖叫,胳膊抡圆了,瞄准他的头,抡过去。不解恨,咬紧槽牙,又抡一家伙,像打在冬瓜上,发出的不是脆响,是闷声。听声音都知道,打重了。
何海硬挨了这两下,一脸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打完,杜晶晶就后悔了。那两胳膊,像是交接仪式。现在,他轻松了,因为交接仪式已经完成,没他的什么事了。他该负的,都通过那两胳膊卸到她这边来了。剩下的,就是她的事了。
杜晶晶像被抽了筋似的瘫软无力。
等她情绪平稳后,何海坐起来,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上官绛珠那女人,长的一般,还没你好看,不过仗着身材好、气质好、出身好。她居然跟一个农民爱了十几年——你想想,能跟一个农民爱得死去活来,而且一爱就是十几年,这个女人能是个什么好东西?
这话杜晶晶不爱听。特反感。什么叫“居然跟一个农民”?你何海难道离“农民”十万八千里?去你妈的,你也不过一在乡兽医站上班的兽医。
她哼哼冷笑,说:她能跟你好上,确实可能不是个好东西!
杜晶晶对上官绛珠的老公充满好奇,想不出什么样的男人,能被老婆戴如此大的一顶绿帽子。何海说,就是。那个男人很瘦,很黑,样子很猥琐,是单位的小司机。
是么——我就不明白,上官绛珠图你什么?
一,她爱我的小说。二,性,她是性亢奋,谁都满足不了她。就我能。
对于第一点,杜晶晶认为简直是胡扯,她不相信有哪个女人会弱智到分不来什么是水泥蛋什么是银蛋的地步。也许,后一点,倒是合理的解释。何海在性上确实行,很行,像骡马一样行。但是,男人再好的床上功夫,也像夜光杯,只有在暗室里才看得清楚。杜晶晶也是女人,她不太相信真有女人肯单纯为了性跟男人好的。
她想起于小凤意味深长的笑,浑身不自在。何海点拨她:上官绛珠不会善罢甘休的,她会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最有可能的可能是,她攻上门来,把他抢到手。
杜晶晶一声长叹。是的,她不能让上官绛珠攻上门来。何海说得对,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得化被动为主动。
她按何海的策划到上官绛珠单位找上官绛珠。但上官绛珠的同事说,上官绛珠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至于原因,对不起,不知道。
何海又在电话里的指示,杜晶晶可以去找上官绛珠的老公——
见到上官绛珠的老公,杜晶晶暗暗吃惊。
眼前的男人是瘦,是黑,但瘦得清爽,黑得洋气,穿着打扮很有品味,看不到一丝何海所谓的“猥琐气”。而且,人家也不是什么“小司机”。人家确实开车,不过车呢,是公家配的。人家是单位领导,一把手,所长。
弄得杜晶晶直眨巴眼睛。她硬撑着,用下巴报上家门,说我是何海的老婆。
上官绛珠的老公盯着看了她好大一会儿,一副我不找你,你倒找我来了的诧异。
请问大姐您有什么事?请她落座后,他客气地问。
杜晶晶尖声说你凭什么打人!话一出口,她就在心里皱眉,她觉得她说话的声音像是卖菜的大嫂们的声气。
他平着脸,低声说,对不起,这是上班时间,不方便谈私事。
噎得杜晶晶说不出话。略加沉吟,她只好直接进入何海策划中的第二步:把一沓票据掏出来,展平,放到他办公桌上。
他瞄了一眼,一愣,不相信似的,伸长脖子仔细地看了看,一张张地翻过去,嘴慢慢地张开来,惊异地看着杜晶晶,突然间就笑了,拿笔在票据上啪、啪、啪敲打着,一脸的意味深长。
哦,该死的,跟于小凤一模一样的表情。
一瞬间,杜晶晶把何海周密的计划全忘光了。她意识到她在丢人。她想,我已经在丢人了,我不能再丢人了。她调整坐姿,力图让自己显得优雅些,斯文地说,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来,一是告诉你,管好你老婆。二呢,你把我老公打得拍片子,花了不少钱——但是这钱,毛毛雨,我们出得起。我们不差钱。就是让你知道而已。
他依旧看着票据微笑,但已经笑得不是让她那么难堪了。
他顿了顿,斟酌着用词:我不想过多地解释。如果您一定要解释,那么只好等绛珠本人回来,问确切了,再说。
她怎么……?杜晶晶心悬起来,问得有些结巴。
她目前么,没在家,上官绛珠的老公不肯再说。沉默中,他从肚子深处吸出一口气,缓缓地呼出来。
他失神地望向窗外。
窗外空调主机上,放着个青花大瓷碗,碗里种着花。碗华贵,但种的花却不怎么华贵,居然是太阳花。各种颜色的太阳花开得像傻子一样单纯。这应该是上官绛珠的手笔吧?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杜晶晶不敢往下问了。
你老那么笑来笑去的,今天你说,你什么意思?坐在超市休闲区里,杜晶晶恼火地问于小凤。
那好,于小凤笑嘻嘻地说,说了,同志,你可得给咱顶住啊。
神经,说!
好好。你老公,啊,听好——于小凤拖着长音儿,用吸管搅动杯底的珍珠粒儿,卖关子,看杜晶晶真恼了,才举手投降说:咱就说那天莲湖公园的事儿。那天我一去,就见何海的车在湖边倒着,我嘛,就过去扶,亭子里打麻将的老头儿一看,就问我,你谁呀?我就说我是谁谁谁,是谁谁谁让我来推车的。说完了,看他们挺感慨的样子,我就坐下来,跟他们闲聊。据他们说,你老公何海,那天运气很不好,“奸夫和淫妇”——对不起,是老头儿们这么说的,你瞪我也没用——在湖边站着没说上几句话,“淫妇”的正夫就看见了。人家那正夫,那天偏不偏,就蹲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看别人钓鱼。正看在兴头上,看见他们,想都没想,低头捞根棍子就冲上去了。可笑吧?更可笑的还在后边。“淫妇”眼尖,一眼瞥见,啊一声,没等“奸夫”反应过来,好家伙,她先冲上去了,死命抱住正夫的腰,不让往前走,一边大声喊着,让“奸夫”快跑。“奸夫”吓傻了,像被胶水粘在地上似的,一动不动。正夫怕他跑,甩“淫妇”又甩不开,让她松手又不松,急得没办法,一咬牙,狠命拿棍子在“淫妇”腿上打。好在是根糟木头,要不然,恁粗的棍子,她的腿怕得瘸上半年。棍子一下子就断为几截,眼看着“奸夫”反应过来了,要跑,正夫就地把棍子扔过去。不知道究竟打没打着你家何海,据那些老头们说压根儿就没挨上,反正是只见何海抱住头,像个球,滴溜溜往地上一团,滚来滚去。正夫拖着“淫妇”奔过去,抬腿要踢。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淫妇”一看不好,英勇地返身一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把“奸夫”覆盖了个严严实实,正夫的拳脚每一下都中在她的身上。
于小凤不说了,嘬着嘴儿笑。看她的样子,显然是没说完。
然后呢?杜晶晶紧张万分。
然后嘛,正夫一脚,于小凤连说带比划,一脚把“奸夫淫妇”蹬湖里去了。听老头儿们形容,就像“沿着锅边把叠在一起的两根面条下进锅里一样”。
呵呵,于小凤再也忍不住了,捂嘴大笑起来。
从来从来,杜晶晶都没像今天这样,如此这般地讨厌于小凤。
看着杜晶晶铁青的脸,于小凤有所收敛,她擦着笑出的泪花说,也就是你,要是我,跟何海这样的,我可过不下去。你为啥不离婚?
这个问题杜晶晶没办法回答,也不想回答。她想于小凤真不是个好鸟,居然巴不得好朋友离婚。于小凤的说法和何海说得大相径庭,和她的直觉也有出入。看来那天何海的一系列表现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无中生有”。如果真是“无中生有”的话,她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怪不得那天上官绛珠的老公那副表情呢。他妈的。
信谁?
杜晶晶最后决定,信何海。他们两口子之间,此时此刻绝对不能内斗,不能被外人趁虚而入。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扑朔迷离,鬼影幢幢。
先是很快听何海说上官绛珠离婚了,净身出户,搬回娘家住。杜晶晶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她掰开了跟何海讲,主题只有一个,何海和她的婚,离不得。何海让她放心,他说我没那么傻,一次教训足矣,我再也不会染指那个骚娘们儿啦。他说什么都过去了,老婆老婆你放心。

云朵、人体习作 李岩1997年 圆珠笔、纸 19.5m×13.5cm
杜晶晶能放心吗?你想嘛,“农民”跟她的差距有多悬殊,她能深爱十几年,义无反顾的性格可见一斑。虽然何海一再声称他绝不爱她,玩玩罢了,是她自己傻,入戏了,他立场坚定得很,绝不会假戏真做。但这不重要,有句俗话不是说嘛:不怕贼偷,就怕贼掂着。
她问何海要上官绛珠手机号码,她要打电话骂她。何海略加思忖,就把号码给了她,只是叮嘱她:说话“抻活”些,别让人抓住把柄。
接到她的电话,上官绛珠仿佛在意料之中,略一沉吟,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向她问好。她的声音苍凉、衰老,听起来,像五六十岁的老女人发出来的。杜晶晶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声音出自一个三十三岁的小三儿之口。太意外了,她还以为能听到像传说中的狐狸精那样骚嗒嗒的声音呢,心里咯噔一愣。
两个女人的谈话很不顺畅。
原因在杜晶晶身上。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杜晶晶竟也说起了普通话。她平时只说方言,偶尔说普通话,充满醋溜味儿。电话那头儿的上官绛珠对杜晶晶的醋溜普通话显然很不适应,她轻轻地清了几遍嗓子,暗示杜晶晶正常下来。无效后,她试着改用方言配合。就像杜晶晶说不了普通话一样,她也说不了方言,结果也说得磕磕绊绊。意识到这一点后,上官绛珠轻轻叹了口气,无奈中改回她的普通话。而杜晶晶呢,固执地继续着她的磕磕绊绊——对着电话那头儿的小三儿。
形势完全失控。不应该是这样的。她打电话,本意是想给上官绛珠难看,让她知难而退。这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呢,骂她,让她滚远。但她却在上官绛珠苍凉衰老的声音下动了恻隐之心,她身不由己地被一种怪异的混合感情裹着往前走,她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指责、诅咒、命令、要求、请求、恳求,一直到哀求。电话那头的上官绛珠不辩解,不发怒,偶尔轻轻地说一句“怎么会这样呢?大姐,对不起。”
然后,忽然间,杜晶晶听到她自己的哭声。
她听到她的哭声很醋溜,就像她醋溜的普通话一样。
嫂子,您保重,在她高低不平的哭声里,上官绛珠礼貌地挂断电话。
真丢人。
她是自取其辱。
晚上躺床上,杜晶晶病人似的,有气无力地跟何海学说电话经过。何海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抿嘴儿扑扑笑。他的鼻毛好久没修剪过了,这么一笑,鼻毛耸出多长,看着可恶心。
知道厉害了吧?那破货最擅长的,就是让人对她我见犹怜。你那里是她的对手。
杜晶晶苦笑着承认,唉,是不行。
何海脱吧脱吧,脱成光身子,往她怀里拱。
杜晶晶厌恶地推开他。
他再拱,她再推。
他仰脸儿刁顽地看她。
看半天,再拱。
你小是吧?乏味不乏味?杜晶晶不想让步,她已经傻了,不想傻到让自己都觉得恶心的地步。
是小。姐,好好的,爱爱我。
何海确实比杜晶晶小。小半岁。
唉,我是上辈子欠你的,杜晶晶叹口气,把他搂进怀里。
日子好像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上官绛珠离婚半年后,杜晶晶那个像阳光一样的伯父去世了,她和何海住在伯父家帮忙料理后事。恰恰在那几天的某一天,于小凤告诉她,上官绛珠的前夫将再次走入婚姻殿堂。杜晶晶知道这一消息,先是心里一惊,然后是解恨。这下好了,犟猪,你就作吧,看以后谁还要你!
在那几天里,杜晶晶意外地发现何海口袋里的钱挺多,陪奔丧的客人打麻将时,他居然敢上五十一百的场子。
自从知道上官绛珠的事后,杜晶晶在财政上迅速做出反应。男人没钱,就是翻了盖儿的王八。她对何海收紧银根。何海为此没少抗议。对不起,抗议无效。
那么,他的钱,从何处来?
她的直觉是:来自上官绛珠。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断,而是一直来往着。以某种秘密的方式。
丧期结束后,一回到家,杜晶晶就逼问何海钱的来处。见她一副你不说真话我就撒泼放野的架势,何海没敢说钱是从朋友处借的。杜晶晶手里拿着手机,随时准备问过去,明显表明防着他这招儿。看绕不过,他只得胡应付。
这就是承认了。
我就知道你们没断,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杜晶晶野猫子一样蹿到他身上,叉开五指,抓他的面皮。
他淡定地用胳膊一格,淡定地说,劝你好好的。
他且格且退,退到门内,大力推她出来,啪,反锁上门。
有高人向杜晶晶指点:你笨。对何海这种情况,柔为上。
于是,就柔。
怎么柔呢?睡前,只洗一个苹果,咔咔咬着吃,听着都让人馋。
何海伸脖儿瞅瞅,见没他的份儿,欲恼,杜晶晶已将苹果咬出一个图钉形,笑意盈盈儿地递他嘴边,只消他咔嚓一口,毫不费力。
何海哎呀一声,喜出望外。
他倒成功臣了!杜晶晶气闷闷地想。真他妈乱了套了。
问题是,她做的所有的这一切,好像起不到预期的效果。
上官绛珠像雾一样渗进来。杜晶晶把篱笆扎得再紧,都奈何不了雾的渗入。在吃饭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有一次,她听见何海在梦里喃喃叫着上官绛珠的名字。叫的是“珠珠”,亲着呢。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狐狸精啊,有恁大的魔力?
上官绛珠长什么样子?杜晶晶问何海。
何海审视着她,看她并没恶意,遂撅屁股趴床底下找出一双棉鞋,抽出鞋垫儿,从里面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来,里面赫然是一张上官绛珠的照片。哦,好你个王八蛋,杜晶晶嘟噜着,把照片接过去仔细看:的确不算太好看,中游略偏上。主要是身材出彩,还有就是气质——朦胧记得听人说过,女人只有一样东西能和高贵的男人相匹配。不是她的美貌,也不是她的青春,而是气质。长头发,穿旗袍,扶树站立,一脸的跟旗袍相冲突的冷傲和倔强。有点像电影里的军统女特务。
看毕,杜晶晶瘪瘪嘴把照片丢还给他,表示一不咋地,二我大度,不制裁。
何海想了想,嘿嘿笑着,当着她的面把照片撕碎,扔进烟灰缸里。
算他聪明。
她并不为所动。心里想,哪天,趁你不在,我要把家里包括老鼠洞在内的所有的角角落落,来个彻底搜查。指不定能搜出什么好的来呢。
搜查的结果是没再翻出照片,却翻出一本日记。那本日记混迹于电脑桌下面厚厚几沓书里,装得像普通老百姓。其实这本日记早在多年前,杜晶晶就看见过。她偷偷地从这本日记里了解到何海的很多心事。比如他对她的评价:“一个贤淑的女人,一个把整个世界放到她手心里都可以放心的女人,一个可以终生相守的女人”,她清楚地记得当年看到这样的评价时,她的感动和喜悦。没人这么说过她。比如他说他是怎样的愤世嫉俗,以至不被世人所容,被兽医站头儿暗算,等等。这些又勾起了她的痛惜的情绪。她能那么快地嫁给他,可以说这本日记功不可没。结婚后,没再见过何海写日记。他把它当摘抄本用。有时是名人格言,有时候粘张剪报。这会子看见它,杜晶晶心里一动,顺手拿起。
翻到后面,她看到上官绛珠的名字出现,大量的出现。
夸的,骂的,怀疑的,依赖的,爱的,恨的,什么都有,比他告诉她的那些丰富得多,可谓五味杂陈。他们经常见面。在超市,在书店,在路上,哪怕是惊鸿一瞥,也要见上一面。时常在杜晶晶家座机上响起的那一声振铃,也不是像何海说的是哪家小孩儿的恶作剧,而是他们在实在不能见面时相互约定的一声“我想你!”。在日记夹层里,杜晶晶又发现一张手机卡。她把它安进她的手机里,调出通话记录,上面全是上官绛珠的号码。打过来的,打过去的。异常频繁。无疑,他们平常就靠这张卡联系。怪不得呢。多高的聪明才智啊。
在初秋依旧闷热的房子里,杜晶晶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瘆。
冬天说到就到了。
一天杜晶晶开着车,在县街道正游荡,看见前边有个女人,披肩长发,穿着银灰色大衣,一根腰带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细腰。女人大踏步地走着。杜晶晶被她的背影所吸引,下意识地盯着看,心里暗笑:还说男人呢,其实女人也挺好色的。美的东西,谁都愿意欣赏。经过女人身边时,杜晶晶忽然间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觉得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上官绛珠。心马上咚咚大跳。她感到口干舌燥。
透过后望镜,她看得清楚,确实是上官绛珠那张冷傲倔强的脸。
一定是鬼附身。杜晶晶在一刹那间理解了刘邦的老婆吕后把刘邦的宠妃戚妃砍掉四肢、薰聋耳朵、弄瞎眼睛装在坛子里置于厕所的心情了。因为是敌人。敌人就得剁成肉泥,就得除之而后快,甚至死后挫骨扬灰。她杜晶晶居然可怜她的情敌。上官绛珠可从来没可怜过她。她想起她的屈辱。她凭什么屈辱呢?她住着自己挣来的五间两层子的洋楼,开着自己挣来的私家车,穿着自己挣来的价格不菲的大衣……
哦,上官绛珠。
近在咫尺。
她飞快地将车开出百余米远,戛然而止。打开车门,她站在车门边,掏出手机,做出跟别人通话的姿势,她开始了高声大嗓的谩骂。从小三儿、狐狸精、骚货、潘金莲、淫妇、公共汽车到抽水马桶。街上行人纷纷侧目,有人指点,有人驻足。暂时无人围观。
都来围观啊,杜晶晶恶毒地祈盼。
上官绛珠听到她卖菜大嫂式的叫骂,皱着眉看了她一眼,显然是没意识到这种谩骂跟她有关,她只是反感这样的不文明行为。然后,她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接着,她全明白了——她并没有像杜晶晶希望看到的那样满脸羞惭、落荒而逃,而是眉尖一扬,脸上弥漫开来怜悯的、轻蔑的、讥诮的笑意。
她目不斜视地从杜晶晶身边掠过,带起一股空谷幽兰般的香气。
杜晶晶张口结舌。
何海最近神态安详,坐在电脑前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看起来超然物外。仿佛,由他引起的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跟他毫无关系了似的。走进书房后,打开电脑,为图坐着舒服,他把两条后腿——看错了,他一共只有两条腿,没前后之分——擎在电脑桌上夹住电脑,把键盘放在他的裆部。他左手摸在卤牛肉上,时不时地往嘴里撕进一条,右手夹烟,时不时飞快地敲打键盘。
杜晶晶盯着他的后背琢磨他,越琢磨越觉得何海像只长满了腿的、胜算在握的、盘踞在网中心的巨大的蜘蛛。
她想,除了上官绛珠,以后无论哪个女人要这个男人,我都双手奉送,外加陪嫁——不,就是上官绛珠要,我也马上给。背个输名就背个输名。我认了。这是他妈的什么鳖羔操的破玩意儿啊。
杜晶晶对何海的后背说,于小凤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不跟你离婚。
何海很警觉,马上回头,露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问她,她还说什么了?
你认为她还能说什么?杜晶晶紧盯着他的眼珠子问。
没说什么,最好,何海阴森森地说完,扭过头继续敲他的字。
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于小凤没跟杜晶晶联系。奇怪。她以前隔三差五总要打个电话的。杜晶晶给她打过去,电话通着,那边不接。有时干脆摁断。路上偶遇,于小凤一副活见鬼的样子,一溜儿小跑,避着走。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杜晶晶到于小凤家里找她。
于小凤打开门,见是她,不好把她拒之门外,可也不想让她进去。倚着门,愁苦着脸说,娘呀,你放过我吧。
杜晶晶估计得不错,果然是何海找过于小凤。
于小凤说,那天,何海来了,问他不理,不用人让,他直接进厨房开橱柜找饭吃,弄得我们莫名其妙。吃完了他抹抹嘴,倒沙发上就睡。我老公肯定觉得不对么,这是寻事的架势么,是耍死狗的架势么,就问何海何海你咋了?咱有话好好说么。何海说,哥吔,好说不成,我都快没家咧。兄弟可怜。你家小凤挑拨我老婆跟我闹离婚,那位现在正在家里杀鸡抹脖子地闹腾。兄弟以后没家了,只好在你家吃,只好在你家睡。——你想想,这阵仗,我老公能不骂我吗?骂了,何海还是不起来。我老公没办法,拉住我,扇了我一嘴巴。扇得不响,何海哼了一声,还是躺着。我老公没办法,只好又扇了我一下。这下响,何海满意了,这才晃晃悠悠走人。
于小凤说得声音哽咽,眼泪长淌。
杜晶晶气得直往地上吐唾沫。
最近一段日子,何海露出狂躁不安的样子,连卤牛肉都不太吃了,烟头儿扔得满地都是。人渐渐消瘦下去,马瘦毛长,胡子就长得分外旺势,他不刮,弄得胡子与鼻毛共处。
杜晶晶冷着眼看,懒怠问。
不消问,“失恋了”呗,让人家上官绛珠给踹了呗。
杜晶晶打叠起千百样儿的软语温言,赌咒发誓再也不把于小凤说的每一个字向何海透露之后,于小凤相当不情愿地被杜晶晶拉进超市。杜晶晶请老朋友吃“焦太郎”下菜。
于小凤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吃完后,抹抹嘴,主动把在坊间听到的传闻往外倒。她说,上官绛珠这次彻底跟何海断绝了关系,据可靠人士说,就算“何海这次给人家跪下,人家上官绛珠也不可能跟他再好了”。
又说,莲湖公园的事出来后,上官绛珠的老公确实觉得可丢人,但是,提出离婚的,不是他,是上官绛珠。上官绛珠的老公想不通,拖着不离。上官绛珠说,这么着过下去,对谁都不人道。非离不可。上官绛珠的老公很生气,骂她说,何海那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个地痞流氓无赖么,你居然当个宝。你跟谁都行,就是不能跟他。上官绛珠哭着说我全知道,我离婚不是因为他,我是因为我自己的心。我以后谁也不跟了,我就跟我的心过。上官绛珠离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她老公是什么都可以给她,就是不给她孩子。她老公的说法很冷静,很客观:你的性子不适合带孩子,把孩子交给你我不放心。
你的何海——见杜晶晶皱眉,于小凤吐着舌头改口道,何海在外边到处跟人说上官绛珠的三围多好多好,性需求多大多大,说上官绛珠无论以后嫁给谁,他都有本事给搅黄,还说上官绛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就算县长对上官绛珠下手,他都要把县长拉下马。
他?杜晶晶眼睛眯成一条缝,满是鄙夷。她想像得来,要是上官绛珠真的跟哪个县长好了,何海会如何做事。他确实有本事给搅黄。当然,他绝不会真枪实弹地上场。他会鬼鬼祟祟地踅摸到县长跟前,掏心掏肺地说,那个女人么,我都看不上,扔了,您这大的人物,您捡我的狗剩儿?……那女人有性病呢,咋治都治不好,您防着些……那女人疯狂得很,可怕得很,会搅得您家无宁日……
于小凤叹气道,上官绛珠受不了何海的骚扰,把手机号儿换了。听说何海没辙了,就总往上官绛珠父母家座机上打电话,把人家老父老母吓得惶惶不安。上官绛珠没办法,把座机号也换了。何海到处打听人家的座机号,逢人就说,说是你在要,说你要找上官绛珠那个骚货算总账。
杜晶晶坐了起来。
——她确实那么干过。
那是在上官绛珠刚离婚那会儿,何海撺掇她给上官绛珠父母家打电话跟老人“沟通沟通”。沟通的主要内容是上官绛珠的离婚是她个人的决定,跟何海无关。杜晶晶当时虽然犹豫,觉得那么做对人家老父老母太缺德,但形势严峻,何海在侧又一直催逼,由不得她犹豫——于是就打了。
杜晶晶想,我得找到上官绛珠本人,好好坐下来聊聊。
没等杜晶晶找上官绛珠,杜晶晶先收到了一封来自上官绛珠寄往她补课学校的手写信。
正文如下:
请原谅我曾经带给您的困扰。无论何海在我面前怎样诋毁您,您在我心里都是一个不错的女人。错的不是您,是我。我承认曾对这个世界有过绝望,绝望使我愤怒,我只有通过堕落才能化解这份愤怒。在堕落的路上,我遇见了何海。不瞒您说,曾经有个时期,我对何海的感情很深。他苦难的人生经历让我下不了离开的决心。我视他为孩子,一个被世界无情抛弃苦苦挣扎的孩子。然而,何海只视我为敌人。何海似乎把一切人都视为敌人。他时时刻刻想着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他对我全封闭式的控制,也让我感到窒息。
您怎样地不原谅我都行,怎样找我算总账都可以。老天推我了一把,我还过去了一把。结果呢,还过了。现在,我得承担再被推一把的报应了。老天确实在以因果报应的形式维持着某种平衡。我的意思是,一切皆是我为,与我亲人无关,与我朋友无关。要推,请您直接来推我好了。我认。还一分,了一分,我会平静地接受。
请您转告何海,他真的很聪明。如果他肯把全部精力用在正事上,而不是整天战天斗地上,他也许会成功的。但是,像他那样的男人,就算成功了,我担心,他的成功果实,怕不会让您和他来共享的吧?我想自然也不会是我。他对我和农民的事一直暴跳如雷——杜姐,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可以转身离开。可您呢?假如他成功了,没您的什么,如果他不成功,他会寄居在您的体内吮吸您。日日、月月、年年,至死方休。
各人承担各人的命运吧。
杜晶晶驱车来到郊外的一座桥上。她憋得慌,想散散心。
凭栏远望。即使在汛期也不曾宽阔过的河面,在干燥的秋季,更加萎缩成窄窄的一溜儿。
她眯缝着眼睛静静地站着,从中午一直站到夕阳西下。她想,我是不会离婚的。离了就不好玩儿了。那多没意思啊。为了有意思,她必须得长长久久地跟他生活在一起。有句粗话说得真他妈好:屌毛比眉毛生得晚,但屌毛比眉毛生得长。她妩媚地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