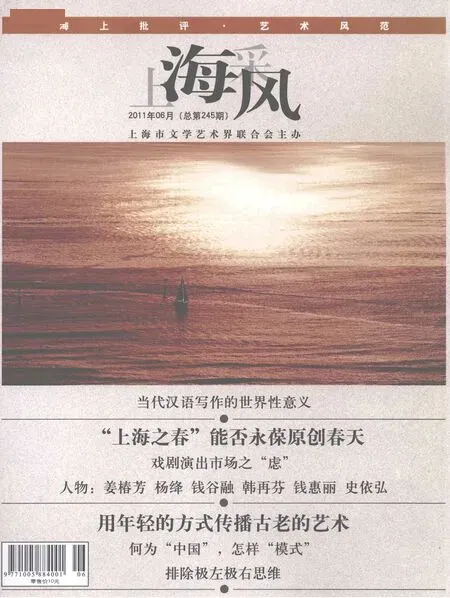我的上海情结
2011-01-04马识途
文/马识途
我的上海情结
文/马识途
如果照时新的说法,对什么迷恋就叫什么“情结”的话,我要说,我有“上海情结”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曾经把我的一段青春时光,抛掷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里。上海,不仅让我这个四川农村的孩子,在这里求得真才实学,使我得以进入高等学府去深造,更重要的是,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是上海的众多的进步书刊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把我推上革命的道路。是上海决定我的人生轨迹的。我在上海的那几年生活,至今时常来到我的梦中。
1992年我到上海为巴老祝九十大寿。回到上海,我为上海的日新月异、繁华昌盛感到欣喜,也跟同伴们去逛大马路,看外滩夜景,欣赏东方明珠,穿行悬索大桥,还到浦东新区去观光,到高桥保税区看热闹。大家都为上海的变化之大赞叹不已,我当然也一样。但是我却有另外的情结在这里。我在宾馆得闲的时候,一个人便溜到原来法租界那些古老的弄堂,去寻找我住过的石库门老房子。虽然没有找到,却到那些依然如故的梧桐小道散步,去捡回我失落在那里的脚步。华灯初上的傍晚,在从梧桐树枝缝洒落下来的灯光下,一个人偶偶而行,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这感觉真好呀,就像又回到了我18岁的青春年代。
到上海不到浦东新区去走走,等于没有到上海。我也跟同伴们坐小车过杨浦大桥,直奔高桥,去看保税区。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稀奇,我却很想去看看海滩。那里曾经是我们当时夏天常去作海水浴的地方。那温暖柔和的沙滩,那汹涌的浪涛,那寥廓的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那里现在怎么样了呢?听说那里已经隔断,过不去了。
我们继续驱车南行,去看南浦大桥。我却坚持要先去六里桥,去看看我的母校浦东中学。浦东中学当时在上海是比较有名的中学,由一个叫杨斯盛的木工发了财出资兴办的,黄炎培任董事长。据说有不少名人在这学校上过学。至少我听大科学家王淦昌说,他就是从浦东出来的。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学,在那里决定了我的一生。五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怎么样了?我得去看看。
车到六里桥,我下车在桥上引颈瞻望,景象完全变了,我已无法辨认。惟有那条通往黄浦江的小河,仍然在平静地流淌,沿远远的杨柳岸逶迤而去。那船码头也还在。我们就是从那里上小火轮,出黄浦江到斜对面十六铺上岸到上海租界去的。
我走进浦东中学大门一看,校容已经面目一新。原来的木质教学楼和宿舍早已不知去向,在我面前的都是焕然一新的大楼。惟有操场还是老样,许多学生在那里打篮球,我似乎在其中看到我的身影。我急于想再去瞻仰杨斯盛的铜像,走到校园里的小花园,却没有看到铜像,问起来才知道已经挪了地方。我们被带到铜像前,向这个志存高远的木匠鞠躬致敬,并在那里照了相。
我还急于想找到杨家院子,我记得就在校园背后的河边,凭着记忆,竟然把那个老房子找到了。那房子已经很破败,我却依依不舍地看了一阵。因为我在那里租房住过半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们曾经在那里油印过传单,策划过同学们一起过江到上海参加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记得那时我们打起爱国抗日的旗帜,排队走向南码头,但还没有到码头,便被警察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怎么也冲不出去,全被押回学校。后来上海学联的领导批评我们太笨,竟然不懂得打游击的办法。以后我们得到通知后,便化整为零,三个两个地自己乘小火轮到上海,到了开会地方,才集合打出旗号,参加游行。
我们的爱国行动却不容于正在和日本讲亲善的国民政府,我们学校中一群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唆使的同学,暗地里在军事教官的指挥下,向我们故意寻衅,打起群架来。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赶出学校,我们只得去寻亲靠友暂时躲避。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心。这便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走马观花地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走出校门,却忽然想找寻我过去曾经常去光顾的小面馆。那汤面的味道使我想起来仍然流口水。还想去寻找那个专门做夹肉芝麻烧饼的小铺。我明知这是徒劳的,然而还是站在那里呆看一阵。六里桥,我又回来了。那乡村小路上咿咿呀呀唱着的独轮小车还有吗?那在小溪边靠牛力吱吱转动的水车还有吗?我想,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景,无论时代怎么变,总还是有的吧?啊,想起来了,就在这条小河上,我们坐上由小姑娘摇着橹的船,在小河的港汊里缓缓而行,我们少年同学,唱歌欢笑,互相打闹的往事,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我们从南浦大桥过江回到宾馆。虽然身体疲乏,可是我不等吃晚饭,便一个人溜了出去,想自己去逛街。我来到南京路,只见霓虹灯满街闪耀,彩灯通明,更比旧日繁华。但我的目的地是四马路,当年那里书店林立,我每次进城是必去的,往往在那里的书店里流连忘返,寻找那些进步书刊,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坚定自己走抗日救国道路的决心。但是我再来四马路,书店虽不少,却都已经关了门,很是憾然。我回到二马路,随意而行,使我惊奇的是那里仍然有卖“菜饭”的小铺,还正开着门呢。这“菜饭”是当时我每次到上海必吃的,价廉物美。不想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居然在上海老地方又吃到“菜饭”!那不是吃,是享受一种回忆的情趣。我吃了很久,才把这一顿夜饭吃完。店员都不知我这老头怎么这么慢嚼细咽,长久不愿离开,已经过了打烊的时候了。
啊,上海,是在我的脑子里记忆积累最多的地方。短暂的旅程,无法让我去一一寻找我失落在那里的脚迹,徐家汇、江湾、吴淞炮台……都无法去了。但是我终于在造访朋友的余时,一个人坐车从北四川路到了虹口公园。我想去重访鲁迅故居、内山书店和鲁迅墓。过去我曾拜访过的西郊万国公墓中的鲁迅墓,听说已经搬进虹口公园了。我东问西问,终于打听到鲁迅故居。我从弄堂进去,却没有开放,说是尚在装修。我十分遗憾地离开那里,想去寻找我过去曾来买过书的内山书店,却没有找到。又一个遗憾。幸得我到底走进虹口公园,走进鲁迅的墓园。这和我过去看到过的鲁迅墓大不一样,气派多了。许多游人在参观。我一个人坐在石条凳上,在西下的夕阳光照下,在那里享受回忆的快乐。1936年lO月,在宋庆龄、巴金、茅盾等人的带领下,群众为鲁迅送葬的景象又回到我的面前了。太阳西下,游人已少,我到鲁迅墓前鞠躬致敬后走出公园,回到宾馆。
那次到上海,捡拾了不少我洒落在上海的脚迹,勾引出我无穷的回忆,然而并没有解开我的“上海情结”,相反的,这情结缠得更紧了。
现在,我已年过九十,风烛残年,好在腿力尚健,去年参观了上海世博,算是解开了一次“上海情结”。

马识途 著名作家,曾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