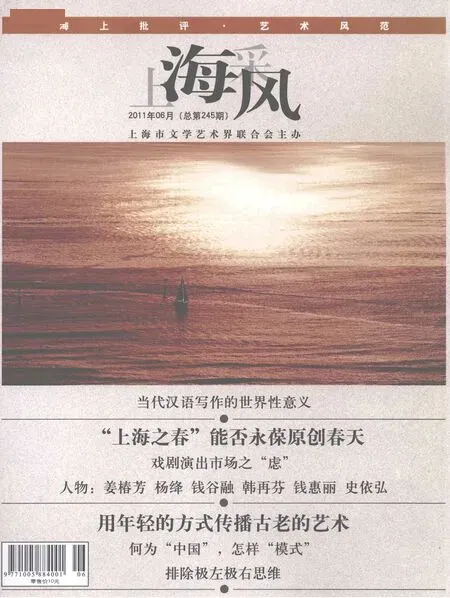我的“戏迷”生涯
2011-01-04张德林
文/张德林
我的“戏迷”生涯
文/张德林

张德林在《将相和》中饰蔺相如
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点情趣,有点业余爱好,否则就活得太累,太枯燥,太没意思了。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我经常跟研究生们打交道,上课,开学术讨论会,审批学术论文,平时忙得不亦乐乎。精神劳动不比体力劳动的强度差,心灵的弦绷得过紧,对身心健康有损害。真正懂得工作的人,也一定善于休息,会找乐趣。唱流行歌曲、听摇滚乐、跳摇摆舞,那是年轻人精神宣泄之道,对我来说,则格格不入。我有我自己的爱好,那就是京剧艺术。
酷爱京剧,自小养成
我酷爱京剧,酷爱到了入迷的程度。
这种爱好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话得从我的童年时代说起。我的父亲是个小业主,对京剧相当热爱。有一次,他从旧货商店挑来一担旧唱片,是百代公司、长城公司、胜利公司、开明公司、大中华公司……的出品,有二三百张之多,其中大多是京剧唱片。家里有一架手摇留声机。那时我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十岁光景。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便摇着留声机听京戏。我听得滚瓜烂熟的唱片有:马连良、梅兰芳的《打渔杀家》、谭富英的《定军山》、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让徐州》、余叔岩的《搜孤救孤》,等等。当时我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高庆奎,他那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气拖得有多长,我和我的隔壁邻居庆官(徐云峰)小伙伴一起屏住气跟着拖,二人合起来也没有他拖得长;另一个是谭富英,他的嗓音刮拉松脆,太棒了!有一张唱片,金少山的《牧虎关》,每听到那句“她行走好似风摆柳,扭扭捏,捏捏扭,扭扭捏捏你甚风流”,我和我的母亲都笑得合不拢嘴。还有两张唱片,给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便是露兰春的《独木关》(《薛礼叹月》)和《苏武骂毛延寿》。这位女文武老生,嗓音甜美,是当时京剧舞台上一位新星,在我听来,并不比孟小冬的录音差。可惜艺术生命短暂,做了黄金荣的小老婆。对京剧的兴趣要从小培养,此话一点不错。长期听唱片,训练了我懂得京剧语言的耳朵。当时的京戏,是名副其实的国剧,只要你打开收音机,随时都可以听到著名唱段的播放或舞台实况转播,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从不中断。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段流水板几乎人人会哼几句(包括黄包车夫)。大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传播京剧艺术,对培养京剧爱好者和戏迷,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是在这一文化环境中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对京剧的兴趣,自小养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京剧的爱好逐渐加深了。我开始跟随父亲上戏馆看戏。我家在浙江嘉兴,离上海、苏州、杭州很近,是个三等城市,第一流的名角儿,如梅兰芳、马连良他们不会来,但有一定名望的京剧演员则经常来演出。我看得最多的是宋家班子——宋宝罗、宋紫萍、宋义增三兄妹的戏。他们合演的全部《四郎探母》,我看过无数遍,宋宝罗那一声“站立宫门叫小番”,直冲云霄,多有劲!宋宝罗的拿手戏是《斩黄袍》《哭秦庭》,属于高庆奎、刘鸿升的路子。宋宝罗个子高,声音高亢嘹亮,激越铿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一句高腔,声如裂帛,全场为之振奋。我还看过高雪樵的《驱车战将》、高盛麟的《铁笼山》、小高雪樵以及李仲林的《金钱豹》、梁一鸣的《击鼓骂曹》……他们都是上海来的名角儿,演出时场场客满。还有一批在杭嘉湖一带“走江湖”的“艺人”,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演员。有一名须生叫黄汉培,年岁已偏高,他演唱的《四郎探母》,嗓音之脆亮,堪称一绝。还有一位青衣吴艳琴,年纪很轻,扮相俊俏秀丽,她演唱的《生死恨》,每到凄楚哀怨处便声泪俱下。我母亲最爱看吴艳琴的戏。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演戏“感情很投入”。他们非常辛苦,每天日夜两场,有时难免伤风感冒,嗓子哑了,仍得演出。他们名不见经传,虽有好的技艺,也得不到流传。他们是否还活在人世间?作为他们的忠实观众,我至今还在怀念着他们。
到了青年时代,我随父母来上海的机会多了。每次来上海,“头等大事”是晚上看京戏。上海的京戏馆真多: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中国大戏院、皇后剧场……每天都有多家班子同时演出,任你挑选。这里有京派戏,也有海派戏。我看过的京派戏有:全部《潞安州》,包括《陆登自刎》、《八大锤》、《断臂说书》,高盛麟前饰陆登,后饰陆文龙,李万春饰王佐;林树森的《走麦城》,台上慷慨悲歌,台后焚香燃烛。我看过的海派戏有赵如泉的《怪侠欧阳德》,陈鹤峰的《血滴子》,机关布景,热闹非凡……
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潜移默化,自然而然便会哼上几段。看着《大戏考》,听着唱片或收音机,一句句跟着唱,唱出来的东西倒有些京味,并非洋腔洋调。我最初学会的唱段是管绍华的《坐宫》、马连良的《打渔杀家》、谭富英的《定军山》、余叔岩的《搜孤救孤》,完全凭感觉唱,无师自通,杂得很,既不懂得打板眼,也没有胡琴伴奏。
记得嘉兴有个唱小生的票友,曾经登过台,会拉几下京二胡。经长辈的介绍,有一次请他来为我拉琴。或许是出于他的虚荣心,表现自己“有两下”吧,他故意把琴拔高调门,逼得我无法把嗓子吊上去,我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他则洋洋得意,暗暗好笑,我恨不得往地里钻。这件事虽已过去六十多年,每想及此,内心便十分懊丧。
解放初,我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赵景深教授上民间文学课,可谓别开生面。他酷爱唱昆曲和京戏,在课堂上,他经常抽一二十分钟,唱戏加表演,过过戏瘾。赵先生有个绝招,会画各种京剧脸谱,而且用两支粉笔,左右手在黑板上同时画。每逢国庆或迎新晚会,赵先生都会主动出场表演,他唱《太白醉酒》、《打渔杀家》,一边唱一边做,引得同学们不断地鼓掌和喝彩,我们真是乐极了!有一次,他把夫人请来了,老俩口一起唱《长生殿》,先生唱唐明皇,师母唱杨贵妃,载歌载舞,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老教授的熏陶下,班级里有几位同学开始爱上了京戏和昆曲。我的同寝室有位会拉小提琴的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京胡。其实他不懂京戏,只是凭借小提琴的指法和乐谱原理,勉强会拉几段京戏。他拉得最熟练的是《乌盆记》中那段二黄原板。他拉我唱,在寝室里唱来唱去是那几句“老丈不必胆怕惊……”不管多么幼稚,我总算第一次配上胡琴唱京戏了。可惜这位同学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去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我的伴奏伙伴从此被拆散了。
偷偷摸摸,苦中作乐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过不少的坎坷。我复旦毕业后,分配在华东师大任教。1958年春,我被凑数补划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留在资料室工作。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寄托的。白天八小时坐班,埋头整理资料,晚上在家里干些什么好呢?总不能整天整夜看书吧。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迷恋京剧,那时已进入六十年代前期了。那时我每二周必去市内“人民大舞台”或“天蟾舞台”看一次京戏,几乎到了“痴迷”“疯狂”的程度。只要票价不超过一元(一块高级白熊冰砖八角),我都去看。上海京剧院所有的名角儿,各自有什么特点,我如数家珍。汪正华所有的戏,我全部看过了,我最欣赏他的《宋江题诗》。北京来的名角儿,我最欣赏李世济《英台哭坟》一场极度悲愤的演唱,我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也在滚滚落泪。天津来的长靠武生厉慧良,他演唱的《王佐断臂》,唱腔的深沉、圆润、精美,令我吃惊,显然可与李少春媲美……附带说明,厉慧良八十年代声带长疖,几乎失声,那是后来的事。

在家练功
我还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钱,花了一百八十元,买了一台凯歌牌收放两用机,这在当时是最豪华的电器设备了。我走遍上海文化商场,购买京剧密纹唱片,三年内收集了三大盒,六十多张,每收集一张,那种喜悦心情,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肉票可以上交,饭菜可以少吃,衣服可以不添,京戏则不能不听不看。八小时以外,关起房门,那是我的小小的自由天地!我喜欢听须生唱腔,也喜欢听青衣唱腔,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在须生中,艺术大师很多,他们的造诣都很高,各有千秋。根据个人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不妨作点比较。谭富英的唱腔,快板最佳,犹如一发发子弹从枪口射出,节奏明快。他的“导板”结尾处往高处飞越,清脆、明亮,常能博得满堂采声。可是谭富英的唱腔,也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如有点飘浮气韵不足,这或许跟他的晚年身体欠佳有关系。马连良的说白甚佳,唱腔潇洒、飘逸、自然,不露斧凿痕迹,但少了点力度、深沉感和艺术激情。那出《苏武牧羊》一反常态,长年囚禁北国的苏武,登上城台,遥望千里以外的故国和家乡,思念君主、老母、贤妻,那种郁懑、悲怆、切盼和彻骨痛苦之情,演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深沉内蕴远远超过《借东风》唱段。言菊朋的唱腔秀丽、纤巧,哀而不怨,娓娓动听,最适合老年人一字字一句句品味、把玩。它给人的印象是:小家碧玉,缺少点大家气派。杨宝森的唱腔也有弱点,他缺少高音,音色不够明亮。但他的嗓音开阔,中低音甚佳。他的运腔浑厚、坚实、苍劲、深沉,气韵充沛,耐人寻味。杨宝森的唱腔设计富有书卷气。在全部《伍子胥》中,有那么多“二六”,板式虽然相同,但根据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人物特定心理的规定,其唱法没有一处是雷同的,情感的呈示或疑虑,或忧伤,或悲切,或祈求。《鱼肠剑》伍员见姬光时那六司“反西皮散板”——“子青阀阅门楣第,落魄天涯有谁知?可叹我父母的冤仇沉海底,俺好似凤脱翎毛怎能飞……”每一句的唱法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委婉、凝重的情态,悲伤中蕴含祈求的心境,都通过低沉纡回的唱腔,细致入微地传达给了每个听众。杨宝森的唱腔,品位高,文学性强,这一优势,经过时间的考验,愈来愈扩大。学杨、崇杨、迷杨的票友,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就是个证明。我在青生时代,最喜欢谭派和马派。到了中年以后,见多识广,选择性增加了,比来比去,我更喜欢杨派。我的嗓音较宽厚,中低音佳,能翻高音,但较累,音域低沉。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这也是我学习杨派的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京剧因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罪名,首当其冲,被“砸个稀巴烂”。不少京剧艺术大师,如马连良、周信芳、叶盛兰、李少春、裘盛戎、“京胡王”杨宝忠等等,都被活活折磨死。像我这样的“摘帽右派”,满脑袋“封资修”,不受冲击才怪呢!家被抄了,近千册藏书被一抢而空,我还不怎么可惜,最使我惋惜的是,那三大盒密纹京剧唱片被拿走,里面有我所珍藏的全部杨宝森唱片,我感到非常痛苦,我的灵魂寄托的最后一块精神园地被捣毁了,那是什么滋味啊!“红卫兵”小将没有拿走我家里的收放两用机,要我好好听“样板戏”,接受无产阶级教育,换换脑筋。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年代:造神论在全国泛滥成灾;只有一个调子可唱,一种雷同的话可说;服饰上灰蓝绿黑成为时代的主色;十亿人民的精神食粮只有八个“样板戏”。
神州大地一片精神沙漠!精神上的饥渴症,比什么都难熬!
总算碰上了一个好人,学校里有位工人贾洪殿师傅,他在仓库的废品堆里发现三盒京剧密纹唱片,知道是从我家抄来的。贾师傅也是个京剧迷,他出身好,不怕缠麻烦,便悄悄地把三盒唱片交还给我,我当时真是感激涕零!于是我每天晚上听杨宝森的《文昭关》《李陵碑》《清官册》《击鼓骂曹》……听陈大濩的《沙桥饯别》《法场换子》,听李少春的《野猪林》,听李世济的《梅妃》《锁麟囊》,听张君秋的《春秋配》《三堂会审》,听杜近芳、叶盛兰的《白蛇传》……有时候听得如痴如醉,不觉忘乎所以,低低吟唱几句,真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好在我是个“牛鬼”,朋友不敢上门,六亲均已断绝,门窗是关得紧紧的,唱机的音量是减得小小的,耳朵紧挨着唱机头细细听,生怕声音传出去,隔墙有耳,被人打“小报告”。我的老娘看着我像做贼那样听京戏,只得苦笑:“孺子不可教也!”这种偷偷摸摸苦中作乐的情景,后代人是无法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真是如同隔世啊!
京剧社长,粉墨登场
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四人帮”倒台后,教育界出现了一派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华东师大工会开始成立京剧社,邀请我这个一向关在房里唱戏的教授参加,后来又选我当京剧社的社长。那时工会的经费充足,肯花钱,向京剧院和戏曲学校聘请专业演员和教师来教我们唱戏和演戏。陆振声原是上海京剧院二路老生,当过周信芳的配角,他来师大京剧社任教多年。戏校的陈小燕、李秋萍老师,上海京剧院著名青衣吴颖,也来任教过。我们的计划气派不小,要求每年粉墨登场一次。京剧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各系,有教授、副教授、工程师、博士生,还有部分硕士生和大学生。每星期至少一次学唱、练习走台步或排演节目。我们已坚持了将近十年,演出过三十多出戏。演唱配上胡琴和锣鼓,要求就严格了,每一个板眼都得注意,不能脱板,稍有差错,教师、琴师马上指正,重新唱,错了再来,直至正确为止。我原有的唱腔功底较好,经过长期的训练,在“尺寸”把握上提高较快。我前后演过的戏有:《龙凤呈祥》(饰刘备),《文昭关》(饰伍子胥),《坐宫》(饰杨延辉),《二进宫》(饰杨波),《将相和》(饰蔺相如)。关于舞台上的甘苦体验,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小说界》上,收在《上海人的一日》里面,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少年时代,我在看宋宝罗演《四郎探母》时,羡慕他的扮相和唱腔,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在舞台上扮演杨四郎,显一显身手,让台下的观众为我喝彩、鼓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欲望是种内驱力,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精神宣泄均属于欲望的范畴。想不到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到了五十开外的年岁竟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我在师大的礼堂内,在全校师生和亲朋好友面前扮演了杨四郎,还扮演了其他的角色。每次演出,我都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好像越活越年轻了。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6月7日,我演《将相和》中的蔺相如,挡道那一场戏,我把我夫人高亚真女士请出来当车夫推车,把我的三名研究生张闳、郭熙志、郭春林和一名助手陈佳鸣请出来当卫队,台上演得火热,台下的学生和亲朋好友一个个乐开了怀,掌声不绝,做到了师生同乐,夫妻同乐,亲朋好友同乐。当年赵景深老师演出《长生殿》的情景又在我眼前重现了。
1990年,我的一位儿时一起长大的中学同学徐云峰,1947年参加蒋介石卫队,1949年随军去台湾,后升至某舰艇的舰长,两岸开放后,他回乡探亲,并特地从嘉兴来师大探望我。两人见面后第一次对话,不由自主地在客厅内合唱一段《箫何月下追韩信》:“这三生有幸……”我的爱妻笑得合不拢嘴。时隔四十多年,两个小戏迷已变成头发花白的老人了,艺术情趣一点没有变,古老的京剧竟有如此大的魅力!

张德林(前中)偕夫人高亚真与众弟子合影

张德林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前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