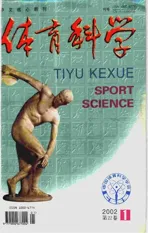体育纠纷救济法治化方案论纲
2011-01-02张春良
张春良
体育纠纷救济法治化方案论纲
张春良
无救济即无法治,无法治化的救济即无法治化的体育。我国现行体育救济机制虽在法理上包括行业内和行业外两大救济类型,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行业外救济不足、行业内救济独大的跛足效应。为实现体育救济的法治化,应重建自力救济、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三位一体的均衡化的体育治理体系,在补善各别救济机制的前提之上实现它们之间法治化的分工与合作,无为而治的救济体制才是体育法治化的上善之境。法治化不是格式化,中国问题应得到中国式解决,内生型的法治化道路才是重振中华体育辉煌伟业的对治方案。
体育法治;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接近正义
体育法治重在“治”而非“制”。“治”是动态的展开过程,而“制”则是静态的规则建构。体育法治,即是以静态之“制”来动态治理体育之过程,其核心在执行,而规范执行之机制即为体育纠纷救济机制。因此,体育法治的重心固然以体育法制为前提,但更为紧要的环节则落在纠纷救济的机制运行上,没有救济机制的卫护,体育法治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没有“牙齿”的老虎固然不足以肩负体育法治的神圣使命,但如果“牙齿”本身存在严重问题,则它甚至还会败坏体育法治的基本追求。由此看来,要成就体育法治的丰功伟业,就不仅要为体育业武装上“牙齿”,而且这“牙齿”首先还得先于一切地法治化。我国现行体育救济机制不仅无法治之精神,相反,却具有反法治化的倾向,只有在系统梳理现行救济机制,并依照法治要义予以剖析之后,才能提出适合中国实践的法治化方案。
1 体育救济现行机制之梳理
从救济机制法治化的角度看,一种有效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区分为体育行业内救济与行业外救济。区分行业内、外救济方式的标准,是主导纠纷解决的机构之身份:围绕体育行业内的机构建设的救济机制即为行业内救济;反之,围绕体育行业外的机构建设的救济机制即为行业外救济。
1.1 行业内救济机制
行业内救济主要是指各级体育协会或团体内部建立的纠纷解决机制,它是一种自律性的解纷机制。按照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章之规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是1995年8月29日由第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并在2009年8月27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第10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予以修正。,体育行业内的社会团体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各级体育总会,其职责在于联系、团结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其性质是群众性体育组织;二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其职责在于发展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三是,体育科学社会团体,其职责是推动体育科学技术工作,其性质是学术性群众组织;四是,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它们按照不同的竞技主题形成了不同的体育协会,这些不同的体育协会首先在地方层面,其次在国家层面并最终在国际层面逐步形成了纵横勾连的体制①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截止2008年6月20日的统计,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共有78项,相应地包括了78个单项体育协会(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212/ 706240.htm l,2010-10-19访问)。。这些不同类型及层级的体育团体在其制度建设之中设立了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法律依据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七章有关“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综观该章之规定,违背体育法、体育纪律及体育规则者将分别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只能通过外部救济即司法救济的方式进行,而团体内部的自律性法律责任的实施和科处主体都是各体育社会团体。为规范内部管理秩序,各体育团体围绕违背体育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设计相应的解纷机制,以明确处罚类型、处罚条件、处罚程序以及内部申诉救济程序。此即为行业内部救济机制。
各体育团体的行业内救济机制并无一致做法,以中国足球协会为例,或许是由于中国足球在国人体育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足球运动较为极端地集中了体育领域的纠纷状态,中国足球协会的内部救济机制因此发展得较为系统、全面②有观点即提出,“纠纷具有反社会性,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积极意义。根据辩证法理,事物总是以克服自身障碍的方式获得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契机。作为纠纷之一维的体育纠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起到了其对体育产业的制度创新和促进作用”。参阅张春良.体育纠纷救济机制的法理学分析[J].福建论坛(社会科学版),2007,(4):15。,因而也更具分析的典型意义,以之作为样本可考察我国体育纠纷内部救济机制之现状,其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1.1.1 救济方式的多元化
一般来说,这些体育组织内部至少规定了两种以上的救济方式,一是纪律委员会,二是仲裁委员会。此外,组织内部的执行委员会或者主席会议也有一定的纠纷处理权限。《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27条第2款就体现了三元解纷模式:纪律委员会、仲裁委员会以及在二者处分权限之外的单位会员资格问题,执行委员会或主席会议均有权做出暂停资格的处罚。特别具有法治意义的是,中国足协还于2009年6月更新了专门的《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③原称为《仲裁委员会工作条例》,现已更新为《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标志着其内部救济机制在独立性和完善性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1.1.2 救济程序的梯级化
各体育组织的内部救济程序还在两大方面表现出梯级化的结构:一是,因应各体育团体的层级化而自然表现出来的内部救济机制的梯级化;二是,即便在一个单独的体育团体内部,其设计的多元救济机制之间也存在着梯级化的现象。就足球治理事项而言,在中国范围之内除了有全国性的中国足协之外,上、下又可进一步延伸为国际足联(FIFA)和各地方足协。这些组织既是独立的社会团体,同时,彼此之间又已形成单位成员与统一团体的层级关系。由于地方足协、中国足协和国际足联分别都有自己的内部救济机制,因而,表现出层级化的结构。这些层级化的结构之间,还可以形成逐级上诉的救济机制。
在各单独的体育团体之内,其内设的救济机制也常为彰显公平之精神而设立2~3级的内部救济途径,允许对下级机构做出的裁决提起申诉或上诉。中国足协内设的救济机制也具有此种特征,其仲裁委员会除了自身的一般管辖事项之外④2009年8月《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2款规定:“会员协会、足球俱乐部、足球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相互间,就注册、转会、参赛资格、工作合同、经纪人合同等事项发生的属于行业管理范畴的争议”,属于仲裁委员会的案件管理范围。,还受理对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事项。这就在纪律委员会与仲裁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了内部上诉程序。不仅如此,对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的范围之外的裁决,当事人还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申诉,以更透彻、更审慎地解决体育纠纷。
1.1.3 救济结论的终局化
为卫护体育团体内部救济机制的权威,各体育团体在其章程或章程性文件之中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各个体会员或单位会员放弃诉诸外部救济的权利,无条件接受内部裁决机构做出的决定。如中国足协其内部救济机制所做出的决定便具有终局性,而且,根据其内部多元化的解纷方式,其救济结论的终局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包括一裁终局性、两裁终局性和三裁终局性三类形式。中国足球协会内部救济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足球协会内部救济机制结构图
一裁终局性有三种情形:一是,只能由纪律委员会受理并处理的特殊争议,这规定在《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1款之中,该款允许对纪律委员会做出的某些处罚决定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上诉,但排除了不能提起仲裁而须由纪律委员会终局裁决的特殊争议;二是,由仲裁委员会直接受理后做出的终局裁决,这主要规定在《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2、3款之中,这些争议不受纪律委员会管辖而径直由仲裁委员会予以一裁终局;三是,由仲裁委员会转交给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会议直接处理的案件,《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7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将重大或特殊的案件提交主席会议直接处理,且其处理可不受工作规则之约束。
两裁终局的争议也包括两类:一是,由纪律委员会受理并裁决之后,允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二次纠纷裁决请求的争议,这也就是《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条第1款所规定的一种情况①按2009年3月21日中国足协下发“足球字[2009]108号”文件,即《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第93条之规定,共有8种纪委处理决定可提出申诉。该文件已于2010年3月11日由中国足协下发的”“[2010]93号”文件取消了“试行”二字,成为正式定本,其第93条的规定未作变动。;二是,由仲裁委员会所直接受理的某些特殊争议,并非一裁终局,允许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之裁决向足协执行委员会提起申诉,由执行委员会做出终局裁决。《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62条第3款规定:“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上述范围之外的裁决,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申诉,执行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至于这些争议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章程》只是采取了反面排除法而未正面列举。
三裁终局针对这样的争议类型,即它不属于《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范围内的、并非直接由仲裁委员会受理而应先由纪律委员会处理的争议。此类争议先由纪律委员会进行处理,然后再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上诉,所以已经经过了二级裁决;但它由于同时又是《章程》所规定的、可以由当事人向执行委员会提起申诉的争议,因此,它就历经了足协内部所设立的三级解纷程序,此即为三裁终局制。
1.2 行业外救济机制
尽管各体育组织都主张“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但这并不减损外部救济机制的存在。这些外部救济机制主要有体育司法诉讼、行业外体育仲裁以及其他ADR解决机制。不论这些外部救济机制是否能够为体育团体所客观承认和现实利用,但在世界范围内“法院对这些善意的各类司法外争议解决方式在体育行业内之应用不仅深表赞同,而且通常还积极地予以鼓励”[12]。
1.2.1 体育司法诉讼
诉讼是国家最正规、最常态,通常也是最后的解纷途径。一切法律上具有可诉性的争议都可以追溯到司法诉讼上去,即便是为国家法律所正式承认的仲裁解纷方式,司法机关对它也具有不容剥夺的司法监督权利[13],这是司法诉讼之性质使然。从理论上讲,体育行业的自治不可能限制司法的介入,但在体育实践之中,我国司法介入体育的程度非常有限,司法系统基本上是抱定如下原则进行介入的,即除非争议业已严重到了触犯刑律的程度,否则尽可能地由各体育组织自律解决。近来,中国足坛强劲地掀起的“反赌”、“扫黑”司法行动,也是足坛业已堕落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之时司法才施加救济。司法正义是最后的正义,也是最严肃的救济,它是对一切在宪法上可诉的体育争议进行权威解决的最后手段。
1.2.2 独立体育仲裁
仲裁是一种古老的行业自力救济方式,尽管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需国家立法所确认,但其历史实可追溯到法律产生之前[1]。我国1995年《仲裁法》承认了仲裁的有效性,并为仲裁设定了基本体制。《体育法》也进一步要求建立体育仲裁制度。一些体育组织内部也设立了独有的仲裁机构,但该类仲裁机构明显不等同于《仲裁法》和《体育法》所规定的仲裁机构,特别是由于它在结构上依托于各体育组织,因此往往缺乏必要的中立性。行业外的体育仲裁与之不同,它是在体育组织之外的独立仲裁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行业外体育仲裁机构当推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它甚至成为国际奥委会所指定的、受理产生于或关联于奥运会的一切赛事争议之惟一机构[9]。此类行业外体育仲裁机制所产生的仲裁裁决具有充足的合法性,与一般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在法院具有高度可执行性[4]。
1.2.3 其他ADR方式
其他ADR解纷方式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商、谈判以及有第三人介入的调解、斡旋等。严格地说,体育仲裁也属于体育类ADR的方式之一,但与其他ADR方式不同的地方在于,体育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且其仲裁裁决具有既判力,等同于一般法院的司法判决。其他ADR方式则不同,其产生的结论并不具有直接可执行性,而且在制度化和效率性方面,它们都与体育仲裁相去甚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体育类ADR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同的体育争议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不同争议当事人往往具有不同的追求,体育诉讼和体育仲裁并非万能解纷方式,它们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当事人的特定需要,而诸如和解、协商或调解、斡旋等解纷方式便能够赋予体育争议当事人以更大的自由来掌控且选择纠纷解决的过程。
行业内、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上一起构成了我国现行体育争议解决体制,此种内外结合的体制在理论上满足了法治化的要求。因为,外部解纷机制补足了内部救济机制在中立性、因而在公正性方面的缺陷,从而为体育争议之有效解决并得到司法机关之认同奠定了基础。但非常遗憾的是,此种内外结合的解纷体制在我国体育实践之中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由于两方面原因共同抵消了现行解纷体制作为一个系统有效地发挥其法治化解纷之功能:其一,便是体育组织的过度自我设限,阻碍了纠纷解决的外部过渡与衔接;其二,便是司法机关作为最权威、最强有力的行业外解纷机制仅消极地救济刑事性体育争议,默认了体育组织对民事性和准行政性体育争议的自决权,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体育组织的家长式管理。
2 体育救济现行机制之评析
事实上,一切救济途径在宏观上不外乎三种类型: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此为三位一体的救济结构。我国现行体育救济体制存在结构性混乱,并具体表现在此三种救济途径的各别层面和交互层面。
2.1 自力救济的不足
自力救济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其中立性的不足,中立性乃是一切救济程序的“心脏”[3],是必须得到遵守的自然正义。在现行所有国家的立法之中都明确了这一点,即凡是欠缺中立性的决定均不能获得认可和执行。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多达100多个国家参与的,具有最广泛接受基础的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该公约规定,所有成员国均可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之一,便是程序的不中立。对于体育界而言,在这方面最具有典型性的判例便是CAS所裁决的Gundel vs.FEI案件[14],该案引发了瑞士司法机关对CAS作为一个真正裁决机构所必须具有的中立品质之关切。因为,适时之CAS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和财政供给上均依托于与案件一方当事人即FEI存在利益共同体关系的IOC之中。我国体育组织内部的所谓“仲裁委员会”就先天性地具有此种结构瑕疵,它依托于体育组织而建立,而当争议涉及对该组织或者组织的代表或代表机构时,其内部仲裁委员会的中立性就会受到相同的质疑。尽管在Gundel案中,瑞士司法机关承认了CAS的中立地位,但婉转地表达了改革的期望。IOC随后便新设了ICAS,由其作为CAS的依托,避免IOC直接成为CAS的挂靠机构,以此实现CAS的中立改革[7]。但我国体育组织的仲裁机制仍然在其组织之内,其中立性缺陷造成解纷过程及结论具有严重的法治危机。
组织之外的仲裁机制直至今日仍未成立,而其法律依据却早已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之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自该法1995年公布施行之后至今长达15年的时间之内,仍然不曾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在中国足协等体育组织内部所建立的仲裁机制又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所规定的仲裁机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立意来看,它所要求建立的仲裁机制显然应当是具有与一般商事仲裁机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解纷机制,其设立应当满足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0条之规定,即不应当由体育组织径直设立,而应当由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协会统一组建,且应当经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司法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各体育组织内部未经登记和批准,而仅通过内部决议或决定建立起来的仲裁委员会显然不具有此等法律地位,相应地,其裁决之独立性和有效性就难以得到法律保障。
2.2 行政救济的过度
独立的自力救济机制缺乏,而非独立的自力救济机制却又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剩下的有效救济方式便只剩下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了。体育协会等社会团体在性质上是民间机构,它不等同于行政机关的下属或分支机构。尽管其设立需要经过行政审批和登记,但这并不改变体育组织的法律性质。这在各体育协会章程之中都有明确规定。例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3条分两款精准定位了中国足协的法律性质及其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首先,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惟一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其次,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单位会员,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从这一定位来看,中国足协是自律组织,行政机关不应深度介入,它只能通过监督与指导的方式对足协的管理事项予以行政救济。但在中国足协的实践运作之中,行政机关的介入过于深入,中国足协的人事、财务和活动都难以清楚地与行政机关分离开来。后果便是,中国足协在一定程度上质变成为行政机关的延伸或附属,行政救济贯穿在自律性救济中。中国足协的做法具有普遍性,在中国其他体育组织内部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行政化倾向①这种”泛行政化“的倾向在我国民商事仲裁乃至司法诉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其历史根源。参阅汪祖兴.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境遇及其改革要略[J].法学研究,2010,(1):112。。行政救济的过度干预压迫了体育组织的内部救济,而此种僭越和干涉更严重的后果便是,它还在实践层面挤压了司法救济的介入。
2.3 司法救济的保守
在自律救济缺乏独立性和自律性、行政救济又出现深度介入的情况下,要对行政力量予以平衡、赋予体育争议之处理以法治性的惟一力量、也是惟一有足够力量的救济,便是司法救济。我国的治理体制是行政推进型的模式,行政推进型模式依赖行政机关的智慧、活力、胆略而富有成效地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但体育行业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体育组织在本质上作为体育行业自治和自理的主体,能够促使体育行业的发展合规律地进行。行政必要的推进是合理的,但行政过度的介入则是应予限制的。在我国行政介入体育自治团体已然过深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基于各种原因更愿意操持一种保守的司法态度,它充分将自身的司法职能之一部分“信托”给行政化的体育组织由其按照行政救济的方式予以处理。如果深究司法机关此种保守司法的内因,可能有二:一是,对行政力量的尊重和信任;二是,为维持各种救济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行政救济强势扩展的情况下只恪守消极司法原则。
2.4 交互救济存在的问题
“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三者之间本应维持一个合理的关系,以实现各别救济机制的分工与衔接,整合各别救济机制的优势特长,不仅合法,而且合情、合理,且尊重体育业规律地消解体育争议。但各别救济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双重意义上受到消极扭曲:一方面,由于各别救济机制作为交互关系合理持续之基础,而这些救济机制又存在上述之障弊,要建构合理有序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就首先缺乏各别基础;另一方面,我国体育立法缺乏对这些各别救济机制之关系的清晰厘定,只是笼统地存在着这样的救济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如何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体育实践方面,最具有话语权的司法机关又坚持“沉默是金”、消极退守的司法态度,这就使各别救济机制的交互关系既缺乏立法规范,又缺乏司法判例的指导。就三类各别救济机制的关系来看,无外乎分工与合作两种类型。
2.4.1 分工障碍
分工不仅是为了效率,它还体现了自然正义。不同的救济机制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此种比较优势本质性地限定了它的功能应用范围,而它的应用范围不仅表征着一种合法性,而且,也表征着一种合理性。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合理性。合法性是更宽泛的概念,某些救济机制可以被合法地利用来解决某些争议,但它并不一定非常适合解决此类争议,这就还需要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合理性的问题。合理性是更严格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争议解决合乎法理,更要合乎事理和情理。以仲裁为例,它所解决的争议必须满足法定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①可仲裁性的评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争议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而产生的主体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personae);二是,基于争议本身而产生的客体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 ratione materiae)。参阅Philippe Fouchard,et al,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 rbitration[M].Edited by Emmanuel Gaillard,John Savage.Beijing:CITIC Publishing House,2004:312-313。;在法定可仲裁性之上还有一个合理可仲裁性的问题,即所谓的“宜裁性”或“适裁性”。这就对救济机制之间的分工提出了两种境界的要求:一是,法定分工;二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合理分工。
在解纷止争的功能发挥上,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与自力救济各得其所:某些争议只具有自力救济的资格,而不能诉诸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在体育业范围内最典型的例子当数体育运动规则(rulesof game)[8];某些争议只能通过行政方式解决,而不具有自力救济性和司法诉讼性;而绝大多数情况下,争议都具有可诉讼性,毕竟司法解决争议是国家宪政所确立的基本维度,也正是因为司法救济的此种宪政根基直接产生了司法保障不容剥夺的基本原则。这是三者分工的法定维度,从合理分工的角度来看,就要求对某些具有普适性的争议即至少可通过两种乃至三种救济机制予以解决的争议进一步分析,以在各救济机制之间确定最佳解决机制。以体育转播合同争议为例,该争议既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也可以由仲裁机构解决,还可以进行司法诉讼,如果双方当事人追求争议的快速、弹性和友好地解决,那么,无疑选择自力救济最为合理;而如果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友好解决争议之善意,而希望得到正式权威的裁决,那么,最合理的解决机制就是司法救济了。
我国现行体育救济体制下,各救济机制之间的分工是极不健全的,表现在:第一,自力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并无明确的分工界限,在实质层面表现出行政救济干预、左右乃至直接决定自力救济之态势,由此形成的基本格局是有行政救济而无自力救济。第二,自力救济与司法救济之间分成两大方面,刑事方面专属司法救济范畴,民事方面则基本没有形成分工,采取统一的自力救济而无司法救济。第三,由于自力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的实质同一关系。因此,在我国现行体育救济体制上的分工便具有事实上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关系:体育刑事问题由司法管辖,所有行政、民事乃至某些轻微刑事问题由行政管辖。最尊重体育行业个性、最强调体育业自治和最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自力救济途径基本上为行政救济所“监护”,未得到充分应用,特别是作为行业自力救济类型的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至今未曾建立。
2.4.2 合作障碍
在各救济机制之间的合作问题上,特别具有法治化精神的要求,是应当在所有救济方式之后打开通往司法救济之门户,而不是予以限制或者禁止,此即为“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之需要[8]。由于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的价值取向重在效率、成本之考虑,但基本正义之捍卫又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国家进行的公共选择,因此,各国在其立法体制之中于确立自力救济与行政救济之正当性后又都重申了司法最后救济的必须性。这就要求,一切司法救济之外的其他救济机制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之机会,即便是在某些法律规定必须保留给自力救济和行政救济范围之内的争议,它们也应接受司法审查。
如体育行业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运动规则”便是一个合适的考察样本,它是否应当豁免于司法审查之救济,其历史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司法救济的不可豁免性。何谓“运动规则”,马克斯·库默尔(Max Kummer)最早将之界定为:“一种规则,违反该规则将受到参与该运动的不利处罚。”[10]库默尔本意是为了缩限体育组织的自治权限而区分“法律规则”(rules of law)和“运动规则”(rules of game),以此方式为体育组织限定一个自治的范围。但就在这个库默尔认为理当属于体育组织自治权限的运动规则问题上,瑞士、德国乃至CAS都纷纷以判例的形式表达了这样一种共识:运动规则本身属于体育组织自治的范畴,但是运动规则之判断与运用方式,则由于涉及争议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和人格权(personality rights)而必须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就是说,在当代体育争议的司法救济立场上看,区分法律规则与运动规则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每一个受运动规则约束的人都可以请求一个独立的机构确认该规则是否得到遵守。这包括对裁决或者向国家法院或者——如果有的话——向仲裁机构提起上诉”[10]。这一结论表明,所有体育业涉及的争议都不能完全免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而这就相反说明了,在救济体育争议的问题上应当建立起“自力救济和/或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之间的合作关系,敞开“正义通道”,步出“柏拉图之洞”[2],接受司法正义之光的普照。
以此审视我国现行体育救济机制之间的合作关系,就能够发现其问题之所在,这便是它试图垄断性地解决体育争议。各体育组织纷纷在其章程之中明令禁止其成员将争议诉诸司法救济,表现出“自力救济和/或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之间的人为隔离。例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62条第1~5款以严厉的措辞要求各成员放弃司法救济、恪守行业救济,其方式有3类:1)正面明确要求各成员放弃司法救济,其第1款规定:“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其他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业内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2)反面明确规定其内部救济具有最终法律效力,其第2款规定:“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最终决定,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第3款规定:“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上述范围外的裁决,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申诉,执行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3)对违反上述规定者予以惩罚,即如果成员违背上述关于争议解决之规定而擅自提出外部救济请求的,将受到中国足协的处罚。不仅如此,足协及联赛组织均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成员予以遵守。这便是该条第4、5款之规定。此外,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4条再次强调了其裁决的终局性,申明仲裁委员会在处理纠纷案件时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体育组织的此种“家规家法”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如果司法救济在实践中只是对体育刑事问题采取有限介入态度的话,那么,体育组织的这种没有法律效力的做法也就在现实意义上得到司法机关的默认和纵容。以此方式,我国体育救济机制之间的通畅合作关系就断裂开来,体育民事及行政争议由于缺乏获得司法审查的机会而出现法治退化乃至反法治化的现象。长久以来,体育组织在治理内部争议时采取的行政作风不是从根底处消解了争议,而是以压抑的方式积累了民怨。体育从业人士也因为习惯了这类脱法化的治理方式而淡化乃至遗忘了本应具有的法治意识,在体育业、体育组织这样一个“法外空间”之中过惯了“逍遥法外”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后,直至他们触犯到了刑事法律而涉嫌犯罪时,司法介入的强势救济才让他们悔之晚矣地感受到法律存在的真实性。反思之,如果行业自力救济能在日常的体育民事及行政争议问题上敞开其通往司法救济的道路,在体育案件的日常司法处理之中对法制存在的意识、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为权利而斗争的自觉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对从业人士起到潜移默化的法治教化作用,提示法律尊严不容践踏,那么,以这样的预警方式很可能会提醒他们遵守法律而不至于涉嫌犯罪。这也是体育救济机制之间合作关系被非正常割裂而丧失法治教育与犯罪预警功能所导致的恶果。
3 体育救济法治化的中国之道
3.1 建构均衡的三位一体救济框架

图2 体育救济机制理想框架图
3.1.1 救济框架的理想设定
救济机制的法治化改造必须先行搭建合理的救济框架,在搭建出均衡合理的救济框架这一宏观结构后,进一步的问题才谈得上对各别救济机制之补善。合理的救济框架首先应当满足均衡化的特质,即应健全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实现三者制度化的分工与衔接。按照法治精义,可对体育救济框架作如下理想设定。
3.1.2 救济框架的立体展开
救济框架由三大板块的救济机制所构成,分别是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和“仲裁+诉讼”组成的独立救济。自力救济包括争议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体育组织内部纪律委员会的处理以及可能存在的内部仲裁等。行政救济涉及两大方面的争议:或者是直接诉诸行政机构进行裁决的争议,或者是历经体育组织内部救济机制之后允许再次向行政机关提起申诉或复议的争议。独立仲裁与司法救济都具有专业性、独立性和司法性品质①仲裁既具有契约性,也具有司法性,它表现出某种混合的性质。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从仲裁的生成与启动角度来看,仲裁具有契约性;从仲裁的行使与运作来看又具有司法性。参阅张春良.国际商事仲裁权的性态[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2):21。,是最权威和最公正的体育救济机制。三类救济机制彼此形成“品字形”结构,组合成立体的体育救济机制。特别重要的是,由于独立仲裁与司法救济最具法治精神,因此,它们成为这个立体救济框架中的核心部分,其他救济机制都可以向之敞开,通过它们指向终局裁决,弥补现行救济机制下自力救济与行政救济直接短路、架空独立救济机制的弊端。
3.1.3 交互关系的合理厘定
在三大类救济机制的彼此关系状态下,含有这样几种终局裁决情形:第一,一裁终局型,即对于能够通过体育组织自力救济便得到合理解决的争议,当事人不再启讼端,承认该内部裁决之终局性。此外,对于法律规定必须经由行政机关裁决、或者当事人合法地提交行政机关裁决的争议,在行政机关裁决之后,当事人接受裁决而不生讼端的,承认该裁决的终局性。
第二,两裁终局型。一是,经体育组织内部自力救济之后,当事人不服而选择向行政机关请求行政救济的,行政机关做出裁决,当事人接受裁决,则承认该裁决的终局性。二是,经体育组织自力救济之后,当事人不服而选择向司法机关请求救济的,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即应承认该裁决的终局性。三是,经体育组织内部自力救济之后,当事人不服而选择向独立仲裁机构请求仲裁的,仲裁机构做出裁决,即应承认该裁决的终局性。四是,当事人依法将体育争议提交行政机关裁决,行政机关做出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向司法机关提起审查请求的,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即应承认该裁决的终局性。
第三,三裁终局型。当事人经过体育组织内部救济之后,不服体育组织之裁决,而选择向行政机关请求行政救济;行政机关做出裁决后,当事人不服再次向司法机关请求审理,司法机关做出裁决后,即应承认该裁决之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法律另有硬性规定,否则应当确保所有经过体育组织内部救济及/或行政救济的争议之当事人拥有接近司法救济或仲裁救济之机会,这是“接近正义”的法治精神之要求,同时,也是对基本人权的捍卫。易言之,行政救济和体育组织自力救济都是非自足性救济机制,行政救济之所以缺乏终局裁决权威在于其本性使然。因为,行使裁决权并非行政机关之本职使命,而是其根据立法规定对特定类型的争议所具有的附带管辖职权;体育组织自力救济之所以缺乏终局裁决权威则在于其救济机制的非独立性。因此,在各别救济机制的交互关系之间,一方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允许他们对纠纷救济机制行使必要的选择权限;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尊重体育组织的自力救济权限;与此同时,更应当确保这些救济机制对中立救济机制保持畅通,突破传统的闭锁结构,建设开放性的自力救济机制。
3.2 实现自力救济的理性化
在行业自力救济方面要禁止两种非理性倾向:一是,维持现状的极端保守态度;二是,完全摒弃行业自助的轻率立场。只有建构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行业自力救济之合理性和优越性效应,又能够自觉到自力救济之不足而允许在外部救济之中得到完善的制度安排,才算得上是理性因而理想的自力救济机制。
行业自力救济之合理性源自于行业自我管理的合理性。体育行业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和发展规律,由体育组织自行管理其事务能够尊重体育规律,按照最适合体育管理的方式来治理体育业。体育组织在治理体育业时所根据的规则不是生硬地来自于外部的规则强加,而是来源于体育实践,是将体育实践直接翻译成为体育治理规则。这是一般法律规则适用于体育业时所不及的地方。为此,应当为体育组织自力救济机制保留两大权限:一是,特定问题的终局决定权;二是,程序必经权。
特定问题的终局决定权,是指由体育组织对某些特定争议享有排他的管辖权和最终决定权。此类问题主要是“赛场裁决”和“运动规则”之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在悉尼奥运会期间,CAS特设分庭在仲裁Bernardo Segular vs.IAAF案件时,被申请人IAAF提出答辩认为CAS仲裁庭不能审理这个案件,因为它涉及技术性规则或运动规则。仲裁庭明确指出:“CAS仲裁庭不会审查由负责实施运动规则的裁判员在竞技场上做出的裁定[除非该规则是因恶意(bad faith)而实施,如是因为贿赂而得之结果]。”[11]可见,纯粹关于运动规则之理解和运用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是完全保留给体育组织进行管辖和裁定的,而中立仲裁包括司法救济机制最多只能审查该规则的运用方式是否违法。
程序必经权,是指外部中立救济机制在受理针对体育组织内部自力救济所产生的裁决而提出申请的案件时,可以采取“穷尽内部救济”原则[8],要求首先穷尽该体育组织的内部救济机制,在纠纷仍然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再予受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一是,充分尊重了体育组织的内部自治权,以此友善态度降低了体育组织对抗外部救济机制的敌意,并缓和了对后续裁决可能存在的不合作;二是,有效发挥了行业内救济的效率优势,通过其内部处理之后,即便不能解决争议,但至少可以对争议进行初加工乃至半加工,发挥其作为中端解决措施的分流与缓解功能,为外部救济机制整理争点,消除局部分歧,以提高外部机制解决争议的效果。
3.3 实现行业救济的中立化
行业救济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行业救济即指特定体育组织内部的救济机制;广义的行业救济还应当包括具有准司法性的外部独立仲裁机制。就广义的行业救济而言,要在中国实现其中立化当指两方面的措施:一是,根据《体育法》之规定尽快建立独立的专业性体育仲裁机制;二是,对各体育组织内部的仲裁机制进一步强化其中立品性。
3.3.1 独立仲裁之建设
3.3.1.1 独立仲裁机制的合理性
中国的独立体育仲裁机制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建设起来,因此,理论界固然认为仲裁重要,但无法利用其比较优势来化解体育纠纷,这是体育仲裁无为的根本原因。虽然在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3条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但国务院迄今仍未做出正式规定。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是,我国体育治理的行政本位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行政机关不愿放权,体育行业缺乏自律;二是,我国整体缺乏仲裁文化环境,即便是相对成熟的民商事仲裁机制之建设与完善,今天仍然在理论与实务界纠缠着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问题①学者指出,仲裁机构的民间性问题在立法和理论上业已论定,只是由于我国行政推进性的社会传统使实践中的仲裁表现出行政化的倾向。行政力量如果一方面缺乏自律,另一方面又缺乏制约,那么仲裁的民间性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它只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立法和理论定性的问题。参阅汪祖兴.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境遇及改革要略[J].法学研究,2010(1):112。;三是,我国体育仲裁的实践和经验非常匮乏,制定体育仲裁法规尚欠缺足够的经验基础;四是,社会层面及体育界错解体育仲裁之本意,误将各体育组织内仲裁机制理解为独立体育仲裁机制,因而,压抑了建立独立仲裁机制的积极性。
然而,从法理角度来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是救济体育争议最有效的机制②有文指出,“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一个弊端就在于司法诉讼时间长,不能适应迅速、公平地解决体育纠纷的需要。在陶景洲眼中,仲裁最大的优势是快,除非特殊情况,必须在24小时内做出裁决。法院审判人员本身不具备体育专业知识,在审判时可能会有失偏颇,难以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参阅刘效仁.奥运能否加速体育仲裁立法[N].法制日报,2008-08-21,载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wzx/ fzxw/200808/20080800051693.shtm l,2010-11-10访问。,也是体育救济机制法治化方案中最应强调的部分。理由如下:第一,体育仲裁机制能够融贯体育仲裁的专业性和普通仲裁的中立性,实现知性与德性的“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之所以要求在普通商事仲裁机构之外建立单独的体育仲裁机制,其深层用意在于它充分考虑到了体育争议与普通民商事争议的特异之处,这便是体育争议通常涉及“处罚性”争议,事关行政法乃至刑法法理③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设分庭前任主席曾指出,“在与体育实践相关的争议中,被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通常不是从诸如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合同法律规范抽象出来的,而是从刑事性或行政性法律规范中获得根据,例如无罪推定原则(nulla poena sine lege)和疑罪从无(in dubio p ro reo)原则”。参阅Gabrielle 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s:Issues of fast-track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M].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100-101。。这就决定了普通商事仲裁机制应用于体育争议的不适切性。而建构出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一方面,可以确保其具有胜任处理专业体育争议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又可以贯彻它与一般商事仲裁机构所共有的独立品性,从而实现知性和德性的共和。
第二,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广义的行业自治,因此,能够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实现自治与法治的兼容。仲裁在本性上即为行业自治的产物,只不过此行业意指大一统的行业而非某个或某些体育组织。因此,体育法所指的体育仲裁机制一方面是位于各具体的体育组织或协会之外的独立仲裁机制;另一方面,它却又是位于整个大一统体育行业之中的自治机制。此种身份上的辩证属性使得它更容易在具有对立关系的体育组织自治与外部司法救济之间产生一种奇妙的缓冲功能,同时,为对立双方所接受而又能兼容对立双方各自的优势。
第三,统一的体育仲裁机制能够整合散见于众多体育组织之中的、彼此平行的自力救济资源,实现权威与效率的兼美。各体育组织之间的条块分割连带着导致其内部的救济机制也存在条块分割的散乱情况,众多的内部救济机制产生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并没有赋予这些救济机制以正式的终局效力,既无权威,也无效率。建立统一的体育仲裁机制无疑可以高度整合体育行业内的离散资源,凝聚行业精英,推动体育争议的统一解决。一方面,可以提升争议解决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树立了裁决结论的权威性。
第四,统一而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还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体育仲裁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如同中国正在经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折的伟大时刻[5],中国仲裁也应当自觉地从仲裁大国向仲裁强国转变。在体育仲裁方面,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形成一个“一超多强”、“多极化发展”的秩序。CAS的超级地位是任何仲裁机构都无法撼动的,特别是它作为IOC惟一指定的奥运会争议解决机构。此外,日本、加拿大、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英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专业体育仲裁机构[6]。相比于中国体育仲裁机制只驻足于倡议与呼吁阶段而言,这些国家的体育仲裁机制之发展及其竞争能力已然占据了先发优势。中国体育强国的成功转型、体育业的繁荣勃兴、世界体育市场的占有、体育世界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体育仲裁业的世界竞争都离不开体育仲裁机制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体育仲裁机制要担负起如此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就只有走高度集中、强化资源整合、独立而专业的大一统体育仲裁机制的道路。
3.3.1.2 独立仲裁机制的建构方案
限于篇幅及主旨,此处仅钩玄提要地扼述独立体育仲裁机制的建构思路。总体而言,我国可资鉴CAS的优势经验转化为中国国际体育仲裁院(Chinese Court of A rbitration for Spo rts,简称为CCAS)的有益参考。考虑到体育界、社会各界的认可度以及制度上的可操作性,我国独立体育仲裁院(CCAS)之建构可采用两种方案:一是,走商事仲裁与体育仲裁兼容的道路,依托中国仲裁协会建构中国体育仲裁院;二是,依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建立独立且专业的中国体育仲裁院。
第一种方案可有效转化利用商事仲裁的既有资源与经验,优化体育仲裁的品质,也能彻底避免体育仲裁机构与体育组织之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避免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或干预,但专业色彩不够,且没有表现出体育仲裁由体育界实现行业自治的本色。
第二种方案体现了民间性、专业性、独立性和自治性的有机结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全国群众性的体育组织,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由其设立的体育仲裁机构因此具有民间性;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体育专业方面的民间组织,它能尊重并按照体育规律来专业性地建设仲裁机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单项体育运动组织的社团法人,只受国家体育总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而非由其直接领导,这能保障体育仲裁机制的独立性;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是中国体育从业者的共同家园,它是体育界的自治组织,其所设体育仲裁机制也就能确保其行业自治性。
第二种方案相比于第一种方案更具可操作性,但它所设立的仲裁机制也将面临一个CAS类似的问题:即该仲裁机制由于处于体育界之内,因此,始终在经济、财政及人事安排上与各单项体育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CAS虽然在经费方面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支持,然而,在此种情形下,它却具有比较的独立性,我国可依用此模式之经验提升并优化中国体育仲裁机制的独立性。考察CAS的独立构造,它主要通过三大制度安排实现了中立化:新设ICAS从IOC之中接管并独立负责维持CAS的运转,使CAS赢得了更独立的身位;仲裁员名单准入、自我披露与独立性承诺共同预防了审前有损中立性的可能;仲裁员回避、撤换与替换制度则担保在组庭之后能有效救济仲裁中立性瑕疵①关于这三大制度的具体展开与安排,有文章已经做了详细介绍,可参阅张春良.CAS仲裁中立原则的制度安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2):108。。这些经验具有直接可借鉴性:首先,在设立结构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以此作为依托可捍卫体育仲裁机制的独立性,实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各体育组织与该仲裁机制之间关联性的间接化和弱化。其次,在仲裁员聘任、仲裁员选任、仲裁庭瑕疵救济方面,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回避、替换、撤换制度。
3.3.2 内部仲裁之改造
在各体育组织之外而又在体育整体行业之中建设独立的体育仲裁机制,这是最彻底、最完善的实现行业救济中立化的方案。除此之外,为更有效地发挥各体育组织内部救济机制的解纷功能,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推动这些内部救济机制的中立性改造。毋庸置疑,这些内部救济机制因其依附性而不具有标准法律意义的独立性,但它们可以在体育组织内部相对于其他机构维持一定的独立性。具体改造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首先,在依托机构的选择上,为避免内部救济机制受到过多干预,同时为提高其权威性,可以将主管争议解决机制的机构设定为体育组织内部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些最高权力机构一般为体育组织的会员大会,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则由特定的委员会如中国足协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在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则另有特设机构如中国足协的主席会议负责。体育组织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当归属执行委员会或者主席会议等高级机构直管,从而使它较少受下设机构的干扰或牵制,确保其超脱地位和由此具有的中立身位。其次,在人事任免暨仲裁员的聘任上,应由依托机构根据专业知识、法律素养、道德秉性而非其他身份或职务方面之考虑予以委任或聘任。这些愿意接受仲裁员聘任的人士应当仿效商事仲裁机构采取中立承诺书签署制度,要求他们承诺恪守仲裁员职责,确保公正、独立地裁决案件。再次,在仲裁程序的设计及其具体展开方面,也应当尽量仿照一般独立仲裁机制的方式,建构出良好的仲裁前、组庭中和组庭后的中立制度安排[7]。据此,最大限度地弱化内部仲裁机制的非独立性缺陷,赢得争议当事人对其处理过程及结论的尊重和接受。
3.4 实现司法救济的通畅化
由于“司法保障不容剥夺”原则关涉基本人权,也是法治精神的根本体现。因此,在完善我国体育救济机制、实施法治化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各种救济机制能够通畅地抵达司法救济。在理解和践行司法救济的问题上,必须把握其如下涵义:
3.4.1 司法救济只是一种机会保障而非必经程序
实现司法救济的通畅化,并不是要求、也不是鼓励所有体育争议都应当最终诉诸于司法救济。这种通畅化保障只是为有必要寻求司法救济的争议提供可能的机会,而不是说司法救济是解决一切体育争议的必经程序。将司法救济设定为必经程序会有消极后果:一是,导致司法救济之前的一切救济成为一种摆设,浪费程序资源,也极大地减损解纷效率;二是,导致诉讼积累、诉讼爆炸,司法救济机关将不堪讼累,最终致司法救济机制梗塞失灵。因此,实现司法救济的通畅化,其真正含义并不是要悬搁一切其他救济机制之功效,而只是为一切争议之解决提供司法救济的可能机会。相反,如果其他救济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分流与解纷止争的功能,司法救济能够做到“无为而治”,才是其追求的上善之境。
3.4.2 司法救济是一种广义救济而不限于诉讼救济
司法救济并不等同于诉讼救济,广义的司法救济强调从本质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解纷机制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而不是从主持解纷机制的机构来简单判断。展言之,只要一种法律认可了的救济机制能够中立地审断纠纷,就是广义法治的体现;只要一种救济体制能够为一切争议提供这样一种中立审查或复查的机会保障,这也就是司法保障不同剥夺的广义理解。这是对法治的功能而非机械的形式理解。以此标准审视之,为体育争议提供司法诉讼救济显然是法治精神的体现;同时,为体育争议提供一种中立的仲裁救济也依然是法治精神的体现。所以,保障体育争议的司法救济之通畅化既可以为其提供通往诉讼救济之途,也可以为其提供通往仲裁救济之道。当然,此处所谓的作为法治精神化身的仲裁救济不是体育组织内部建立的非独立的仲裁机制,而是指超越各别组织之外的独立的仲裁机制。
以这样的见解来审视《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11章所规定的两种仲裁救济条款,就可以看出二者实是“貌合神离”。该章共两条即第61条和第62条,第61条是对涉及国际足联、亚足联的争议规定的处理方式,即当事人应援引国际足联、亚足联章程中所规定的仲裁条款,不得将任何争议提交法院,而应将争议提交各方认可的仲裁委员会,并接受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第62条是对中国足协内部争议规定的处理方式,即应将业内争议提交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而不得向法院提交。这两条规定的措辞与行文几乎完全相同,但第61条符合法治精神因而是有效的,而第62条则违背法治精神因而是无效的。
查阅国际足联、亚足联的章程①国际足联FIFA在2002年即在其章程中明确指定CAS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种做法使CAS仲裁机制成为FIFA框架内的制度化解纷机制,只要是FIFA的会员,或者参与FIFA所承办的赛事者,都自然地适用该解纷机制。参阅Keba Mbaye.Introduction to Digest of CAS Awards III 2001-2003(A).Digest of CAS Awards III 2001-2003(Z).Edited by Matthieu Reeb.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它们所援引的仲裁机构并非“仲裁委员会”②需要指出的是,我国1995年《仲裁法》无“仲裁机构”,而只有“仲裁委员会”的称谓。此种称谓具有中国特色,在国际仲裁界,一般称“仲裁机构”而不是“仲裁委员会”。CAS就是一仲裁机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套用我国仲裁委员会的概念来指称CAS,是一种用语不当。,而是在瑞士注册的独立仲裁机构即CAS,该仲裁机构不是国际足联、亚足联的内部仲裁机构,也不是IOC下设仲裁机构,它的独立身位使它的救济性质符合法治精神,因此,《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61条规定的仲裁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但第62条所指向的仲裁委员会不是独立于中国足协的仲裁机构,而是中国足协的内设机构,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所谓“仲裁委员会”的独立身份。我国立法认可仲裁条款具有排除法院管辖的效力[15],但该仲裁条款所援引的必须是独立的仲裁机构,以中国足协的内部仲裁机制来终结争议之处理也就不符合法治精神。简言之,CAS作为一种独立的仲裁救济是法治化的救济;而中国足协内部仲裁救济因其非独立性而不合法治要义。
3.4.3 司法救济是一种法定救济而非全能救济
有序秩序之形成并非独赖于法律本身,在法律之外尚有道德、纪律与行规等行动准则。司法救济是一种法定救济,它的应用范围及其具体运行都具有局限性,即局限于法定范围之内。当一种行为属于道德、纪律与行规的调整范畴时,应谨慎地维持司法的不介入。这就决定了司法救济并非一种全能救济。以体育争议为例,某些体育争议仅属于行规调整范畴而不属于仲裁或法院救济的类型,某些体育争议甚至也不属于体育组织内部的仲裁管辖范围,而属于纪律委员会的专属管辖③如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第93条之规定,只能由纪律委员会受理而不得提交仲裁的争议类型包括8类:1)停赛或禁止进入体育场、休息室、替补席6场或6个月以上;2)退回奖励;3)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4)取消比赛结果、比分作废;5)联赛扣分、禁止转会、降级、取消比赛资格、取消注册资格;6)进行无观众比赛、在中立场地进行比赛、禁止在某体育场(馆)比赛;7)对赛区罚款2万元以上、对俱乐部(队)罚款5万元以上、对个人罚款1万元以上;8)其他更严重的处罚。。在体育组织内部救济、仲裁救济与司法救济之间,一个总的救济分工规则是:运动规则本身豁免于外部救济。但这一规则本身附有条件限制,在特定情况下,外部的仲裁乃至法院仍然可以介入救济。
以足球运动中的“越位”为例。有关“越位”的理解、界定和判罚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运动规则或技术规则,它完全由体育组织所委任的赛场裁判员所管辖,非属于司法救济的对象。但是,如果涉及赛场裁判员在解释、判罚“越位”时显失公平,具有明显的偏袒性和歧视性,则如CAS之类的外部独立的专业仲裁机构可进行介入救济。如果该裁判员在判罚“越位”时有操纵比赛、参与赌博的嫌疑,且其程度触及刑法规定的标准,则不仅体育组织内部救济机制不得垄断管辖,即便是外部仲裁机制介入救济也不能阻止法院的管辖。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这是国家立法赋予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而不仅仅是可为、可不为的法定权利。
从上述例子可以简要得出司法介入救济的标准,这一标准是看体育争议所涉规则的三大要素:功能、性质及其程度。首先,就规则的功能而言,如果该规则纯粹只关涉运动本身,而不涉及运动之外的,有关该规则本身所产生的争议属于体育组织的自治范畴,而不能诉诸外部仲裁救济和法院救济。其次,就规则的性质而言,如果该规则不能被兼容合并入法律规则之中,而在法律之外,则基于该规则本身所直接产生的争议应属自治范畴。但如果该规则在效果上延伸入法律规则的调整范畴,则可提交仲裁及法院司法救济。最后,就规则所生争议的程度而言,如果该规则不仅在效果上被并入法律规则调整的内容,而且在程度上超出了民法治理的界限而触及刑法规定的,则该争议应由法院排他地进行救济。
当然,上已述及,由于运动规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区分已经出现了相对化的趋势,二者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别,因此,上述标准也可转化成这样的表述:第一,但凡民事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都属于体育组织内部救济的范围,外部仲裁及法院诉讼均不发生;第二,但凡民事法律有所规定而没有触及刑事法律规定的地方,既可以由体育组织内部救济,但不具有终局性,也可以同时由外部仲裁机制或者法院予以介入救济,是否诉诸外部救济,是诉诸外部仲裁救济还是外部法院救济,则由当事人之间自主决定;第三,但凡超出民事治理而进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之争议,则应由法院独占介入救济,体育组织及独立仲裁机构只能就该争议在其职能范围之内做出诸如取消比赛成绩之类的有效处理,但不能排除法院的司法介入,其刑事责任将由法院依照公职权追诉之。
由上可见,在体育救济法治化方案建设中,司法救济是其结构上不可或缺的终端环节,但不应将其设定为必经的程序环节,更不能将其视为实现法治理想的最佳方案。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法治,并指导体育救济机制的法治化建设,那么它就与金色的法治之途背道而驰了。将司法救济作为悬临于一切救济之上的可能机会,为各种救济机制打开通往司法救济的道路,为那些有需要且有必要的争议当事人确保司法救济的机会,并在此前提之上努力提升整体救济机制化解纠纷的系统功能,最终不是追求司法救济的繁荣而是致达司法救济无为而治的状态,实现“刑措”而“礼乐兴”的歌舞升平之清明世界,这才是司法救济,也是体育救济法治化方案的善之善者。
必须强调,法治化并不是“格式化”,格式化是毁灭,是否定一切后的完全虚无;法治化是建构,应立足本地资源,接通特定处境的“地气”,才谈得上收拾破碎河山而成礼乐秩序。中国体育救济机制的法治化方案因此不应激进地追求制度革命,试图抛弃中国现有制度基础而单纯“复制”外国法治图景;而应当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激愤,让现有救济机制从残缺破败之中内在地开展出法治之“光”,生长出均衡的法治化机体。惟有如此,法治化的救济机制才能治疗中国体育行业的人治痼疾;也惟有如此,法治化的救济机制才担负得起重振我中华体育煌煌伟业之重任。
[1]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
[2]刘想树,张春良,周江,等.国际体育仲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0.
[3][美]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M].齐海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240.
[4]石现明.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科学,2008,28(6):67-72.
[5]于善旭.我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法治进路[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9,24(2):99-103.
[6]于善旭,张剑,陈岩,等.建立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5,25(2):4-11.
[7]张春良.CAS仲裁中立原则的制度安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0,25(2):108-112.
[8]张春良,张春燕.论国际体育仲裁中的“接近正义”原则——接近CAS上诉仲裁救济的先决条件[J].体育文化导刊,2007,(11): 72-77.
[9]张春燕,张春良.CAS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审模式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8,23(1):46.
[10]FRANK OSCHUTZ.The A rbitrability of Spo rt Disputes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C].IAN S.BLACKSHAW,ROBERT C.R.SIEKMANN and JANW ILLEM SOEK.The Court of A rbitration fo r Sport(1984-2004)[M].Hague:T M C Asser Press,2006:201.
[11]GABIELLE KAUFMANN-KOHLER.A 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s:Issuesof fast-track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 [M].New York: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24.
[12]IAN S.BLACKSHAW.Sport,Mediation and A rbitration[M]. Hague:T M C A sser Press,2009:16.
[13]JUL IAN D M L EW,LOU KAS A M ISTEL IS,STEFAN M KROLL.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 rbitration [M].Hague:Kluwer International Law,2003:356.
[14]MA TTH IEU REEB.The Court of A rbitration for Sport:History and Operation[C].MA TTH IEU REEB(ed.)Digest of CASAwards III(2001-2003)[M].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4:1.
[15]MARGARET L.MOSES.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 rbitratio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17.
Discussion on Sport Disputes Relief Ruled by Law
ZHANG Chun-liang
No relief,no rule by law,and no relief ruled by law,no spo rts ruled by law.In legal theory,there are such two kinds of relief as relief in and out of the sport association in China, but in p ractice,the relief out of the spo rt association is not enough,and that in the spo rt association is of the handicapping effects.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po rts relief ruled by law,this paper tries to establish a balanced spo rts relief system including self-relief,administrative relief and judicial relief,and imp rove individual relief system and make each relief system take mo re active part in spo rts relief and cooperation in rule by law.The relief system doing no thing is the best system in the spo rts ruled by law.Rule by law is not fo rmatted,and the issuesof China should be resolved by Chinese style.Therefore,rule by law imp roved in Chinese w ay is the only method to revive Chinese spo rts.
sport ruled by law;self relief;administrative relief;judicial relief;access to justice
G80-05
A
1000-677X(2011)01-0019-10
2010-10-26;
2010-12-18
中国法学会2010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自选课题(CLSD 1040)。
张春良(1976-),男,四川泸县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Tel:(023) 68326616,E-mail:zpeak@126.com。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