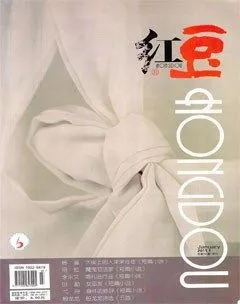草(五篇)
2011-01-01王族
红豆 2011年1期
王族,甘肃天水人。1991年底入伍西藏阿里,后调入新疆。现居乌鲁木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新疆作协首届签约作家。曾获总政第9届“解放军文艺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新疆“首届青年创作奖”,“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等。
1、行走
我决定随便走走,于是便选择了一条中间有草地、牧场、树林和村庄的路线,大约十公里,用半天的时间可以走完。
一场雨又下了起来。山里的雨已经遇到多次,感受没有多大的变化,这里也不需再费笔墨,但我没有想到这场雨却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体验。雨下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我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坐着歇息,突然,我听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一惊,这是什么声音呢?正在疑惑之间,我还是凝神倾听起来。很快,我就惊奇起来在一阵风吹过之后,被雨淋湿的草叶悄悄舒展开来,有隐隐约约的声音响起,像是大地在轻轻扭动着肢体,这些声音是从内层暗暗传出来的。
太阳已经变得灼热起来,阳光洒在草地上,草叶迎接上去,迅速舒展着,那些细碎的声音不时地响起。这样的遭遇只需屏气凝神地倾听,不用多想。过了一会儿,四周平静了下来。我像贪婪的孩子,仍坐在原地不动,渴望刚才的声音能够再次响起。
额上有了汗,用手一抹,手也变得湿湿的。草地的湿气早已散去,摊开的绿色重新让它焕发了原来的颜色。我无法准确说出草原在刚才的雨中经历了什么,但草叶发出的细小声音却超越了全部过程,给了我一个极好的答案。万物皆有灵。我想,在帕米尔高原涌现出了那么多动人的故事和好听的歌,是不是都与这块土地的底气有关呢?
这时,一阵细小的声音又突然响起。一种浓烈的感觉犹如几座大山挤压过来,我又停下来,用一种享受的心态倾听着这些声音。较之于刚才,现在的声音大了许多,我怀疑这可能是它的高潮期,由于是一种力量使然,在到达一个高度后将跌落。果然,仅仅几分钟时间,四周就寂静下来了。像一曲音乐戛然而止,我既迷惑又惶恐。在这样的场景中,在这奇异的声音结束后,人犹如从梦中走出,一下子清醒过来了。
草场上彻底恢复了平静。在这面大镜子表面,一股股绿浪纠缠着、挣扎着,跌下又起伏,到了远处,便汇集成一团绿色火苗。
我兀立原野,心情异常复杂。我觉得草场是一个躺着的泪流满面的汉子,他着急地想站起来,但最终却无能为力。
傍晚,我们到达了另一个村庄。一次真正的行走结束了,我疲倦得昏昏欲睡。但我在一丝惋惜里还是挣扎着睁开了眼——我想再次看看被我抛在身后的山林是什么样子。草原已涌起了长长的绿浪,这种浪花疯狂地蔓延在大地上,像是已完成了一个壮美的祭奠。我又向远处看去,突然发现这股绿浪已在原地凝固了千万年,不管愤怒还是沉静,都一直保持着向前涌动的姿态。
——在它的怀抱里,牧场、村庄、树木和河流都——成长起来了。
2、细草
那仁牧场的草好,在阿尔泰是出了名的。好草必养好羊,所以,在那仁牧场长大的羊皮毛柔软,肉鲜嫩,而且长得壮实。阿尔泰富饶,被誉为“金山银水”。而阿尔泰又是大牧区,所以有人便戏称阿尔泰的羊走的是黄金大道,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牧民们对草的感情很深厚,除了草喂养了牛羊以外,大概还有一种感情在里面。一天,我看见一位牧民蹲在一个地方在用手刨着什么,好半天都不离开。我走过去,见他神情专注,双手小心翼翼地在刨一株草周围的沙子。我问他:“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我在帮这株草。”
我不解,便问他:“你怎么帮它?”
“去年的风调皮得很,刮到这里,不光刮来了雪,还刮来了沙子,把好好儿的一株草给埋住了。草的力气小嘛,我帮它一下。”
“它今年能长出来吗?”
“能。能长出来。去年它喂了我的羊,今年我们不能不再见面。”
我不再问他什么。一个牧民已经细致到了这一步,外人就不能再打扰他什么了。他知道一株草今年没有长出来,就用手把压住它的土刨去,在他心中,牧场和牛羊一定会有更确切的位置。
细看那仁,几乎是碧草连天。这是一个草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许多细微物的集合体,庞大由细微完成,伟岸由细致完成,极致由真实完成,美丽由纯朴完成……一片树林可以细致到一棵树,一片草原可以从一株草上呈现出全部生命。所以,世界其实只是一个量的呈现体,它不应该独霸时空和专制。如此这般具体到一棵草,就可以触摸到它的细致和真实。一个生命在细致和真实之处总会有许多感人的地方。
有一年牧场起了一场大火,火势很快就蔓延到了那仁,但烧了只有十几米,却奇怪地熄灭了。那场火使其他牧场都遭了灾,牛羊因为没草吃被饿死了很多。人们都惊讶那仁牧场的草为何不着火,便都过来看。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讶不已,火烧到那个地方后,留下一道齐刷刷的痕迹,像是有谁在那里及时砍了一刀,将火制止了。那道痕迹旁边的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却没有被烧伤的痕迹,让人目光虚虚地敬畏。从此关于那仁牧场的传说就多了起来。人们说,这个地方有神看着牛羊,牛羊都是上天的神降到人间修炼呢!所以,上天不会不管它们,派另外的神在关照它们呢!在火烧过来的那一刻,神就用大刀将火斩断了。这是一个在中国常见的神话,基本上遵从的仍是神力高于一切事物的规律,突出神力,使故事变得完美。
也有在现实中有意思的事情。一位牧民告诉我,看一只羊有多高,就知道它吃了多少草。我问他怎么个看法。他说,去年嘛,我有二十只羊和红梏草一样高,今年和麻黄一样高,明年就和柴胡一样高了。和柴胡一样高的羊,要吃五年那仁牧场的草;和麻黄一样高的羊,要吃四年;和红梏一样高的羊,要吃三年。我深信他这种计算法的正确性。多少个日子,他就这么盯着羊看,看着看着,便看出了门道。后来,去他的帐篷里喝奶茶,见他帐篷里挂有多种草。他告诉我,他发现了草与羊身高的关系后,便将这些草——采来,与每一只羊测量,果然很是准确。于是,他便向外公布了自己这一发明。牧民们往外卖羊时,纷纷采用这一方法与商人谈论价钱,不按这个标准给价,死活不卖。
他成了一个规则的创造者。多少年后,牧民们也许仍将沿用他发明的这个方法。一只羊,不用再去称,再去用手掂量,瞅一眼就可以知道它吃了几年的草,有多重,值多少钱。
“你是白哈巴村的功臣!”我赞赏他。
他却嘿嘿一笑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嘛!草嘛,每年都长着哩;羊嘛,往草那么高长着哩。长到啥草的高度就值啥钱,每个人一下子就会算了嘛。我不是功臣,草场是功臣,是草场给了我们一切嘛。”
当晚,他给我们宰了一只羊,吃手抓肉的时候,他问我:“羊肉怎么样?”
我说:“好吃。”
他感叹一声说:“这只羊也长了一身好吃的肉。前年嘛,它红梏一样高,去年它一下子长得柴胡一样高,直接越过了麻黄,一年长了两年的身子嘛!这么好的羊,我舍不得卖出去,我放羊辛苦嘛,吃个好羊也是对我的回报。”
我停住了刚抓在手里的一块羊肉,不知是吃还是不吃。一只好羊,对我来说应该预示着什么,吃下它的肉,我将怎样在感情中消化它?他发现我走神,一笑说:“羊是吃草长大的嘛!好草喂好羊,你就当自己是一只羊在吃草就行了。”说完,他诡秘地一笑。我不多想,抓起羊肉就吃。人生在世,不就像一只到处觅草的羊?而能遇到好草,“一年长两年的身子”,实在万幸,我就当自己是一只遇到了好草的羊,放开吃吧。吃罢羊肉,体内燥热,似有火在烧。
入夜,从他的帐篷里出来,见月光洒了一地,草地上光芒一片,明闪闪地有什么在动。多么像一双双眼睛,正躲在细密的草丛中间在看着我。
3、向大地觅食
我跟在长眉驼后面,感觉自己很像一个牧人。长眉驼们吃草,我看沙漠,看雪山,看两只鸟儿谈情说爱。一转身,我发现长眉驼们已经走出很远。我原以为,地上有草,它们可以吃一会儿,不料它们转眼间便把我扔在了后面。
被它们扔在身后的不光有我,还有沙丘、草丛和石头。它们的身躯太高大了,有很多东西都被它们一跃而过,变成寂静世界中的沉默者。
我赶到它们身后,紧紧跟上它们。说实话,被它们扔在后面便觉得颇为孤独,甚至有一种恐惧感在内心蔓延。我想,在很多放牧的日子,牧人与牲畜们之间其实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牲畜彼此调解着对方的生活,时间久了,放牧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人畜共存的那种和谐和默契。游牧——这赤野蛮荒之地的古老生存法则,就这样维持了下来。所以,每一个放牧者到了这里,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这一法则。慢慢地,人和牲畜变得像石头一样沉默。风从一个地方刮过来,又向另一个地方刮过去。就在风来来去去之际,地上的草绿了,青了,枯了,大雪也就落下来了。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顺应了一种规律,时间便也就过得平静而又舒缓多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一代又一代牧人在沙漠中完成生命的担负,然后又——老去。
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骆驼只吃一种草。怪不得它们跑得这么快呢,原来它们在寻草。这种草很少,往往走很久都找不到一株。找到之后,它们如视神物一般对其凝视片刻,然后从鼻孔里喷出鼻息,将草叶上的灰尘吹去,再伸出舌头慢慢将草叶卷入口腔里。它们嚼草的速度很慢,口腔里有“咔嚓咔嚓”的声音。沙漠中寂静无声,这种声音便显得很大,像是这些骆驼的到来终于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沙漠。也许沙漠中的很多东西都在沉睡,在等待着富有灵性的生命来唤醒。
我有些好奇,被骆驼视若神物的究竟是什么草呢?脚边有一株,我蹲下身细看。这种草的叶子很少,而且还长在全是尖刺的枝上,骆驼们要吃到草叶,先受到尖刺的威胁。但骆驼们的舌头似乎很灵敏利落,总是巧妙地伸过去把草叶卷入口中。也许,这残酷的觅食现实早已教会了它们生存的技巧,那些尖刺已算不了什么。
一峰骆驼把枝上的叶子吃干净后,卧下又去吃根部的叶子。根部实际上也就两三片叶子,它完全可以将其忽略,它却小心翼翼将头伸过去,把草叶卷入了口中。它的头几乎贴在了沙土上,那几根有尖刺的枝划在它脸上,出现了明显的划痕。吃完之后,它站起身子又往前走了。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我又怎能相信一只高大的骆驼为了两三片叶子屈下了身躯?在平时,骆驼们遇上再大的风沙都不会低头,但为了生存,它们却无比艰难地让自己的嘴伸向了那两三片叶片。在这一刻,我看见了生命的艰辛,也看到了在这种艰辛中体现出的不屈。
下午,我再次看到了骆驼为生存而表现出的一种艰辛。一峰母驼带着两只小驼在沙丘中间不停地转来转去寻找草吃。草很少,它即使寻找到草,也只是为了两个小生命,而它几乎没吃上一口。它们就这样不停地在沙丘之间转来转去,把一个小范围重复着转成了一条艰难的长途。我从母驼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茫然,但也看到了一种不屈。我想,我只能从骆驼的眼睛里看到这种茫然和不屈,而我看不到但可以感受到的,便是隐藏在背后的爱。
终于,母亲找到了一株草,但它和两个小生命今天的运气实在太差,就在它们刚刚把头要伸过去时,一峰高大的骆驼却把头已经伸到了那株草跟前。母亲眼里充满了无奈,两个小生命眼里充满了失望。我不知道骆驼们之间有没有交涉,或者说,它们之间会不会产生一点同情。总之,这峰高大的骆驼横蛮地把自己的身躯立在了它们面前,嘴里“咔嚓咔嚓”地吃着叶片。母亲和两个小生命绝望了,不得不转身离去。
茫茫沙漠,它们去哪里觅食?
一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动物已倒地多日,只剩下了白森森的尸骨。两个小生命好奇地跑到跟前,用嘴去拱。尸骨下本无草可吃,但它们却甚为好奇,拱着尸骨玩得很开心。母亲在一旁默默看着它们,眼睛里有了一层冷悯,同时也有了一层酸楚——作为母亲,今天带子女出来却一无所获,它内心一定很不好受,但看着两个小家伙这么高兴,它便让它们先玩一会儿,不急着带它们去觅食了。看着它,我突然觉得它身上在这时显示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母性。
玩了一会儿,它们才想起妈妈,回到了它身边。它们又往另一个沙丘走去。别的骆驼都因为有草吃而停住了脚步,只有它们得继续往前走。行之不远,它们运气转好了,找到了一株草。两个小家伙高兴极了,张嘴“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母亲一口都不吃,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两个爱子,一副很满足的样子。不一会儿,两个小家伙吃完了,回到了母亲身边。一株草的叶子转瞬间都不见了,只留下了几根光秃秃的枝条。但母亲从这光秃秃的枝条上仍然看到了希望,它卧下身子,把嘴伸过去啃两个爱子忽略了的残叶,它甚至把它们啃过的地方又啃了一遍,将残剩的一点点叶根啃进了嘴里。有半片叶子藏在几根尖刺中间,两个小家伙怕受伤而放弃了,母亲却看成了一口不可多得的美餐,跪下前腿,把嘴伸到刺跟前,然后伸出舌头巧妙地把叶子卷入了嘴里。为了吃这一片叶子,它神情严肃,似乎在举行着一场神圣的仪式。
它们将草叶视若神物,所以它们甘愿为其跪下。
4、沙漠中的刀
小草,从沙砾与沙砾身体的窄小空隙长出来尽管没有多高的身躯,但却生出了几根坚硬的枝,因为是冬天,枝上无叶。枝便摇动,将阳光反射出几丝光芒。它们有的是骆驼刺,有的是芨芨草,还有一些则叫不上名字。一位哈萨克族牧民曾对我说,沙漠里有一半的草没有名字。有一次我在沙漠中见过一种草,没有枝,叶子直接从根上长出来,在地上覆成一片,很是显眼。
这些草是沙漠中唯一可以看得见的绿色。在万物中,草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类在多少年前就对草发出了赞颂。有史以来,这是人对草最高的赞颂。如果是大山里的草,想必生得并不艰难,而长在准噶尔盆地这样的地方,就艰难得多了。此处不见野火焚烧,却有一种更长久的磨难。或许,有很多种子都落进沙漠了,但终因这块土地对生命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一一夭折了,只有这少数的几株,得以生长起来。
该怎样看待这些野草呢?它们几乎就是从一条死亡的道路上走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被死神的双手卡住脖子。所以,在它们身后,其实站着一条长长的幽灵的队伍。但这些野草一旦得到生根发芽的机会,就再也不会放弃,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也要努力生长上来,生枝长叶,把生命袒露于大地之上。
几只鸟儿飞来,欲落向那几丛草,却恐于我们这些大活人,盘旋几圈,便又飞走。鸟儿们或是要落在草根上歇息,再或是原本它们与这些干草枝熟悉,飞过这里时,要落下来看看。鸟儿一天要飞很远的地方,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它们担心这些干草枝会有什么变化,便飞回来了。鸟儿,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我走到一株骆驼刺前,见它的枝很是尖细,虽已没有了叶子,但仍伸得很直。我见过夏天的骆驼刺,叶子泛黄,几乎与沙漠一个颜色。据说,骆驼们见了骆驼刺,也绕道而行。在南天山的一个牧场上,一位柯尔克孜族牧民说,他一辈子走过了无数大山,从不畏惧,却从来没有去过门前的一个小山坡,让他“肚子胀得很”(生气)。问为何。他说那个山坡上长满骆驼刺,牛不敢上去,羊不敢上去,人更是不敢上去。人要是上去,不是脚被刺破,就是手被划伤。疼得很。牧民们谈骆驼刺色变,这是事实。
望着眼前的这一株骆驼刺,我突然产生了想抚摸一下它的愿望。走到沙漠里来,我们又能看到它的什么呢?尽管它是阔大和辽远的,但它又是沉寂的;它几乎可以掠夺时间,让我们为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而惶恐不已。当我们感受到沙砾的呼吸后,就觉得沙砾才是真正的生命,而沙漠是不存在的。这种意念中的贴近,不是真正的贴近。真正的贴近,哪怕它再庞大,也可以和它比一比;哪怕它多么细小,也可以倾其一生。
我伸出手,握住了骆驼刺的一根枝,坚实,有一种硬朗之感。因为是冬天,它透着一股凉意。我松开它,突然感到手心一阵钻心的疼。摊开手一看,有血已经流了出来,隐隐约约的一道伤口出现在手心。
就这么一握,骆驼刺就刺破了我的手。但我却变得高兴起来。终于有了一种贴近让我感到是这么真实。血,平时在我体内悄无声息地循环流淌着,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但就在陷身于人生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中时,它却在默默地支撑着我的躯体。它的无私与人的无情构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现在它流了出来,为我的一次迫切渴望和体会,也许它是要让我清醒,因此还带出了阵阵疼痛。血流出来的时候,才是生命真正有深刻变化的时候。
现在,我已经远离了准噶尔盆地的那株骆驼刺,被划伤的右手在握笔写着这篇文章。我终于可以说,我握过沙漠中的一把刀。
5、那不是野草
太阳底下,我和金工低着头往山谷深处走着。我们的背部已经被太阳晒疼了,风一吹,便有一种钻心的痛。这种痛加上迷路的惶恐,似乎一阵更比一阵剧烈。
在藏北阿里迷路是痛不欲生的,这个地方宽广、辽阔,一旦迷路,你便不知该往哪里去才好。这时候,惶恐和烦躁便袭上心头,让人感到头疼胸闷,身体似乎快KHHSRaR9leS/ZldoeC/GkA==要炸了。我和金工不想让自己暴尸高原,便强压着惶恐和烦躁,在绝望中往远处走着。
上午的时候,勘察完红山河的营房地基,老唐带车去寻找石料。我和金工好奇,想趁此空余时间在红山河溜达溜达。我们俩先是下到山脚的河套里捡拾花花绿绿的石头,后来跟着几只羚羊进入一条峡谷,出了峡谷,爬上一块石头偷看一只野公羊和一只野母羊交配……当时高兴得不亦乐乎,等从高兴中回过神,想起要返回时,才发现不知道路了。于是我们俩到处找路,与其说是在找,不如说在是乱闯,闯来闯去,倒闯乱了。感觉每个方向都有一条通向红山河机务站的路,但却都不敢轻易迈出一步。高原以那种骇人的宽广呈现着死寂与恐怖,一种沉闷的感觉重重地压在心头。停下休息了一下,我俩觉得还得继续找。我和金工像太阳下的小甲虫一样,缓慢地挪动着身躯。望一望宽广的天地,唯一的感觉是往远处走,走远了,或许会碰到什么新的希望。
下午四点的时候,是藏北高原的正午。太阳像着火一样灼热,我和金工先是嘴皮裂开,接着是心肺阵阵撕痛。我想到了水。我们车子的后箱里,放了许多矿泉水和八宝粥。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一瓶也没带。在焦渴之中,它们无疑是天堂圣水,人间佳酿。过了一会儿,实在渴得不行了,我们于是没有了找路的心情,像两只慌张的野狼一样,瞪大了双眼向四周寻找,恨不得求老天爷能网开一面,给我们降下些水来。
在意志快要崩溃的时候,几根野草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金工从地上一跃而起,一把抓住我的手,向那几根野草奔跑过去。这几根草长得神奇,在苍凉干燥的高原上,蓬勃着嫩绿的叶片,迎着太阳反射出几丝亲切的光芒,甚至还有两个花骨朵已经显形,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我和金工屏住呼吸,缓缓蹲下凝视着它们。一阵风吹来,草迎风飘舞,妩媚婀娜的姿态把我的心撩拨得起伏跌宕。
“挖吧,下面绝对有水。”金工一声喊,我便像强盗一样将手伸进沙子挖了起来。没挖几下,手指头触到冰冷而又坚硬的东西。一挖,是骨头;再挖,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是一副骆驼的骨架,驼峰里有一汪清水。我们俩停住了,不是因为沮丧,而是被眼前这过于神秘的一幕彻底震撼了。一头骆驼死后,驼峰中居然水分不散,滋养了另外的生命。一头骆驼的死是神秘的,而它死后,岁月让几粒重负使命的草籽降落在它背上,在驼峰永不干涸的水的滋养下,静静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生命永不枯萎的神秘的源啊!这是藏北高原用事实给我们讲述的一则神话故事。
我和金工重新将驼骨埋好。我们已经忘记了干渴,一种圣洁的水在心间流淌,我们为目睹了高原的神秘生命而欣慰。骆驼的骨架又被埋入了高原,又进入了一个生命的梦中。但愿这个梦长久,与藏北高原齐头并肩,同生共死。
我和金工从一个梦的边缘返回,走在路上我们只说了两句话:“那不是野草。它是长在高原的梦里的。”
我想,我和金工是幸运的,在这场不大不小的灾难中,像两根草一样,浑然无觉地被一种潜藏在生命深处的水喂养,获得了信仰的威严,获取了心灵的力量。因为我们返回时,是憋着一口气走到红山河机务站的。
那几棵草被我和金工破坏了,但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它们救了我们俩的灵魂,在另一种形式中属于了我们俩,它们经由我们俩由野草变成了精神意义中的圣草。明年,那个地方一定又会长出几株草。野草永